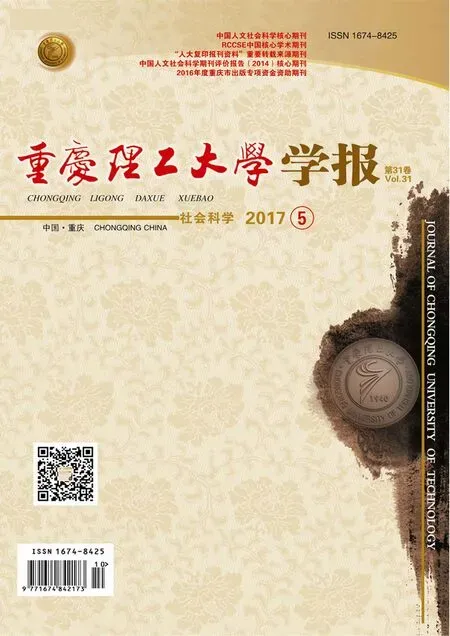風險溝通視角下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公眾參與研究
李 穎
(中共重慶市委黨校 應急管理培訓中心, 重慶 400041)
?
風險溝通視角下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公眾參與研究
李 穎
(中共重慶市委黨校 應急管理培訓中心, 重慶 400041)
風險溝通作為一種隨著風險社會發展出來的治理工具,是風險社會里人們應對風險的有益方式,也成為多元主體進行社會治理、促進社會良性運行的有效手段。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離不開社會公眾的參與,公眾參與政策風險評估的過程亦離不開對風險問題的溝通。在分析程式化的風險評估機制給我國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所帶來的問題的基礎上,提出應從加強風險信息的交流與整合、社會參與渠道的建設與拓展、政策風險議題的管理、整體風險評估框架的構建等方面來促進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中的公眾參與,使整個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能夠更加科學。
風險溝通;政策風險;評估;公眾參與
作為隨著風險社會發展而出現的一種治理工具,風險溝通已經成為處在風險社會里的人們應對各種風險的重要方式,被廣泛運用于社會運行的各個環節和社會治理的多個層面,如環境保護、政策議程、突發事件處置與應對等等。風險溝通是多元主體,特別是政府和企業做好自身管理、進行社會治理、促進社會良性運行的有效手段。
審視我國近年來的政策實踐,可以看到這樣一種現象:由于缺乏充分的風險評估,作為政策制定者的地方政府和作為政策作用對象的社會公眾之間對政策的意義、政策的目的、政策實施期望取得的效果等缺少溝通,以致在政策制定、頒布、施行的過程中缺乏足夠的風險共識,也就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政策的風險,從而使政策目標的實現遇到阻礙。近兩年發生的“XX古城收費事件”等,就是政策在出臺和執行的過程中缺乏風險溝通所引發的。
基于此,筆者認為應該從風險溝通的視角來審視我國今天的民生政策,特別是重大民生政策的風險評估,通過風險溝通這一“雙向”的向度,強調公眾參與的作用與意義,來探索化解政策風險、提高政策效能的路徑。
一、重大民生政策風險溝通的必要性
正如有學者指出的,一個社會越發達,社會功能就越復雜,意味著人們離未知的風險也就越近。隨著我國進入社會轉型的深化期,不管是在利益格局的調整上、社會資源的分配上,還是在社會價值的建設上,作為對全社會價值進行權威性分配的公共政策,都面臨著新的考驗。特別是以關注民生為要旨的重大民生政策的制定,在解決民生問題、化解“民生風險”的同時,也面臨著“社會性風險”的考驗。
(一)重大民生政策風險溝通的涵義
美國國家科學院(The National Academy Sciences)對風險溝通作過如下定義:風險溝通是個體、群體以及機構之間交換信息和看法的相互作用過程,涉及多側面的風險性質及其相關信息,它不僅直接傳遞與風險有關的信息,也包括表達對風險事件的關注、意見以及相應的反應,還包括發布國家或機構有關風險管理的法規和措施等。風險溝通是利益團體之間對有關風險的本質、重要性或控制等相關訊息的交換,其主要目的是知情、說服和咨詢。風險評估者、管理者以及其他各方為了更好地理解風險及相關問題,就政策風險及其相關因素交流信息和意見的過程,就是風險溝通[1]。
根據這一定義可知,風險評估是以“風險”為核心,以“溝通”為手段,以“交流、說服”為目的的,最終是為了達成風險上的“共識”。公共政策的出臺,就是為了解決社會問題、化解社會風險,實現特定群體的利益訴求。特別是重大政策的制定,由于涉及范圍廣、利益關聯度高、敏感度高,政策風險也就高,因而風險溝通就很有必要。風險溝通涵蓋著政策制定者和政策作用對象對政策的認知、感知和價值判斷,影響著政策執行的效果。風險溝通雙方基于共同的政策目標進行多回合的“相互回應”,表達看法、發表意見、提出質疑、做出解釋、進行宣傳等等,就政策內的具體做法反復進行交流。政策風險溝通的目的是要通過溝通更加全面細致地認識風險、掌握分歧、尋求解決政策問題的最佳途徑,實現重大政策風險的最小化,以利于社會的穩定。
(二)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風險溝通的重要性
重大民生政策雖然是公共政策的一種,但由于它總是與重要民生問題緊密聯結在一起,是解決重要民生問題、發展重要民生事業的重要依據,且立足于所有社會問題中最基礎的民生問題,與社會公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因此備受社會公眾的關注。社會公眾紛紛圍繞“政策話題”表達各自的利益訴求,希望政策的條款與自身的訴求能高度契合[2]。
雖然隨著信息社會的發展,互聯網、移動互聯網等現代信息技術的迅速進步給信息的公開帶來了極大的便利,但像政務信息與社會公眾之間天然隔著一道屏障一樣,由于現有政策模式、不同利益考量等因素的限制,政策信息在政策主體與政策客體之間依然存在著很大的不對稱。這就要求:在政策風險客觀存在的情況下,政策的制定者要充分知曉風險的程度,對政策風險進行客觀評估,作好應對政策實施可能帶來的社會風險的準備;同時政策的作用對象應該對政策的風險有一個客觀的認知,積極配合對政策的相關風險評估,共同促進政策的優化。風險溝通的主要作用就是降低風險的威脅性,促成公眾對政策的支持,幫助政策的實施,防止政策資源的誤用和浪費,從而既使決策者很好地了解風險,又培育社會公眾的政策風險意識,建立社會公眾對政策的信任,以利于政策的穩步推行。
(三)風險溝通中的公眾參與
“風險溝通”作為聯結利益相關方的紐帶,是多元主體間觀點交流、交換意見、資源整合、價值引導的重要手段。它強調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對話”,致力于調和政府、企業界、科學界和公眾之間關于風險問題的不同看法,通過各種溝通方式增進相互了解,促進一種新的伙伴和對話關系的形成。重大民生政策的對象是社會公眾,風險溝通自然離不開公眾的參與。風險溝通是一個特殊的溝通過程,總體來說,公眾一方總是處在接受信息、詢問信息的位置,因此溝通的另一方,無論是政府部門還是其他管理機構,是否能將公眾視為伙伴,對于溝通的有效性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公眾有權參與那些可能對其生命、財產產生影響的重大民生政策決策。風險溝通的目標不僅要降低公眾的憂慮和提高采取行動的效率,而且要培養知情的、參與的、有興趣的、理性的、有思想的、致力于解決問題的合作群體[3]。
就重大民生政策而言,能否通過政策決策過程迅速并徹底地解決社會問題,公眾的參與至關重要。可以說,缺少公眾參與而制定的民生政策不但缺乏社會基礎,更會面臨更多未知的風險。因此,應重視風險領域的對話空間及平臺的構建,爭取實現所有的利益相關方都可以平等地參與評估過程,促進不同利益主體之間的對話、協商和辯論,避免由此帶來衍生性的、棘手的諸多政策風險。特別是關系到一個地方穩定和社會良性運行的重要問題,公眾參與機制的構建對于化解政策風險,包容、消解分歧與沖突,有效地彌合多元主體間的風險感知差異和政策分歧,切實增強政策的可接受度,進而達成某種一致即形成政策共識是非常重要的。
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離不開公眾的參與,風險溝通既是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的重要組成部分,亦是公眾參與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的重要方式,相互間緊密的邏輯內聯,要求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應“以參與促溝通,以溝通促參與”。
二、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中的公眾參與困境
與一般性的政策風險評估有所不同,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有其自身的風險特征。在社會訴求碎片化、公眾參與無序化的背景下,公眾參與風險評估還存在一些制約性因素。這就需要分析在利益訴求多元化背景下,利益相關者如何能平等自由地表達政策主張,從而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多元主體的合法權益,實現重大民生政策公眾參與和社會治理的高度契合。
(一)差異化的風險感知多元并存,制約著公眾參與的有序性
目前已有的風險評估中,常常把被評估對象對風險的感知作量化的評價,比如風險評估中常用到的雙因素模型,已成為感知風險研究的主流模型。該模型用于不同情境下對風險因素進行分析,這有利于風險評估的科學性、精確性。但對于重大民生政策而言,因其涉及復雜的社會問題,背后又是復雜的多元化的利益主體和社會關系,對風險的感知更是千差萬別,因此在進行精細化的量化評估的同時,還應該注重風險因素的社會性評價[4]。
正是這些分散的、零碎的、多元并存的風險感知,使得公眾在整個政策議程中的參與表現出一種較為明顯的無序狀態,比如網絡上涌現出的大量積極熱烈卻沖動的非理性言論,以及意見表達時的隨心性、隨意性等等。有時就是在同一利益群體內部,在政策意見上也表現出較大的分歧。這種無序性還體現在政策風險評估的過程中,雙方對權利與義務要求的不對等,以致對政策風險的理解出現較大的偏差。
公眾參與的無序性和隨意性也給政策風險評估帶來了負面影響。在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的過程中,作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受信息負擔能力的局限,僅靠其自我評估是很難實現政策風險評估的科學化和專業化的,因而很需要社會公眾積極參與,然而出于對難以整合的碎片化的風險感知,相關部門對公眾參與政策風險評估工作有天然的抵制[5]。而重大民生政策的目標群體是較大的,對于這么龐大的政策目標群體,如果沒有規范有序的引導,必然會造成參與的無序性和隨意性,從而加大政策風險評估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二)閉合式的風險評估參與流程,制約著公眾參與的積極性
隨著互聯網+的發展,社會公眾參與的方式越來越立體化、網絡化、開放化,這對傳統政策風險的評估流程提出了挑戰。從今天的政策制定流程來看,政策議題的確立、風險評估辦法的出臺、評估方式的確定等,仍然是以行政機構內部的工作流程為主,對社會參與的開放還很不足[6]。雖然也有事先的“聽證會”“政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等,但就其整個過程來看,還是一種“閉環”式的政策制定過程。因此,在面對重大民生政策價值目標時,閉合式的政策風險評估方式就很可能會受到個性化、多元化、綜合化的公眾訴求與潛在性、模糊性、多變性的風險特性的沖擊。尤其是在社會治理框架下,公眾參與作為政策風險評估中的核心要素之一,必然會提出更加開放的政策追問,這也正是民生政策中的風險評估的重要意義之所在。
同時,現有建立在行政命令基礎上的控制—反饋式的閉環式運行模式使得地方政府出于一元治理的慣性,對公眾參與整個政策制定流程工作還不太情愿,加之受信息安全保護的制約,導致整個政策制定流程難以對社會公眾充分開放。這就造成政策制定流程的閉合程度越高,政策信息的發布越不充分,公眾也就越會因政策的敏感程度而激發出更多的疑問。當這些疑惑得不到及時有效的回應時,比如“聽證會”流于形式,公眾的參與積極性就會降低,就會表現出對風險溝通的漠視或抗拒。
(三)整體性的風險評估框架尚未建立,制約著公眾參與的規范化
對于重大民生政策而言,好的風險評估框架所組織和呈現的信息,既可以幫助決策者更加科學全面細致地了解風險的特征、程度、脆弱性,也有利于社會公眾參與。一個整體性的風險評估框架可以幫助組織了解哪些系統受濫用或攻擊的風險最低和哪些風險最高。風險評估框架提供的數據對積極主動地解決潛在威脅,形成一種基于價值的風險共識也是很有用的。這種風險共識正是重大民生政策形成過程中凝聚社會共識、彌合意見分歧、彰顯政策公共價值的關鍵要素之一。
目前,雖然各地都對重大決策和重大項目做出了進行社會穩定風險評估的規定,政策風險的評估也在不斷地進步,但從已有的實踐來看,這種評估更多是一種事前的、相對靜態的評估,對事中和事后的風險評估卻不足。而風險是一種不確定的因素,即使是已知的風險,也會隨著情景的變化而不斷變化,對于未知的風險,其變數就更大。特別是重大民生政策在多久時間內、多大程度上能取得什么樣的政策效果,每一個條件都充滿了風險變量,故沿用相對不變的風險評估方式是很難奏效的。而且,評估方式若單一化和程式化,就對公眾的意見缺少一種價值上的凝聚,公眾的政策風險意見也就很難被吸收進評估意見中。
風險評估整體框架的建立,還有利于做到公眾參與的規范性。對于公眾來說,民生政策與自身息息相關,都高度關注,只要條件允許,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參與其中。但對于多數社會公眾而言,怎么參與、參與什么、參與的方式與方法等,都需要一個明確的規定來引導,否則其參與就是無序的、零碎的,在某些促發因素的激發下,就可能造成參與的失范。
(四)程式化的風險評估機制還不完善,制約著公眾參與的有效性
重大民生政策風險的評估離不開社會公眾積極而有效的參與。其有效性表現為:一是在社會公眾的參與下,風險的各種要素以及風險的性質能夠得到精準的識別,從而對政策進行優化;二是通過公眾的參與,能夠形成一套有效的風險應對方案,以避免政策性輿情事件或突發事件的發生,使政策的實施能夠有效地解決民生問題,促進民生發展。但從目前的評估過程來看,程式化的風險清單編制、調查問卷發放、風險指數加權等做法,使得對風險的評估一開始就受到很大的主觀因素的制約,導致公眾的意見不能充分地體現出來。
加之重大民生政策不僅牽涉多個政府職能部門,有的還會牽涉不同層級、不同地區的政府部門。簡言之,就是包括“屬事、屬地、屬人”三個方面。這三個方面橫向交叉、縱向交織,權責界限很難分清。這與高效的政策風險評估需要相互配合、相互協調、形成合力的要求極不相稱。這種情況往往導致相關部門和相關人員各自為政、相互推諉,從而影響了政策風險評估的效率和質量。比如在具體的重大民生政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中,如果主體責任模糊不清,沒有明確規定應該由哪個部門或單位負責,就會造成責任主體的模糊分散,為重大民生政策社會穩定風險評估工作中“誰決策,誰評估,誰負責”的基本工作原則帶來執行難度[7],也使得民生政策風險的評估失去了應有的社會參與的協助與配合。
三、基于風險溝通的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公眾參與提升
根據重大民生政策的重要性和關注度,作為政策制定者的政府在面對具有一定程度模糊性和非連續性政策演化規律,以及多變性、綜合性的公眾訴求時,相對不變的風險評估和風險溝通方式很難奏效。這就需要針對目前存在的制約因素,構建多元主體參與的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機制,在明確主體責任邊界和利益關聯對象的基礎上,通過渠道建設、方式建設、流程優化等,實現公眾對政策風險的識別與研判、風險的控制與轉化、風險的化解與利用、風險動態跟蹤全過程的有序參與,促進公眾的參與。
(一)打破條塊分割的信息共享機制,提高政策信息的公開透明度
做好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的前提條件之一在于整合各種信息資源,為評估所需的各個環節提供基礎信息。但在目前的政策風險評估過程中,信息資源條塊分割的問題較為突出,信息資源整合共享與收集存在一定的難度。相關部門信息難以有效共享歸集,有些部門以涉密或信息安全問題等為由,既不愿將本部門的信息共享給其他部門,也不愿向社會公開。加之部門間、地區間信息平臺建設的參差不齊,技術功能完善存在較大差異,也給風險信息資源的搜集、整合、歸集和共享帶來一定的難度。
信息資源的充分整合與共享是做好風險評估的前提條件,更是保證公民知情權、促進公眾參與的重要條件。近年發生的若干政策性突發事件,有一個較為突出的原因,就是信息的公開透明度不夠,信息公開不及時、不充分。信息的公開與透明還有利于政府、決策者與社會公眾之間形成一個良性的互動,即信息質量越高,社會公眾越能對政策風險做出正確的感知。公眾客觀理性的風險感知是科學評估政策風險的重要前提,同時還能夠把公眾的意見較為準確地傳遞給政府,使政府在風險評估時能做出更加準確的分析和判斷。
(二)充分利用互聯網+的技術優勢,拓寬政策風險溝通的渠道
在“互聯網+”時代,互聯網在政府與公民之間搭起了一座相對平等、自由、快捷的橋梁,使得人們無論身在何地,只要能上網就能議政,極大地激發了公眾參與社會事務、表達個人意愿的興趣和熱情。目前的政策風險評估主要依靠制定政策文件和層層落實責任等方式進行,雖然在制定一些關系群眾切身利益的政策時也會公開征求意見,但總體來說,社會公眾參與互動的渠道和方法還比較少[8]。政府決策從經驗型決策向更加科學化的數據決策轉變是“互聯網+”時代的政策決策的轉型趨勢。長期以來依據局部抽樣數據而做出的決策,重視的是因果關系而非相關關系,缺乏與公眾的充分溝通和交流,更多是基于理論、經驗和主觀價值判斷,很難保證重大民生政策的科學性和最優性。
因此,需要充分借助“互聯網+”的技術優勢,利用“兩微一端”等新興互聯網平臺,為社會公眾參與風險評估創造便捷、暢通的渠道。特別是當前一些民生政策輿情事件所體現出來的參與群體的青年化、知識化的現象,表明“互聯網+”的利用更應該成為今天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的渠道。另外,要充分借助互聯網做好政策風險信息的傳遞與交流,為社會公眾參與提供一種簡潔易操作的方式,讓重大民生政策所涉及的各利益相關者能夠高效地表達自己的意見,從而降低社會參與的成本。雖然公眾在網絡上的表達不可避免地會存在一些弊端,但這些散落在網絡上的各種意見正是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搜集、整理民意所需要的重要資訊。
(三)加強政策風險議題管理,促進公眾參與風險評估的有序性
議題的產生與現代社會公眾對其利益的覺醒與關注密不可分,正是由于公眾對于事實、價值、政策等主張的關注,使得議題在現代傳播條件下具有廣泛的參與性和影響度。議題管理已經成為今天不管是在危機管理、風險管理,還是政策制定過程中一種被廣泛使用的工具。它對于那些可能進入立法程序或政策程序,與公共政策、公共事務密切聯系的,容易引起公眾關注和爭議的問題進行確認、分析、評估,對這些議題的發展趨勢施加必要影響;并在這個過程中,捕捉這些議題給組織發展帶來的各種機遇,規避防范這些議題給組織帶來的危機,使議題的發展結果、趨勢更加有利于政策目標的實現。
這里需要指出的是,重大民生政策中的政策風險議題與政策議題是有所區別的。政策議題是圍繞政策的事實、價值觀、政策內容和預期的社會行動展開。政策風險議題則是在政策風險評估中加強風險議題的管理,實際上就是通過社會公眾的參與,與政策制定者一道將政策的核心風險提煉出來,并就其中的價值差異進行辨識,對政策內容進行溝通、磋商、協調,最后對政策進行擬定和修正,將政策風險控制在可控的范圍內。這樣,在風險議題管理的框架和規范下,公眾就可以圍繞議題的各種設計分層次、分類型、分階段地參與到政策風險的評估之中,從而做到對公眾參與的有序引導。
(四)完善與優化政策風險評估框架,達成公眾的政策風險共識
在我國目前已有的政策風險評估中,相關部門根據不同的政策類型設置了“政策環境風險”“政策制度風險”“政策選擇風險”和“政策倫理風險”等指標[9],但這與整體性的風險評估框架的要求還有不小的差距。政策風險評估一般應包括原則、主體、流程、指標、方法、問責機制等核心要素。構建整體性的風險評估框架就應該包括識別政策風險要素、確定顯在風險和潛在風險、記錄風險和確定行動、分配風險等級、評估現有的風險控制手段、制定風險控制的預案并優化等。而且,政策風險的評估還應該是一個持續的過程,在記錄政策風險程度的同時,更主要的是要確定社會愿意容忍和接受的風險級別,并在每個實施過程中確定控制風險的機制。
完善與優化政策風險評估整體框架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加深政策風險認識、強化風險意識、不斷尋求政策資源的交流與整合的過程。對重大民生政策來說,確立風險評估的整體框架,針對復雜的跨部門的民生問題,跨界研究處理整體性的風險評估問題,實質上就是給了公眾一個規范化的操作要求,政策風險評估整體框架在對評估內容、評估過程、評估形式做出整體性要求的同時,也給社會多元主體如何參與明確了方向和目標。整體性的風險評估框架還有利于對風險的動態性評估,并根據這種動態性的評估做好動態性的風險控制,從而使政策的持續性作用優勢能夠得以體現[10]。
民生政策關系社會公眾的切身利益,重大民生政策更是如此,因而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尤為重要。通過風險評估,讓決策部門真正做到科學、民主和依法決策,確保重要民生政策不違背民意,不引發影響社會穩定的矛盾,并且以評估結果作為依據,增強風險溝通的有效性,提高溝通的效率,從而形成一種系統性的信任,以減少、化解政策風險,使重大民生政策能夠更好地發揮其應有的政策效用。
[1] 杜俊飛.危如朝露 2010—2011中國網絡輿情報告[M].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470-472.
[2] 孟曉敏,張新亮.基于風險管理視角的公共政策風險評估及應對[J].西南石油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2):36-41.
[3] 王東.小議“風險溝通”機制[N].中國青年報,2011-06-27.
[4] 黃建宏.參與視角下的社區協商民主[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6(7):115-121.
[5] 張煒達,王肖婧.公眾參與食品安全有獎舉報制度論析[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5(2):72-76.
[6] 李穎.基層政府社會風險治理流程優化研究[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 2015(11):109-114.
[7] 朱正威,石佳,劉瑩瑩.政策過程視野下重大公共政策風險評估及其關鍵因素識別[J].中國行政管理,2015(7):102-109.
[8] 朱浩.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治理[J].領導科學,2016(5):34-35.
[9] 林敏娟.局限與突破:公共政策風險評估研究[J].理論與改革,2015(2):96-98.
[10]季春東.論公民參與與政策評估主體構建[J].江西行政學院學報,2006(7):21-23.
(責任編輯 張佑法)
Study on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Major Livelihood Policy RiskAssessment Under the View of Risk Communication
LI Ying
(The Training Center of Emergency Management,Party School of Chongqing Municipal Committee of CPC, Chongqing 400041, China)
The risk communication is a useful way of dealing with social risks and an effective method of governing as a tool of governance which developed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Major livelihood policy risk assessment needs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while the public’s participation in policy risk assessment needs the risk communication. According to the difficulties of difference of risks perception, the closed-off process of policy risk assessment, the failure to establish a frame of policy risk assessment and the rigid mechanism of risk assessment of the major livelihood policy risk assessment, it is essential to improve the communic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risk information, expand the way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strengthen the risk topic management and construct the frame of policy risk assessment to make the major livelihood policy risk assessment more scientific.
risk communication; policy risk; assessment; public participation
2017-01-20 基金項目:重慶市社會科學規劃青年項目“地方政府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公眾參與機制研究”(2016QNSH21)
李穎(1977—),女,重慶人,副教授,研究方向:社會風險與社會治理。
李穎.風險溝通視角下重大民生政策風險評估公眾參與研究[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7(5):53-58.
format:LI Ying.Study on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Major Livelihood Policy Risk Assessment Under the View of Risk Communication[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7(5):53-58.
10.3969/j.issn.1674-8425(s).2017.05.009
D630
A
1674-8425(2017)05-005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