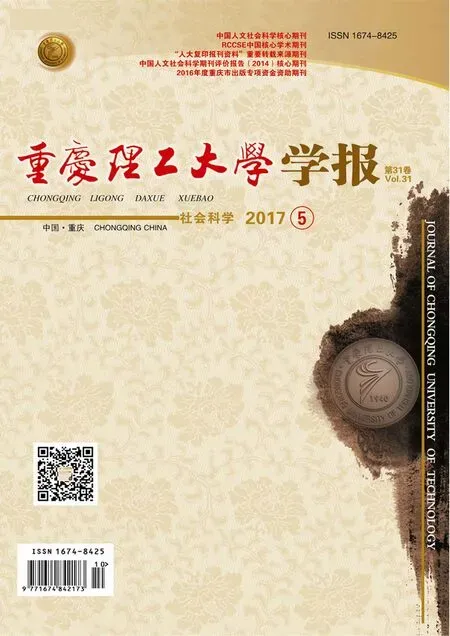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的政治批判探析
孫全勝
(中國社會科學院 當代中國研究所, 北京 100009)
?
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的政治批判探析
孫全勝
(中國社會科學院 當代中國研究所, 北京 100009)
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的政治批判蘊涵的理論主題是對空間生產政治現象形態的批判。他考察了空間生產與政治的關系,認為空間生產與政治是互動機制:政治影響空間生產,空間生產執行政治功能;其理論方法是運用馬克思唯物辯證法闡釋空間生產政治化的悖論及其克服路徑;其功能特質在列斐伏爾看來,要拒斥空間政治霸權,就要憑借總體人和身體革命實現空間政治權利。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的政治批判能夠展現政治意識形態和空間生產的互動效果,其中蘊涵著對日常生活微觀領域的考察,從而能夠推動社會政治的研究視域。
空間生產;政治批判;總體人;身體革命
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的政治批判是他對空間生產引起的政治現象形態批判的理論。與“歷史政治”在社會批判理論中的長期被關注相反,“空間政治”則是在不斷地被“拯救”中才能引發人們的關注熱情。因此,列斐伏爾重點考察了資本主義空間生產的政治意識形態功能,并促成了考察全球政治格局與空間架構關聯為內容的宏觀空間政治研究和闡釋具體空間政治權利布局的微觀空間政治研究。
一、空間生產的政治性
列斐伏爾借助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視域,由空間經濟學研究走向了空間政治學研究。埃爾登也指出:“因為空間是政治的而產生了空間政治學。”[1]空間生產的政治性呈現為政治統治工具和意識形態操控。“空間在資本主義國家已經成為最重要的政治工具。”[2]50空間生產的政治性就是空間生產展示出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并為政治統治服務的特點。
(一)作為政治統治的空間生產
1.空間生產是新的政治統治形式
列斐伏爾指出,空間生產是政治工具,時常擔負著政治任務:“空間的表達經常會通過在一個實踐(社會—空間的)之內將意識形態和知識組合起來。”[3]45國家權力空間構成了資本主義政治壓迫的載體,既將空間生產組合為龐大的控制網絡又讓空間生產變得壓抑、恐怖,空間生產因此變成政治權力運作的媒介和策略。空間生產不僅在經濟領域進行,而且向政治領域滲透;不僅面向資本增殖,而且面向政治統治。空間生產已經成為統治人、壓迫人的工具,空間生產的進一步政治化必然導致空間成為權力的化身,政治權力行使者憑借空間生產掩蓋自己統治的正當性危機。空間生產已經變成國家維護政治統治的工具。資本主義憑借空間政治來達到對公民的監控,保證空間的等級性、間隔性,讓社會空間變成政治權力控制、警察監管的空間。“在這個過程中,那些和另外一些分離出來,盡管這并不意味著所有這些控制對于一個運動是罷手的:作為一個整體的社會在從屬于政治實踐中繼續——就是說國家政權。”[3]8因此,空間生產既是具體的社會實踐長期發展的結果,又是政治現象形態的一個主要組成要素。統治階級利用資本原則建構空間秩序,“每一社會構成特有的生產、再生產及具體場景和空間體系”[3]45。
列斐伏爾指出,空間生產中充斥著政治意識形態,布滿政治訴求。國家政治權力及其構成要素呈現著空間政治格局。空間生產正走向微型化、生活化、消費化,資本主義的空間布展構成了空間政治權力的要素。發達工業社會空間生產的主導模式就是占有并使用空間,并憑借空間擴張克服危機,維護資本主義社會的政治統治體制,“資本主義是通過對空間加以征服和整合來維持的”[4]。空間生產實質上是強制性的,既是祛除社會批判的利器,又是政治的強制結構;既是有組織的話語體系,又是系統的控制行為。科技的進步造成了商品過剩,人們由被物奴役變為被空間支配,以實現資本最大利潤,同時維護著資本主義政治統治。政治空間既是資本主義統治的關鍵環節,又是新的政治操控手段,引領一切經濟、歷史、社會的空間都成了政治統治的手段。“換句話說,絕對的政治空間——那種戰略的空間,將其自身作為一種現實而不管如下的事實,即它是一種抽象,雖然人們賦予它巨大的權力,因為它是權力的地點和中介。”[3]94
2.空間生產體現著階級斗爭
列斐伏爾很注重考察階級斗爭對空間政治的影響,但他很少談及種族政治和性別政治,并反復強調,“今天,階級斗爭已經被刻入空間”[3]55。實際上,列斐伏爾空間政治觀不僅是階級意識形態學說,而且是其他意識形態學說,蘊涵著無限的可能性。“空間是‘社會存在’的實體化。”[3]102空間生產的政治性集中體現為空間生產的階級性,圍繞空間的斗爭成了階級斗爭的重點。空間生產和消費帶有階級利益取向和階級斗爭色彩,既讓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更加對立,又讓空間呈現出明顯的政治性。空間政治具有意識形態性、種族性和性別差異,不僅體現著階級意識,而且展現著種族和性別意識,因此,種族、性別也具體呈現在空間生產中。空間生產的思想霸權體現著社會主流意識形態,思想霸權憑借空間生產制造政治等級體系。空間按照社會地位分配,造成貧富不均。“空間鋪設了一種規則,因為它蘊涵著一種特定的秩序。”[3]143空間斗爭始終蘊涵階級斗爭,空間是政治活動的重要條件,階級斗爭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爭奪更多空間。只要資本主義私有制繼續存在,空間生產與階級斗爭就緊密相關。“沒有空間概念和空間生產概念,權力的框架(不管是現實還是概念)不能獲得它的合理性。”[3]281政治活動內部始終充滿著利益糾葛,這既導致了政治空間內部權力分配的不均等,又導致了一些政治團體要比另一些政治團體擁有更大的支配權。空間生產的階級性既讓空間成為階級沖突的新戰場,又讓空間帶上濃厚的階級意識色調。空間生產并沒有消除階級差別,而是讓資本主義變成隱形的官僚化體系,讓其統治更加隱蔽。
列斐伏爾指出,隨著城市化的高速進行,各種空間沖突此起彼伏,空間斗爭日益激烈。空間產品進入日常生活不是因為其實際功能而是因為其符號意義,體現著符號、身份、地位和名聲,這樣就制造了新的等級差別。空間生產既是不斷沖突的場域,又是階級斗爭的對象和目的。“對于階級斗爭,它在空間生產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種生產完全是通過階級來展現的,階級的碎片和各自階級的團體。”[3]55在空間生產中,各種利益集團都激烈爭奪空間權利和空間資源,引起人們對政治的不滿。政治權力在空間生產中的胡作非為引起了空間矛盾,空間矛盾讓階級斗爭加劇、社會矛盾更加突出,引起了人們更多關注。空間生產中的順服與反抗、擴張與壓縮、中心與邊緣始終存在。“對確定秩序的反抗和挑戰總是最終被歸因于階級斗爭。”[3]418空間意識形態將空間隔離,促成了空間的等級秩序,讓空間生產成為政治經濟體制的組成要素和資本增殖的工具。“空間的層級和社會階級相互對應,如果每個階級都有其聚居的區域,屬于勞動階級的人無疑比其他人更為孤立。”[2]50工人階級只有打破空間等級秩序,建立新的空間形態,才能摧毀舊的國家制度。而種族和性別的平等,也需要打破空間內的種族和性別等級秩序,從而實現平等和自由。空間生產的階級性和等級性,讓階級和居住區域對應,弱勢群體陷入空間孤立,階級壓迫更加嚴重。階級斗爭可以激發出差異空間和空間抗爭因素。
3.城市規劃集中展示著空間政治性
列斐伏爾揭示了城市規劃中的政治性。他指出:“在城市空間的生產過程中,國家政治權力主導一切。中心地區主宰邊緣地區,并把局部地區與全球聯結在一起,在此方面,權力起了關鍵作用。”[2]99城市規劃已經由具體考察變成了抽象認識,而走向工具化和技術化,不僅是大規模的數據測算,而且是服務于政治意圖的手段。城市規劃體現著政治統治的訴求,變成政治統治工具,成了利益集團爭奪的戰場。“關于當今之城市規劃,保守派評論強調小家庭、獨棟住宅和個別動機等概念。”[2]67城市空間的設計、利用、分配無不與政治相關,無不體現維護政治統治的目的。空間政治既導致了城市空間的中心化,又加劇了邊緣地區的貧困。作為空間政治集中體現的城市規劃不僅是國家權力的產物,而且內蘊著種族和性別意識形態。資本家試圖將白人的城市空間生產建立在對黑人的奴役之上,并建立了種族意識形態。城市空間呈現著政治意識,政治意識也必須憑借城市空間展現。當代發達工業社會的空間生產集中體現在城市空間的膨脹。城市規劃是工具性和高度組織性的,體現著資本主義主流意識,將社會矛盾和空間矛盾混淆。
城市空間生產集中體現為城市空間建設、城市空間規劃和城市空間決策。城市空間規劃以政治形式把不同地區、不同空間結構聯系起來。由于城市空間規模的無限擴大,城市規劃已經無暇進行實地考察,而成了主要決策者對數據、資料和報表的簡單立項定案[5]。城市空間規劃是政府主導的政治行為,行政強制手段時常摻雜其中,而行政強制手段往往代表著個人及小集團的經濟利益。城市空間規劃者變成主流意識形態的維護者,城市空間規劃傾向于工具化,讓房地產爆發。“一種更隱蔽的公理是:規劃的空間是客觀的和‘純凈的’;它是一種科學對象,并且因此是中性的。”[6]城市空間被科技規劃成客觀對象,讓工具理性滲透其中。城市空間實踐的主體包括“科學家、計劃者、城市規劃專家、社會工程師以及有科學傾向的某種藝術家等”[3]38,他們也參與了資本的城市空間增殖過程,并受著科技干預和資本邏輯的影響。“可以肯定的是,遵循建筑師、城市規劃師或者計劃者作為一種專家或者最終的權威,在聯系到空間上可能是一種最大的幻象。”[3]95城市空間規劃無法漠視空間生產中的社會關系、經濟模式和政治抗爭,城市空間規劃已經變成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組成要素,制造出資本增殖所需要的思想意識形態。“城市的空間可以說包括了一種權力話語,一種權力語言。”[3]142城市空間規劃造成了空間擴張和空間權利的矛盾。人們在空間擴張的緊逼下不斷爭取城市空間權利。城市空間權利不是宏觀抽象的群眾利益,而是弱勢群體的居住、工作等具體權利;不是回到傳統的階級斗爭,而是實現革新的都市生活,應該有時間節奏和瞬間狀態。
(二)作為意識形態的空間生產
1.空間生產呈現著意識形態性
列斐伏爾指出,空間并非祛除了政治意識形態的純粹對象,而是蘊涵著社會意義的關系機制。他進一步分析道:“空間一向是被各種自然的、歷史的元素模塑鑄造,但這個過程是一個政治過程。”[3]1社會空間既是政治斗爭的場地,又是意識形態布展的工具。資本主義政治統治的強化,既讓意識形態滲透進空間的每一個角落,又讓社會空間成為文化意識產生和布展的場所。空間生產意識形態是思想文化層面的國家機器,立足于一定的空間生產力和空間生產關系。資本主義意識形態讓空間生產呈現著政治內涵,體現著意識形態統治功能。因此,空間并非純粹的空白器皿,而是帶有濃厚的政治意識形態色彩。批判空間意識形態和空間拜物教,是為了消解空間政治霸權的強迫機制。“如果關乎空間內容,空間展示出中性冷漠色彩,因而好像是純粹形式、理性抽象象征,那是因為它曾經被占據和使用,曾經是歷史過程的焦點,而這些歷史過程在山水間留下的痕跡并不很明顯。”[7]空間實踐與政治緊密結合,讓一切空間都帶有意識形態色彩。
列斐伏爾一再強調政治意識形態,而對種族、性別意識形態卻較少論及。埃爾頓指出,列斐伏爾的都市空間研究更受人們重視,“地理學、都市研究以及文化研究對列斐伏爾的重新發現是以忽略列氏論著的政治和哲學方面為代價的”[8]。空間生產不僅具有經濟意義,而且變成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統治工具。政治權利行使者憑借空間生產彌補自己統治的正當性危機。空間生產不僅具有異質性的內容,而且具有碎片化的形式,這導致了日常生活中無法避免的割裂。空間生產由理性建構,經實踐活動產生,最后通過自身展示,由此呈現了其與經濟、政治、文化、生活的互動狀態。空間生產自始至終體現著意識形態功能,是綜合各種政治力量的結果。資產階級利益也體現在空間生產中。“這個屬性是一個階級的霸權。”[3]10政治統治和空間生產聯系緊密,受著階級利益的制約,讓政治空間內部的不同利益集團發生矛盾,能制約經濟空間、文化空間和生活空間。“那些日常話語中的詞服務于區分,但不是說隔離,區分特殊的空間,以及一般用來描述一個社會空間。”[3]16因此,政治與空間生產相關,資產階級要獲取更大利益,就必須占據最高統治權,讓空間帶有濃厚的意識形態色彩。“我們所稱之為的意識形態通過在社會空間中的干預和它的生產獲得一致性,并且在那里也接受了身體。意識形態可能在一種關于社會空間的言論中保持下來。”[3]44資本主義意識形態竭力追求權力,在懲罰他人和自我反叛中服從于隱形的資本權力目標。因此,空間生產具有意識形態價值。
2.空間生產推動階級意識產生
列斐伏爾指出,空間與階級意識沒有必然的聯系,討論空間也不會混淆階級意識,但空間生產展示著各個階級的思想狀態。“甚至有一些人,他們偏離得更遠,聲稱任何關于空間、城市、地球和城市圈的討論都會導致模糊‘階級意識’,這種意識只要階級斗爭被關注就存在。”[3]89空間生產作為一種意識形態行為,不僅蘊涵著階級意識形態色彩,而且帶有政治意圖和意識形態策略性。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人為地把社會空間等級化,分為主導和附屬兩類。空間生產是意識形態和階級斗爭工具,讓資產階級意識成為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載體和工具,占據了社會主導地位。“各種擁有不同類型的城市空間可能會有一種中心權力強加的特征。”[3]152空間生產沒有消除階級意識對立,而是造成了新的階層意識分化。空間生產在拓展著自己,也瓦解著自己,不僅制造了社會矛盾,而且制造了反抗這些矛盾的階級意識。空間階級意識形態既遮蔽了人們的真實需求,又壓制了反抗的革命力量,是反日常生活的空間意識。空間反抗意識展示在對遮蔽空間的重視和關切。社會革命的主體已經不是赤貧的無產階級,而是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在當代發達工業社會,無產階級的生活水平已經得到提高,從而也讓無產階級喪失了革命意志。階級矛盾被空間生產控制和遮蔽,讓空間生產凝聚著階級意識形態的沖突和階級關系的矛盾。空間生產“很容易被資產階級力量所同化,很容易被新自由主義的市場滲透機制所利用”[9]。列斐伏爾參照馬克思的批判思路,不僅發現了空間意識形態生產過程,而且發現了空間的階級意識對立和內在的階級反抗意識。資本主義的僵化空間意識否定差異,掩蓋資本剝削,祛除反抗力量。
列斐伏爾還指出,資本主義利用媒介技術把社會變成官僚等級社會。“相同的抽象空間為營利而服務,通過在某種等級中安排它們以賦予那些專門場所特殊的地位,并規定了排斥和綜合。”[3]288城市空間生產為工人階級提供了住房,更讓資本家獲得了最多利潤。資本主義憑借媒介機器讓無產階級自覺服從資本意識形態,用個人權利和自由等空洞的名目麻痹無產階級的斗爭意志,讓無產階級非政治化。“一種政治化的空間摧毀了政治條件,即這個條件產生了空間,因為這樣一種空間的占用和管理開始反對國家,反對政黨。”[3]416技術理性推動了消費控制,也阻礙了個性的發揮,讓革命活動擱淺,但無產階級的革命意識不會完全喪失,因為資本矛盾在不斷加深,民眾的革命呼聲也始終沒有停息。無產階級深受壓迫,所以是革命的中心,但無產階級自身所具有的局限性讓其不能提出總體性革命策略。無產階級的革命意志不是自發生成的,而需要思想改造和教育培訓。無產階級革命是各種階層都發動起來才產生的,因此需要思想政治教育激發無產階級的革命斗志。列斐伏爾不把革命希望寄托在無產階級暴力革命上,而寄托在青年和知識分子的日常生活改造上,寄托在社會主義差異空間生產上。空間意識的不同讓空間生產形態有資本主義抽象空間生產和社會主義差異空間生產的不同,社會主義差異空間生產就是在消除意識形態對立和階級沖突的前提下制造出集體管理的社會空間形態。
二、政治的空間性
(一)政治在空間中形成和發展
1.空間是政治形成的前提
列斐伏爾對政治的空間性作了詳細考察。政治權力不斷傾向操控空間,并在空間政治的形成和發展中具有重要意義。政治權力體現在空間中,并反映著空間結構和空間生產方式。空間政治權力關系構成了空間生產方式中最有影響力的關系。“生產關系,不僅是生產工具的再生產,而且呈現在作為整體的社會空間中。”[10]238同時,政治權力能夠對象化為一定的空間結構,讓政治機器憑借空間生產實施權力。空間生產的失衡時常展示為政治權力的不平等。列斐伏爾指出,政治權力在空間生產運行過程中起著推動作用,“空間的政治生產被中心國家的權力所操控”[10]238。社會空間既是階級統治的媒介又是革命的場地,在社會空間的遮蔽處孕育著“新政治”的萌芽。空間生產和政治權力的結合在空間政治形成中起著重要作用,不斷建構新的空間政治形態。空間生產既是政治革命的組成部分,又是政治斗爭的場地。“那么,空間的政治作用是什么?當去政治化提到日程上的時候,空間就承擔了一種政治的角色。”[3]416空間形態經歷了從絕對性空間到抽象性空間再到差異性空間的演變過程,而社會的政治形式也將從資產階級統治過渡到無產階級專政。空間的自然屬性逐漸消解,而政治日益滲透進空間,并占據了主導地位。資本主義的政治革命很大程度上就是空間形態重組。在資本主義的空間政治統治過程中,強制、高壓、支配成了空間政治的主要特色。沒有空間視角,就不能完整理解資本主義政治統治。空間生產不僅是社會生產、政治控制與文化教化的斗爭場域,而且是集約化資本主義空間重組的集中表現。“它通過自身的方式肯定的積極的運行:技術,應用科學,和與權力相伴的知識。”[3]50空間生產變成資本主義政治統治和思想意識的核心范疇,既是政治統治和政治格局形成的基礎,又是政治格局和政治斗爭的產物。空間生產作為政治權力運行的舞臺,被資本家強制操控,“生產進入了一個清查存貨和強制接受的時代”[3]290。
在資本主義政治統治形成過程中,空間生產的同質化讓一切空間都轉化為政治統治要求的格局。資產階級推行著等級化的空間體系,個體的日常生活受到政治操控,處于高度專制和破碎的情形,技術化的媒介宣傳和消費體系制約著人們的生活空間,原本多元、差異的日常生活空間墮落成一個充滿壓抑、能夠轉化為交換價值的政治空間。政治一直竭力操控公民的日常生活,革命和反抗的力量也孕育其中,政治高壓集合到一定程度,就會爆發空間革命。發達工業社會為了延續政治統治,必須對社會空間進行嚴格控制,以實現大規模的空間生產。空間生產既是政治統治和意識形態的工具,又是充滿政治斗爭的生產領域。“空間不僅是發生沖突的地方,而且是斗爭的目標本身。”[10]181空間生產既是資本主義政治的空間化呈現,又是政府主導的政治行為。“空間是斗爭的媒介和最終場所,因此是重要政治問題。”[11]資本家憑借國家這一機器控制大眾的消費,通過專家學者讓政治意識形態滲入日常生活的每一個領域。“有一些專門的機構強使空間本體成為一種難以控制的機構,他們努力想它在一個范圍內工作,然后管住它、奴役它。”[3]127政治對空間形成的基礎作用還展示在空間生產和階級利益、權力運作的緊密聯系中。在空間生產政治化中,空間成為同質性、碎片化的政治權力活動空間,人與人之間、組織之間、國家之間的政治關系都能通過不同尺度的空間產品呈現出來,統治階級依照他們認為有用的政治形式來制造空間等級體系。
2.空間是政治發展的基礎
列斐伏爾認為,空間是政治統治的基礎條件,確保了資本政治統治等級秩序的穩固,讓整個日常生活空間都被嚴密的等級秩序組合起來了。“統治階級通過各種有效的方式維持它的霸權,其中知識就是這樣的一種方式。知識和權力的勾連就變得非常清晰了,而且盡管沒有一種方式可以禁止和顛覆這種形式的知識。”[3]10政治的發展也需要空間條件,需要空間生產的不斷推動。空間生產既是產生意識形態體系的過程,承擔著政治交往的功能,又是社會等級和秩序產生的過程,制造了社會秩序和交往關系。空間政治規劃延續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政治統治模式。都市化是空間生產和基礎設施創建的過程,是空間交往和空間意識形成的過程,于是,政治空間既是生產資料,又被空間消費規定;既是政治斗爭的對象和場所,又是新政治形式形成的條件。政治反抗能夠改善空間的等級化體系,假如沒有政治反抗,空間將變成一潭死水,政治反抗能夠孕育出差異空間形態。列斐伏爾指出,空間格局的優化組合,是變革空間政治秩序的前提。政治是在不停的空間重組中確證存在的,空間壓迫擴張之時,空間反抗也在擴大。資本增殖讓空間政治矛盾不斷蔓延,加快了空間生產政治化,間接延長了資本政治統治。發達工業社會讓無產階級喪失了戰斗力,自覺成為資本主義的維護者,被資本主義的政治觀念所滲透。空間生產建立在社會的貧富差距上,不是為了滿足普通居民的衣食住行,而是為了實現資本主義政治統治。發達工業社會憑借市場拓展、資本掌控、金融、技術等把資本政治統治法則擴散到全球各地。資本主義在政治的推動下,重塑了空間生存結構,獲得了空間政治霸權,導致了區域上的政治地位差異性。資本主義按照政治規則和市場原則向全球擴張,把資本主義政治模式推進到全球各地,取得了全球空間霸權。
資本主義政治空間并不是總體性的鋼板,而是充滿斷裂和分離,空間的斷裂處即是政治革命的爆發點。資本主義政治統治危機讓工人階級覺察到了聯合革命的重要性。社會空間具有交換和使用功能,政治斗爭摻雜其中,是政治行動的基礎場域,社會關系也會成為空間革命的障礙。空間生產變成政治統治體系的關鍵環節,“這種空間是均質的和破碎的,一種通過它的結構施加了魔力的空間”[3]301。有計劃的空間生產,不僅參與了商品制造,而且參與了資本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制造。空間生產與政治權力、統治技術結合,掌控了個人日常生活。資本主義空間統治的手段是:空間分離、空間分化和空間瓦解。革命者需要認清資本主義的空間政治圖謀,加強團結和聯合。只有生產出社會主義差異空間,才能消解資本主義抽象空間政治,才能真正達成人的自由發展。建構理想政治模式的路徑是變革日常生活空間,讓生活空間變成革命場域、成為差異空間,以消除抽象空間政治統治體系,開啟人類新的解放議程。解放問題首先涉及人在政治上的解放,政治解放就是用革命或改良的方法實現人在政治上的平等權利。資產階級利用空間生產將人從封建壓迫中解放出來,卻用技術和資本進行宰制。工業化和城市化為人的解放創造了條件,但不能最終解放人,必須變革空間形態,進行日常生活空間革命,才能實現人的最終解放。
(二)政治對空間生產的滲透
1.政治參與空間生產過程
列斐伏爾指出,國家政治干預力量在日常生活空間中起著重要作用,讓整個社會屈從于權力。“在這個過程中,盡管所有這些都是相互分離的,但并不意味著即便是瞬間放棄了整體控制,社會空間作為整體繼續屈從于政治實踐,即國家權力。”[3]8資本主義政治意識形態塑造著空間生產,成為空間生產的重要推動力量。隨著政治控制的強化,全部國家機器都變成空間生產的維護力量。政治權力始終在加強總體操控,并從整體上操控了日常生活空間。國家機器作為強大的組織力量在背后操縱空間生產。隨著技術的進步,國家政治權力暫時緩和了資本主義的危機和矛盾,讓資本主義空間生產處于穩定的狀態。國家政權對空間生產起著主導作用,因此列斐伏爾考察了空間政治的運行機制。他指出,政治參與空間生產,是受經濟利益的驅動。“政治權力庇護了一種固有矛盾。它控制了物流并且也控制了企業集團。”[3]338國家政權對資本的控制以城市空間生產為載體,因此,國家政權始終牢牢控制著城市規劃和生產。空間生產政治化不僅讓空間成為生產對象,而且造成了空間異化和碎片化。資本主義政治把空間分割成各種空間形態,加劇了貧富差距。空間地理的不平衡往往會導致社會矛盾和階級沖突,空間生產已經被政治化了,到處都充滿著政治斗爭。空間政治形態是現實空間體系及關系的扭曲反映,當資本主義政治形態以空間的形式如此這般地物質化時,資本主義通過自動化經濟生產的具體實踐成功實現了政治形態的物化。由此,空間生產不是純粹的經濟工具,而是與政治統治緊密相連。政治權力操控空間生產,造成了政治意識形態的空間生產化。“事實上,在一種非常有意義的方式上,這樣的意識形態與空間有關,因為它們以一種戰略的形式在空間中介入。”[3]105空間生產如同政治操控和社會交換,有固定的流程和秩序,承載著政治格局,不是純粹自然的,而是政治權力斗爭的產物。
列斐伏爾指出,發達工業社會運用隱蔽的統治手段、強制的文化意識等方式進行空間生產,以實現資本增殖和維護全球政治霸權。“今天,國家和它的官僚機構以及政治制度繼續在空間中干預,并且通過它的工具屬性制造空間,為了在各個層面上、每個經濟領域都能關涉到,社會實踐和政治實踐開始在空間的實踐中整合力量。”[3]378隨著信息技術和網絡時代的到來,資本主義政治模式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范圍擴張,影響著全球的政治和思想變遷,從而維護了資本主義政治霸權,引導著落后國家的政治革新和階級革命發展。空間生產在飛速提升生產力的同時,也呈現著國家機器的強制力量,展示著統治階級的目的。在當今時代,誰能主導空間生產,誰就能在政治中占據支配地位。空間生產與貨幣一樣,并非客觀中立的,而是蘊涵著階級斗爭和社會關系,是政治斗爭的對象和目標。
2.階級革命推動空間生產發展
列斐伏爾認為,空間政治矛盾越嚴重,引發的抗爭運動越激烈。“空間的國家管理蘊含了一種穩定性的邏輯,既是摧毀性的又是自我摧毀的。”[3]378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空間已經取得和時間同等的地位,成為資本政治統治的最主要工具。暴力機關組成的國家高壓統治是資本增殖的手段。“支配空間慢慢成為軍隊、戰爭、國家和政治權力的附屬物。”[3]166無孔不入的政治權力滲透進空間,讓人們無力反抗、失去家園。空間既是壓迫的場所,又是反抗的基地。空間生產引起了激烈的階級革命運動,空間生產的斷裂處往往潛藏著新政治秩序。總體性的階級革命是反抗抽象空間霸權的現實路徑,只有總體性的階級革命爆發,才能消解空間的僵化和神秘、促成總體性革命意識的建構、實現社會變革。只有全面地認清空間政治的剝削本質,才能激起空間反抗斗爭。階級革命就是要解放被空間剝削和壓制的人們,讓空間生產按照差異、開放、透明的方式運行,獲得面向未來的無限開放性和可能性。階級革命是對具有等級性、強制性、控制性的資本主義抽象空間的革新力量,它讓日常生活空間變成人能夠自由選擇和不斷創新的空間形態。取代抽象空間生產的將是一種差異性的空間生產機制。空間革命和階級斗爭不是抽象的階級分化,而是微觀日常生活的多元化權力的追求。
列斐伏爾空間政治學不太關注社會是由群體還是由個體構成,而更關注日常生活空間的宏觀或微觀層次;不太關注宏觀的人類歷史解放,而更關注微觀的日常生活空間變革和藝術批判。列斐伏爾始終執著于人類解放,并立足于日常生活空間變革的政治策略。卡斯特也指出:“將新社會斗爭與另一種民主政治結合起來,可以使基于開啟社會主義道路計劃的左翼選舉獲勝。”[12]社會主義革命能夠解決空間矛盾和空間斷裂,并制造出差異空間用于調節不同空間利益主體的沖突。空間矛盾必須憑借政治和社會手段才能克服,必須先解決階級矛盾才能消除。“社會主義這種社會的轉變,預設了空間的擁有和集體管理,被利害相關的各方不斷干預,即使他們有著多重的利益。”[2]58無產階級革命必定導致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制度和生產模式的消解。社會主義需要創造出適合自己的空間形態,假若沒有適合自己的空間形態,社會變革和人類解放都只能是空想。提高生活品質就要變革空間結構,階級革命也要先變革空間形態或改變生活本身,而并非只改變政治意識形態等形式。階級革命就是創造出適合人類生存的具有真善美特質的異質性和多樣性的日常生活空間,消解同質化、抽象化、矛盾性的資本主義空間。
三、空間生產政治化的悖論

(一)空間政治霸權
列斐伏爾指出,空間生產和政治的互動機制既加劇了空間生產政治化,又導致了資本主義空間政治霸權。“‘霸權’這個概念是葛蘭西引進的,用來描述未來社會構建的工人階級所處的角色,然而這也是用來分析資產階級的行為,特別是涉及到空間的時候特別有用。”[3]10空間生產改變著世界政治格局,其內在驅動力就是政治權力,政治權力強化了資本主義空間霸權,因此,空間霸權是資本主義政治擴張性的反映。
1.強化了資本掠奪
列斐伏爾認為,空間政治霸權潛藏著野蠻和暴力。“霸權暗含著更多的影響,更多的是壓制暴力的永久使用。”[3]10資本主義因為空間政治的支配結構,更具有霸權主義的特質。空間生產有著等級、匱乏和專制的特性,沒有帶來自由和平等,卻帶來了新的政治異化現象。空間生產讓政治異化滲透進日常生活,控制了整個社會。發達國家為了維持全球空間政治霸權,繼續利用高技術手段侵占別國空間,以獲得更大利潤。空間生產就是資本家利用全球化,將全球空間納入資本主義統治體系,維護全球空間政治霸權的過程,既讓資本主義政治統治體系得到擴張,又讓資本主義找到新的政治統治手段。維持資本主義空間政治霸權的重要經濟因素是金融虛擬資本,強制、征服、認同是取得空間政治霸權的傳統手段,金錢、科技和武裝力量都能長期維護空間政治霸權,這些要素讓空間政治霸權在不同時期有不同呈現形式。哈維指出,資本主義空間政治霸權已經不是機器化工業生產,而是金融虛擬資本。“金融資本在這一時期進入了美國霸權的核心舞臺,并已經擁有足夠的力量對工人階級運動和國家行為施加決定性的影響,尤其是在那些陷入嚴重債務危機的國家里。”[13]資本主義空間政治霸權是資本掠奪性的積累所導致的,并引發了很多空間矛盾和沖突。金融虛擬資本呈現出極強的剝奪性,不斷掠奪空間資源以獲取更多經濟利益。
2.引發了政治危機
資本主義空間政治霸權引發空間矛盾,既強化了資本的剝削體系,又導致全球性的政治危機。資本空間政治霸權是制度性的,布滿欺騙、掠奪和危機,也引起了很多不滿和抗爭。全球化幫助資本主義政治模式走向世界的每個角落,讓絕大多數國家都實行民主政治體制,不斷突破空間界限,將資產階級意識投放在全球空間,在世界范圍內普及。資本主義為了實現全球空間政治霸權,不僅對無產階級進行殘酷的剝削和壓迫,而且對原本和諧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空間進行無情的破壞。資本的空間政治霸權遮蔽了人們純真的內心,破壞了自然生態平衡,制造出一個單向度的社會,這如同卡斯特指出的,“空間是一個物質產品,它相關聯于其他物質產品,包括在特定的社會關系中賦予空間一種形式、一種功能和一種意義的人”[14]。資本主義還利用媒介制造出發達工業社會的虛假繁榮,營造出迷霧般的日常生活。媒介成了空間異化的主要中介者,變成日常生活碎片化的主要誘因。媒介把發達工業社會的空間異化現象遮蔽在真實生活之下。由此,社會空間異化現象既是日常生活異化現象的強化,又是資本政治的剝削和擴張。空間政治權力高度集中,讓資本主義全面控制了居民的日常生活。“支配的空間在這個領域實現了軍事和政治(戰略)模型,然而比這更多,因為由于權力的運作,實踐的空間是規范和約束的載體。”[3]358空間政治矛盾取代階級矛盾,讓一切矛盾都聚合于空間中。“交換功能和實際功能之間的對立,雖然它開始是一種純粹的對立或者非辯證的分析,但最終卻假定了一種辯證的特征。”[3]356資本主義抽象空間憑借政治權力和資本邏輯來實現擴張,將人們的生存空間裹挾在抽象空間中。解決資本主義空間政治矛盾,需要差異空間和差異權利,需要打破資本主義的空間政治霸權。
(二)消費官僚體制社會
在列斐伏爾看來,空間生產將整體的社會生活撕裂為碎片,讓其處于分裂狀態,空間的分離造成了世界的無產階級化,導致了交換功能和實際功能的對立,造成消費官僚體制社會。空間已經變成消費的工具,讓空間生產布滿消費關系。空間生產將消費關系布滿社會生活,資本主義憑借對消費的控制,掌控了社會關系,形成消費官僚體制社會。空間生產不僅制造了影像,而且影響著生產和消費。總之,空間生產是由資本推動的,在商品符號化的推動下,形成媒介世界。
1.制造了顛倒的世界
作為顛倒的世界,空間生產導致了物欲橫流、人心冷漠,造成了社會內部的極度分裂,讓日常生活成為零散的碎片。分離導致形象成為幻象,分離的發展形成幻覺化的世界,讓日常生活成了虛假的幻影。空間生產加重了文化領域的消費主義傾向,造成了意識形態的物化現象,也就是說,文化成了幻覺,而虛假的意識形態卻成為“真實存在”。當代社會是“分離的政治體制”,空間生產以技術為基礎,是無聊的循環過程,沒有把人解放出來,而是加深了剝削和奴役。空間生產造成了單面的人,單面的人生產了異化的世界。空間生產讓人們沉迷于物質的享樂之中,而無法思考資本統治邏輯背后的靈魂空虛問題。當人們沉湎于空間消費的符號體系中時,只是活在自己的臆想中。鮑德里亞指出,消費這一活動“是(通過對消費個體進行分化作用)實現社會控制的一種有力因素”[15]。消費社會造就了空間生產,深深壓抑了人的真實需求,加劇了資本剝削。空間生產是資本的代言人,弄得人們目眩神迷,沉迷在無節制的消費中。空間生產的政治功能已經從滿足生活需求轉變為社會等級和身份的區分。因此,空間生產經歷了從物品匱乏到物品豐盛、從實際功能到符號功能、從客觀到主觀、從滿足需求到社會區分的轉變。表面上看,生產者能夠自由選擇,其實空間生產行為受資本的意識形態支配。晚期資本主義用奢侈浪費的符號消費取代節儉的道德,從而改變了消費文化。所以,人們消費的不是具體的空間,而是空間關系和空間的象征意義。空間變成社會價值和身份地位的象征。資本家用夸張的手法把人們帶入夢幻的迷宮,淡化了現實的無聊與慘淡,在滿足人們精神幻求的同時,也制造了新的等級和身份。于是,后現代消費社會中的資本家把很多的精力投放在了操縱空間消費、空間產品流通上,讓消費者沉湎于夢幻,產生自戀情節。
2.造成了消費的總體控制性
發達工業社會的政治危機既是技術理性發展的結果,又來自技術和消費結構。資本家制造消費欲望、引導消費活動、影響生產機制,憑借媒介宣傳和城市景觀,影像不斷被生產出來,用影像激發起人們的消費欲望,潛移默化地讓人們認同其價值法則。空間生產導致過剩的物品積累,不僅表明需求的增多,而且表明供需矛盾的加劇。人的欲望是沒有限度的,即使再多的物質財富也不能滿足人的需求,人們的消費行為非但沒有實現享受功能,而且是脫離享受功能的。空間作為消費的對象,信息、編碼、影象都變成不折不扣的空間產品。總之,品牌、氛圍、個性、差異等符號意義都變成了空間政治霸權的中介和工具。空間生產憑借媒介制造稀有的信息獲取身體空間的象征意義。“空間性被一種內在于生命的死亡所刻畫——當它進入與自身的斗爭以及尋求自己的解構的時候,它就增生擴散了。”[3]135豐盛的信息和透明的體系構成了空間生產的內部機制。空間生產制造的符號影像引導了人們的思想和行為,讓街道和墻壁也成為宣傳媒介。空間生產是當代社會的政治權力話語體系組建的,“它作為一個整體,通過文化和知識在社會中運行,而且一般來講是通過文化的中介:政策、政治領導人、政黨,還有很多知識分子和專家”[3]10。因此,空間生產造成了消費的總體控制性,用符號編織出整個后現代工業社會政治的虛幻圖景。
四、空間生產政治化悖論的克服
在列斐伏爾看來,空間生產政治化引起的空間政治霸權和消費官僚體制社會,需要靠“總體的人”和身體空間革命來消解。
(一)“總體的人”的實現
列斐伏爾對空間政治進行論述的起點是“總體的人”。實現“總體的人”,既是克服空間政治異化現象的工具,又是實現更好的政治生活的目標。
1.需要現實實踐
列斐伏爾將馬克思“全面的人”改造為“總體的人”,“‘總體的人’是有生命的主客體的統一,既是行為的主體又是行為的客體”[16],“總體的人”建立在克服現實政治異化的基礎上,需要現實實踐的驗證。列斐伏爾指出,人的自由發展要憑借“總體的人”來實現,“人的前進和發展,只有通過總體的人的概念才能獲得意義”[17],“總體的人”到目前還沒有實現,還只是遙遠的夢想。作為夢想,它不只是理論解釋,更是立足于現實實踐。因此,“總體的人”要憑借社會實踐活動來實現,“無論從理論還是現實角度來看,歷史不僅僅包括時間的變遷,同樣包括空間的變遷”[18]。實現“總體的人”需要克服異化,復歸自然狀態,實現人類本真存在的復歸,讓人成為充分自由的具有理想的人。“總體的人”是方向和期望,是擺脫了生活庸常性和物欲的人。
2.需要人道主義和自然主義的統一
要拒斥空間政治異化,就要實現“總體的人”。“總體的人”體現著主動和被動的生產主體的結合,不是主宰,而是平等共存,實現個體與他者的共存。“總體的人”不是理論假定,而是扎根于現實的實在性,既消除了異化,又是真實的存在。“總體的人”是克服社會空間的異化現象,是人性的回歸,是人道主義和自然主義的統一。“總體的人”要憑借藝術行動實現。藝術是高度個性化和共同化的統一,這能讓總體人保持個性和集體性的統一。列斐伏爾的“總體的人”既是對馬克思“全面的人”的改造,又繼承了尼采的超人和酒神精神,但“總體的人”仍具有顯著的烏托邦幻想色彩。“總體的人”就是要復歸人的感性的多元性和個性的整體性,不受異化現象制約的和諧生存境遇。因此,“總體的人”的實現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辯證過程。封建社會以及之前的社會,人們沒有意識到社會的總體性和自己的地位的原因是當時的社會關系是受自然約束和社會禁錮的,所以不可能意識到自己是社會存在物更不可能把自己看成總體性存在。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建立,才讓人真正成為社會意義上的存在,如同盧卡奇指出的,“人成了本來意義上的社會存在物。社會對人來說,成了名副其實的現實”[19]。
(二)身體空間革命
列斐伏爾的身體空間革命論蘊涵著身體空間生產、身體空間異化和身體空間復歸等層次:資本主義社會之前的人的身體空間沒有被異化,時常處于節日當中;資本主義社會的人的身體空間已經異化,時刻處于抽象控制之中;社會主義社會的人的身體空間將是多元和差異的藝術空間,將讓人的身體空間復歸節日。
1.需要激情的節日空間
列斐伏爾指出:“考慮所有這些,社會實踐預設了身體的使用:手的使用,器官和感官的使用,與作為相關工作的姿勢。”[3]40身體空間并非先天的東西,而是社會實踐的產品。“生活的身體,‘使用者’的身體——不只是抓住了各種各樣的空間,而且構成了哲學家所謂的‘比擬’的網絡:圖像,符號。那些身體通過眼睛傳送自身、轉移自身、騰空自身:每種呼吁、刺激和誘惑被動員起來表達一種修飾、微笑和高興的神態。”[3]98列斐伏爾的“空間哲學”圍繞人的身體空間而展開。“空間——我的空間——不是一種我所構建的文本性的語境,相反,它首先是所有我的身體,然后是我的身體的對應物或者‘他者’的鏡像或者陰影,它是一方面觸及、滲透、威脅或者有利我的身體與另一方面所有其它身體之間的轉換交集。”[3]184“身體空間”是超越傳統邏各斯二元對立的范疇,既是面向未來開放的概念,又是充滿活力和激情的人體。動植物也能憑借身體制造出屬于自己的空間,并憑借身體劃分自己的領地,但它們的身體空間生產是沒有意識的本能行為,是不摻雜意識活動和心理活動的生存行為,而生產出的空間也是冷冰冰的。“身體在空間中的布置和它在空間中的占據之間,存在一種直接的關系。”[3]170列斐伏爾指出,動植物的“身體”是沒有理性的軀殼,而人的身體是能動的機器,具有多元的空間性,并呈現著兩個構成要素:為了生存而積蓄的物質能量和由激素引發的身體欲望、激情和沖動。“性器官是人體巨大能量的匯集之地。”[3]91身體空間革命需要充滿激情的節日空間,以消除日常生活的庸常。節日空間既具有物質形態,又具有精神性;既體現出強大的物質能量,又彰顯出鮮明的情感;既呈現著一定的造型,又具有動態的美感。
2.需要詩意的藝術化生產
列斐伏爾還指出,身體空間體現著生產力水平,制造了空間產品、社會歷史。“我們已經遇到了這種身體——我們的身體——在當前的討論中就碰見了許多次。”[3]194動植物身體生產出的空間是冷冰冰的,人身體生產出的空間則充滿了社會意義。在當代,人的身體空間更加主動地參與空間生產。“作為一種‘機器’,身體空間是雙面的:一方面通過能量的大量提供而運行(從消化到新陳代謝的來源),另一方面通過提煉和記錄能量(感官數據)。”[3]196身體空間是空間生產的機器,但不是僵化的機器,而是能動的、靈活的機器。各個階級的身體空間需要聯合,以消解抽象空間控制,建構起差異空間。社會主義空間生產就是要消除私有制等國家制度對身體空間的支配,消除空間政治異化,讓身體空間獲得自由,進行藝術化的詩意生產。身體空間的詩意生產是既蘊涵社會生活生產又蘊涵身體的沖動、愛欲、激情和充滿想象力的詩性生產實踐活動。
總之,“空間生產”的政治批判是列斐伏爾在面對發達工業社會的城市化運動,用社會空間辯證法對如何克服資本運作弊端的思考所得。他把馬克思社會空間批判方法用于城市空間生產研究,并對空間生產過程進行了政治經濟學批判。他的研究既拓展了馬克思城市社會學的視域,又促進了人們反思自己的空間觀念和空間行為模式。
[1] STUART E.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rve:theory and the possible[M].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4:181.
[2] 包亞明.現代性與空間的生產[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
[3] LEFEBVRE H.The production of space[M].Translated by Donald Nicholson-Smith.Oxford UK:Blackwell Ltd,1991.
[4] 亨利·列斐伏爾.空間與政治[M].李春,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33.
[5] 夏鑄九,王志弘.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M].臺北:明文書局,2002:34.
[6] 李彪.古鎮旅游空間生產的動力及其在旅游資本循環中的博弈[J].財經理論研究,2015(6):91- 99.
[7] LEFEBVRE H.Reflections on the politics of space[M].London:Antipode,1976:31.
[8] STUART E.Between Marx and Heidegger:politics,philosophy and lefebvre’s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London:Antipode,2004:95.
[9] 大衛·哈維.馬克思的空間轉移理論——《共產黨宣言》的地理學[J].郇建立,譯.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5(4):21-34.
[10]STUART E,Understanding Henri Lefebrve[M].London and New York:Continuum,2004.
[11]ENTRIKIN J N,BERDOULAY V.The pyrenees as place:Lefebvre as Guide [J].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2005,29(2):93.
[12]CASTELLS M.City,class and power[M].New York:The Macmillan Press Ltd,1978:60.
[13]大衛·哈維.新帝國主義[M].初立忠,等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9:53.
[14]CASTELLS M.La question urbaine[M].Paris:Francois Masperro,1972:152.
[15]讓·鮑德里亞.物體系[M].林志明,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23.
[1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94.
[17]亨利·列斐伏爾.辨證唯物主義[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8:100.
[18]徐冠軍.重新解讀馬克思的發展理論——基于空間生產的視角[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6(6):89-94.
[19]格奧爾格·盧卡奇.歷史與階級意識[M].杜章智,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92:47.
(責任編輯 魏艷君)
On Henri Lefebvre’s Political Criticism of “Spatial Production”
SUN Quan-sheng
(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Studie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09, China)
Lefebvre’s political critical of “spatial production” implies the criticism to the political phenomenon of spatial production. He examin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patial productionand politics, and thought that spatial production and politics are interactive: politics influences spatial production, and spatial production performs a political function.Its method is using Marxist materialist dialectics to explain the paradox of politicization of spatial production and its solution. In Lefebvre’s opinion, to reject political hegemony space, it is necessary to realize spatial political rights by virtue of revolution of the overall people and body. Lefebvre’s political criticism of “spatial production” can display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political ideology and spatial production, which implies a field of microscopic examination of daily life, thus promoting social and political studies.
production of space; political criticism; the whole person; body revolution
2016-09-11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生命倫理的道德形態學研究 ”(13&ZD066);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產業結構演變中的大國因素研究”(11BJL015);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現代倫理學諸形態研究”(10ZD&072)
孫全勝(1984—),男,浙江麗水人,講師,哲學博士,研究方向:法國哲學、當代中國經濟哲學。
孫全勝.列斐伏爾“空間生產”的政治批判探析[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2017(5):96-106.
format:SUN Quan-sheng.On Henri Lefebvre’s Political Criticism of “Spatial Production”[J].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7(5):96-106.
10.3969/j.issn.1674-8425(s).2017.05.015
C912.81
A
1674-8425(2017)05-0096-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