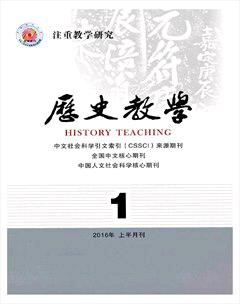關于開展國際關系史研究的兩點意見
齊世榮
[摘要]研究國際關系史,要注意兩點._是必須以史料為基礎。官府文書與私家記載應當并重兼采,綜合利用。二是要注意政治、經濟、意識形態等多種因素所起的作用,并對它們作綜合性的研究。
[關鍵詞]國際關系史,史料,史學方法
[中圖分類號]K1[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0457-6241(2016)02-0003-05
有幸參加今天的會議,見到許多中青年同行,十分高興。會議主持人一再要我講話,只好勉為其難。年老,缺乏新知,下面淺談兩點意見,請指正。
第一,研究歷史,必須以史料為基礎,國際關系史也不例外。史料大約可分為三類:文字史料、實物史料和口頭史料,其中文字史料包含的信息最多、最重要,是我們尤其要重視的。
文字史料可分為兩大類:官府文書和私家記載。先談官府文書。到今天,許多國家(美、英、德、法、日、意等國)都出版了大量的外交文件匯編。沒有出版的外交文件及其他文件,可到各國檔案館去查。現在各國檔案的保密期限一般定為30年,這對研究國際關系史是十分有利的。看外交文件,當然不能僅從字面上去理解,還要深入了解它提出的背景以及它所要達到的實質性目的。例如,美國總統威爾遜在1918年1月提出的“十四點原則”,表面上說得冠冕堂皇,是建立“世界和平的綱領”,實際上要達到的目的是美國在戰后主宰世界。因此,只看“十四點”本文不夠,還要看1918年10月李普曼和科布受威爾遜親信顧問豪斯上校委托所擬的“十四點”的注解(恰得到威爾遜的批準)。研究國際關系,不能只看一方的文件,要看雙方的,甚至多方的,互相參照比較,才能明了歷史的真相。還要注意的是:西方議會的辯論紀錄,其中涉及外交方面的,不可輕信。一些議員和政府官員的發言,往往言不由衷,必須看他們平日的一貫主張和表現。例如,在1939年1月26日和27日法國國民議會進行辯論時,外交部長龐納“激昂慷慨”地說:“法國的領土一寸也不能割讓(給意大利)”,還說在法國同它的蘇聯和波蘭盟友的關系方面,從來沒有過現在這樣“密切而經常接觸”,等等。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愛國的斗士。他的整個演說從頭到尾是一連串的謊言。據德國大使韋爾茲克伯爵說.幾天以后,龐納向他直率地承認,“在議會的外交辯論中說的話,往往很明顯地是適應國內的需要,而并不準備傳到國外”。
私家記載包括日記、書信、回憶錄等,它們所記的內容常有官府文書中所沒有的,往往能揭示歷史的真相。
日記這一類,例如20世紀20年代英國駐德大使阿貝農的日記《和平大使》,是研究《洛迦諾公約》非看不可的。《公約》的簽訂被英國外交大臣奧斯汀·張伯倫吹噓為“戰爭年代與和平年代的分界線”。真相如何呢?英國為什么要竭力促成公約的締結呢?阿貝農(有《公約》的“教父”之稱)在他日記里對英國的意圖說得十分清楚。一是扶德抑法。1923年8月20日寫道:‘關于中歐的整個形勢和英國應該采取什么政策的問題,最清楚的結論看來是英國的根本利益在于防止德國的崩潰。只要德國是一個整體,歐洲就能或多或少保持均勢。一旦德國分崩離析,這個均勢必然消失,而法國則依靠它的軍隊和它的軍事同盟,依然無可置疑地在軍事上和政治上處于支配地位。……任何人如果認為,一個像拿破侖在提爾西特和約以后那樣支配歐洲大陸的法國政府依然對英國友好,他就是對民族心理的一個可憐的判斷者。……在這種情況下,要我們對法國友好同樣是不可能的。在希望維持英法協約的同時,我不得不希望一個強大的德國的存在。”
英國的另一個目的,是把德國拉入西方集團,防止蘇德接近,1925年8月11日日記寫道:“公約的第二個效果是將使德國解除被迫投入俄國懷抱的危險。……熱那亞會議的情況可能重演,隨之發生的是另一個更壞的拉巴洛條約。根據公約,德國被接納為一個平等的成員,并作為一個英國與法國的伙伴維持西歐的現狀。如此,德國被吸引到俄國共產主義勢力范圍的危險就明顯減低了。”
一些私人通信,也有相當高的史料價值。研究20世紀30年代英國的綏靖政策,首相張伯倫的書信是必看的。張伯倫這個人很愛寫家信,他給他一個妹妹寫了大量的家信,而且內容基本是談政治。由于是私人信件,談得很露骨,是官府文書中不可能有的。2005年塞爾夫編了4卷本的《尼維爾·張伯倫日記書信》,提供了不少重要史料。例如,1937年11月26日張伯倫在給他妹妹艾達的信中談到他要以犧牲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換取與德國的妥協:“我不明白為什么我們不該對德國說,‘請給我們以滿意的保證,表明你們不會用武力對待奧地利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我們也愿意給你們同樣的保證,表明我們不會用武力阻止你們所需要的變更。只要你們以和平手段取得這些變更。”
這封信表明,張伯倫早已決定犧牲奧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以換取與德國的妥協。他之所以強調“和平手段”,主要是為了避免刺激國內外輿論,以便更順利地推行綏靖政策。
回憶錄也是需要使用的一種史料。二次大戰臨近結束時,美國在日本投了兩顆原子彈。這不僅是美國軍事上的需要,也有強烈的政治目的。杜魯門在他的回憶錄中講到,史汀生(時任陸軍部K)對他說:“原子彈對于我們與其他國家的關系一定產生決定性的影響”。貝爾納斯(日寸任國務卿也對他說:‘他相信這種炸彈有可能使我們在戰爭結束時處于發號施令的地位。”一句話,美國把原子彈看作一種戰后稱霸世界政治武器,特別是用來威懾蘇聯的武器。
我們也要注意到私家記載的局限性。例如,西方政治家所寫的回憶錄,往往揚己抑人。丘吉爾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回憶錄》就是一例。這本書第二卷的標題是“光輝的時刻”,從1940年5月法蘭西之戰寫起,到1940年底英國在埃及打敗意大利軍隊。他給第二卷定的主題是“英國人民怎樣單獨堅守堡壘直到過去半盲的人們作好一半的準備”。第二卷下部的標題是“單獨作戰”。這完全是不顧事實的自吹自擂。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一場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戰爭。1940年6月法國雖已戰敗,蘇、美尚未參戰,但無論如何也不能說只有英國單獨作戰。中國人民早自1937年就已英勇奮戰,全面抗擊日本侵略者,開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丘吉爾竟然視而不見。又如,20世紀30年代曾任英國外交大臣的艾登(1935 1938年)把他的回憶錄取名為《面對獨裁者》,標榜自己是一個一貫反對法西斯獨裁者的斗士。但實際上,艾登和首相張伯倫兩人在推行綏靖政策方面的總體上、基本原則上是一致的,都主張把德國作為首要的爭取對象。1938年1月31日,艾登對張伯倫說:“我完全同意我們必須盡一切努力與德國達成協議。”分歧僅在于艾登認為意大利的重要性遠遜于德國,不值得作出過多的讓步,而張伯倫則主張對德、對意都要搞緩和,如果能先同意大利成交,又何樂而不為呢?
二
路德的教義一般被近人稱為“因信稱義”,或“唯信稱義”。其實,“因信稱義”這個說法并不完全,因為路德認為信仰并不是交換,真正的信仰是純粹的,沒有任何功利目的。信仰是指人對上帝的皈依,而得救則是上帝對人的慈悲,人的靈魂得救完全取決于上帝的意愿,甚至是前定的。路德的名言是:‘做好事的不一定是好的基督徒,但好的基督徒一定做好事。”路德認為得救完全靠上帝給人的無償的恩惠。根據這種理解,路德否定善功在靈魂得救中的作用,也否定了人可以通過善功得到“自救”。靈魂得救不是依靠個人的功德,而是靠對上帝的信仰。人只有信仰上帝,接受上帝的恩賜,才能成為真正的基督徒,其中有些人可以因上帝的慈悲而得救。
路德認為:苦修的方式、做好事的方式,都只是屬世的工作,與屬靈沒有關系。除了信仰之外,人和上帝再也沒有別的關系。人幫助鄰居,那只是對人的鄰居有幫助:人在世界上行善,那也只是對人的世界有所益處,與進入上帝之國沒有關系。更為重要的是,既然人和上帝只是信仰關系,那么,關鍵是要看人有沒有信仰,而不是看人有沒有成就或功德。人在世界上所取得的成就,遠非人與上帝關系的基礎。這是因為,人與上帝建立的是一種信仰的關系,而不是人靠自己的成就去博得上帝的喜愛。以己意行事,卻把這說成是上帝的意愿,就是人不信靠上帝的表現。以為行善和積累塵世的功德,就是滿足了稱義的條件,這是人的一種驕傲。路德提倡“因信稱義”,要講究人對上帝的信靠和上帝對人的救贖關系。講明“因信稱義”,就是要說明人是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功德來自救的,而是要把自己完完全全地交給上帝。“因信稱義”把善功和得救完全分離,只有這樣,人才能恢復在上帝面前的謙卑之心,才能夠明白“稱義”完完全全是出自上帝的恩惠,出于上帝的救贖。
路德是一個卓越的《圣經》研究者,認為《圣經》具有至高的權威,進而否定羅馬教廷具有解釋《圣經》、制定宗教傳統儀式的權威。路德提出“凡信徒皆祭司”的觀點,不僅否定了教會的等級制度,而且還建立了人與上帝的直接溝通,并且指出了每個人得救道路和方式的不同。在路德那里,接受神職只是一種職業,教會和神職人員都不具有神性。真正的權威來自《圣經》。這些觀點在1517年后得以廣泛流行。
1519年萊比錫爭論時,路德提出教會是世俗組織的論點,指出得救依靠信仰而不是依靠羅馬教皇和自封神圣的教會。1520年,路德發表《羅馬的教皇》一文,稱教皇為基督教王國一切異端的根源。在《教會的巴比倫之囚》一文中,路德指出信仰的重要性和要廢除以往的奇跡。在1520年出版的《致德意志基督教貴族》中,路德宣布:教廷借以保護其權力的三道羅馬護墻都被推倒了。因為一切信徒皆為祭司,所謂屬靈等級高于世俗等級純屬無稽之談:一切信徒皆為祭司這一真理又推倒了第二道護墻,即唯有教皇有權解釋《圣經》:它同時也摧毀了第三道護墻,即除教皇外,其他任何人無權召開教會公會議。旨在改革教會的“真正自由的公會議”,應由世俗當局來召開。其后,他又列舉了一系列需要解決的實際問題:教皇的管理不善、神職任命、稅收需要加以限制:,累贅的職務應予撤銷德國教會的利益應置于一位“德意志總主教”的管理之下:允許神職人員結婚,宗教節日太多不利于過勤勞莊重的生活,應予減少包括托缽修會在內的沿門乞討應加以制止,妓院應關閉,奢侈揮霍應受限制,太學神學教育也應改革。
路德還提出了“基督徒自由”的概念。基督徒自由可以分為現世和來世兩個階段,真正的自由將出現在來世。現世的基督徒有兩種屬性:精神的和肉體的。在精神方面,基督徒是自由的,只服從于上帝,不服從世俗的秩序。不過,現世基督徒還有著“肉體”的屬性,因此在物質方面,基督徒也與其他人一樣,應當服從世俗秩序,因此就可以當兵,可以嫁娶,可以過世俗生活。路德區分了“神之國”和“人之國”,還給了基督徒精神上的自由和世俗世界生活的自由,使基督教能夠與人間的秩序和睦相處。
在路德的思想中,存在著從體制出發解決教會腐敗問題的方案教會由政府來管理,教會的財產用于濟貧等公共慈善事業。路德發現,中世紀后期修道院的純潔運動無補于事,因為是否獲得“純潔”歸根結底是個財產的分配問題,而不是精神克制的問題。中世紀后期的修道院宗教改革有兩個目標:一是指出羅馬教會的做法是不符合基督教傳統的(如圣職買賣、蠟燭費、反對十字軍攻擊基督徒),需要改革;二是希望找到一種糾正腐敗的途徑(如宗教會議,如推行內部純潔、禁欲,如派好的神父擔任地方教聊。這樣的改革,旨在廢除一些不符合基督教傳統的弊端,卻不能改造整個基督教體系和教會體系。路德改革也提出兩個目標:一是指出教會傳統本身存在嚴重問題:二是指出教會腐敗的根源是權力和財產,要求把教會的財產和權力交還給政府和社會,以此來解決“靈與肉”對立的問題。
三
路德追隨奧古斯丁的榜樣,尋求真理,分辨圣俗。布雷迪告訴我們:1510-1520年間,路德從通過對奧卡姆的研究追溯到奧古斯丁,又從對奧古斯丁的研究追溯到圣保羅,并且通過對奧古斯丁兩元論(精神與肉體、永恒和暫時、天堂和人世、將來和現時、隱蔽和公開、不可見與可見,內部和外部、福音和法律)的探索,發展出自己的兩個王國理論。路德指出:
世俗的世界,由寶劍統治,能夠被眼睛看到;精神的世界,由恩典統治,并寬恕罪。
上帝建立了兩個世界精神的和世俗的。精神的世界只在真正的基督徒中實施,它的領袖是基督。這個世界充滿著愛和相互服務的精神,一切的基督徒都完全平等。信徒們享受基督徒的自由,世界上的法律、權威都不能高過基督徒的天良之上。對上帝的愛,也不是強迫的,而是自愿的。這個精神世界也是一個真正的教堂,不同于塵世中任何的外在的教堂——它是完全精神的、福音的世界。
另外一個是塵世的或世俗的世界。這個世界與自由平等的上帝之國完全不同。世俗世界中有一個政府,那政府也是上帝建立的,目的是進行控制,防止人們相互之間的撕裂。因為塵世中充滿著罪惡,必須要有一種力量來維持秩序。這種力量就是世俗統治者,他們掌管著上帝神授的權力之“劍”。真正的基督徒是生活在精神王國之中的,因此不需要世俗的政府,但為了他的鄰居,他應當支持這個世俗政府,甚至應當接受像士兵那樣的公職。如果統治者的法律和命令違背了《圣經》中的原則——神法,基督徒必須拒絕服從。但是,基督徒的精神地位使他們只能拒絕而不能反抗,因為“劍”的權柄來自神的授予,基督徒因此不能用暴力去反對統治者。在塵世中應當承認等級:低位者應該服從高位者。
1523年至1525年間,路德提出了“三種秩序”的理論。路德認為在人間有三種基本秩序是不可侵犯的,分別是政府、教會和家庭。政府必須掌握在諸侯和貴族手里,家庭必須對政府服從,教會又分為“不可見的教會”和“可見的教會”,前者存在于天國之中和信仰者的心靈之中,是絕對精神性的、不可見的,后者存在于人間,但只是一種世俗的組織,如同政府和家庭一樣,是信仰者學習《圣經》的地方,歸世俗政府管理。
路德要求每個人在世俗的秩序中找到自己的位置:“首先,你們必須成為家庭的一份子,或父親、或母親、或子女、或奴仆、或婢女。第二,你們須在城市或農村以一個公民、臣民或統治者的身份生活。第三,你們要成為教會的一個成員,或牧師、或助理、或教堂司事,或其他什么的教會仆人,假如你要了解上帝之言的話。”
路德的宗教改革運動見證了封建制度的解體和資產階級的興起。在政治方面,德意志市民階級獲得了執掌城市政府的大權在國家層面,制止了羅馬教廷對于德意志的控制和剝削,關閉了修道院,沒收了修道院的財產,廢除了教會凌駕于國家和民眾之上的特權,實現了國家主權完整。在地方邦國的層面,形成由邦國政府決定領地內的宗教信仰、邦國政府管理宗教事務的制度:從教會那里奪回的政治權力和從修道院那里沒收來的財產,現在歸于政府,對德意志政治的近代化起到了重要作用。更為重要的是,宗教改革在城市平民和廣大農民的參與下,擴展為百姓大革命,民眾用革命的方式參與政治,自下而上地推動了政治的民主化。
在社會、文化和宗教方面,宗教改革提升了德意志的綜合國力,實質性地推進了建立德意志民族國家的進程。新教教育制度的建立,婚姻的世俗化、僧侶結婚和修女還俗,宗教儀式的簡化,宗教秩序與世俗秩序的分離,以及新教對家庭道德教化的重視,都意味著一個真正的近代世俗社會在興起。在這個世俗社會里,各行各業的人們努力工作,工作被認為是在履行天職。由此可見,宗教改革是通過社會、文化、宗教制度方面的關鍵性轉變來反對封建主義的一種努力。這場運動的推動力量不僅僅來自馬丁·路德那樣的僧侶,而且還來自于廣大的下層市民和普通農民。運動的社會目標,消極地說是廢除特殊僧侶群體獨有的一切權利和特權,掃除德意志近代化的障礙,而積極地、用宗教改革的語言來說是實現社會、經濟、文化的平等,以便在“基督教兄弟之愛”的旗幟下,建立起一種團結互助的社會新秩序。
在農村,1524-1626年間爆發了偉大的德意志農民戰爭。農民戰爭的作用,不僅表現在運用革命的手段抵制封建地方貴族和諸侯對于農村的侵犯,而且還通過革命,提出了建立“人民共和國”的設想。根據農民戰爭領袖蓋斯邁爾撰寫的《蒂羅爾憲章》和匿名作者撰寫的《致全體德意志農民大會書》等文獻,可以清楚地看到1525年起義者有著廢除私有制、建立人民共和國的意圖。正如恩格斯在《德國農民戰爭》中所指出的那樣:“正如閔采爾的宗教哲學接近無神論一樣,他的政治綱領也接近于共產主義……閔采爾所了解的天國不是別的,只不過是沒有階級差別,沒有私有財產,沒有高高在上和社會成員作對的國家政權的一種社會而已。”必須看到,在宗教改革這樣的早期資產階級革命中出現這樣的共產主義綱領完全是真實的和可能的,因為“路德的和加爾文的宗教改革=資產階級革命第1號:農民戰爭是這個革命的批判的插曲”。因此,“閔采爾的綱領,與其說是當時平民要求的總匯,不如說是對當時平民中剛剛開始的無產階級因素的解放條件的天才預見”。
宗教改革無疑促進了德意志向近代社會過渡——它奠定了德意志近代社會政治的、宗教的、社會的和文化的基礎。因為德意志的特殊背景和德意志皇帝對市民階級建立德意志民族國家要求的抵制,使德意志向近代社會的過渡,無法通過資產階級與新君主結盟來完成,而是采用了市民與農民的大聯合,走出了一條自下而上推動德意志近代化的道路。這樣,宗教改革成了德意志近代社會的開端,致使得德意志遠離了中世紀的封建時代,朝著近代的政治體制、社會體制、經濟體制向前邁進。
[作者簡介]朱孝遠,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歐洲中世紀史和歐洲近代早期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