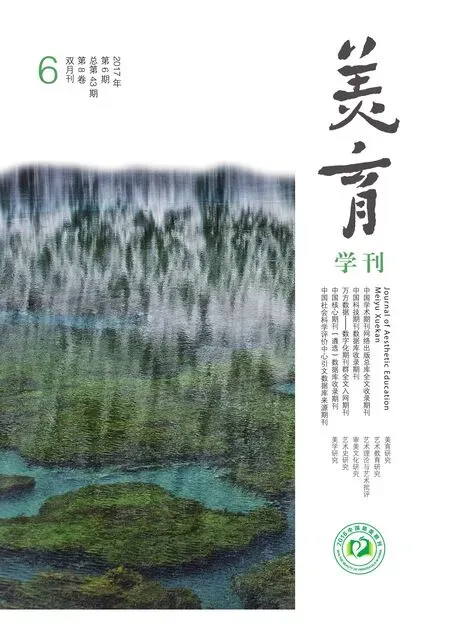審美文化的建設:網絡時代的電影批評思考
周 星
(北京師范大學 藝術與傳媒學院,北京 100875)
文藝批評的當代性思考
主持人:周星教授
主持人的話:這是一組關于當下文藝批評思考的文章。主持人約請不同藝術類型研究的師生圍繞共同主題,對當下各門類藝術批評進行學術探究。其中包括有關于藝術批評人才組織的宏觀研究,對于電影批評、音樂批評、舞蹈批評、美術批評、電視劇批評等在內的多門類藝術如何適應當下環境而進行藝術批評的思考。無疑,藝術批評是藝術構成中與藝術史、藝術理論、藝術創作等相輔相成的重要組成部分,沒有藝術批評的藝術是不完善的,沒有藝術批評警示的藝術創作也難以實現闡釋和創造的價值。藝術批評猶如一面鏡子,可以映照出許多藝術創作者自身難以察覺的東西。傳統藝術批評在互聯網時代,既遭遇藝術創作所帶來的諸多創作因素變化與傳播導致的變化,又遭遇網絡批評影響的藝術批評的對象接受與批評者風起云涌的現實。各門類藝術自身的變化也許是微妙的,但藝術批評所受到的影響卻是明顯的。因此藝術批評的當代性思考就需要兼顧多重因素而給予新的闡釋,本專題也許可以具有參考價值。
審美文化的建設:網絡時代的電影批評思考
周 星
(北京師范大學 藝術與傳媒學院,北京 100875)
電影批評是一個和電影理論、電影史相互支撐的學理性存在,批評家需要文化涵養和理論支撐的認知。在網絡時代,批評受到沖擊也得到泛眾擁戴,人人都可以做“批評家”,但電影批評適應時代卻需要堅守價值觀,需要有文化含量,從作品的針對性入手把握批評的審美追求和精神鞭策。電影批評家需要明白:適應時代而能超越時代,針對現實而能指點現實,給予電影切中藝術審美的分析,是電影批評的任務。
電影批評;網絡時代;價值觀;審美追求
近年來,電影批評已經泛化,人們關注電影市場擴大,也人人批評電影,以為批評就是隨機點評幾句,而自以為都成為批評家了。當然,隨著電影在文化中的影響力日漸擴大,電影認知的廣泛度和娛樂性能夠相互促進,而電影批評的簡單性與看低的趨向也相互擁抱,于是,電影批評的再認識也需要給予新的闡釋了。實際上,這都與互聯網以及大眾文化發展相關。當下網絡文化帶來創作指向、傳播境遇、觀眾需求以及審美趣味的諸多變化,許多方面今非昔比,于是藝術所接受的環境已經存在很大差異。理論的改變與批評的位移,使得如何看待批評成為認識不一的難題。批評有沒有效應、批評的方式是不是需要適應當下受眾、批評者的生存方式以及批評的分層等,都成為批評界熱議的對象。網絡時代電影批評顯而易見已經不同以往,單論眾多的網絡“批評者”的涌現,自發和自命名的批評者帶來的變化,似乎使得傳統批評家有些失落,而作為視覺時代文化傳播重要對象的電影,更為明顯地顯示出大眾批評者的興旺,隨之傳統批評家的失場不期而遇。新型的電影批評是否需要重新確認規則、理論依據與存在價值成為思考中無法回避的命題。無論人們如何看待、研判都不能不面對電影批評的境遇、電影批評的對象接受、電影批評的方式、批評者的分類、網絡帶來的批評多重性、電影批評的學術規則等現實問題。
我們難以回避的是網絡時代的電影批評是什么,這似乎依然是基礎問題,但顯然認識已經有所變化:以往我們認定的批評,是包容著評價和批判等含義在內的理論話語解說。電影批評自然是對于電影本身的評價分析,其主要內容是對于作品給予好壞的判定、得失的所在分析,以及什么原因造就如此的理論界說,段落鏡頭長短處等研判。但網絡時代的電影批評卻似乎不全如此,一種產生于網絡的直率批評樣式,可以全然不顧創作大走向,完全從個人喜好的口吻來炮轟、鼓吹、挑剔、揶揄某個電影。于是當下“電影批評”成為個人自由評點、大眾的喧嘩喜好噴嘴對象,而蔚然成風的互聯網時代批評時常成為隨意吐槽、任性褒貶的語言玩笑。正因如此,我們必須正對電影批評所存在的現實,必須重新梳理并且設定適應時代的批評規則。
一、電影批評是對于電影作品的有理據的分析判斷
一般而言,電影批評是有知識積累的人對于電影認知、分析的批評,因此,具備一定的電影知識和文化學養的批評才具有效力。但時過境遷,電影批評的泛眾化局面,讓人們以為批評就是個體簡單的喜好說辭,而誰都可以說三道四又讓批評的價值降低。最近網絡上對于《戰狼2》的主創吳京全家是外國籍的攻擊性言論就引起軒然大波。這已是一種基于陰暗心理的議論,試圖給予熱度正旺的電影以重創。在網絡受眾不辨真偽的情況下,往往會造就不良的后果,幸好吳京本人出來駁斥,避免謊言流傳。實際上,類似的電影評價隨處可見,批評成為相互攻擊的東西。
批評必須基于事實的基礎,這在網絡時代會遭遇不同程度的破壞。批評家更感受到嚴肅批評某種程度的失場。這一問題是基于網絡時代眾語喧嘩的肆意評說而言,當人們以為電影批評就是一種隨機性的語言張口即來,而無需去顧忌邏輯和對象整體時,似乎多樣的民間批評,卻成為絞殺批評存活的力量。巨量的所謂“評說式批評”造就了電影批評的泛化的“繁華”,不僅是民間眾說紛紜的熱鬧,學術界也不能不日漸重視網絡批評,但止不住的大眾批評的隨意性改變了批評的常態,失卻規則而隨波逐流漸成習慣。也許這就是網絡時代強勢造就的“批評”景觀,新的一代人喜歡批評的愜意短促而自由,但顯然,沒有邏輯的恣意而行,讓批評自身的價值淪為口舌之辯與“口水的戰斗”絕非好事。對于大眾而言,習慣了這一淺嘗輒止的論說,也容易加入“批評”的行列,感性直接有余,但理性和深度卻難免失卻。問題在于,網絡批評的長處是迅捷的談論和直截了當的評點,批評口吻的大膽而不顧及創作環境與整體看待的弊端顯而易見。電影作為大眾容易感受的對象,直率的認知似乎容易,好惡的表達也無需遮掩,但藝術所蘊含的意味顯然不能被納入接受的范疇,藝術探索的樣式被冷落也難以避免。總之,新的環境帶來批評認識的差異性,如何看待批評的學術性與大眾論說的合理價值,是當下批評需要思考并且確認原則的難題。
二、電影批評不是隨意的感興點評而是文化性的堅守
網絡時代大眾批評的興旺,既是一種主動性評點的結果,也是改變精英型批評的必然,但隨之的問題是批評的文化性狀改變。電影批評是一種文化性質的論說,對于電影而言,無論是當成市場產品還是商業票房獲取對象,電影本質上都是文化精神的承載對象。人們看待電影,哪怕是娛樂性十足、技術性嘆賞,其實都沒有脫開文化判斷的喜好認知,都可以從中窺視到文化潮流和時尚趣味。顯然,按照批評原本是給予創作文化點評和引導的功用而論,批評者的文化素養決定是否能承擔批評的基礎。網絡上的“拍磚”和感興式的語言,激憤而不著邊際的責難,片言只語的隨意發泄等,或多或少將批評變成了私人的感懷。遑論批評的分析引導必要性,就是批評本身可否給予人們文化氣性的熏染都做不到,批評的泛眾化造就了對于批評的誤會,也稀釋了批評的文化含量。直率不是缺點,但無遮攔的謾罵和泄憤的聚集,對于網絡文化的反向影響令人憂慮。我們強調批評的基本職能是以理服人,批評者的文化擔當是以理論述說來說服人心,缺乏基本理性和沒有理論思維的基礎,批評只能是隨性而泛濫的情感語言,理據和邏輯都難以實現。
我們的批評無論是對于具體細節的分析還是對于電影現象的認知,文化評判都是一種背后的支撐,由此構成超越簡單性的俗念論說的層次。比如,在2017年關于《閃光女孩》叩求排片的事件中,需要給予市場定律的必要性和未必合理性的解說。同時,對于創作作品是不是需要借用叩求以及叩求到底能起什么作用的判斷,是回答大眾莫衷一是議論的良方。文化分析顯然是批評認識的核心。其實,這在早一年的《百鳥朝鳳》跪求事件中已經有了端倪,而批評家需要作出辯證的分析。
《百鳥朝鳳》初始階段只有1%的市場排片,是因為按照以往市場接受的經驗而不被看好而應付上映;而后來的一個反撥回潮,還是因為掀起了市場呼應觀影的期望而開始改變排片習慣,居然就獲得意外的逆襲。但顯然,所有的經驗都有人為的印記,排片的保守是過去經驗的人為結果,后來的一跪翻盤依然是因為人為因素的改變……其實,人們受到呼吁和一次跪請召喚,開始進入影院,多半既有懷念吳天明和他的功績,也不免帶著對于藝術電影的惋惜之情,如此這般情懷,《百鳥朝鳳》的情感因素,合理地抬高了影片的價值。……但單就影片而言,是一個頑強的堅守自己的時代,和抗拒被喧囂漠視的精神,卻難免因為堅持的固著性,在藝術表現上顯得比較老套,這一問題的提出并非貶低創作,恰恰是需要提出有沒有一種自我堅守的罔顧時代的頑強性。我們自然可以無限期望藝術可以保持一貫的態勢,但漲落是一種自然現象。對于吳天明而言,創作也有高下不等的區別。只有站在更為客觀的立場上,我們的電影長遠發展才能有堅實的動力。[1]
無論時代如何變化,無論網絡批評如何搶奪受眾,我們依然要堅守客觀辯證的文化分析。事實上,在網絡時代習氣熏染中,一些傳統批評家也學會了嘩眾取寵,用絕對性的語言來取得適應時代的批評存在,其實更降低了批評家本來應該具有的獨特性存在。比如最近所謂中戲老師批評《戰狼2》被總結為:
No.1《戰狼2》靠血腥來制造燃點,反政府武裝屠殺平民,沒有政治信仰;No.2太血腥不適合小朋友看;No.3故事毫無邏輯;No.4劇中張翰的角色就是一個戰爭販子;No.5導演簡直是心理變態!剛總結完就遭到網友的怒懟![2]
電影自身并非一目了然地直白呈現,影像后面的情感精神表現,需要揭開和闡釋,批評正是幫助觀眾理解得失,給予文化上的點撥。而文化應當是實事求是積極性的建設意見!從一定意義上說,傳統電影批評自身是否接地氣和泛眾的電影論說是否有文化含量,是左右電影批評改變的雙向因素。
三、電影批評的價值觀需要強化
在網絡時代背景下,評價對象的認知差異性加大也許屬于正常,眾說紛紜之時,自由無拘的說辭也放任四散。但顯然,電影批評是一種價值觀支配的呈現,判斷電影的得失也依據于批評者自身的價值觀高下。無論是個人好惡還是針對創作表現的點評,都透露自身的價值取向。作為文化產品的電影藝術,無論如何娛樂或者堅守藝術風格,都包含著某種不由自主的價值選擇。而觀眾在審看欣賞中,也必然用自身的價值判斷標準來衡量好壞。問題在于,批評的意義在于指出創作的優劣得失,為觀眾展開可見或隱藏的內在因素,分析點評創作正誤高下,于是電影批評就不僅是簡單的觀后感而是指點者的意見表達。
我們時常在網絡中看到吐槽的堆積和攻擊性的言論,依憑自身的情感喜好不遺余力地貶低對方抬高自己的愛物,而不允許他人的不同意見。這除了不知道批評就是研討而不是專制外,還需要明了公正的分析和傾聽才是批評建立的基礎,并不只是針對創作而要兼顧他人的意見,自身的價值觀是執守的核心。沒有良好的價值觀,一味任性地泄憤和褒貶,不是批評所需要的。
在網絡時代,不僅大眾抱持的觀念不一,批評家也各有批評觀念的差異。我們需要警覺的是,將放棄國家大局和核心價值觀作為顯示別具一格的存在,對主流形態的對象不分青紅皂白地給予批評,既能迎合部分網絡輿論的支持,又顯示所謂獨立反叛的標簽,其實也只是投合某種潮流的不良心態而已。作為批評家不能強求顯示整齊劃一的價值觀,但必須崇尚光明給予人間美好的期望。
所謂互聯網時代人人都是批評家的時候,真正有見識的批評家更為重要,有高遠理想和主流價值認知的批評家更為重要。英國人彼得·伯克所著的《知識社會史》中對于知識的認識,同樣可以移用到對于批評家的要求:“伯克認為,知識是經過處理或系統化后的信息。”*轉引自李果《知識與求真精神》,載《財經》,2017年第17期。實際上,批評家需要具備基本的理論知識,由此形成自己判斷事務的標準,因此,無論是網絡批評者還是傳統批評家,混同流俗博取喝彩顯然不是正道,尊重創作但具有高于創作的世界觀和認識論卻是需要具備的。
四、電影批評的審美性應當放在重要位置
電影批評的審美性應當放在重要位置,這似乎還是老生常態,卻是尤其需要凸顯的要求。當電影成為市場產品的認知日漸強化時,對于電影仍是藝術創作的對象這一認識日漸式微,市場收益的票房指標幾乎被認為是成功與否的簡單標志,這固然與電影需要市場檢驗和認可息息相關,卻未必是對于電影評判的全部要求。可惜,批評家們在一段時間內被商業性的市場指標左右,言必稱票房,漸漸導致電影只有票房的認知標準。產業指標的重要性決定了電影生存,但其實電影生存和票房根本離不開內容產品的價值意義。
在談論電影批評究竟應當如何把握時,我們至少可以從當下的誤區來透視:除了上述論及看待電影只有市場指標,因而一切得失只注重票房的偏見外,對于電影只看到所謂工業成功和類型到位的言論也是另外一種偏見。近日對于《戰狼2》創造華語電影第一高票房究竟該歸咎什么原因時,一些批評家大呼是電影工業的成功,這顯然就是一種只看到外在因素的延續。對于做足了電影工業就能成功的認知,既是簡單化地崇拜成熟的好萊塢電影工業,也沒有看到《長城》等創作更為地道的工業化卻未必成功,更為重要的是依然漠視了電影在藝術創作上的重要性。毫無疑問,《戰狼2》更需要從創作者的精神追求所導致的專業執念和審美追求的層面探討來進行文化品質對于大眾內心期盼的呼應分析。
近年來,批評的失場和創作的不甚如意一樣,文化和審美上的堅守低于功利性的市場盤算與主觀揣測,追風逐浪地想象觀眾需要而不是創造自己感知到的人生需要,一窩蜂地尋求他人成功的IP而不是探索原創的精神情感創作,將所謂有市場的“小鮮肉”捧上天而不是去創造適合角色的人性角色,依照所謂的大數據發布而試圖投其所好地臆斷題材拍攝而不是遵循大千世界的人生感悟等。簡言之,創作不是出于自身熱情的需要,且沒有得到批評的審美性點撥。
對于電影批評的要求,無疑最重要的是注重藝術批評。作為藝術生產,電影在精神情感的表現上是體現創作者文化思想的追求,而電影作為現代藝術,其藝術審美的獨特性正是觀眾接受的所在。因此,藝術審美的評判應當成為電影批評的主要內容。電影的審美判斷,包括電影創作文化性觀念的認知,藝術表現方式的體現,電影語言的掌握,人物性格的塑造,敘事邏輯性的表現,以及情感表現的深淺等要素。一部影片的諸多因素造就了電影的審美層次的高低優劣,電影批評如果不去觸及而只在市場和票房數據上彷徨,永遠不能獲得批評的效應,更不會被創作者所接受。
五、電影批評的針對性和細致度是實現價值的重要基礎
電影批評不是理論的轉移,而是建立在理論準備基礎上的實踐盤點。電影評判需要有高屋建瓴的認知,對于具體的電影創作能夠從社會文化層面看清其創作觀念和精神實質,從內在里把握創作基于何種原因需要表達,在整個電影歷史中做到了何等程度等。所以好的電影批評自然要有宏闊的歷史觀和審美把握,闡述具體作品與時代人心的關系。比如,《建軍大業》上映后,發生了包括若干位早期軍事戰將后代對于電影的批評,這種批評是否定所謂的“小鮮肉”扮演他們的父輩們的角色,抗議機構容忍這一現象發生等。
作為批評者自有其情感的理由,但顯然從抗議角色扮演選擇的藝術角度看,錙銖必較未必合理,而且反對演員的理由和依據亦有不足,關鍵是這種親屬的反對其實源遠流長,我們甚至可以從1949年以前石揮在《假鳳虛凰》中的扮演角色是理發師,而影片上映后曾經釀出上海理發師集體抗議對于所謂的理發師污蔑的事端,來比照此次的事件是否存在對于影片的苛求分析等。這些都是一種宏觀的理論判斷的所然,前述的批評需要價值觀和審美意識等要求,正是強調宏觀視野的意義。電影批評者需要把握主流批評的堅守信念和針對性的靈活度,需要具有學術批評的深入淺出與邏輯性要素相結合,尤其是不能忽略網絡批評的鮮活性和文化性作品細讀的批評守則,以及在尊重原作細致分析基礎上的批評認知。
在批評問題上,網絡大眾所需要的顯然是直接的針對性,盡管我們會挑剔眾口難調的粗淺駁雜的議論,但其中透漏出的是直接觀影對象的喜怒哀樂,只及一點不及其余固然不合理,指向具體細節、人物和橋段卻正是大眾需要的批評。我們顯然不能只是夸夸其談大原則大走向,而忘卻了電影是一個個鏡頭構成的影像,如果要實現電影批評對于青年受眾的參考接受度,有針對性而不是虛浮的分析絕不可少。比如,對于歷史影片,你要分析為什么《城南舊事》中小英子的眼神那樣天真清純,而她與張豐毅扮演的偷兒在草地上的對視和對話中包含了何等的人間關切,由此又怎樣地透露出作者對于底層百姓不得已偷竊背后人性的善良心態。對于爭議頗多的“小鮮肉”在《建軍大業》中具體人物細節表現的分析,遠比簡單地概念揣度青年演員是不是合適飾演當年葉挺、林彪、周恩來、粟裕等來得有說服力。實際上針對細節的網絡分析可以借鑒,比如一則文字:“《建軍大業》最后的三河壩戰役更是賺盡了在場所有人的眼淚。蔡晴川營長主動領命斷后,朱老總說,父子二人上陣殺敵的,父親留下;兄弟二人同赴沙場的,兄長留下。有戰士喊著我要留下,他的兄長拉住他大吼‘我留下!’中國人自古講一個忠義孝悌,在這種時刻,最能體現人性本來面目的時候,他們用自身行動證明給我們看到了,即使在這樣的時候,中國革命軍人舍小家為大家,舍生取義的精神,是永遠不會變的。”上述具體性批評對于認識影像的意義在于哪怕有不同意見,也觸及了創作實際而更有說服力。
電影批評是一個與電影理論、電影史相互支撐的學理性存在,在網絡時代,人人都可以做“批評家”,但電影批評家需要明白:適應時代而能超越時代,針對現實而能指點現實,給予電影切中藝術審美的分析,是電影批評的任務。
[1] 周星.媒介影響造就的藝術電影特異現象——《百鳥朝鳳》思辨[J].藝術百家,2017(1):45-50.
[2] 《今日頭條》網.中戲老師怒斥《戰狼2》五大罪狀:吳京簡直是心理變態![EB/OL].[2017-08-11]. http://mb.yidianzixun.com/article/0H2kdy1e?ref=browser_news&s=mb.
(責任編輯:劉 晨)
ConstructionofanAestheticCulture:ReflectionsonFilmCriticismintheInternetEra
ZHOU Xing
(College of Arts and Media,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Film criticism is an academic entity which supports and is supported by film theory and film history and it is imperative for critics in this field to have cultural refinement and theoretical support. In the Internet era, criticism has been adversely affected as well as widely applauded as if everyone were a "critic", but while adapting to the needs of the age, film criticism must adhere to its values, retain a high cultural content and strive for aesthetic pursuit and spiritual encouragement. Movie critics need to understand that it is the task of film criticism to transcend the age while adapting to it, guide reality while adhering to it and criticize films aesthetically.
film criticism; network era; values; aesthetic pursuit
2017-08-19
周星(1958—),男,福建福州人,北京師范大學藝術與傳媒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電影評論學會副會長,中國高教學會美育研究會常務副會長,主要從事藝術學理論與影視文化傳播等研究。
J905
A
2095-0012(2017)06-007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