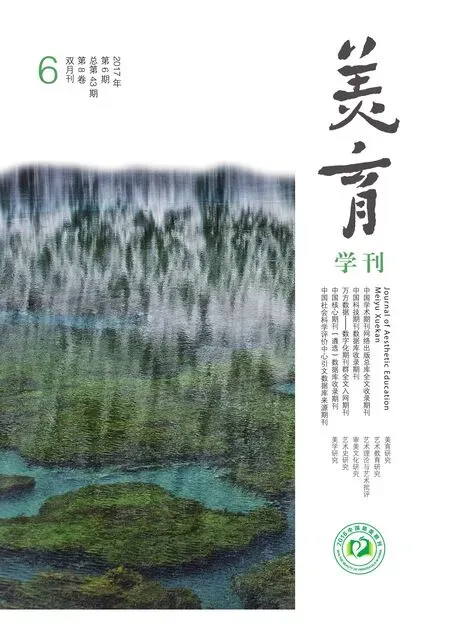文藝批評隊伍建設、生存環境及其他
吳 戈
(云南藝術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文藝批評隊伍建設、生存環境及其他
吳 戈
(云南藝術學院,云南 昆明 650500)
文藝批評必須重視批評隊伍建設,娛樂性文化環境、官本位話語體制、市場化標準口徑和維持型創作現狀所導致的批評隊伍建設遲緩必須有所改變。營造良好的文化環境,樹立正確的價值觀,培育具有文化思想涵養的批評家,將改變文藝批評的局面。
文藝批評;隊伍建設;價值觀;環境建設
一、文藝評論隊伍建設是一項新任務
很長時間里,中國文藝界有文藝批評家,但是沒有文藝批評隊伍。
一個時期以來,人們對文學藝術界批評隊伍的失語、缺位、違心、無效等充滿了負面評價甚至是社會問責,占據了輿論主流。似乎是文藝批評隊伍失職造成了這種現象,但是,這種評價在筆者看來是失之公允的。我們可以環視周邊、顧盼左右,造成我們的文藝批評這樣疲軟無力不到位狀況的,難道僅僅是文藝批評自身的原因嗎?很大程度上,批評界失語、缺位、違心、無效的狀況并非真正的文藝批評者所希望的,最重要的原因并不是來自批評家或者似有似無的文藝批評界,而是我們的娛樂性文化環境、官本位話語體制、市場化標準口徑和維持型創作現狀所導致的。
認真說來,指責文藝批評隊伍渙散、缺位、失職,其實也沒有道理。因為我們的文藝界從來就沒有一支常備的批評隊伍在文藝隊伍中。在筆者印象當中,文藝批評隊伍是近年才匆忙組建起來的。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中國文聯)的各協會中,中國文藝評論家協會是2014年5月30日才成立起來的年輕的協會,成為中國文聯機構里的第12個協會。這應該可以說明,在文藝界,原來并不存在組織形式上的文藝評論“隊伍”。原有的文藝評論,其實就是一些理論研究者面對文藝現象偶發性地發言發聲給人留下“評論界”的印象。“文革”前的中國,文藝評論家屈指可數,新時期的中國,小說、詩歌、報告文學、戲劇、電影的研究性和學術性評論趁著文學藝術的復蘇而潮頭涌動,形成一個蓬勃發展的“新時期文學藝術批評”大潮。這個時期,“文藝評論界”隊伍的形成幾乎可以說是呼之欲出了,因為有一個群體存在。北京、上海集中了最多的文藝評論家,一些省份,也或多或少有在全國文藝批評話語里有份額、有席位的評論家。他們分散在高校、社科院文學研究所、文化廳藝術研究所之類的單位。他們彼此聲氣相通,相互呼應,雖然并無組織聯系,最多是某種松散的“文學研究會”方式有一些活動,但是那種精神氣象是一體的。后來,這種存在感又淡化了。直到2014年5月30日才算是有了全國性人民團體的文藝評論家組織——中國文聯文藝評論家協會,全國各省市文聯也或前或后地成立了相關組織。
成立之初,就文藝評論家隊伍的建設及其所關涉到的因素做一些探討和觀察,也許是必要的。
二、文藝評論隊伍建設要有正確的歷史觀點和價值導向
如果早在20世紀80年代提出建設文藝評論家隊伍,不但會從老中青文藝學者、美學學者、文學學者當中迅速集結起一個強大的陣容,而且,當時的文學熱、報告文學熱、文藝思潮熱、美學熱、比較文學熱、文藝方法熱、文化熱——文壇上少長咸集,群賢畢至;思想界洋洋乎大觀,滔滔兮奔流。沉重的使命,神圣的憂思,灼熱的追問,悲壯的絕叫,激越的吶喊,簇擁著、滌蕩著、推動著那個時代的文壇。
但是,后來變了。娛樂型生活到來,很快顛覆了文壇盛世。不知從什么時候開始,觀眾習慣于所謂的后現代、解構主義對既成的文化價值的消解,對熟識的歷史敘述的顛覆。輕薄的娛樂魔棒點化戲說著社會生活環境中人們熟悉的一切,輕歌曼舞、流連戲蝶催眠了民眾,漸漸地,熟悉的陌生了,虛幻的置換了現實。娛樂化文化環境取代了思想性文化社會,其特征就是從戲說歷史走向褻瀆歷史和歷史虛無主義,進而掏空了民族價值的歷史根基和文化土壤。遺憾的是,對于我們的整個民族來說,這體現為時代性。
娛樂性文化環境的潛在危險在于拒絕深刻、嘲笑崇高、貶損優雅、矮化英雄。實際上,從這種泛娛樂時尚的洪流中,我們可以明白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重寫文學史”就開始了對價值的重新評判,言說的是“顛倒被顛倒了的歷史”,其實矯枉過正,脫離歷史背景抽象地談論一些人和事,結果是搞亂了價值標準和歷史判斷。被現任中國文藝批評協會主席仲呈祥在從前許多場合批評過的當下文壇狀況:“趙、小、李”(趙本山、小沈陽、李宇春)取代了原來文化坐標中的“魯、郭、茅”“巴、老、曹”,實際上,這種令人焦慮的情形其實正是從20世紀某一階段戲說歷史、嘲弄崇高的那個時候點滴漸變開始的。張愛玲、廢名、沈從文、周作人等,成為被找回來的瑰寶;那些在現代人性啟蒙、國家意識建立和民族意志張揚中起到了關鍵作用的文化先驅和思想先哲,卻被矮化、貶損甚至被佛頭著糞式地形象顛覆。從《走下神壇的毛澤東》開始的一系列“走下”書寫,《紅墻內外》的所謂“真相”“解密”的顛覆性描繪,一定程度上是民族文化價值受損和民族歷史標尺下滑的一個拐點標志。寫“有缺點”的英雄人物漸漸變成了痞子化、流氓化、妖魔化的所謂“還原歷史真相、凸顯肉身本色”的“重寫”和“戲說”,一部偉大的民族歷史、一些偉大的國家英雄、一群又一群的革命先驅就在一次次戲說、一次次矮化中被漸次顛覆掉了,一個有燦爛文明發展史的民族、一個經歷了浴火重生的磨難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國家,似乎成為毫無道理的存在、沒有邏輯的僥幸。在這樣的認識基礎上,中國就是一個沒有任何優秀傳統也沒有任何遺產力量可以發展的國家。
我們失掉了分寸尺度和價值標準。
要建設文藝批評隊伍,我們首先就要清理這樣的文化亂象,要有“待從頭,收拾舊山河”的使命和擔當,去對文化藝術重整秩序,重建價值體系,這就要求我們的文藝批評隊伍成為一個有正確歷史觀和正確價值觀的群體,關注文藝創作實踐卻不僅僅去解釋和欣賞實踐,要在分析、總結實踐當中去指導實踐、引導實踐。文藝批評應該諳熟文藝創作的感性邏輯,應該善于欣賞文藝創作的感性智慧,可以尊重文藝創作的感性經驗,卻應該比文藝創作更理性、更宏觀、更高瞻遠矚,更具民族文化建設的整體觀和全局感。
建立一支有正確歷史觀和價值感的文藝批評隊伍,是我們的當務之急。
三、營造有利于文藝評論健康發展的環境
文藝評論健康發展的環境,是一個需要精心培養營造的環境。
首先應該鼓勵百家爭鳴,創造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局面,這是“健康發展環境”的前提。如何能夠百家爭鳴、百花齊放?就是應該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作為價值基礎、“為社會主義服務、為人民服務”作為文藝發展的方針的前提下,鼓勵流派紛呈、百舸爭流的“百花齊放”的局面,文藝批評才會言之有物,各抒己見,百家爭鳴。“雙百”方針互為條件、互為表里、互為因果,相得益彰。喜聽諛辭,怨懟諍言,是一種不健康的社會心理環境,還是要提倡聞過則喜的健康心態和文化環境。
其次是應該設定愛國、健康、向上、美感的基本價值框架后鼓勵批評家從不同方法出發建立不同的批評體系,面對百花齊放的文藝現象才能夠避免一把尺子量盡天下風流的現象。中國近現代文藝發展的歷史經驗值得總結:一邊倒的“易卜生主義”標準,只選擇一點的“寫實主義”管窺;“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是階級斗爭工具”的要求;“市場功利主義”的戥子……反思起來,一種流派、一家觀點、一種價值的“一把尺子量盡天下”的做法不但讓文藝評論眼光狹窄、尋章摘句、僵化陳腐,成為“灰色的”表述,不招人看,而且也剪裁、阻礙了文學藝術創新中最有價值、最活潑生動的內容。不要從固有“尺子”出發而應鼓勵批評家從藝術創造的新樣態、新美感、新內容出發去開展文藝評論。
再次是要把文藝批評當專業。政治家、思想家、道德家、教育家、美學家、文藝家、科學家、哲學家在社會生活中為人類的存在、建設、發展各顯其能,藝術批評是一種專業工作,與我們的大眾文化時代高度自由便利的傳媒背景下大家都可以談談感受、說說看法、講講觀后感之類的“門外文談”“門外藝談”的“民眾評論”要區別開來。不能區別這一點,就不能把藝術創造和藝術批評的能在動力調動起來。因為,不能充分認識到文藝批評是專業工作,就會使之變成一般性茶話會、菜市場的“眾語喧嘩”甚至是茶館談資的信口開河、小編剪裁的花邊傳聞。那樣,文藝批評家就得不到尊重,文藝批評就沒有社會地位和價值空間。
眾語喧嘩不一定是繁榮,大眾口味不能取代專家批評。眾口鑠金的網絡時代,那種盲從跟風的集體無意識,那種“吃瓜”群眾的口水成河與自由隨意的大眾文化背景下,可能更需要專業人士的引領指導。關鍵是,專業人士應該真正訓練有素,是真知灼見的文藝批評家。
四、用尊重激發評論家開展文藝批評的積極性
如果承認文藝批評家是一些專業人士,如果明白文藝批評家不僅僅是文藝創造活動、文藝欣賞活動的評介者和引導者,如果了解文藝批評家對文藝創造心理、激情、美感的深入研究、深刻體察和深層分析,就應該用尊重科學家一樣的心態來尊重他們。
應該冷靜地區別一般人包括官員們談談感受、心得、看法的業余隨意與專業批評人員文藝批評的專業專注之間的不同。尤其不要把專業人員變成文化官員個人隨口意見的注疏者,不要把專業人員變為流行術語、流行口號、流行觀點的學舌鸚鵡。一方面專業批評家應該意識到批評主體性的不可喪失,另一方面也應該強調要營造那種讓平庸的話語無處容身的社會風氣和文化氛圍,而不是相反。
首先是專門領域的文化官員要慎言慎行,要避免我們不難見到的那種情形經常性地發生:官員用自己的業余愛好、一知半解、娛樂趣味去左右藝術生產和指導創作活動。文化官員因為有權力,掌握著資金也就掌握了文藝生活的話語權,這不但給藝術生產帶來不良影響,實際上也否決了文藝批評的專業性。久而久之給人們留下的印象就是:文藝批評不重要,分管文化和掌控資金的領導意見和長官意志才是最具要害的“批評”。在這樣的現實環境中,要想有一個正常的文藝批評風氣,也是天方夜譚。
其次是文藝批評家的心態、行為很重要。不尊重文藝批評的人不把文藝批評當作專業尊重、不看作學術活動去敬重,文藝批評者不能夠逆來順受,太不把自己的批評工作當專業。雖然很多時候出發點是個人自身,但是,很大程度上許多問題也是社會風氣、文化特征在文藝家個體身上的折射。問題在于,社會風氣是客觀的一面,文藝批評家主觀的一面必須有鮮明的定位:文藝批評家應該堅持獨立見解而不是看領導臉色行事,不是注疏分管領導意見的文職人員。文藝生產的內在規律、藝術創造與審美欣賞特征、藝術尺度公約與思想價值原則等,不應屈從于領導意圖和長官意志。這個問題沒有解決就當不了文藝批評家,屈從于長官意志的筆墨,也會諂媚于人情。因為,評論者的立足點并不在文藝。在筆者看來,沒有風骨的批評,首先是從沒有脊梁的人格開始的。
五、通過學習積累有效提高文藝批評的總體水平
首先要強調“史、論知識的系統”學習。一個夠格的文藝批評家,必須有正確穩固的歷史觀、哲學觀、價值體系、民族文化的知識構架,要有深厚的一般歷史、專門歷史和文藝理論包括藝術史、文學史、文學理論、藝術理論的系統學習,才能夠在面對社會生活和文藝作品的時候,敏感地把握“意識到歷史內容和巨大的思想深度”,至少敏銳地看得到創作人員的思想高度、生活厚度、歷史深度、思想銳度,因此正確地闡發、傳導那些感人的現象描寫背后深厚的情感內容和思想礦藏給讀者大眾。
其次還得知識更新。一個活躍的文藝批評家,必須有豐富的歷史文化知識,有對新事物的敏感、新生活的熱情、知識疆域的擴大、新知識的補充。他必須學習文藝批評的新思潮、新方法、新派別,要知道辨別這些新思潮、方法、派別的“新”的價值。哪些“新”能夠看到新景觀,產生新內容,猶如新器具的功用產生的功效一般,那就應該迅速掌握;哪些不過是雕蟲小技,障眼魔法,那也得火眼金睛,避免花拳繡腿的出乖露丑。人類的思想發展史,是角度不斷變化、方法不斷更新、景觀不斷豐富、認識不斷加深的歷史。文藝批評也不例外,有方法手段的更新變化帶來的發展,沒有這樣的學習以適應變化發展,文藝批評家就會僵化陳腐,在豐富多彩、日新月異的文藝發展面前力不從心、褒貶無詞、進退無據,最后陷入“失語”。
最后也是強調學習。盡可能學習藝術門類學科里的各種藝術種類的知識,學習藝術種類中不同藝術流派的知識,學習藝術史、藝術批評、藝術教育、藝術鑒賞的源遠流長的知識,學習當下不斷發生的藝術創造的方法、手段、特征、優劣的知識,所有這些知識要轉化為個人的知識體系、價值框架和美感經驗。這樣,當他面對一個鮮活的藝術想象或者一件具體的藝術品的時候,所有積累就聚集、就發生作用、就自動處理文藝信息,整合、爬梳、剝離、剔析、聚焦……最后得出自己的判斷結論與總結分析,這恰恰是沒有長期藝術準備和精細美感經驗積累的人所不能做到的。美的敏感,拖著美感經驗的長長的歷史,讓批評家的評價有理有據,好的批評家帶領讀者或者觀眾進入一件具體作品的時候,品咂的實際上是文學史、藝術史前進到那一刻時候的高光點與聚焦處。
美感的敏銳、思想的洞見、歷史的意識、民族的精神、文化的價值等,是批評家在面對作品時內心產生出來的長期積累、知識整合的集合效應,這是一種能力。沒有這樣的能力,就很難勝任批評家的工作,就只好根據個人喜好談談感想、隨意說說感受,如此而已。
好的文藝批評家,對文學藝術發展的歷史脈絡、對簇擁推動文藝創作的文化思潮、對具體作品所負載的時代印記和所收納的精神氣象、對族群文化的美感母題和創新趨向,常常有別具慧眼的感悟力,他們應該是時代文化的總結者、文學藝術的美感發掘者和民眾美學趣味的引導者。
六、加強文藝評論人才的培養和隊伍建設
加強文藝評論隊伍應該是一個長期計劃和綜合工程。在我們的文化體系與教育現狀當中,可以充分利用好現有條件。
一是長期計劃。文藝人才隊伍的培養,有大學文學院、藝術學院培養的理論批評人才。要加強大學、藝術院校的相關課程建設和專業建設,以史、論為主干的基礎課程和以流派、文體、風格為核心的實訓課程要精心設計好,為“訓練有素”的人才培養開設可靠、管用、有效的課程。通過四年本科甚至碩士、博士研究生階段的教育,培養一批又一批在宣傳部門、文化部門、高等院校、博物館、文化館從事相關工作卻又能夠擔負起文藝批評的社會責任的基礎性人才。
二是開展集中培訓的特殊項目。20世紀五六十年代北京大學的“全國文藝理論進修班”、中國人民大學等四個單位聯合舉辦的“文藝理論進修班”做法很好,時間不短,多則兩年,少則一年,有意識地將那些有潛質的青年才俊招聚在一起,系統學習,強化訓練。結果,參加者后來大多成為全國各地的文藝理論的研究大家與批評權威。
三是不定期舉辦短訓的文藝批評骨干人才強化班。宣傳部門、文聯系統平時聯絡的文藝骨干中長于理論思維與批評文字的人才,應該定期不定期地集中,有針對性地學習培訓,讓他們在文學藝術發展中成為活躍的力量。文學批評人才的強化訓練,不僅僅是方法訓練,而且是能力提高,這種提高以強調藝術感受力、文藝實踐經驗的積累為前提,要特別避免缺少實踐經驗和美感積累的空頭評論家面對鮮活的文藝實踐褒貶無辭、進退無據或者信口雌黃、胡說八道。現實生活中這種把鮮活的文藝現象分析得枯燥無味、面如死灰的理論評論,實在是隨處可見。
四是組織專題學習、專題筆會的方式,在研究、實踐中培養人才。選擇重大專題、基礎課題、具體任務,一個一個地開發研討,一批一批地組織規劃文章,開展健康的文藝批評活動,也能有效地訓練人才。這樣既有利于集中優勢兵力體現在實踐中學習中相互影響、彼此砥礪的“群體效應”,又有利于引導年輕批評家關注一些重點問題、熱點問題、基礎問題,在學習鉆研中夯實理論素養與社會觀察能力的基礎。
七、走出文藝批評陳詞濫調的怪圈
當代中國文藝評論的一個黃金時代,似乎是20世紀80年代的“美學熱”推動下出現的。當時的文藝理論工作者老當益壯者、鼎盛春秋者、后生可畏者形成了三代人疊加攀登與梯次沖鋒的景觀。
這是頗為熱鬧了一陣子的景觀。
但是,時過境遷,消失了。
認真檢討起來,那種熱鬧一方面開拓了中國文藝理論評論者的視野,但是又使得人們有些兼收并蓄的浮躁,中國學術界的二度西潮(第一度是近現代中國從洋務運動開始到五四新文化運動過程中波瀾壯闊地展開的,第二度自然是中國新時期的解放思想、改革開放)最有代表性的年份就是1985年的所謂文藝理論研究的“方法年”,之前的比較研究、新批評思潮、人學理論、接受美學理論、闡釋學理論、符號學理論、結構理論、系統論、控制論、信息論理論、熵理論、協同論、突變理論、神話學理論、儀式理論、文化學理論、民族學理論、城市空間理論……走馬燈般地卷過中國文壇,用別人的尺子量自己的地,用別人的剪刀裁自己的布——一方面顯得視野開闊、思維活躍,但是另一方面漸漸地也出現了主體自我迷失的負面影響。一是沒有自己的話語體系,跟隨著西方文藝理論的視點轉來轉去丟失了自己,就是“話語”轉述者;二是生吞活剝、生搬硬套、名詞爆炸,表面研究角度很新,實際上不解決研究對象的實際問題,是為食洋不化。無非是用新思潮、新方法、新概念佶屈聱牙地將眼前的現象重新說一遍,所謂研究和批評就變成了新方法、舊內容、老問題的重新妝點,形新而實舊,這些所謂新思潮弄潮者,并不解決實際問題;三是引經據典這個思潮那個學派滿篇注釋、斷章取義、望文生義地“六經注我”敷衍成篇,端著所謂學院派、大理論家的架子,下那種把簡單的問題復雜化、把明朗的事情晦澀化的功夫,文藝批評就花拳繡腿、面目可憎了;四是脫離文藝現象實際、撇開文藝作品本身,借題發揮,賣弄概念,自說自話,讓人如墜煙海,一頭霧水。結果是文藝實踐界對文藝批評界的集體唾棄,這種現象還不能說與文藝批評者的離開文藝現象、文藝創作作空虛玄想卻又指手畫腳的行為沒有關系。
沒有自己話語體系的理論批評真是讓人欲說還休。我們的賣力耕耘,收成卻不能高估。
在這種狀況下,民眾文藝批評的興起,有一定的革命性和合理性。說人話,講實話,強調有針對性的鮮活的話,形成了與食洋不化的陳詞濫調迥然有異的個性色彩與真切內容。我們應該就此清醒,引經據典的掉書袋癖好應該革除,裝腔作勢的洋八股癡迷必須喚醒,還文藝批評以自然清新、親切平易的狀貌。
八、迎接新形勢下的新批評生態的到來
我們常常聽到一種說法,就是萊辛雄踞劇壇評論的精彩與俄蘇時期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簡稱別車杜)的權威,才是文藝批評的黃金時代。一方面感嘆時代不再,一方面滿臉迷醉的神往。筆者想說,那種時代、那種權威一去不復返了,應該沉下心、睜開眼仔細想一想、認真看一看,全媒體時代的到來已經將貴族式的話語壟斷和官方式的話語權威送上了末路。
應該看到媒體技術革命帶來的信息發表和資訊傳播便利,由此帶來的社會生活方式的革命,也決定了這種社會生活中的文藝批評的革命,民眾批評時代到來了,這是不依個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網絡批評、手機自媒體信息平臺批評、個人信息平臺、公眾信息平臺、朋友圈、轉載復制文化,等等,為民眾批評提供了極其方便的時間、空間、渠道,簡易的發表方式、迅捷的傳播渠道、可復制的增長空間,以及可累積、可變化、可延伸的量變過程……肯定地,全媒體時代的民眾批評要與傳統的紙質報紙雜志上的文藝批評分庭抗禮,而且,其影響力越來越勢不可擋,其覆蓋面越來與寬闊無邊。在建設我們的文藝批評隊伍的時候,必須讓成長中的文藝批評者了解、面對、積極迎接這種民眾批評時代的到來,加入其中去大顯身手。
(責任編輯:劉 晨)
TheConstructionofanArmyofLiteraryCritics,TheirExistentialEnvironmentandOtherThings
WU Ge
(Yunnan Arts University, Kunming 650500, China)
Literary criticism must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rmy of critics and its retardation caused by a cultural atmosphere characterized by entertainment,an official standard discourse system, market standardization and production orientated toward the maintenance of status quo must be addressed. It will change the situation of literary criticism to create a good cultural environment, set up the right values and train critics with intellectual and cultural refinement.
literary criticism; team building; values; environmental construction
2017-08-19
吳戈(1958—),男,云南楚雄人,云南藝術學院教授,主要從事戲劇文化學研究。
I03
A
2095-0012(2017)06-0083-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