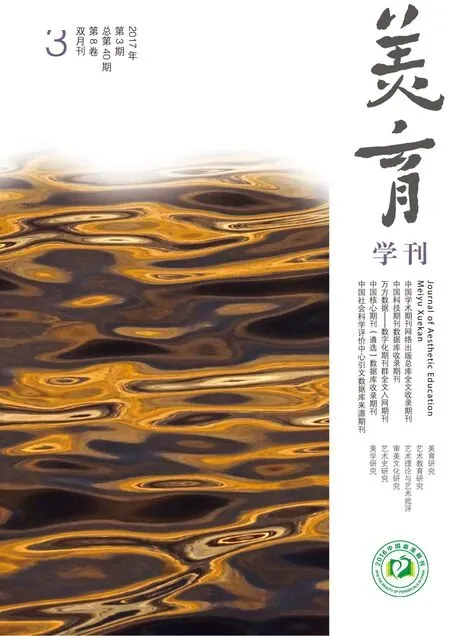“美感”一詞及其中國現代美育發生
賴勤芳
(浙江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
“美感”一詞及其中國現代美育發生
賴勤芳
(浙江師范大學 人文學院,浙江 金華 321004)
20世紀初漢語語境中的“美感”一詞,與“美學”一樣,都是外來詞。“美感”一詞初顯為“中國”的美學術語,大致體現為從納入1903年《新爾雅》到1915年《述美學》一文的闡釋這一過程。作為譯詞,“美感”在王國維、蔡元培前期的文本中有所浮現,但并不明顯和穩定,這是美學在初入中國過程中必然出現的現象。在梁啟超前期的文本中,雖然幾無出現“美學”“美感”等詞,但是以功利性作用為主導的美感觀念得到突出表征。“美感”一詞能夠在后來得以普及,很大程度得益于美育之提倡。把“美育”釋為“美感教育”,這是對“美感”的中國美學身份的一次重要確認。中國現代美學起源三大家的漢語體驗,是他們切近中國現代美學尤其是美育發生于本土實際問題解決的直接方式。
“美感”;美感觀念;“美感教育”;中國現代美育發生;漢語體驗
美感問題在美學中具有根本性,“牽涉到美學領域里所有的基本問題”[1]。中西美學圍繞這一問題而形成的見解不勝枚舉,因此形成的爭議也是不可勝計,這與“美感”一詞本身有重要關系。“如同美一樣,‘美感’這個詞也是詞意含混而多義,包含著好些近似卻并不相同的多層含義。”[2]漢語“美感”一詞具有間性的詞性特點,在流行用法里出現雜亂狀況,這是必然的。廓清“美感”一詞,避免不必要的爭議,杜絕理解簡單化、泛化,較好的方式就是從漢語語源上進行考察,追溯歷史,在美學上進行觀照。眾所周知,近代以來因西學東漸而產生了一批新名詞,它們進入日常生活,亦進入思想文化領域,其中許多發展成為包括美學在內的中國現代學術基本用語。王國維、蔡元培、梁啟超是中國現代美學起源三大家,他們無不是西學東漸的介入者。借助他們的相關文本,可以探得“美感”一詞在20世紀初(大致以1915年為界)漢語語境中的呈現情況,以及識得中國現代美學尤其是美育發生的一種特殊性。
一、作為譯詞的浮現
美學術語的形成是在特定的美學條件下展開的,具有一個從日常的到專業的或者說從邊緣到中心的美學化過程。就“中國”的美學而言,美學之有是以入中國為前提,故又存在術語譯介等一系列復雜問題。“美學”本身就是一個外來的譯名。“美學這個學名和學科,猶如哲學、文藝學(或稱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心理學等學名和學科一樣,是舶來品,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隨著西學東漸從西方引入中國的。”“美學”一詞代表了中國美學術語形成的一種典型情況,即作為文化舶來品,有一個“漢化和合法化”的歷程。[3]對于“美感”一詞,首先亦應做如此觀。其次,“美感”一詞詞義在現代漢語中并非單一,它的形成也有一個增加過程。在古代漢語中,“美”與“感”基本是分開使用的,如唐代經學家孔穎達對《禮記·學記》“善歌者使人繼其聲”所作的疏解:“善歌,謂音聲和美,感動于人心,令使聽者繼續其聲也。”因此,“美感”往往不可作為一個詞看待,甚至不能承認它是一個原始的漢語詞。20世紀初中國知識界就是把“美感”當作外來詞的。1903年上海明權社發行的《新爾雅》是20世紀最早出版的漢語辭典。在“釋教育”部分提到“美感”一詞:“離去欲望利害之念,而自然感愉快者,謂之美感。”[4]值得注意的是,該詞被著重加點,顯然是把它作為一個日譯詞看待。辭典、教材、譯作、學校等都是近代中國傳播外來知識的重要載體,它們提供的用語是中國現代學術話語形成的語言基礎。作為外來詞的“美感”,成為本土的美學術語,同樣需要借助各種載體,并與本來就是外來的“美學”一道譯入和并行。這一過程頗為復雜,但其結果是顯然的。
清政府于1902年制定《欽定學堂章程》和1903年頒布《奏定學堂章程》。這兩個章程都明確規定設立教育學、心理學等課程的重要性,由此出現了一批從日文轉譯而來的西方著作。在這些譯介的教育學、心理學教材中,包含著與“美感”一詞十分接近的情況,如:1902年東亞公司新書局發行的《心理學講義》(服部宇之吉)有“純粹悅美之情”,1903年上海時中書局編譯的心理學講義《心界文明燈》有“美的情感”,1905年留日學生陳榥編譯的《心理易解》有“物之足使吾人生快感”,1907年楊保恒編寫的《心理學》提出以“體制”“形式”“意匠”為“三要素”的美感概念。[5]相比之下,美學的譯介在當時并不十分突出,這種局面的改變直至20世紀10年代中期以來。世紀之初的十余年,是中國現代美學觀念的重要發生期,起著承前啟后的作用。事實上,現在通行的許多美學術語已在那時浮現。在譯介的各科教材、專業著作中,都存在大量的專業術語現象,其中有些是無意識地帶進或夾入,有些則是被有意識地運用。總之,它們都是美學術語得以生成的條件和環境。以下著重前期的王國維、蔡元培的文本。
據統計,王國維前期(1889—1911年)的哲學、心理學、邏輯學譯稿約20種,包括署名的和未署名的(均刊于由他主編的《教育世界》)。在這些譯稿中,已出現諸多現代美學基本詞匯。如在1901—1902年翻譯的《教育學》(立花銑三郎)、《教育學教科書》(牧瀨五一郎)、《心理學》(元良勇次郎)中,已出現“美感”“審美”“審美的情感”“美術”“美之學理”等。又如1905年在兩本“教育學”譯著基礎上編成的《教育學》中有“審美之情”一說:“其由美丑而生者,謂之曰審美之情;……教育不可不以制裁下等之感情,及養成高尚之感情為務。”[6]再如1907年的譯文《孔子之學說》(蟹江義丸)中有這么一段:“詩,動美感的;禮,知的又意志的;樂,則所以融和此二者。茍今若無禮以為節制,一任情之放任,則縱有美感,亦往往動搖,逸于法度之外。然若惟泥于禮,則失之嚴重而不適于用。故調和此二者,則在于乎。”[7]這里兩次出現“美感”一詞,前者屬古代漢語用法,后者已屬現代漢語用法。就這些而言,王國維已創造了包括“美感”在內的各種語詞,但它們的區別并不十分分明。
蔡元培前期(1898—1912年)含著、譯、編等多類文本,涉及教育學、哲學、倫理學、美學等各種學科,亦以譯介為主。1901年10月他在紹興及上海搜集國內外參考資料的基礎上寫成《學堂教科論》。該文對各級學校的課程進行研究,并分析清代學風敗壞的原因。文中提到日本學者井上甫水把學術分為“有形理學”“無形理學”和“哲學”。寫于1901年10月至12月的《哲學總論》指出心理學是一種“心象之學”,是考定情感、智力、意志三種心象之性質、作用的“論理學”,其中“論情感之應用”的“應用學”為“審美學”。1903年的譯作《哲學要領》(科培爾講述,下田次郎筆述)把“宗教哲學及美學”都作為“心界哲學”。其中有對“美學”的介紹:“美學者,英語為歐綏德斯Aesthetics。源于希臘語之奧斯妥奧……其義為覺與見。故歐綏得斯之本義,屬于知識哲學之感覺界。……要之,美學者,固取資于感覺界,而其范圍,在研究吾人美丑之感覺之原因。好美惡丑,人之情也,然而美者何謂耶?此美者何以現于世界耶?美之原理如何耶?吾人何由而感于美耶?美學家所見、與其他科學家所見差別如何耶?此皆吾人于自然及人為之美術界所當研究之問題也。”[8]9-10還有對“美術”的介紹:“美術者Art,德人謂之坤士Kunst,制造品之不關工業者也。其所涵之美,于美學對象中,為特別之部。故美學者,又當即溥通美術之性質,及其各種相區別、相交互之關系而研究之。”[8]101906年的譯作《妖怪學講義錄(總論)》(井上圓了)出現了許多談“美”說“情”的譯句:“論理、倫理、審美為心性作用之智、情、意各種之應用,以真、善、美三者為目的;教育學者,智、情、意總體之應用,以人心之發達、知識之開發為目的。”[8]94“世人知美之為美耳,以學術考之,必分析其所謂美者,而一一示其成分,如美麗、宏壯、適合、一統等是也。”[8]169“怪情者,非獨美情之反對,具寫之于美術,轉示美性,而生幾分之快樂。故人多喜妖怪之小說,及妖怪之繪畫。”[8]171這兩部譯作出現了“美學”“美術”“審美”“美情”“美性”等一系列詞,頗耐人尋味,有的顯然與“美感”近義或等義。
蔡元培前期矢志“教育救國”,歷經從“委身教育時代”到“教育總長時代”,期間赴德留學(1907—1911年)。他對西方的哲學、倫理學、教育制度等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并開展了實際工作。如在倫理學方面,編《中學修身教科書》五冊、《中國倫理學史》一冊,譯泡爾生《倫理學原理》一冊。這些作品對“人格”“平等”“權利”“義務”“公德”“私德”等倫理學重要概念進行厘定,在中國倫理學史上具有拓荒的意義。倫理學與宗教、美學之間具有內在統一性,故也不可避免地涉及美學。如《倫理學原理》(1909年,據蟹江義丸日版再譯)譯道:“美學也,倫理學也,皆無創造之力,其職分在防沮美及道德之溢出于珍域,故為限制者,而非發生者”[8]356;“多神教常畀諸神以人類感官之性質,至為自由,故在美學界,極美滿之觀,是吾人今日所以尚驚嘆于希臘諸神也”[8]413。又如《中國倫理學史》(1910年)指出傳統(儒家)倫理學為“我國唯一發達之學術”,又稱哲學、心理學、軍學、宗教學屬倫理學,“評定詩古文辭,恒以載道述德眷懷君父為優點,是美學亦范圍于倫理也”。[9]468蔡元培在萊比錫大學期間,學習哲學、文學、文明史、人類學等課程,特別注重實驗心理學及美學,給他留下“極深之印象”的是美育。1911年10月歸國后,他開始全力提倡美育。而他之所以提出美育,原因在于“美感”具有這樣的性質和作用:“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見;美感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的顧忌,在教育上應特別注重。”[10]這是他在《我在教育界的經驗》(1937年)中特別說到的。而“美育”“美感教育”是他在“教育總長時代”正式提出的(另論)。
美學是西學。美學進入中國是一個不斷譯介的過程,而之所以被譯介又是一種選擇行為。受時代風氣影響,王國維、蔡元培注目西學,自覺、主動地學習外文,體驗異域文化。王國維兩次游學日本,蔡元培則三次赴歐洲,在德國學習哲學、美學。作為將美學譯入中國的先行者,他們代表了西方美學漸入中國的兩種路徑。當然,譯入中國的“美學”并不就是“中國”的美學,它包涵了許多異質成份,特別是日本因素。王國維22歲時到上海,入羅振玉主辦的東文學社。他學日文,譯日書,結交日籍老師。蔡元培而立之年在北京學習日文,先后試譯日文版的《〈萬國地志〉序》《日人敗明于平壤》《俄土戰史》《日清戰史》《生理學》。他們在日文方面用功甚深,廣泛涉獵譯本書,不僅增長了見識、拓寬了視野,而且與日本文化結下了難解之緣。從前期的譯介情況看,他們無不首先從日本文化中汲取滋養。日本在美學從西方到中國的過程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中介,是中國現代美學術語得以形成的最重要渠道之一。
美學在20世紀初的中國尚處于起步階段,美學術語不明顯、不穩定都是必然出現的現象。隨著譯介的增多,“美學”“美感”等將作為完整的漢語詞形式并被普遍接納,這種情況大致發生在1915年,茲舉二例。一是《辭源》列有“美感”詞條:“[美感]謂審美之感覺也。其要質有三:一曰物質,如色、音之類。二曰關系,即集合物質而變化調和之,如圖畫之顏色、音樂之節奏。三曰理想,即趣味,為構成美感所尤要者。”[11]114同時,所列詞條有“美學”“美育”“美情”等。如:“[美情]心理學名詞。由美丑之判斷而生之情操曰美情,亦曰審美的情感。如見天然風景及繪畫、雕刻之美者,則愉快。見不潔丑惡者,則不快是也。”[11]113二是徐大純的《述美學》言及“美學的定義,及其歷史,其要素,其分野,其內容與形象之種類”。他稱“美學”是“最新之科學,亦最微妙、最繁賾之科學”,“美”是一種“特別之感”,“而凡特別之感之中,惟快感為美之重要元素。……而其快感是名美感。Aesthetic feeling,美感者,由美而生之感者之謂也。”還說“快感”為“美之重要元素”,“然快感與美感,正自有別。……即如何之快乃為美,如何之情感乃非美。此在美學上,誠最有研究價值之問題也。”[12]《辭海》和《述美學》都對“美感”一詞予以解釋,利用“審美的感覺”“快感”等不同概念進行揭示,釋義內容比較豐富。不僅如此,兩者代表了日常的(辭典的解釋)和專業的(美學的解釋)兩種釋義方向。這種分化傾向表明“美感”一詞已具術語特征。當然,進一步將“美感”專業化,提升它的美學內涵,還需要后來者的不斷努力。
二、美感觀念的表征
語詞與思想是表里關系,特別是外來詞,這種關系更為顯著。一種外來語之輸入即代表某種外來的思想的進入。作為外來詞的“美感”必然因此而成為美學期待,亦唯此才能成為地道的美學術語。20世紀初是一個思想雜陳、新舊過渡的時代。中西文化的交流、碰撞為新觀念的產生提供了歷史機遇。蔡元培、王國維譯介外國美學,多少是在直接“接觸”各種外來美學術語的基礎上實現的。相比之下,梁啟超顯得特殊。作為中國現代美學起源三大家之一,他是個不談“美學”的美學家。他的筆下竟無“美學”二字,“美育”也僅是在1922年4月北京美術學校講演《美術與科學》中提及(“貴校是唯一的國立美術學校,他的任務,不但在養成校內一時的美術人才,還要把美育的基礎,筑造得鞏固,把美育的效率,發揮得更大”)。至于“美感”一詞,他首先使用是在1910年初《國風報》創刊號上發表的《說〈國風〉中》一文(“即以一身論,舍禽息獸欲外,不復知有美感”),而再次用及直至在1920年出版的《歐游心影錄》(“湖景之美……助長起我們美感”)。故對梁啟超,需要單獨在這里論及。
先說“觀念”。觀念是需要借助語詞(或曰關鍵詞)來表達的可社會化的思想,有一個選擇、吸收和再創造的形成過程。作為觀念,它往往由諸多的概念共同構成。觀念的復雜特點之一就在于它的表征方式。用于表征某種觀念的并非一定就是某詞本身,還有與這種觀念相通的其他語詞。外來詞有一個本土接受過程,起初在詞形、詞義上必然并不固定,但是這種情況并不意味時人缺乏相應觀念。溯源“美感”一詞還需要考察美感觀念的其他表征語詞,如“美術”“文學”。兩詞在蔡元培、王國維那里同樣是十分重要的美學概念形式。蔡元培在1900年前后多次談到“美術(學)”,如:“美術學,為抒寫性靈之作,如詩詞繪事”(《剡山二戴兩書院學約》,1900年);“文學者,亦謂之美術學”;“近世乃有小說,雖多寓言,頗詳民俗,而文理淺近,尤有語言文字合一之趣”(《學堂教科論》,1901年)。把“文學”歸為“美術”,而“美術”又可作“美學”(“審美學”),這種說法在今天有所影響。我們常把“美的”“美感的”或“審美的”,皆視為可通用。王國維不僅譯介了這些概念,而且有更為深刻的見解,如:“美術之為物,欲者不觀,觀者不欲;而藝術之美優于自然之美者,全存于使人易忘物我之關系也”(《紅樓夢評論》,1904年)。又如:“古雅之致,存于藝術而不存于自然”;“可愛玩而不可利用者,一切美術品之公性也”(《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1907年)。再如:“文學者,游戲的事業”(《文學小言》,1906年);“詩歌者,情感的產物”(《屈子文學之精神》,1906年)。王國維以西方美學(文論)來反觀“美術”和“文學”,確立了審美獨立性原則,而這與他的“學術獨立”“哲學獨立”等觀點是統一的。他重視“美”的性質、功用的闡釋,專注的是“美”而非“美感”,所建立的是一個以“美”為核心、以人生價值為取向的思想理論體系。他偏于形而上學,注重的是哲學、美學,指向的是現代人生。蔡元培、王國維的見解,都已包含美或美感的作用是超功利的先進認識。
再看集政治家、文學家、翻譯家于一身的梁啟超。戊戌政變之后(1898年秋),梁啟超負笈東渡,在日本先后創辦《清議報》《新民叢報》《新小說》等,發表了大量的政論文,還有詩(話)、文、小說等,后輯成《自由書》(1899年)、《新民說》(1902年)、《德育鑒》(1905年)、《飲冰室詩話》(1902—1907年)等。此時期是梁啟超美學思想的初發期,以“三界革命”說最著名。他在《夏威夷游記》(1899年)中提出以“新意境”“新語句”“古人之風格”為“三長”的“詩界革命”和以“覺世之文”“歐西文思”為內涵的“文界革命”。他又在《新小說》創刊號上發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1902年,以下簡稱《論小說》),成為“小說界革命”的宣言書。此文倡言“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不僅思想深刻,而且影響深遠。正如張法所評價:“他以《小說與群治的關系》等文章,在一種‘革命’營造中,一方面使小說為藝術的最上乘而改變了中國傳統文化中以詩文書畫為主體的藝術結構,另一方面讓藝術成為喚起民眾、塑造現代性新民的有力武器,顯示了美學巨大的政治/社會功用。”[13]藉此名篇,并結合其他,我們可以一窺梁啟超遣詞造句的特點,而這恰恰能夠彰顯梁啟超前期美學話語的特色。
延用。這是指保留已有語詞形式(但詞義有所增減)或者進行簡單的改造(如增減字數)。古代漢語文論范疇不勝枚舉,一個顯著特點是言簡意賅。體現在《論小說》中就是把小說“支配人道”的“四力”概括為“熏”“浸”“刺”“提”。其中談“浸”時又這樣說:“人之讀一小說也,往往既終卷后數日或數旬而終不能釋然,讀《紅樓》竟者,必有余戀有余悲,讀《水滸》竟者,必有余快有余怒,何也?浸之力使然也。等是佳作也,而其卷帙愈繁事實愈多者,則其浸人也亦愈甚;如酒焉,作十日飲,則作百日醉。”[14]884-885還有稱“此四力所最易寄者惟小說”,“小說”既“可愛”又“可畏”,等等。梁啟超在具體說明時,好用“余×”“可×”“大×”等構詞方式。又如《惟心》(1900年)先這樣說:“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虛幻,惟心所造之境為真實。”接下來舉例說:面對月夜、黃昏、桃花或江、舟、酒時,分別產生“余樂”/“余悲”、“余興”/“余悶”、“歡憨”/“愁慘”、“清凈”/“愛戀”、“雄壯”/“冷落”的“絕異”之“境”。同樣的美感對象,產生不同的美感境界。他認為,造成美感的不同,“其分別不在物而在我,故曰三界惟心”。此文中還有這樣一些表述:“天下之境,無一非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樂之、憂之、驚之、喜之,全在人心”,“境則一也,而我忽然而樂,忽然而憂,無端而驚,無端而喜”,“是以豪杰之士,無大驚,無大喜,無大苦,無大樂,無大憂,無大懼。”[15]361-362這些盡管并非純粹談美和美學,但都與審美(美感)現象直接相關。梁啟超善用例證的論證方式和對舉、排比、比喻等多種修辭手段,在措詞方面頗有講究。
借用。這是指利用日常的、倫理的或宗教的術語、概念進行說明的一種方式。中國傳統文論本具有這種特點,如“取象”“比興”蘊含的就是一種借物喻人的倫理觀念,再如“境界”原是道家、禪家的用語,而在后來成為重要的審美范疇。《論小說》包含了許多佛語、佛義、佛理,茲不詳舉。梁啟超對佛教、佛學從社會、文學等多方面展開討論。如《論佛教與群治之關系》(1902年)指出信仰佛教的六大條件:“智信而非迷信”“兼善而非獨善”“入世而非厭世”“無量而非有限”“平等而非差別”“自力而非他力”,同時還指出佛學之“廣”“大”“深”“微”。[14]906-9101920年代初他轉向佛學研究。《翻譯文學與佛典》(1921年)指出佛典的輸入和翻譯具有重要意義,如拓展中國人的視野、擴大漢語詞匯、增辟人們的想象空間,能帶來漢語語法及文化的某些變化,同時還對學者思想、文人創作產生深刻影響。可見,翻譯文學對中國一般文學、國語(包括詞義、語法、文體)的影響很大。梁啟超對佛教、佛學的深刻體會,還表現在《什么是文化》(1922年)一文借用佛家術語“業”(即創造、創造力)來形象地說明“美感”:“美感是業種,是活的;美感落到字句上成一首詩,落到顏色上成一幅畫,是業果,是呆的。”[16]佛教成為包括美學在內的梁啟超思想的重要來源和組成部分。
新用。這是指在不參考已有的各種語詞的情況下進行創造的方式。一般地說,外來詞是一種新造詞,典型的如音譯這種方式。《自由書》是梁啟超的留學日記,其中有一篇《煙士披里純INSPIRATION》。他這樣解釋:“‘煙士披里純’者,發于思想感情最高潮之一剎那頃,而千古之英雄、豪杰、孝子烈婦、忠臣、義士以至熱心之宗教家、美術家、探險家,所以能為驚天地泣鬼神之事業,皆起于此一剎那頃,為此‘煙士披里純’之所鼓動。故此一剎那間不識不知之所成就,有遠過于數十年矜心作意以為之者。”[15]375“煙士披里純”,今譯“靈感”,本是一種在文學創作過程中發生的但并不神秘的審美心理現象,這里卻把它當作包括美術家在內的一種人格動力機制。梁啟超的新造詞,當以“移人”為代表。該詞兩次出現在《論小說》:“茍能批此窾、導此竅,則無論為何等之文,皆足以移人”,“文字移人,至此而極。”又如《佳人奇遇·序》(1898年):“其移人之深,視莊言危論,往往有過。”再如《新民說》:“天下移人之力,未有大于習慣者”,“崇貴逸樂,最足移人。”與“移人”相似的還有“情之移”“移我情”,前者如《飲冰室詩話》第87、179則,后者如《飲冰室詩話》第161則、《致湯覺頓》(1910年10月23日)、《〈秋蜷吟館詩鈔〉序》(1915年)、《佛教教理在中國之發展》(1915年)、《趣味教育與教育趣味》(1922年)、《致胡適之》(1925年7月3日)。出現在論文、詩話、書信、序文等之中的“移”詞,顯然是與“移情”一詞十分接近。但從來源看,并非出自立普斯美學,而是梁啟超自創。
梁啟超文本用語講究,思想蘊含豐富,構成了近代以來中國文化史的一道獨特景觀。作為最早的西學譯介者之一,梁啟超以融西入中、除舊啟新為理想之追求。他在小說方面獨樹一幟,理論、創作、翻譯并舉,尤其是提出的“力”“移人”等美學范疇具有標識性。而他之所以在這方面用力甚多,實際是把“小說”作為“文學美術”的代表,以之進行啟蒙宣傳。正如他在《新民說》中所言:“凡一國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國民獨具之特質,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風俗習慣、文學美術,皆有一種獨立之精神,祖父傳之,子孫繼之,然后群乃結,國乃成。斯實民族主義之根抵源泉也。我同胞能數千年立國于亞洲大陸,必其所具特質,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異于群族者,吾人所當保存之而勿失墜也。”[17]單就“文學”而言,這也是他一以貫之的主題。如他對小說、詩、戲曲、美文等文類采取“離合、重組以及等級的升降”的態度,“于文學版圖的分割屢屢變異”,但是最終也都指向“從偏向文學功能到注重文學美感的理念轉化”。[18]如此看來,梁啟超“善變”中有“不變”的一面,體現之一就是重視“文學”本身的美學價值與啟蒙功能。他幾乎不提“美感”,但“新民”、文類等諸多問題并沒有游離于美學視域之外。事實上,談文學、美術都無法避開談及美和美感,而美與美感又是十分接近甚至一致的概念和問題。當然,從建立美學身份的角度而言,“美感”一詞需要在相應的理論、學科和思想的不斷發展中確立和完善。
三、關于“美感教育”
“美感”一詞能夠在后來得以普及,很大程度得益于美育之提倡。美育是中國現代美學的特色。從世紀初的王國維開始,美學就被烙上美育的標簽,而美育大行其道,又始于蔡元培在民初的提倡,以《對于新教育之意見》(1912年,以下簡稱《意見》)一文的發表為標志。該文先后在《民立報》《教育雜志》《東方雜志》上公開,特別是以“對于教育方針之意見”之名登載在《臨時政府公報》,顯示出權威性。在《意見》中,蔡元培初次提出“美感之教育”:“美感者,合美麗與尊嚴而言之,介乎現象世界與實體世界之間,而為之津梁。……故教育家欲由現象世界而引以到達于實體世界之觀念,不可不用美感之教育。”[19]而這個“美感之教育”,在教育宗旨令(1912年9月2日)中明確為“美感教育”:“注重道德教育,以實利教育、軍國民教育輔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美感教育精神也在隨后的各類各級教育規程中得到體現。如:“圖畫要旨在使詳審物體,能自由繪畫兼練習意匠,涵養美感”(《中學校令施行規則》,1912年12月2日);“陶冶情性、鍛煉意志,為充任教商之要務,故宜使學生富于美感,勇于德行”(《師范學校規程》,1912年12月10日)。提倡美育作為教育宗旨的一部分,由官方公布并逐級落實,這種“自上而下”的途徑,在有利于盡快完成改革教育制度的同時,使得美育理念得到廣泛傳播。
蔡元培是致力推行美感教育的主要倡導者。他宣傳美育是一個不斷闡釋“美感”的過程。“美感”是構成美育觀念的關鍵詞。從《意見》一文使用情況看,“美育”18次,“美感”9次,兩者相得益彰。而這個由康德所創造、具有中介作用的“美感”概念,被蔡元培嘗試利用,成為“超軼政治之教育”的“世界觀”和“美育主義”的主體內涵。在約寫于1912—1916年期間的《孑民自敘》中還一度稱“美學(之)教育”:“欲完成道德教育,不可不以一種哲學思想為前提。而哲學思想之涵養,恃有美學之教育,故美學教育為最當注意之點。”[20]隨著“五四”前夕發表“以美育代宗教”,通過演講等方式的不斷深入闡明,至1930年代初他已表述得十分清晰。如為《教育大辭書》(1930年)而撰寫的專門條目:“美育者,應用美學之理于教育,以陶養感情為目的者也。”[21]又如《美育與人生》(1931年前后):“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偉大而高尚的行為,這是由于感情推動力的薄弱。要轉弱而為強,轉薄而為厚,有待于陶養。陶養的工具,為美的對象;陶養的作用,叫作美育。”[22]前者從目的,后者從對象、作用兩方面解釋了美育,強化了美育的內涵,即是對感情的陶冶和激發,而這無疑就是“美感教育”的實質。但就蔡元培在民初初次提出的“美感(之)教育”而言,它畢竟是“新學語”。顯然,對于“美育”的理解不可能只存在一種方式,還有“情感教育”(簡稱“情育”)、“審美教育”“美術教育”“藝術教育”“美學教育”等,有的甚至先于“美感教育”而出現。因此,“美感教育”這一概念的合法性,還需要我們在歷史與邏輯的統一中做進一步分析。
王國維曾發表多篇論美育的文章。如《論教育之宗旨》(1903年)指出:“情”是精神的一部分,“美”是“情感之理想”,而“美育”即是“情育”,“一面使人之感情發達,以達完美之域,又為德育與智育的手段”。又如《孔子之美育主義》(1904年)則是“備舉孔子美育之說,且詮其所以然之理”,用以啟發“世之言教育”。再如《古雅之在美學上之位置》(1907年)指出:“古雅”處在優美與宏壯之間并兼有兩者之性質,而它又是一種能夠通過后天修養而得之的能力,“故可為美育普及之津梁”。這些都已成為中國現代美育思想之經典,具有開創性意義。王國維闡說美育,吸收德國的哲學、美學,致力發掘中國美育傳統,是成功開創中西“化合”的典型。他的“先知先覺”也得到后人的高度評價:“王氏所論,且皆近代教育之先導,其頭腦清新,眼光明銳如此,于開發近代風氣,厥功偉已。”[23]160對于王國維的美學、美育之貢獻,似乎怎么評價都不為過。然而從時間上看,蔡元培比王國維更早地使用“美育”一詞并提出“情育”的觀點。《哲學總論》寫于1901年10至11月,在談到純正哲學研究之目的時,他說:“教育學中,智育者教育智力之應用,德育者教意志之應用,美育者教情感之應用。”[9]357“美育”是“情感之應用”,是與“智育”“德育”相區別的“情育”。蔡元培從一開始就把美育夯定在知意情分立的科學基礎之上,這為后來進一步提出和全面倡導美育做好了鋪墊。“情育”的觀點與稍后的王國維的觀點相呼應。從《哲學總論》到《意見》的十余年間,是蔡元培廣泛學習包括美學、美育在內的成長時期和重要的學術積累時期。他對美育的“美感教育”的理解已不只是定位于哲學的“情育”,而是有著哲學、教育學、心理學、倫理學、社會學等多學科的考量。此時期盡管也是王國維研究美育的重點時期,但是他熱衷“哲學的觀察”,深陷哲學之困境。美育只是王國維為學的一個階段所為,而蔡元培是把美育之提倡作為個人的終身事業。
王國維主編的《教育世界》刊有《霍恩氏之美育說》(1907年,為佚文,或是譯文)。此文是一篇介紹西方美育家的專論文章,其中有“審美教育”“審美的教育”“審美的感動”“審美之休養”“審美之興味”等各種“審美”用詞。在王國維的文本中,則有“審美的嗜好”(《紅樓夢評論》)、“審美之境界”“審美之趣味”(《孔子之美育主義》)等多種形式。把“審美教育”作為一個概念使用,實以李叔同為早。在《圖畫修得法》(1905年)這篇被認為中國最早介紹西洋畫知識的文章中,他寫道:“今嚴冷之實利主義,主張審美教育,即美其情操,啟其興味,高尚其人品之謂也。”另在“自在畫概論”部分提到“精神法”,其中又這樣寫道:“吾人見一畫,必生一種特別之感情。若者嚴肅,若者滑稽,若者激烈,若者和藹,若者高尚,若者瀟灑,若者活潑,若者沈著,凡吾人感情所由發,即畫之精神所由在。”[24]此中提及的“審美心”“特別之感情”等說法接近“美感”。除曾譯“美學”為“審美學”之外,蔡元培也只是在《以美育代宗教說》(1917年)、《美學講稿》(1921年)等中偶爾使用“審美”的說法,遑論“審美教育”。“審美”一詞應當有特殊用法。正如陳望衡指出:“審美,在英語中為aesthetic,它很少獨立存在,總是與別的詞連在一起,構成諸如‘審美態度’、‘審美判斷’、‘審美愉快’、‘審美價值’等概念。這樣說來,審美就不能等同于審美感受——美感了。”[25]故此,“審美教育”與“美感教育”有所不同,前者突出美育實施過程中的客體(美的對象)與主體(受教育者)的主次關系,而后者突出對這種關系的超越及統一,兩者不能完全一致。
把文學、美術作為教育課題,王國維、梁啟超都有切實的思考。王國維在關于“文學與教育”的“教育偶感”(1904年)中,有感于“美術之匱乏”而要求“文學之趣味”,并稱“精神上之趣味”必定是通過千百年的培養和個別天才人物的引領才能達到。他告誡那些倡言教育者:如果不謀求“精神趣味”,那么將是十分愚昧無知的。梁啟超在《自由書》(1899年)中指出:改變“固無精神”的現狀需要“浚一國之智,鼓一國之力”,其方法就是以“自由”為工具的“精神教育”,而“精神教育”就是“自由教育”。他在第77則詩話中又說道:“蓋欲改造國民之品質,則詩歌音樂為精神教育之一要件,此稍有識者所能知也。”[26]他們都提出了用于改造國民性的“精神教育”,其包含的美育精神已昭然若揭。但是他們并沒有直接使用“美術教育”的說法。“美術教育”的核心在于“美術”。“美術”也是一個外來詞。它經由王國維、劉師培、魯迅等一批先見者的主導和鋪墊,通過“南洋勸業博覽會”“上海圖畫美術院”《美術叢書》等會展、學校、出版物的社會輻射面,不斷擴大和普及,終為民初社會所全面接納,被確定為現代漢語的固有名詞。而它的涵義,則從“美育”“美學”“美化”或“文學表現”(即美之“術”)、“藝術”等混用狀態中逐漸疏離出來,成為視覺藝術或造型藝術的特稱。[27]這就是說,“美術”一詞在形、義兩方面至民初已基本定型,并成為流行的美學概念。從這方面說,“美術教育”也就不能等同“美感教育”。當然,蔡元培對“美術”的理解有一個趨于細密、明確的過程。他譯介“美術”始于1900年,是把“美術”作為廣義的概念,包括“文學”,又與“美學”通用(見前述)。至《意見》一文,則視“美術”為“美感”:“美術則即以此等現象為資料而能使對之者,自美感以外一無雜念。”這是取美術的美感作用,故又有“圖畫”“唱歌”“游戲”等皆為“美育”之論。《以美育代宗教說》(1917年)指出“歌詞”“演說”皆有“美術作用”,還把“美術”作為與“宗教”的對應。再至《美育代宗教》(1932年)則直接斷言“只有美育可以代宗教,美術不能代宗教”,而“美育”與“美術”之所以不可互代,是因為“美育是廣義的,而美術的意義太狹”。蔡元培談美育不離開美術,這是他從偏美育理論到重美育實施的思想之體現。
應該說,“美感教育”是一個更為嚴謹、科學的概念。“情育”“審美教育”“美術教育”“美感教育”各有偏重,而“美感教育”更具包容性,其內涵和外延也更大,故也更加適合表明美育之提倡的可行性。蔡元培在民初提出美感教育的美育,固然是他的自覺的選擇,其實也是一種時代必然。正如王善忠指出:“要給美育下定義,一是不可能離開美感(當然,也離不開美,因為沒有美,美感也就無從談起)和教育這兩個基本構成要素,二是還要考慮到這界說能為人們所理解、贊同和把握。”[28]王國維、李叔同、梁啟超的美育觀的影響程度,受制于一些客觀的條件,或因理論精深不易為一般人所理解,或因在域外刊物發表而鮮為國內讀者所了解。而蔡元培美育觀之所以得以廣泛流行,很大程度是與他的特殊身份,與教育革新、政治運動的密切配合有直接關系。正如劉海粟所評:“蔡先生把法國資產階級大革命的口號與儒家學說作了綜合,使新老知識分子皆能接受。美育一說,更加引起我的共鳴。”[23]292
談到“美育之提倡”,我們還不能忘記魯迅的貢獻。魯迅前期(1902—1917年)多次提出有關文學、美術具有美感作用的觀點,如:“至小說家積習,多借女性之魔力,以增讀者之美感”(《月界旅行·辨言》,1903年);“蓋使舉世惟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于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于無有也”(《科學教史篇》,1907年);“純由文學上言之,則一切美術之本質,旨在使觀聽之人,為之興感怡悅”(《文化偏至論》,1908年)。他在加入特別班問學期間(1908年)與章太炎討論文學定義時還說:“文學和學說不同,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29]這些觀點萌生于他留日期間,表達的是通過文藝以“轉移性情”、改造社會的啟蒙理想。1909年夏留學歸來之后供職于蔡元培主持的教育部的5年期間,魯迅做了大量的推廣美育的工作。1913年他在《教育部編纂處月刊》上發表的《儗播布美術意見書》對美術作用作出了獨到見解:“播布云者,與國人耳目接,以發美術之真諦,謂不更幽秘,而傳諸人間,使起國人之美感,更以冀美術家之出世也。”還對美感的產生作了科學的、唯物論的解釋:“蓋凡人有人類,能具二性,一曰受,一曰作,受者譬如曙日出海,瑤草作華,若非白癡,莫不領會感動。”[30]該月刊還載有他的兩篇譯文《藝術玩賞之教育》《社會教育與趣味》(上野陽一)。除傳播藝術美育、社會美育之外,魯迅還做了許多開創性的推廣美育的實際工作,如到“夏期美術講習會”講演,籌辦全國兒童藝術展覽會,籌建京師圖書館、通俗圖書館、歷史博物館,關注新劇(話劇、文明劇)的發展。魯迅前期的美育觀受到日本文化的影響和蔡元培思想的直接引導。隨著“文學革命”的展開和唯物主義美學思想的深入,魯迅對美感的社會性和其中潛在的功利因素又逐漸加以闡明,使之趨于完整。
四、結 語
在20世紀之初的漢語語境中,“美感”一詞處于微妙的境地。把它從外來的轉化為本土的、從日常的提升為美學的,并作為美學術語用于解釋美學問題,這一過程包含了王國維、蔡元培、梁啟超等學人的不斷努力。特別是美育之興起并被蔡元培確立為“美感教育”,這是具有實際意義的。所謂“起國人之美感”(魯迅語)就是激發、培養國人的情感,張揚國人的生命活力。這使得中國現代美育成為有深度的美學理論,成為以“育人”為目標、以“救國”“救人”為直接目的的文化思想。從改造、提升國民精神這一高度審視,中國現代美育的發生的確是在觀念、思想層面展開,但是不可能離棄具有定型功能的漢語。西學東漸背景下,新觀念、新思想的發生需要通過學人漢語體驗才能形成實質性的影響。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的現代性也是漢語的現代性,也正如此,近代以來中國學人才有感于新學語之輸入或者創造的必要。中國現代美學起源三大家的漢語體驗,是他們切近中國現代美學尤其是美育發生于本土實際問題解決的直接方式。至于“美感”一詞在20世紀10年代中期之后的流變,筆者將另行追蹤。
[1] 朱光潛.美感問題[N].光明日報,1962-07-16.
[2] 李澤厚.美學三書[M].合肥:安徽文藝出版社,1999:502.
[3] 杜書瀛.新時期文藝學前沿掃描[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178-179.
[4] 沈國威.新爾雅:附題解·索引[K].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1:255.
[5] 黃興濤.“美學”一詞及西方美學在中國的最早傳播[J].文史知識,2000(1):75-84.
[6] 王國維.教育學[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38.
[7] 王國維.王國維文集:第3卷[M].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147.
[8]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9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9]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10]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8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508.
[11] 陸爾達.辭源[K].上海:商務印書館,1915.
[12] 徐大純.述美學[J].東方雜志,1915,10(1):63-67.
[13] 張法.回望中國現代美學起源三大家[J].文藝爭鳴,2008(1):40.
[14] 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4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5] 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2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16] 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14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4063.
[17] 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3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657.
[18] 夏曉虹.文學語言與文章體式:從晚清到五四[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186.
[19]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2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11.
[20]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17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416.
[21]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6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599.
[22] 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7卷[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290.
[23] 陳平原,王楓.追憶王國維[G].北京: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7.
[24] 郎紹君,水天中.二十世紀中國美術文選:上卷[G].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99:4.
[25] 神林恒道.“美學”事始——近代日本“美學”的誕生[M].楊冰,譯.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1:2.
[26] 梁啟超.梁啟超全集:第18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5333.
[27] 陳振濂.“美術”語源考——“美術”譯語引進史研究[G]//浙江大學美術文集:上卷.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07:351-385.
[28] 王善忠.美感教育研究[M].長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3:10.
[29] 許壽裳.亡友魯迅印象記[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5:27.
[30] 魯迅.魯迅大全集:第1卷[M].武漢:長江文藝出版社,2011:168.
(責任編輯:紫 嫣)
The Term "Beauty" and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LAI Qin-fa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321004, China)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0th century, the term "beauty" in Chinese context is a loan word from abroad like "aesthetics". It first became a Chinese aesthetic term during the time when it became an entry inNewEryain 1903 and was elaborated upon inOnAestheticsin 1915. As a translated word, "beauty" occasionally,not steadily, appeared in the earlier works of Wang Guowei and Cai Yuanpei, a phenomenon that was bound to occur after its initial introduction into China. Although they did not appear in the early works of Liang Qichao, a utilitarian aesthetic concept was clearly visible. The subsequent spread of the term "beauty" was due to the promo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Defining "aesthetic education" as "education of the beautiful" was an important step in establishing its Chinese aesthetic identity.The language experience of these three great masters at the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was the direct way in which they tried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posed by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s or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that matter.
"beauty"; aesthetic idea; "aesthetic education"; birth of modern Chinese aesthetic education; experience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017-02-27
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規劃基金項目《中國現代美學的日常生活維度研究》(14YJA751011)的階段性成果之一。
賴勤芳(1972—),男,浙江金華人,文學博士,浙江師范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主要從事中國現代美學與文論研究。
B83-0
A
2095-0012(2017)03-0026-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