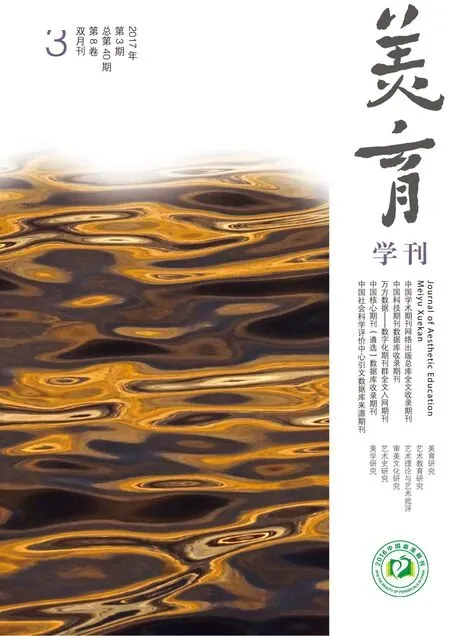近20年豐子愷研究述評(1997—2016)
宋 睿,潘建偉
(杭州師范大學 藝術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
近20年豐子愷研究述評(1997—2016)
宋 睿,潘建偉
(杭州師范大學 藝術教育研究院,浙江 杭州 311121)
1997年至2016年的豐子愷研究取得了豐富的成果,無論是深度,還是廣度,都大大超越了之前任何一個時期,及時對之進行總結便顯得非常必要。現從“美術研究”“文學研究”“藝術思想研究”“生平與作品考證及其他”以及“港臺及國外的研究”五個方面分別進行評述,通過回顧近20年的豐子愷研究,展示所取得的成績與突破,發現所面臨的問題與不足,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參考。
豐子愷研究;述評;逐漸成熟期
大致來說,近百年的豐子愷研究可以分為4個階段。從鄭振鐸、夏丏尊、朱自清、俞平伯等在1925年為《子愷漫畫》作序跋文起至1949年為第一階段。這一階段的豐子愷研究可概括為“摸索前行期”,相關的文章大多為印象式的,但卻形成了一些經典性的意見,比如俞平伯說的“畫格旁通于詩格”(《〈子愷漫畫〉跋》)、郁達夫說的“人家只曉得他的漫畫入神,殊不知他的散文,清幽玄妙,靈達處反遠在他的畫筆之上”(《中國新文學大系·散文二集·導言》)、朱光潛說的“在人品和畫品兩方面都受到弘一的熏陶”(《豐子愷先生的人品與畫品——為嘉定豐子愷畫展作》)以及吉川幸次郎說的“我所喜歡的,乃是他的像藝術家的真率,對于萬物的豐富的愛以及他的氣品、氣骨”(《緣緣堂隨筆·譯者的話》)等等。這些意見在此后的研究中被不斷地深化,可見豐子愷研究從一開始就具有了較高的起點。
從1949年至1976年為第二階段。這一個階段的豐子愷研究為“遭遇挫折期”,尤其到了“文革”,豐子愷本人成了批斗對象,故而此期間中國大陸基本談不上研究。不過,在港臺及海外有一些較有價值的評論,如馬駿的《讀豐子愷漫畫〈護生畫集〉四集》(載1963年1月2日新加坡《民報》新年特刊)、李輝英的《豐子愷和豐子愷的漫畫》(載1972年4月2日香港《亞洲周刊》)等。這些文章是這一時期難得的亮點。
從1976年至1997年為第三階段。這一時期中國大陸的豐子愷研究進入“穩步發展期”,大致說來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回憶、介紹為主,研究性的文章較少。從1983年陳星發表《豐子愷散文藝術的特色》(載《杭州師院學報》1983年第1期)、殷琦發表《豐子愷散文研究初探》(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3年第4期)等起,才逐漸出現系統的學理性論文。相關的年譜、傳記及作品考訂、資料匯編工作也在穩步進行,出現了一些可喜的成果。另外,在這一階段,上海、桐鄉的豐子愷研究會分別于1984年、1992年成立,并推出內刊《楊柳》。
從1997年以來至今為第四階段,是豐子愷研究的“逐漸成熟期”。1997年10月杭州師范大學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簡稱“弘豐中心”)的成立,是這一階段的標志性事件。1998年10月28日,弘豐中心舉行了紀念豐子愷誕辰100周年學術座談會。隨后,出版了由朱曉江主編的論文集《豐子愷論》(西泠印社2000年初版)。從2005年起至2016年,弘豐中心主辦了三次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并出版了三本會議論文集。2016年10月,由陳星任總主編的《豐子愷全集》(全50卷)由海豚出版社出版,這是迄今為止豐子愷作品編纂最全面、細密的成果,也是近20年來豐子愷研究的濃重收筆。概括來說,此階段的豐子愷研究有如下三大特點。
其一,研究隊伍迅速壯大。陳星曾在《豐子愷研究的過去、現在與將來》(收入朱曉江主編的《豐子愷論》)一文中說過:“就目前的情形而言,從事豐子愷研究的學者相對于弘一大師研究的學者,在人數上還不夠多,研究的領域也還有待于進一步開拓。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在研究者們的共同努力下,豐子愷研究一定可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有一個較大的發展。”(第28、29頁)這一看法頗具前瞻性。以近20年中國大陸的碩博論文為例,以弘一大師(或弘一法師、弘一、李叔同)為題目的碩博論文僅24篇,其中博士論文3篇;而以豐子愷為題的碩博士學位論文卻多達93篇,其中博士論文5篇。*此為不完全統計,在筆者寫作本文時,“中國知網”尚未收錄完整2016年的碩博學位論文。另外,歷年沒有上傳到知網的學位論文也未統計進去。張斌的《豐子愷繪畫中的詩意》(中央美術學院2005年)是中國大陸第一篇豐子愷研究的博士論文,并經修訂后由文化藝術出版社在2007年正式出版,書名為《豐子愷詩畫》。她的另一部著作《繪畫與詩意——豐子愷的藝術》(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初版)是對豐子愷繪畫中“詩意”的進一步探究。張斌之后,相繼以豐子愷為題撰寫博士論文的有王文新的《豐子愷美術教育思想研究》(南京藝術學院2008年)、陳劍的《豐子愷藝術教育思想及實踐研究》(山東大學2011年)、黃思源的《豐子愷文學創作與繪畫》(湖南師范大學2014年)以及冉祥華的《豐子愷美學與藝術思想的佛學意蘊研究》(山東大學2015年)。關于“近20年豐子愷研究的碩博學位論文選題分析”甚至可以單獨成文。
其二,研究主題愈加專門。1995年,陳星出版了《清涼世界——豐子愷藝術研究》,對豐子愷的繪畫、文學與音樂之藝術成就進行了多方面的探討。這是中國大陸第一部豐子愷研究專著,具有篳路藍縷之功。但到最近幾年就很難看見這種全方位研究的著作了。隨著研究專門化進程的深入,論者們都傾向于將豐子愷的某一領域的成就加以探討。如陳星于2004年出版《豐子愷漫畫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04年初版),該書是一部較為完整的豐子愷漫畫研究專著,從論述豐子愷漫畫的肇始起,對豐氏漫畫的藝術特色、題材分類、藝術理論等各個方面進行了細致深入的研究。另外,之前對于豐氏藝術成就多著眼于其題材、風格、形式等方面,而結合其藝術理論研究過少,近20年以來在這一方面則大有突破。
其三,研究方法逐步更新。前三個階段很少涉及的城市學、社會史、圖像學、互文性理論、文化人類學等方法被運用于豐子愷的文藝研究,如王文新的《豐子愷插圖藝術研究》(華中師范大學出版社2014年初版)運用互文性理論,以豐子愷為葉圣陶著的《古代英雄的石像》、俞平伯著的《憶》、葉圣陶編寫的《開明國文課本》、茅盾主編的《小說月報》、周作人著的《兒童雜事詩》、魯迅著的《阿Q正傳》而創作的插圖為研究個案,討論了文本與圖像之間的關系,并以“德性之光”總結了豐子愷插圖漫畫的審美品格。再如陳偉、劉飛飛的《空間藝術中的時間敘事杰作——論豐子愷漫畫的時間敘事性》(載《東方叢刊》2009年第3期)借鑒敘事學理論,分析了豐子愷漫畫的空間敘事特點,選題具有創新性。當然,在運用新方法來解讀豐子愷漫畫時較難避免產生“強制闡釋”的問題。如何從新的視角切入豐子愷研究,同時又不曲解、誤解研究對象,或許是今后該研究領域的一個重要方向。
本文通過回顧與總結1997年至2016年的豐子愷研究,展示研究所取得的成績與突破,發現所面臨的問題與不足,為進一步的研究提供參考。必須提及的是,對于豐子愷的研究綜述早有學者努力為之。陳星在1995年出版的《清涼世界——豐子愷藝術研究》第五章“學林探路:豐子愷研究回顧與評析”中就已簡述了從1925年到1995年七十年來豐子愷研究的狀況。該文后略作增補,收入朱曉江主編的《豐子愷論》。陳星另在《豐子愷評傳》(山東畫報出版社2011年初版)的附錄《近三十余年豐子愷研究與紀念活動綜述》中對1978年至2011年的豐子愷研究進行過一次整理,該文偏重介紹著作,較少評述論文。朱曉江的《豐子愷散文研究述評》(收入杭州師范大學弘豐中心編的《第三屆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初版)梳理并評價了從1930年以來關于豐子愷散文的研究成果,對于90年代以來研究者的撰述尤為詳盡。黃儀冠的《豐子愷與臺灣之因緣》(收入杭州師范大學弘豐中心編的《第三屆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第五部分為“臺灣研究成果概述”,主要介紹了臺灣近20年來豐子愷的碩博學位論文概況。限于篇幅,筆者詳人之所略而略人之所詳,擬從“美術研究”“文學研究”“藝術思想研究”“生平與作品考證及其他”分別予以介紹,加上單列一項的“港臺及國外的研究”,故而全文共為五大部分。
一、美術研究
豐子愷的美術成就涉及漫畫、書法、裝幀、木刻等多個方面,而漫畫無可置疑的是其美術成就的主要方面。發展到21世紀的豐子愷漫畫研究,不管是從廣度還是深度都進入了一個嶄新的局面,最可注意的有兩點:一是從藝術思想的層面探討豐子愷的漫畫藝術;二是將新方法、新理論運用于豐子愷漫畫的研究。
先說第一個方面。以往對豐氏漫畫的研究,往往著重于對其漫畫進行風格梳理、類型界定,或對單幅多幅漫畫進行具體分析與鑒賞,在這20年中此類研究已經大量減少(當然也有一些,下面會介紹),而著重從藝術思想的層面,深入研究豐子愷漫畫藝術的整體價值。朱琦的《曲高和眾 雅俗共賞——論豐子愷的藝術觀及其漫畫特征》(載《文藝研究》1998年第4期)認為豐子愷獨特的藝術成就根植于他的藝術大眾化思想,并引葉圣陶評豐氏畫“出人意外,入人意中”一句解釋道:“出人意外,是指所畫的大多是別人沒有畫過的,故而有新鮮感;入人意中,是指這些題材幾乎又都來自現實生活,是大家熟悉或曾經感受的,因而使人感到親切。”成立的《豐子愷的藝術理論與漫畫創作》(載《杭州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認為只有揭示出“他的理論探討和漫畫創作之間存在深刻的內在聯系”,才能“真正認識豐子愷在現代中國畫革新運動中的杰出貢獻”。蔣霞、楊曉河的《豐子愷的中西繪畫比較論及其當代意義》(載《藝術百家》2011年第7期)認為豐氏避免中西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在平等的原則下建構符合中國美術特色的話語體系。查律的《豐子愷漫畫基本思想評述》(收入陳星主編的《豐子愷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初版)從“印象強明”“畫中有詩”及“線的雄辯”概括了豐子愷漫畫的基本思想,由此認識與理解豐子愷漫畫的形態及內理。李兆忠的《東方詩魂的共鳴——豐子愷與竹久夢二》(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4年第11期)認為留學日本的十個月時間在豐子愷的藝術思想發展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與竹久夢二的相遇使得陷于西洋畫困境中的豐子愷找到了創作方向,成功地完成了繪畫道路的轉型。黃江平的《論豐子愷民俗審美的特征及其當代價值》(收入杭州師范大學弘豐中心編的《第三屆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概括了豐子愷民俗審美的特點是鄉土情結、人生情味與現實情懷,同時又指出其在認同價值、教育價值與和諧價值上具有重要的當代意義。陳星的《豐子愷佛教題材繪畫的平民化意識》(載《美育學刊》2015年第5期)一文著重討論了豐子愷的“護生畫”“警世漫畫”和“繪佛千尊”等繪畫作品中所體現的平民化意識,認為這些作品都共同構成了豐子愷佛教題材繪畫創作的內容。作者又于2006年出版專著《豐子愷佛教題材繪畫作品的平民化意識與警世價值研究》(上海三聯書店2016年初版),從豐子愷佛教題材繪畫的作品種類及創作過程到創作因緣及時代佛教背景,再到作品的價值與意義,都進行了深入而系統的研究。潘建偉的《論豐子愷對陶淵明的接受》(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6年第12期)從日常生活、漫畫主題、文化思想與藝術精神四個層面,參照魯迅與朱光潛關于陶淵明的藝術風格之爭,論述了豐子愷對陶淵明接受的獨特意義。作者指出:“魯朱之爭在豐子愷那里很自然地會被消解,他一并轉化了陶淵明勤篤躬耕、堅貞守節的現實擔當與泯化喜懼、任天委運之生命境界,這使他在二十世紀的社會戰亂與政治運動中保持著藝術的獨立與人格的自由。”
第二是新方法、新理論的運用。近20年來,學者們將新方法、新理論運用于漫畫研究,更深入地理解了豐子愷漫畫的意義。小田(朱小田)從社會史的角度考察了豐子愷的作品,連續發表了數篇有較高價值的論文。他的《漫畫:在何種意義上成為社會史素材——以豐子愷漫畫為對象的分析》(載《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將豐子愷的漫畫作為社會史研究對象進行分析,通過藝術與歷史的跨學科對話,使漫畫以獨特的方式擁有了社會史意義。作者指出:“漫畫以其獨特的藝術話語,展現了一個時代日常角色在社群網絡中的互動和流動場景,并讓歷史角色發出自己的聲音,揭示了蘊含于底層——日常生活中的社會史意義,貢獻了漫畫作者自己的觀念。”作者另有《論“社會時間”——依托于豐子愷筆下的村婦考察》(載《河北學刊》2007年第2期)、《豐子愷作品的社會史考察》(載《民族藝術》2009年第1期)與《兒童生活之往昔:豐子愷作品之社會史考察》(載《史學月刊》2006年第10期)等論文也從這一視角考察立論。
陳占彪的《葉淺予、豐子愷、張樂平漫畫中的上海社會》(載《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從文化研究的視角對豐子愷漫畫所體現的“鄉野與都市”之間的矛盾進行了深入分析。陳偉的《都市表情的真實寫照——從都市文化的角度看豐子愷漫畫》(載《文藝理論研究》2009年第6期)立足于藝術創作與都市文化的關系,探究了豐氏漫畫形成的現實基礎與歷史淵源,并進一步思考了這一現象的文化價值及其當代意義。王先霈的《豐子愷〈護生畫集〉對現代生態文藝學的啟示》(載《河南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從生態文藝學的角度考察了豐子愷“向心靈呼吁”的“護生”對于現代生態文藝學的重要啟示。作者認為豐子愷“護生即是護心”的說法,從人與自然歸于一心的角度探討生態問題,擺脫了“人類中心主義和生態中心主義之間徘徊彳亍的困局”。龍瑜宬的《豐子愷與“漫畫”概念》(載《清華大學學報》2012年第3期)在跨文化研究的視閾下,分析了豐子愷漫畫由“正宗”到“異類”的過程。該文認為,豐子愷充分發揮了主體性精神,“在當時過分逼仄的接受語境中,靈活挪用西方資源,為中國文化爭取必要的生存空間,仍然不失為一種有效的策略”。鄭素華的《作為“異世界”的兒童:豐子愷的童年民族志書寫》(載《湖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報》2013第5期)運用文化人類學關于民族志的理論來解讀豐子愷的“兒童相”。該文從“兒童活動的行為與心理層面的‘深描’”“童年‘生活相’的廣泛呈現”以及“童年民族志的社會批判”三個層面認為豐子愷“既融合了盧梭式的自然主義的、浪漫主義的兒童觀,又兼有‘作為文化批評的人類學’的書寫特質,建立了一種具有現實主義取向的童年民族志描述之典型”。唐衛萍的《“印象派”與“詩”:論豐子愷的繪畫思想》(收入杭州師范大學弘豐中心編的《第三屆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認為豐子愷的繪畫創作及理論打破了文與畫的藩籬,從以“印象派”為代表的西洋畫之視角重新詮釋了中國古典詩。作者最后指出:“通過‘詩’這一通道,他重新闡釋了中國的繪畫傳統,而通過‘印象派’,他又抓住了世界藝術發展的潮流。而他本人的繪畫創作也在東西方繪畫目光的交錯中,獲得了一席之地。”
除了以上兩個方面外,在漫畫研究領域還需要提到的是關于豐子愷畫史地位的重新認定、漫畫作品的分析與鑒賞等。畢克官、黃遠林早在1986年寫的《中國漫畫史》(文化藝術出版社1986年初版)第四章第三節中就認為豐子愷“不僅以《子愷漫畫》統一了中國的漫畫名稱,也是抒情漫畫這一畫派的開創者”(第76頁)。新世紀以來的研究對豐子愷的畫史地位都作出了極高的評價,且大都認為其漫畫類型屬于“抒情漫畫”。如甘險峰的《中國漫畫史》(山東畫報出版社2008年初版)第三章第三節的標題就是“抒情漫畫大師豐子愷”,并認為:“在中國漫畫發展史上,應當說豐子愷是影響最大的漫畫家之一。他雖然在漫畫舞臺上出場稍晚,但他一出現就憑著自己扎實的文學功底和獨到的藝術靈感異軍突起,一躍成為漫畫界巨擘,贏得了同時代人及后人的稱贊。”(第82頁)余連祥的《豐子愷:中國“感想漫畫”的開拓者》(載《藝術百家》2006年第2期)也持類似的意見,該文就豐子愷與中國漫畫史的問題展開討論,認為雖然早在1904年現代意義上的“漫畫”就已出現,但統一中國的漫畫名稱的還是“子愷漫畫”。但作者對于“抒情漫畫”的類型歸屬表達了不同看法,他在借鑒豐子愷關于感想漫畫、諷刺漫畫、宣傳漫畫的三種分類法的基礎上,指出豐子愷最具特色的漫畫稱之為“感想漫畫”比“抒情漫畫”更恰當。蕭平的《豐子愷先生的畫史位置》(載江蘇省美學學會編的《城市文化與藝術審美》2008年10月)一文指出,豐子愷開創了一種“中國文人畫的新模式”,其中有著“高雅悲憫的心跡”“人性和禪機”以及“文學與哲學的情和趣”。趙威的《畫中有話,藝中有意——從〈太平洋報〉探析陳師曾與豐子愷漫畫之間的傳承關系》(載《美與時代》2015年第8期)以《太平洋報》中陳師曾的漫畫為研究依據,從構圖和筆觸、留白和邊框、題材與人物、詩意和標題等方面探討了陳氏對豐子愷的多重影響,梳理出了“子愷漫畫”的師承脈絡。
在漫畫作品的分析與鑒賞方面寫得較好的論文有徐型的《豐子愷漫畫的文學意蘊》(載《南通大學學報》2007年第1期),該文分析了抒情性、寫實性和畫題在豐子愷漫畫中的重要作用。王峰的《“子愷漫畫”之“漫”——論豐子愷漫畫與文學創作的精神關聯》(載《時代文學》2012年第4期)通過對豐子愷文學態度和文學主張的研究,體會其漫畫語言的獨特內涵與精神追求,總結了豐子愷漫畫所體現的文學性有如下特點:寫真現實,情意深廣;文圖呼應,古調新韻;綿里藏針,金剛怒目;沖淡簡遠,盡得風流。朱顯因的《朱實相輝玉椀紅——豐子愷的韓偓詩意畫》(收入杭州師范大學弘豐中心編的《第三屆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討論了豐子愷為高文顯《韓偓》一書所作詩意畫的創作緣起與藝術價值。
值得一提的是畫文相映的鑒賞性著述。較早采用這種形式的是明川(盧瑋鑾)的《豐子愷漫畫選繹》(香港三聯書店1976年初版),近20年來這種著述形式也廣為學者們熱衷。葛兆光的《豐子愷護生畫集選》(中華書局1999年初版)從《護生畫集》中選擇了100幅畫,配上簡短的評語。葛氏在后記中稱:“我欽敬這些懷著慈悲胸懷和平靜心情面對世界的人,看著世間種種殘酷、暴虐、無情和奸詐,就有這樣的人,會默默地用另一種人生來顯示著世間的善良、和睦和坦誠,無論他們成功與否,他們使我們看到了世界還有希望。”(第233頁)類似的著作還有陳星與朱曉江編著的《幾人相憶在江樓——豐子愷的抒情漫畫》(山東畫報出版社1998年初版)、蘇學文的《豐子愷漫畫品讀》(江蘇教育出版社1999年初版)、陳星的《都會之春——豐子愷的詩意漫畫》(三聯書店2003年初版)、丁秀娟的《豐子愷護生畫新傳》(東華大學出版社2005年初版)等,都是一畫一文的方式編寫。豐陳寶、豐一吟的《爸爸的畫》共四集由華東師范大學出版,其中第一、二集于1999年出版,第三、四集于2001年出版。由豐子愷女兒們敘述繪畫背后的故事,自然更值得重視。
最后談一下關于裝幀、木刻與書法的研究。畢克官早在1982年的《美術史論》第2期發表的《朱光潛談畫——關于〈子愷漫畫〉的兩次談話》一文中就提到過豐子愷的木刻藝術。作者在1993年的《美術史論》第4期又發表了《現代木刻版畫的先行者——李叔同和豐子愷》,著重討論了李叔同與豐子愷在中國現代木刻版畫領域的貢獻。他的另一篇論文《關于拓展豐子愷研究領域的思考》(收入《論豐子愷:2005年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香港天馬出版有限公司2005年初版)從封面裝幀、書刊版面裝幀、書文插圖和木刻漫畫四個方面談到拓寬豐子愷研究的重要性。在畢克官的研究和提倡下,這些領域都產生了一些成果。陳星的《關于豐子愷的木刻漫畫》(載《杭州師范學院學報》2004年第1期)針對豐氏木刻漫畫的定位問題提出兩種考察角度:其一,如果將此類畫孤立起來看,可以視之為木刻,并可將豐氏視為中國現代木刻較早的實踐者;其二,將“木刻”只是當作漫畫的一種表現形式。該文同時認為,從第二種角度的考察,“符合豐子愷本人的實際”。在裝幀的領域要比木刻討論得更為廣泛,吳浩然編選的《豐子愷裝幀藝術選》(齊魯書社2010年初版)擇錄了豐子愷各個時期為各類書籍、報紙、雜志設計的封面、扉頁、插圖、刊頭畫等共52幅,并在前言《獨領風騷的豐子愷裝幀藝術》中高度評價了豐子愷裝幀藝術的特點。王雙、李昌菊的《解析豐子愷書籍裝幀藝術中的日本趣味》(載《美術向導》2012年第3期)探究了竹久夢二、比亞茲萊、蕗谷虹兒等外國藝術家對豐子愷書籍裝幀藝術的影響,分析了豐氏裝飾趣味的形成原因。吳東辰的《豐子愷與圖書裝幀》(載《圖書館建設》2001年第5期)認為豐子愷的裝幀設計之所以有其獨特的風格原因在于如下四點:一是簡單而生動的漫畫特征;二是詩的意境;三是熟練的書法篆刻功底;四是音樂制作手法的借鑒,這四者使得豐氏的圖書裝幀自然淡雅而獨樹一幟。牟健的《堅守與探索——豐子愷書籍裝幀藝術風格》(載《臺州學院學報》2014年第8期)認為豐子愷的書籍裝幀具有濃厚的人文氣息,尤其體現出“仁”“詩意”與“童真”的特點。但總體上說,關于豐子愷裝幀藝術的論文多著眼于介紹性的內容,或對其書籍裝幀的特點進行泛泛的梳理,而沒有進行更為深入的研究。
在書法研究領域也有一些成果。謝凌云的《民國時期廣西書法教育研究》(廣西師范大學2012年碩士論文)列舉了徐悲鴻、豐子愷、馬萬里等八位代表書法家,其中評價豐氏的書法藝術極為精要,可惜由于主題的關系,所評只是點到即止,沒有展開論述。豐子愷留下的書法作品并不少,并在《藝術修養基礎》第十一章中專門討論過書法,但對于豐子愷書法的研究卻極為貧困。在這些少數的論文中寫得較好的一篇是崔樹強的《蘊藉有味 風神瀟灑——讀豐子愷先生的書法》(載《書法》2013年第3期),該文分別從豐子愷書法的特點、書藝的師承、書法的觀念以及書法史的認識逐一進行評論,文筆優美,邏輯清晰。正如作者所說的,“豐子愷的書法所受到的關注較少,他的書名多被漫畫的盛名所掩。實際上,豐子愷的書法是很有特色的,別具一格,可謂是風神瀟灑,蘊藉有味”,我們期待今后有更多更深入的豐子愷書法研究論文出現。
二、文學研究
豐子愷的文學成就主要是散文,另有4部童話(其中1部為《兒童文學集外文》)、1部短篇小說《六千元》與175首詩詞。朱曉江的《豐子愷散文研究述評》一文(以下簡稱“朱文”)對于豐子愷的散文研究成果的介紹頗為詳備,該文分為“關于豐子愷散文中的佛教思想”“關于豐子愷散文的藝術風格”“關于豐子愷散文的史料整理”“關于《緣緣堂續筆》的研究”以及“豐子愷散文研究中的其他問題”五個部分。“其他問題”中包括了豐子愷兒童題材的散文,豐子愷散文與傳統文化之間的關系,豐子愷與周作人、朱自清、夏目漱石等中日現代作家的關系以及豐子愷散文與現代性之間的關系等議題,大致涉及了豐子愷散文研究中的各個方面。在此筆者只對朱文疏于介紹的部分內容做一些補充。
其一,關于《緣緣堂續筆》的研究。朱文認為:“《緣緣堂續筆》之所以能在豐子愷眾多的散文中成為一大研究熱點,除了它本身的藝術特色及寫作過程中的傳奇色彩,原因還在于20世紀90年代學界對中國當代文學中‘潛在寫作’的發掘。”這一評價基本符合文學史事實,尤其是在陳思和發表《試論當代文學史(1949—1976)的“潛在寫作”》(載《文學評論》1999年第6期)以及寫作《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復旦大學出版社1999年初版)以后,這部隨筆集受到廣泛的重視。陳著當代文學史為《緣緣堂續筆》專辟一節(第九章第二節“老作家的秘密寫作:《緣緣堂續筆》”),并對豐子愷在“文革”期間所體現的“達觀與知命”之境界作出了高度的評價,改變了之前的當代文學史著作對豐子愷于新中國成立后散文一筆帶過的做法。
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在陳思和以前,早已有人專門探討過《緣緣堂隨筆》。韋俊識的《散文天幕的一顆亮星——讀豐子愷〈緣緣堂續筆〉隨想》(載《浙江師范大學學報》1989年第4期)以“隨想”的筆調高度評價了《緣緣堂續筆》的藝術精神,陳星的《清涼世界——豐子愷藝術研究》第三章第一節“散文小品”也用了一定的篇幅討論《緣緣堂續筆》。近20年來最早發表相關論文的是徐型的《論豐子愷的〈緣緣堂續筆〉》(載《佳木斯師專學報》1997年第4期),該文認為正是由于豐子愷對往事的回憶、對傳統的依戀,才使他“暫時脫離塵世”。隨著中國當代文學界關于“潛在寫作”主題的深入討論,《緣緣堂續筆》受到高度關注。景秀明的《建國初浙江散文:在坎坷中行進》(載《浙江師范大學學報》2000年第5期)認為《緣緣堂續筆》“代表了豐子愷在解放后散文創作的最高水平”。章龍福的《自然和易 真淳雋永——豐子愷散文風格簡論》(載《青島大學師范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認為《緣緣堂續筆》是豐子愷“生命最終凝成的心血”。黃發有的《月黑燈彌皎 風狂草自香——當代視野中的豐子愷》(載《當代作家評論》2000年第3期)一文將豐子愷定義為當代文學中的“失蹤者”,認為《緣緣堂續筆》是豐氏“淺醉閑眠”的方式,贊揚了豐子愷在艱難歷史時期通過頑強的堅守保持著自己人格的獨立與人性的關懷。
需要提及的是周仲強的《藝術審美的嬗變表征——讀豐子愷〈緣緣堂續筆〉》(載《小說評論》2010年第2期),該文認為《續筆》中有多篇文章揭示社會的黑暗,解剖人性的丑陋,“昭示豐子愷‘護生’的意識結束,‘殺生’意識彰顯”,并談到晚年的豐子愷“價值取向已偏向于向人表述人性的丑惡,已失去緣緣堂時期淳樸、自然、平和的藝術審美情趣”。這一判斷顯然與陳思和等的理解大為不同,不妨亦聊備一說。
其二,關于兒童題材散文及兒童文學的研究。朱文提到但無暇述及這一主題,筆者在此做一些簡述。在80年代就已有論者專門探討過豐子愷的這一成就,如周小波的《豐子愷與中國現代兒童文學》(載《浙江師范學院學報》1984年第4期)、陳星的《談豐子愷與兒童文學》(載《杭州師院學報》1987年第2期)等。最近20年來,隨著兒童文學學科的發展,加上浙江師范大學兒童研究院的推動,豐子愷關于兒童題材的散文及兒童文學創作更成為論者們討論的重點,主要可以分為兩個方面的內容。第一是探討豐子愷與兒童文學的關系。陳星的《談豐子愷與兒童文學》一文已經明確提出:“豐子愷早年散文中有一些贊美兒童、熱愛兒童的主題并不能說這些散文就是兒童文學。”徐型的《豐子愷的兒童文學創作》(載《南通師范學院學報》1999年第3期)繼續陳星的說法,認為兒童文學是不僅要用兒童的口吻書寫、所寫為兒童之事,同時也需專門為兒童而寫的作品。該文接著對豐子愷的《少年美術故事》《音樂故事》與《博士見鬼》三本兒童文學作品,從內容、特點、意義三個層面進行了分析,并認為:“這些作品具有緊貼兒童生活,力求做到知識的藝術化和藝術的知識化,符合兒童的年齡、智力、興趣等實際情況的特點,在中國兒童文學創作中有重要地位。”楊寧的《童心信仰與理想國的構筑——論豐子愷的童心信仰及其童話創作》(載《贛南師范學學報》2011年第5期)認為豐子愷在中國現代兒童文學史上有其獨特的意義:“他竭力表現的不是他作為成人對兒童的某種俯就或訓誡,而是他對童心世界的虔誠以及對構筑理想國的渴望。”劉建峰的《“兒童教訓”與“兒童崇拜”——葉圣陶與豐子愷的兒童觀比較及其文藝創作》(載《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10年第6期)與王炳中的《冰心與豐子愷兒童題材散文的差異性》(載《湖州師范學院學報》2012年第6期)也持類似觀點。前文認為葉圣陶從成人立場考察兒童,在創作上表現為“兒童教訓”;豐子愷則從童年視角體悟童心,在創作上表現為“兒童崇拜”。后文認為冰心是“五四”后第一個有影響的兒童文學作家,她從“大姐姐”的角度進行創作,而豐子愷是第一個站在“兒童崇拜”立場創作兒童題材散文的作家,兩者在寫作立場、敘事重點、抒情方式都有顯著的差異。第二是結合佛學思想與兒童美育觀探討豐子愷兒童題材的散文創作。王宜青的《豐子愷兒童觀探微》(載《浙江師范大學學報》1999年第4期)依據豐子愷的散文、漫畫與藝術理論,從儒道“童心說”的傳承、佛家“護生觀”的演變以及豐氏本人審美趣味的特征,剖析其兒童觀的多層含義。王泉根、王蕾的《佛心·童心·詩心——豐子愷現代散文新論》(載《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1年第4期)認為佛心、童心、詩心構成了豐子愷藝術追求上的統一。李松的《童心與佛理契合的世界》(載《廣西師院學報》2001年第3期)移用馮友蘭的《人生的境界》中的術語而作了新的解釋:“質樸無華的童心是豐子愷追求的自然境界,仁愛超脫的佛理則是他景仰的天地境界。豐子愷的審美理想就表現為童心與佛理的契合。”王黎君的《佛光隱隱蘊童心——試論豐子愷兒童題材創作的藝術特色》(載《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3年第4期)認為在佛性與童心的牽引下,豐子愷的散文與漫畫在題材選擇、審美觀、審美風格以及創作手法上都表現出了獨特的價值取向與藝術追求。
其三,關于詩歌的研究。朱文的主題是散文研究,詩歌研究也就付之闕如,在這里筆者略作陳述。詩在豐子愷的創作生涯中有著相當重要的位置,豐華瞻在《豐子愷與詩詞》《父親豐子愷對詩詞的愛好》等文章中就一再強調詩與豐子愷其他文藝創作之間的重要聯系。在近20年中,對于豐子愷漫畫中的詩意探討已非常詳盡,而對豐子愷的詩詞創作及其詩學思想的研究則頗為寂寥,只有少數幾篇論文。向諍、涂小馬的《豐子愷舊體詩詞創作探論》(載《蘇州大學學報》2001年第4期)梳理了豐子愷不同時期的詩歌創作,并認為抗戰流離的8年與60年代是其創作的高峰。黃濟華的《畫家豐子愷,本色乃詩人——論豐子愷與詩》(收入《論豐子愷:2005年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指出了豐子愷關于詩的四個意見:詩品與人品統一;詩應該具有平凡而偉大的藝術品格;詩貴自然,宜少用古典;詩應講究格律。作為豐子愷的學生,潘文彥的《讀豐師遺札》(收入《論豐子愷:2005年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重讀了豐子愷寫給作者的三封談詩詞的書信,回憶了兩人之間的詩詞往來。陳星早在1996年就曾講豐子愷的詩詞研究“還是很不夠的”,并說:“這也是豐子愷研究領域中很可有作為的一塊處女地。”(見所著《清涼世界——豐子愷藝術研究》,第195頁)20多年過去了,這一領域依然大有可為。
三、藝術思想研究
豐子愷不但是一位杰出的畫家、散文家,而且在藝術思想上成就卓著。他是中國現代少有的一邊進行大量創作、一邊又進行理論探索的藝術家。但90年代以前,對于豐子愷的藝術思想探討得很少,近20年以來相關的研究才逐漸增多。下面筆者從豐子愷的藝術思想及其淵源的探討與藝術教育(美育)思想的研究兩個方面進行介紹。
其一是關于藝術思想及其淵源的探討。朱曉江從世紀之初就開始關注豐子愷的藝術觀與科學觀問題,他的《對主體性失落的警惕——豐子愷的藝術觀與科學觀》(載《杭州師范學院學報》2001年第3期)詳細辨析了豐子愷關于科學與藝術的討論,認為在西方科學理性的思想進入中國并漸成強勢之時,豐氏強調藝術有別于科學的獨立價值,事實正是在維護人作為主體的獨立和自由。他的《有意味的遺忘:對科學思維的拒斥——豐子愷“中國美術優勝論”解析》(載《華東師范大學學報》2002年第5期)中對此做了進一步的探究,并認為豐子愷:“刻意‘遺忘’了印象派以后西洋美術的科學主義特性,而竭力張揚了它的‘表現主義’傾向。”他的另一篇論文《傳統的回歸:從西洋美術轉向“漫畫”——1922年前后豐子愷藝術思想的轉折及其思想史背景》(載《美術研究》2006年第3期)結合20世紀20年代中國思想界背景與豐子愷日本留學的經歷,深入分析了1922年前后豐氏由西方美術轉向中國藝術傳統的前因后果。作者還有《豐子愷“絕緣說”解讀》(收入《論豐子愷:2005年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與《豐子愷“同情說”解讀》(載《杭州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1期),二文認為豐氏藝術思想大體以抗戰為界,從1937年前以道家思想為底蘊的“絕緣說”轉向1937年后以儒家藝術思想為基礎的“同情說”。朱曉江另有專著《一道消逝的風景——豐子愷藝術思想研究》(西泠印社出版社2001年初版)與《有情世界——豐子愷藝術思想解讀》(北岳文藝出版社2006年初版)二書,陳星的《近三十余年豐子愷研究與紀念活動綜述》有介紹,不再贅述。
王黎君的《從佛境眺望人生——許地山豐子愷創作審美特征比較》(載《紹興文理學院學報》2001年第4期)將豐子愷與同樣深受佛教思想浸染的作家許地山相對照,闡述了兩者對于佛教不同的理解方式。金妮婭通過《亦僧亦俗話人生——試論儒佛融通的人生觀對豐子愷文藝創作的影響》(載《浙江師范大學學報》2003年第1期)、《走在夢與真的邊緣——試論豐子愷儒佛互融的生命感悟及其文藝創作》(載《臺州學院學報》2004年第5期)及《絕緣而有情 曲高而和眾——試論豐子愷儒佛融通文藝觀之特質》(載《山東文學》2006年第9期)三篇文章論述了豐子愷思想上體現的儒佛兼備的文化特性,指出這一特性使豐氏時時矛盾而又高度統一。余連祥的《豐子愷的審美世界》(學林出版社2005年初版)圍繞豐子愷的“審美世界”展開論述,依次探討了豐子愷的“美學思想”與“審美教育”、《緣緣堂隨筆》的“審美價值”、子愷漫畫的“審美情趣”以及其他藝術領域的“審美實踐”等,最后分析形成其“審美個性”的成因。蔣霞、楊曉河的《豐子愷“三層樓”人生境界的審美蘊涵及當代價值》(載《藝術百家》2012年第1期)認為在豐子愷關于現實、藝術與宗教的“三層樓”譬喻中,現實層既是基礎,又是旨歸;藝術層兼備樞紐與本體的雙重身份;宗教層則是最高境界。該文分別討論了藝術與現實、藝術與宗教的關系,認為豐氏在當時社會普遍倡導“科學救國”“道德救國”“實業救國”“宗教救國”的大潮下,能夠堅持自己的藝術救國之路,“它的重要性受到時代的忽視在所難免,但對今天而言卻是預言般的神啟”。王偉的《“儒釋互補”:豐子愷的藝術審美理論》(載《當代文壇》2012年第2期)認為豐子愷在“儒釋互補”的藝術思想基礎上吸收轉化康德等人的西方美學思想,對20世紀中國美學發展具有重要意義。李春堯的《論豐子愷的護生思想》(載《科學·經濟·社會》2014年第1期)認為“護生即護心”是豐子愷護生思想的主旨和中心,這一觀點體現了佛學與儒學思想的結合,“立足于佛教又不拘泥于佛教,融匯了儒學又超越了儒學,訴諸于童心更深化了童心”。該文還就豐子愷護生思想的現實意義做了進一步說明:其一,它將佛教因果倫理暫擱一邊而把護生的意義歸之于一心,這對于在現代發揚佛教倫理有積極意義;其二,守護自然就是守護心靈,從而解決了生態主義與人類中心主義之間的矛盾與悖論。文章思路清晰,見解精辟,值得贊賞。
在眾多的論文中,也有較為“嚴苛”的批評。郭戰濤的《佛教視野下豐子愷的酒肉觀與護生觀》(載《溫州大學學報》2015年第2期)從佛教視野下批判了豐子愷寬松的護生觀和不能精嚴持戒的行為,指出豐氏護生言行有偏差可以歸結為一個原因,即在修持方面不能做到精嚴,并惋惜“若從佛教徒的慈悲精神層面來看,這未嘗不是一種缺憾”。事實上,豐氏在“三層樓”的比喻中就已清楚地表達了自己與弘一大師的差距,認為自己始終未真正居住在第三層宗教的高樓上,但卻時時勉勵自己,向三層上望一望,這就表明了其對于自己人生觀的正確定位。豐氏只是在佛教的終極關懷中找到了與自身知識分子追求的相似點,并不是嚴格意義上的佛教徒,因此在持戒等事情上并不苛責自己。
以上所舉大多是談豐子愷的藝術思想及其傳統淵源,其實他的藝術思想還明顯受到西方美學的影響,但深入探討的論文相對較少。黎萌的《論豐子愷早期的“同情說”——兼與閔斯特伯格的認知主義美學相比較》(載《西南大學學報》2013年第3期)從以下三個層面討論了豐子愷的“同情說”:其一,豐子愷“同情說”的主要來源并非立普斯(Theodor Lipps),而是同屬新康德主義陣營的弗賴堡學派思想家閔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這與受馬堡學派影響的朱光潛有很大區別;其二,“同情說”是豐子愷的整體性學說,“絕緣說”“童心說”等都隸屬于它;其三,“同情說”在豐子愷各個時期各有側重,現實環境的轉變使“同情說”的外延不斷擴大,最終超越了“審美”概念而進入到了“道德”的層面。蕭湛的《論豐子愷審美理論之“以仁為本”——兼與宗白華、朱光潛比較》(收入陳星主編的《豐子愷藝術與藝術教育研究》)論述了豐子愷在“主觀派”美學(宗白華)與“客觀派”美學(朱光潛)之間的徘徊,既體現出兩種范式各自的優長,也呈現了兩者間難以調和的矛盾。該文廣泛采引叔本華、舍勒、柏格森、謝林、克羅齊等西方美學家的思想,詮釋了豐子愷“以仁為本”的審美理論之多種面向。潘建偉的《論豐子愷的詩畫關系觀》(載《美育學刊》2016年第5期)從豐子愷對詩畫關系的討論入手,論述中國詩在感情移入、理想表現、言簡意繁三個層面對其繪畫創作的影響,并認為豐子愷如此重視詩之于畫的意義很可能受到過萊辛《拉奧孔》的影響。
其二是豐子愷的藝術教育(美育)思想的研究。邱春林的《豐子愷早年的“藝術教育思想”與蔡元培美育觀之比較》(載《南京藝術學院學報》2002年第3期)探討了豐子愷藝術教育思想與蔡元培美育觀的異同,認為豐氏繼承了蔡元培“以美育代宗教”的思想,而又有所差異:蔡元培把美育作為變革社會的工具,豐氏則更為強調藝術與人生的密切聯系,認為藝術教育能“視作苦悶人生的解放之途”。尚麗莉、李樹玲的《豐子愷藝術教育思想的特質與啟迪》(載《成都大學學報》2007年第3期)詳細闡釋了豐子愷藝術教育的宗旨、原則、條件和方法,認為豐氏開拓了美育的新視閾,豐富了中國現代美育思想的內涵。張昕的《論豐子愷“以人為本”的藝術教育思想》(載《藝術百家》2009年第5期)認為豐氏藝術教育思想不管是宗旨、原則還是方法、途徑,都緊緊圍繞著人這一主題。蔣霞、楊曉河的《從“入門之道”與“純正之學”走向審美的人生:豐子愷藝術教育論》(載《內蒙古師范大學學報》2014年第4期)從“入門之道”“純正之學”“審美人生”三個維度詮釋了豐子愷的藝術教育體系。王夢雅的《“另一種啟蒙”——從〈一般〉雜志看豐子愷的美育主張與美育思想》(收入杭州師范大學弘豐中心編的《第三屆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通過解析豐子愷為《一般》雜志所撰寫文章,論述其如何突破“唯科學主義”羈絆,繼承和發展蔡元培的“以美育代宗教”之理念,借助“感性啟蒙”而最終建立實現國民信仰之再造的審美理想。五四新文化運動以來,占主導的始終是理性啟蒙,感性啟蒙一直處于附屬位置,該文用“另一種啟蒙”來概括豐子愷的美育思想,有助于加深我們對于啟蒙概念的理解。
豐子愷關于分門藝術形式的見解亦頗為獨到,對其繪畫思想的研究成果可見本文第一部分“美術研究”所述。下面簡述對其音樂思想的研究狀況。
伍雍宜主編的《中國近現代學校音樂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一章第一節中有“豐子愷的音樂教育思想”一欄,對豐子愷音樂教育思想作了較為全面的梳理。陳凈野的《豐子愷與中國現代的音樂教育》(團結出版社2012年初版)既全面梳理了豐子愷從“五四”以來的音樂教育實績,又深入解讀了他的音樂教育思想體系,有論者認為:“該書較為真實地反映了豐子愷音樂教育的實績,并就其音樂教育思想作了概括,闡明了其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是一本音樂教育史論方面的力作。”(徐承:《〈豐子愷與中國現代的音樂教育〉簡評》,載《美育學刊》2013年第5期)劉建東的《豐子愷的音樂功能觀》(載《嘉興學院學報》2010年第2期)認為可以1937年為界將豐子愷關于音樂功能的思想發展分為兩個階段,前期為純粹的音樂審美功能觀念占主導,強調音樂的獨立自足性,解除音樂與世間一切關系而保持“絕緣”的品質;后期則對此進行了修正,認為音樂應以“仁”為本,強調了音樂對現實與人生的作用,體現了儒家藝術精神。作者另有《論豐子愷的音樂美學思想》(載《天津音樂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一文,分別從音樂獨立自足本質的理解、音樂與情感的表達、音樂的欣賞、音樂的功能以及音樂的審美教育五個層面概括了豐氏音樂美學思想。該文同時指出目前學界對于豐氏音樂思想方面的貢獻重視不夠,研究不足。
四、生平與作品考證及其他
1998年是豐子愷100周年誕辰,在各地紀念活動陸續開展之際,出現了許多的緬懷、回憶及生平作品考證的文章。周穎南的《豐子愷與周穎南的通信》(載《新文學史料》1998年第4期)公布了自己與豐子愷從1972年12月3日至1975年5月20日之間共有34封往來書信,信中所談內容非常廣泛,既有兩人關于藝術與佛學問題的探討交流,有在艱難歲月朋友間的相互關懷,還透露了與同時代人物的交游信息。這些書信不但見證了兩人之間真摯的友誼,而且提供了不少藝術史、佛學史的資料。文楚的《“日月樓”訪豐子愷》(載《世紀》1998年第4期)回憶了自己于1962年拜訪居住在“日月樓”的豐子愷,向讀者呈現了一個溫潤爾雅、風趣睿智的藝術家形象。郭若愚的《豐子愷漫畫中的兒女們》(載《世紀》1998年第4期)考證了豐子愷29幅漫畫的兒女形象及創作時間。韋人慶的《記豐子愷抗日時期在宜山、環江、河池的生活片段》(載《廣西廣播電視大學學報》1998年第2期)探訪了豐子愷在宜山、環江、河池三地時的生活場所,走訪了還健在的當地知情人,為了解豐氏抗日時期的生活情景與思想狀態增添了細致入微的內容。
值得一提的是豐一吟為紀念其父所作的努力。豐一吟于1982年就曾與潘文彥等6人合著過《豐子愷傳》(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初版),1998年又出版了《瀟灑風神——我的父親豐子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初版,后由團結出版社于2007年重新出版,改名為《我的父親豐子愷》),這部書被陳星認為是“可信賴的傳記”(見所著《豐子愷評傳》,第421頁)。應中央文史館和上海市文史館的《世紀》雜志之邀,豐一吟先前將《瀟灑風神》的主要內容壓縮成《人生短,藝術長——我父親豐子愷的藝術軌跡》(載《世紀》1998年第4期)一文,簡要記述了豐子愷人生與藝術的重要階段,并配有多張珍貴的老照片。此后,豐一吟另有《我和爸爸豐子愷》(百花文藝出版社2008年初版,后由中國青年出版社于2014年重新出版,改名為《爸爸豐子愷》),據作者自稱,該書與《瀟灑風神》可看成“姊妹篇”,寫作角度完全不一樣,可以相互補充。順便提一下著者另外的兩本文集:其一是《天于我,相當厚:豐子愷女兒的自述》(上海遠東出版社2009年初版),其二是《夢回緣緣堂:豐子愷》。前書選文55篇,其中談豐子愷的有46篇;后書收文共54篇,幾乎全為談豐子愷。可貴的是兩書所選的文章并無重復。
新世紀以來,生平與作品考證始終是豐子愷研究中一個熱門的領域。李連昌的《豐子愷在遵義》(載《文史天地》2002年第6期)考察了豐氏抗戰時期在遵義的藝術活動,介紹并高度評價了《子午山紀游冊》。方繼孝的《抗戰初期的豐子愷和他的創作》(載《收藏家》2005年第5期)提供了豐子愷抗日戰爭爆發初期為編著《冊頁》專集寫給好友鐘器先生的信三封和《自傳》二紙,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肖麗的《河南大學藏豐子愷漫畫的史料價值》(載《河南科技學院學報》2009年第2期)透露了河南大學所收藏豐子愷抗戰時期的漫畫作品有25幅,并著重介紹《嚴霜烈日皆經過,次第春風到草廬》《一間茅屋負青山,老松半間我半間》《今朝風日好,或恐有人來》《吟詩推客去》等六幅畫。王炳根的《豐子愷致新加坡的書簡》(載《書屋》2010年第3期)統計了豐子愷從1935年至1973年給廣洽法師的120多封書簡,并按年代順序,將信的主要內容分為“交往與緣分”“三年困難時期的救助”“弘一大師遺墨的出版”與“《護生畫集》的創作與出版”四個部分。李建平的《抗戰時期豐子愷、廖冰兄、葉淺予等漫畫家在桂林的藝術活動》(載《藝術探索》2014第5期)介紹了抗戰時期豐子愷等數位漫畫家在桂林的藝術創作與抗日宣傳,認為這是“桂林抗戰藝術的重要組成部分”。許慶江、董婧宸的《新見豐子愷致宋云彬信札考釋》(載《現代中文學刊》2016第3期)介紹了豐子愷于1956年到1962年前后致宋云彬的8封書信,內容涉及兩人的交游、商議紀念弘一法師以及關注錢稻孫境遇等事宜。陶小萍的《館藏豐子愷檔案簡介》(載《浙江檔案》2016年第6期)介紹了桐鄉市檔案館所藏有關豐子愷的四類材料:一是翻譯及創作的手稿,二是體現個人重要經歷的一些證書,三是反映日常生活的單據、信函,四是原來家中的一些書架等實物。許懋漢的《豐子愷〈護生畫集〉手稿失而復得》(載《檔案春秋》2016年第7期)介紹了朱南田將辛苦保存的《護生畫集》第二集獻給豐子愷以成全璧的義舉。另外,作為豐子愷長外孫的宋菲君的《“課兒”——外公豐子愷的家庭教育》(收入杭州師范大學弘豐中心編的《第三屆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以親身經歷詳細描述了豐子愷生動的家庭教育之內容與特色,回憶了他關心兒孫們的成長、留意他們的興趣以及注重因材施教的方法。
葉瑜蓀在豐子愷生平考證上做了大量工作,他的《豐子愷與開明書店》(載《出版史料》2008年第4期)梳理了豐氏與開明書店的密切關系。他的《豐子愷書簡(一)(二)(三)(四)》(載《出版史料》2012年第1至4期)選輯并注釋了豐子愷致汪馥泉、趙景深等師友的書簡。作者另有《豐子愷致汪馥泉書信年代考》(收入杭州師范大學弘豐中心編的《第三屆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一文,考證豐子愷致汪馥泉書簡的確切年代。劉晨近年對豐子愷的藝術類文獻多有關注,她的《民國期刊中的豐子愷藝術類文獻尋佚》(載《美育學刊》2013年第2期)評述了豐子愷的《圖畫教授法》《由藝術到生活》《都會藝術》《近世音樂大家》《圖書教育的效果》《藝術教育的本意》六種藝術類散佚文獻,同時列舉了《春暉》《民國日報·藝術評論》《教育雜志》《小說月報》等期刊中的文獻目錄。作者另在《豐子愷藝術類著作的版本流變考述》(載《美育學刊》2014年第6期)一文中梳理了豐子愷的《音樂入門》《西洋美術史》《藝術教育》等藝術理論、藝術雜著類圖書的版本信息。
豐子愷生平史料方面的研究還有如下一些論著需要提及。陳星的《清空朗月——李叔同與豐子愷交往實錄》(百花洲文藝出版社1997年初版)以史家的筆調記錄了李叔同與豐子愷的交往過程,該書除引言與附錄外,共分三篇:上篇包括“幸會”“薪傳”與“送別”,中篇包括“重逢”“緣緣”與“護生”,下篇包括“遙念”“永懷”與“圓滿”。作者的另一部《新月如水——豐子愷師友交往實錄》(中華書局2006年初版)分為“師生情懷”“同門與同人”“交友與藝友”與“異國藝緣”四個部分,尋繹了豐子愷與師友之間的交往過程,為研究者進一步探討豐子愷與同時代人的關系提供了基礎與線索。陳星另有《豐子愷研究學術筆記》(太白文藝出版社2007年初版)與《豐子愷研究史料拾遺補論》(團結出版社2009年初版)二書,其中包含著大量豐子愷生平與作品研究的史料信息。陳凈野的《豐子愷杭州行跡考論》(杭州出版社2008年初版)按豐子愷生平的各個時期為序,詳細尋繹了他在杭州的求學、生活與創作的方方面面,稱得上繪制出了一幅“豐子愷杭州行跡圖”。張振剛的《豐子愷、章桂和“逃難”這兩個漢字》(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初版,后改書名為《和豐子愷逃難的日子:小人物章桂的時代記憶》,由浙江文藝出版社2015年重新出版)通過與曾為豐同裕染坊學徒的章桂斷斷續續的4次共計10天的彌日長談,敘寫了在大時代背景下一個小人物與藝術家豐子愷的共同經歷。
傳記與年譜是思辨研究開展之前提,又是生平考證工作之總結。近20年來關于豐子愷的傳記大量出現,主要有鐘桂松的《豐子愷的青少年時代》(花城出版社1998年初版)、黃江平的《文苑丹青一代師——豐子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初版)、徐國源的《豐子愷傳》(團結出版社1999年初版)、鄭彭年的《漫畫大師豐子愷》(新華出版社2001年初版)、劉英的《豐子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初版,之后又在此書上配上了一些圖像而成《豐子愷圖傳》一書,由同一出版社2005年出版)、盛興軍與盛希希合著的《豐子愷畫傳》(青島出版社2010年初版)及梁晴的《豐子愷》(中國青年出版社2012年初版)等。
這里需要提及的是以下三部傳記。陳星曾出版過《人間情味——豐子愷傳》(北岳文藝出版社1991年初版),采用小說的形式,虛構了很多情節對話,是一部文學傳記,并非嚴格意義上的學術著作。故而作者重起爐灶,另寫了一部《豐子愷新傳》(北岳文藝出版社1998年初版),在“內容豐富”與“形式活潑”的基礎上確保傳記的“紀實”特征。吳浩然的《緣緣人生——豐子愷畫傳》(齊魯書社2008年初版)中的繪畫與文字,都是作者本人所作。繪畫清新,文字簡練,圖文并茂,別具一格。陳野的《緣緣堂主——豐子愷》(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初版),收入由萬斌主編的“浙江文化名人傳記叢書”,陳星在《近三十余年豐子愷研究與紀念活動綜述》中予以較高的評價。
關于豐子愷年譜主要有三部:其一為盛興軍的《豐子愷年譜》(青島出版社2005年初版),其二為陳星的《豐子愷年譜》(西泠印社2001年初版),其三為陳星的《豐子愷年譜長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11月初版,2017年1月修訂版)。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豐子愷年譜長編》,該書在全面研究豐子愷的思想、藝術以及其所在社會背景、文化藝術思潮基礎上,通過浩瀚的文獻甄別、考證,最大限度地反映了豐子愷的生平事跡,是著者30多年來研究豐子愷的一個總結。杭之認為該著在史料的占有與考訂、史料的剪裁以及體例的編制上都有重要貢獻(杭之:《評〈豐子愷年譜長編〉》,載《美育學刊》2015年第4期)。吳明則說該書稱得上是一部“豐子愷文化志”,“是對豐子愷的一種立體式、全方位的文化深描”(吳明:《“豐子愷文化志”:立體式工筆深描——評陳星〈豐子愷年譜長編〉》,載《中國藝術報》2015年7月22日第008版)。
生平與作品考證的研究已如上述,下面附帶介紹一下關于豐子愷翻譯作品的研究。
豐子愷的翻譯作品不僅數量豐富,而且品質精上。王向遠的《二十世紀中國的日本翻譯文學史》(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01年初版)比較了豐子愷與林文月各自翻譯的《源氏物語》后認為:“兩種的譯文風格各具千秋:豐譯本多用《紅樓夢》那樣的古代白話小說的詞匯句法,典雅簡介,華美流利;林譯本則使用標準的現代漢語,將現代漢語的書面語與日常口語很好地結合起來,通俗而不流俗,清新而又親切。”(第396頁)余連祥的《魯迅·豐子愷·〈苦悶的象征〉》(載《魯迅研究月刊》2005年第4期)比較了魯迅與豐子愷各自翻譯《苦悶的象征》的特點,并認為由于兩人的翻譯,廚川白村的這部作品逐漸在中國現代文學中形成了一個“苦悶的話語空間”,影響深遠。中國留學生徐迎春赴日本九州大學攻讀博士學位,于2010年完成學位論文《平安朝物語の中國語訳に関する研究—先驅者としての豐子愷の訳業について—》,2015年由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出版,中文書名為《豐子愷譯日本古典文學翻譯研究》,正文文字仍為日語。該書探討了豐子愷翻譯的《源氏物語》《伊勢物語》《竹取物語》以及《落窪物語》四部日本古典文學作品,評述了豐氏的翻譯特點。徐迎春另有漢語論文《豐子愷譯〈伊勢物語〉的版本考證》(載《日語學習與研究》2014年第4期)探究了豐子愷譯的《伊勢物語》與最為常見的日本天福本《伊勢物語》原文在內容與結構上產生較大差異的原因,指出豐子愷所用的版本是中河與一的現代日語譯本。姚繼中于2014年做了日本山口大學東亞研究科“客員教員”研究報告《『源氏物語』に関する翻訳検証研究の必要性—豊子愷、林文月、姚継中の翻訳した『源氏物語』和歌を例として—(〈源氏物語〉翻譯驗證研究的必要性:以豐子愷、林文月、姚繼中翻譯〈源氏物語〉和歌為例)》*本文在介紹日語文獻時,統一在書名號內用括號加注中譯名。。該文經作者整理后以題為《論〈源氏物語〉翻譯驗證研究——以紫式部原創和歌翻譯為例》的漢語論文載于《外國語文》2015年第1期。誠如姚繼中所言,由于種種現實因素,研究者們“難以潛心進行雙語對比論證,往往以淺嘗輒止的膚淺評論審視翻譯作品”,故而總體上說,對于豐子愷翻譯作品的研究還遠遠不夠。
五、港臺及國外的研究
香港地區的豐子愷研究說不上很豐富,但一直保持著平穩的發展。洪長泰(Chang-Tai Hung)早在1990年就發表過"War and Peace in Feng Zikai′s Wartime Cartoons"(《豐子愷戰時漫畫中的戰爭與和平》)載于ModernChina(《現代中國》)1990年1月第16卷第1期。之后又寫了關于澳大利亞學者白杰明(Geremie R. Barmé)的專著AnArtisticExile:ALifeofFengZikai(1898-1975)的英文書評,刊于ChineseLiterature:Essays,Articles,Reviews(《中國文學:隨筆、論文與書評》)2004年12月這一期。在文章中,作者對該書作出了高度評價:“作者精要地為讀者們提供了社會與政治的多面性語境,他們從中能看到豐子愷藝術的發展、繁榮,到被迫轉型,然后變得黯淡,最后得到重生的全過程。”同時作者也指出該書的兩個缺點:其一是以年代與主題的雙重敘事線索使得某些內容過于重復,其二是詳于總結豐子愷漫畫與散文的成就而疏于敘述他的翻譯貢獻。香港教育學院文學及文化學系霍玉英的《豐子愷兒童漫畫與兒童圖畫書》(載《中國兒童文化》2013年第8輯)重點探討了豐子愷的連環兒童漫畫,認為豐氏用圖文互補的方式不但凝練地表現了鮮活的兒童情趣,而且具有層層遞進的故事情節,雖然豐氏沒有正式創作過“兒童圖畫書”(Children′s Picture Book),但卻“深具現代兒童圖畫書的精神”。香港地區的單篇論文還有孫立川《生死以之 義無反顧——〈護生畫集〉的成書及其宿命論》(載《香港文學》2001年6月號總第198期)、盧鋼鍇的《豐子愷的漫畫》(載《公教報》2001年2月25日總第2975號)及祁文杰的《豐子愷情味》(載《讀書好》2009年7月第22期)等。
關于臺灣地區的研究狀況,黃儀冠的《豐子愷與臺灣之因緣》一文有過介紹,這里只略作補充。賴振南的日語論文《『竹取物語』における「物語歌」中國語翻訳問題試論(試論〈竹取物語〉中的“物語和歌”翻譯問題)》(載《臺大日本語文研究》2003年第4期)認為豐子愷將日語和歌一律譯成五七言句,在精煉了文意之同時,也簡化了文意,無法較完整地呈現原文的意境。林素幸(Su-hsing Lin)于2003年完成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學位論文FengZikai′sArtandTheKaimingBookCompany:ArtForthePeopleinEarlyTwentiethCenturyChina,由陳軍翻譯為《豐子愷與開明書店——中國20世紀初的大眾藝術》(太白文藝出版社2008年初版)。該書旨在探討“豐子愷的藝術職業生涯與20世紀早期中國藝術發展”、“20世紀藝術家與出版社之間的關系,以及藝術家們如何向大眾和后代傳播自己的理念或美學思想的問題”。由于作者的海外求學背景,該書一大優點是介紹了大量的國外相關文獻,充實了豐子愷研究的資料。吳元嘉的《豐子愷童話對古典文學的繼承》(收入杭州師范大學弘豐中心編的《第三屆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從精神內涵、敘述模式、題材借鑒及典故運用四個層面,深入分析了豐子愷童話對古典文學的繼承。臺灣地區的單篇論文還有張俐雯的《“緣緣堂”的符號象征意義》(載《止善》2006年第1期)、《弘一法師影響豐子愷析論——以藝術啟蒙、人格感化與作品思想為中心》(載《止善》2009年第7期)及《豐子愷與書法》(載《慈濟通識教育學刊》2013年第8期),林素辛的《豐子愷的山水風景畫與日本浮世風景畫》(載《美術學報》2006年第1期),李崗的《豐子愷童心觀的概念分析及其于教育上之應用》(載《當代教育研究季刊》2011年第19卷第3期)與《豐子愷的美育思想》(載《課程與教學》第14卷第1期),張卉的《豐子愷與中國近現代藝術精神的締造》(載《書畫藝術學刊》2012年第13期),孫中峰的《植基于藝術教育實踐的文藝觀:豐子愷文藝思想(1919—1949)一個面向的探究》(載《高應科大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013年第10卷第2期)以及蔣勁松的《豐子愷護生思想的內在矛盾及其演變》(載《法印學報》2014年第4期)等。
國外的研究較為零散,筆者的搜集也不夠全面,但以下這些成果是必須提到的。挪威學者克里斯托弗·哈布斯邁爾(Christoph Harbsmeier,中文名又為何莫邪)于1984年出版專著TheCartoonistFengZikai:SocialRealismwithaBuddhistFace(Oslo, Bergen, Stavanger, Tromsφ: Universtitetsforlaget, 1984)。該書陸續產生兩個中譯本:其一為陳軍譯的《漫畫家豐子愷——具有佛教色彩的社會現實主義》(西泠印社出版社2001年初版),其二為張斌譯的《豐子愷——一個有菩薩心腸的現實主義者》(山東畫報出版社2005年初版)。白杰明在1989年就寫過論文“An Artist and his Epithet: Notes on Feng Zikai and the Manhua”,考證了中文“漫畫”一詞的淵源以及其在中國近現代的演變,該文后由陳軍譯為《“漫畫”之蛻變》,收入朱曉江主編的《豐子愷論》。白杰明在博士學位論文基礎上撰成專著AnArtisticExile:ALifeofFengZikai(1898-1975),于2002年由伯克利加州大學出版社出版。201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推出由賀宏亮翻譯的中譯本,書名為《藝術的逃難:豐子愷傳(1898—1975)》。美國學者柯律格(Craig Clunas)也為《藝術的逃難》寫過書評,載于TheChinaJournal(《中國期刊》)2004年1月總第51期。他認為該書擺脫了各類主流傳記的敘事模式,是“對藝術史的一個挑戰,提供了一種可能解決這類歷史的成功方式”。但作者同時也指出該書的一個瑕疵是太過專注于“豐子愷繪畫顯示出來的脫離塵世的形象”,而忽略了豐子愷在當時其實是一個暢銷書作家,書籍的銷量與藝術的價值并不一定成反比。
筆者要著重介紹的是日本的豐子愷研究。日本的豐子愷研究起步很早,成績突出。當整個豐子愷研究領域連碩士論文都難得一見時,楊曉文就于1996年完成神戶大學博士論文《豐子愷論(豐子愷論)》,后于1998年由東京東方書店出版,書名為《豐子愷研究(豐子愷研究)》。楊曉文另有漢語論文《豐子愷與曹聚仁之爭考辨》(載《杭州師范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集中于豐子愷研究中懸而未決的豐氏與曹聚仁之爭的問題,認為曹氏的《一飯之?》實際上應為《一飯之仇》,同時指出豐曹之爭的根源除性情相異外,更多的是時代觀和文藝觀的不同。
西槙偉(西槇偉)是最近20年在日本豐子愷研究領域中作出重要貢獻的學者,必須提及他的兩本專著。其一是《中國文人畫家の近代——豐子愷の西洋美術受容と日本(中國文人畫家的近代——豐子愷的西洋美術接受與日本)》(京都:思文閣出版2005年初版)。該書匯集了作者自1994年以來到2005年前探討豐子愷與日本作家、藝術家之間關系的研究成果,除前言與序章及終章外,正文共為九章,依次討論了西洋美術接受高潮時期的豐子愷、豐子愷與米勒、豐子愷與黑田重太郎、豐子愷通過梵高再發現傳統、豐子愷與竹久夢二、豐子愷與北澤樂天、豐子愷所見之西洋近代畫家、豐子愷的中國美術優位論以及中國文人的近代化等諸問題,在東亞視野中系統闡釋了豐子愷的藝術思想與日本及西洋藝術之間的關系。該書第三章“ゴツホは文人畫家か——豐子愷と黑田重太郎”(梵高是文人畫家么——豐子愷與黑田重太郎)的主要內容由作者譯成《豐子愷與凡高》一文,已收入朱曉江主編的《豐子愷論》。該文通過梳理豐子愷的《谷訶生活》與黑田重太郎的《谷訶傳》之間的關系,探討了豐子愷的凡·高形象之形成過程及原因。該書第六章“豐子愷と北澤楽天”的主要內容也由作者譯成《豐子愷與北澤樂天》,收入《論豐子愷:2005年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文中主要探討了豐子愷的漫畫在“廣羅各種社會的現狀,描摹各種問題的糾葛”等題材上受到北澤樂天的影響。作者的第二本書是《響きあうテキスト:豐子愷と漱石、ハーン(交互影響的文本:豐子愷與夏目漱石、小泉八云)》(東京:研文出版2011年初版)。該書匯集了作者自2005年到2011年前從比較文學的角度探討豐子愷與夏目漱石、小泉八云之間關系的成果,分為三大部分,共十一章。其中第一部分依次探討了豐子愷初期作品中的《法味》與夏目漱石的《初秋の一日(初秋的一日)》《門(門)》,豐子愷的《憶兒時》與夏目漱石的《硝子戶の中(玻璃門內)》,豐子愷的《華瞻的日記》與夏目潄石的《柿》,豐子愷的《緣》與夏目漱石的《ケーベル先生(凱貝爾先生)》等之間的關系。第二部分依次探討了豐子愷成熟期作品中的《林先生》與夏目漱石的《ケーベル先生》,豐子愷的《緣緣堂隨筆》與夏目漱石的《硝子戶の中》等之間的關系,并順勢比較了豐子愷的《林先生》與魯迅的《藤野先生》之間的寫作異同。第三部分依次討論了豐子愷的《蝌蚪》與小泉八云的《文鳥(文鳥)》《草ひばり(草云雀)》,豐子愷的《蜜蜂》與小泉八云的《蠅の話(蠅話)》,豐子愷的《清晨》與小泉八云的《蟻(蟻)》等之間關系。該書從個案的角度深研了豐子愷散文的日本淵源,并總結了這一文學的交互現象在中日近代文學與文化史上的意義。其中第四章“異文化の対話——《縁》與《ケーベル先生》”已先由作者自譯成《異文化的對話——豐子愷〈緣〉與夏目漱石〈凱貝爾先生〉》一文,收入杭州師范大學弘豐中心編的《如月清涼——第三屆弘一大師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2010年初版)。第十一章“アリへの賛歌——《清晨(早朝)》與《蟻》”又由作者自譯為《獻給螞蟻的贊歌——豐子愷的小品〈清晨〉與小泉八云〈螞蟻〉》,收入杭州師范大學弘豐中心編的《第三屆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
日本另外一位頗有創獲的研究者是大野公賀。她早在2002年就以豐子愷為主題完成東京大學碩士論文,之后又繼續深入,于2009年完成東京大學博士論文《中華民國期の豊子愷:新たなる市民倫理としての「生活の蕓術」論(中華民國時期的豐子愷:作為新市民倫理的“生活的藝術”論)》。同時作者又發表了一系列的論文,主要有:《民國期における「子愷漫畫」の流行——新興都市大衆と豊子愷——(民國時期“子愷漫畫”的流行:新興都市大眾與豐子愷)》(載《東京大學中國語中國文學研究室紀要》2005年4月第8號)、《豊子愷における自己確立のための模索——浙江省立第一師範から東京留學まで——(豐子愷自我確立的探索期:從浙江省立第一師范學校到東京留學)》(載《東京大學中國語中國文學研究室紀要》2009年12月第12號)、《豊子愷の仏教信仰における弘一法師と馬一浮:『護生畫集』を中心に(豐子愷佛教信仰中的弘一法師與馬一浮:以〈護生畫集〉為中心)》(載《東京大學中國語中國文學研究室紀要》2010年11月第13號)、《『護生畫集』解題(1)——豐子愷の仏教帰依から第一集まで(〈護生畫集〉解題之一——從豐子愷皈依佛教到第一集的完成)》(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2012年12月第162冊)、《豐子愷の描いた桃源譚——『赤心國』(豐子愷筆下的桃花源——〈赤心國〉)》(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2015年3月第167冊)、《豊子愷『護生畫集』解題(2)──心の自由を求めて(豐子愷〈護生畫集〉解題之二——追求心靈的自由)》(載《東洋法學》2014年1月第57卷第2號)、(《豐子愷『教師日記』研究(一)(豐子愷〈教師日記〉研究之一)》(載《東洋法學》2015年7月第59卷第1號)、《豐子愷による落語の翻案童話『化かされた博士』について(〈博士見鬼〉:由豐子愷從落語改編的童話)》(載《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2016年3月第169冊)。作者于2005年受邀參加首屆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并發表論文《追求精神的自由——從〈教師日記〉讀豐子愷》。該文呈現了豐子愷與曹聚仁等關于戰爭與藝術之間的論爭,并以豐子愷《教師日記》及當時的漫畫創作為文獻基礎,解讀了戰爭時期豐子愷的藝術思想與宗教觀念,最后認為:“也許正是豐子愷——在抗戰的顛沛之中守護心境,追求藝術境界與精神自由從而確立了獨特的護心思想的豐子愷——才能冷靜而泰然地度過波濤洶涌的‘文革’時期。”(見《論豐子愷——2005年豐子愷研究國際學術會議論文集》,第289頁)關于《教師日記》的研究以及豐子愷護心思想的研究,作者之后又有進一步的研究,相關文獻已如上述。

日本的相關論文還有吉川健一(中文名陸偉榮)的《豊子愷作品におけるルーツ:「雅」と「俗」の間に成立した蕓術(豐子愷作品之根:成立于“雅”與“俗”之間的藝術)》(載《中國近現代文化研究》2015年3月第16期)與《豊子愷の蕓術——竹久夢二の影響をうけた中國近代漫畫の鼻祖(中國近代漫畫鼻祖竹久夢二對豐子愷藝術的影響)》(載《勉誠出版》2000年5月第16期)、吳衛峰的《豊子愷訳『源氏物語』の出版の遅れについて(關于豐子愷譯〈源氏物語〉的延遲出版)》(載《東北公益文科大學綜合研究論集》2011年第1輯)、流通科學大學的陳洪杰與神戶大學的李愛華合寫的《隨筆『児女』に見られる朱自清と豊子愷の児女観(從隨筆〈兒女〉看豐子愷與朱自清的兒女觀)》(載《流通科學大學論集——人間·社會·自然編》2010年第22卷第2號)以及田中干子(田中幹子)與鄭寅龍(鄭寅瓏)合寫的《豊子愷訳『源氏物語』の問題點について:「桐壺巻」における林文月訳、銭稲孫訳との比較(豐子愷譯〈源氏物語〉之問題點:與林文月、錢稻孫譯的“桐壺卷”之比較》(載《東亞比較文化研究》2012年6月第11期)等等。
近20年來的豐子愷研究在取得豐碩成果的同時,也伴隨著明顯的問題,主要體現在“闡釋錯位”與“闡釋不足”兩個方面。“闡釋錯位”也即以某種“主義”“理論”隨意剪切豐子愷的具體作品,往往使藝術文本成為理論牽強附會的例子。“闡釋不足”也即在文獻資料尚未充分占有的情況下即行分析、歸納、概括,所得的結論往往與研究對象的本來面貌產生較大的差距。另外,低水平重復也是豐子愷研究領域中非常突出的問題。故而研究者們除了要有理論的武裝,需要盡可能掌握全面的文獻資料,還需要對研究史有一定的把握,因為任何一種研究都不是橫空出世,而總是踏著前人的足跡而來。限于筆者的視野與水平,本文的評述內容或有不當,論著搜集或有遺漏,但我們有理由相信,在海內外學者的共同努力下,豐子愷研究的進一步發展與突破完全是可以預期的。
(責任編輯:劉 晨)
A Review of the Research in Feng Zikai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1997-2016)
SONG Rui, PAN Jian-wei
(Research Institute of Art Education,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Hangzhou 311121, China)
From 1997 to 2016, research in Feng Zikai has yielded richer results, both in depth and breadth, than any other previous period and it is necessary to summarize it. This paper proposes to review this remarkable period from five aspects, namely, "art research", "literary research", "research in artistic thought ", "research in life and works " and "research in Hong Kong, Taiwan and abroad ", showing the achievements and breakthroughs in the research produced in these two decades, identifying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therein and facilitating further research.
research in Feng Zikai; review; period of gradual maturing
2017-03-22
宋睿(1993—),女,山東青島人,杭州藝術教育研究院碩士研究生,主要從事唯美主義藝術思想研究;潘建偉(1980—),男,浙江紹興人,博士,杭州師范大學藝術教育研究院(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中國近現代詩學及弘一大師、豐子愷研究。
K825.4
A
2095-0012(2017)03-0079-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