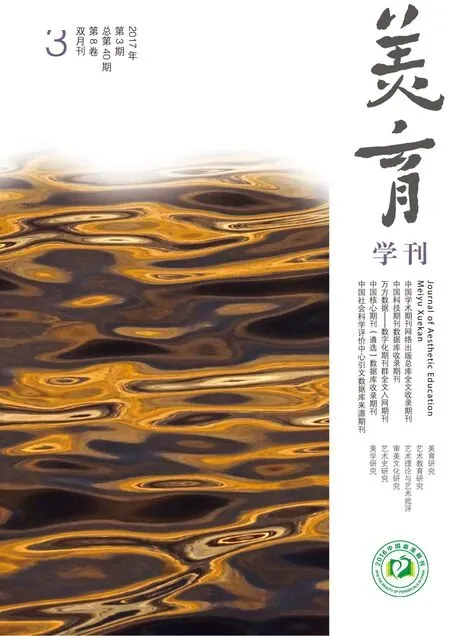豐子愷藝術比較論研究
鄧友女
(中國文聯出版社,北京 100125)
?
豐子愷藝術比較論研究
鄧友女
(中國文聯出版社,北京 100125)
豐子愷藝術理論在中國20世紀藝術理論的現代化進程中發揮了獨特的作用,對豐子愷在門類藝術比較、中外藝術比較、藝術和道德、宗教、科學等方面的藝術比較論進行梳理、歸納和總結,從藝術比較論研究的角度,可從一個側面把握豐子愷的理論貢獻。
豐子愷;藝術理論;藝術比較
引言:一位藝術通才的藝術比較論
豐子愷的藝術理論是中國現代藝術理論史上重要的一頁。缺少這一頁,我們就不能獲得對中國現代藝術理論完整、準確的把握。豐子愷的理論探索是與其藝術創作、藝術教育、藝術類讀物的翻譯工作聯系在一起的。豐富的藝術實踐經驗為其藝術理論提供了深厚的土壤和充足的養料,而豐子愷的藝術理論又為其多方面藝術實踐提供了形而上的指導。因此研究豐子愷的藝術理論不僅為研究其藝術實踐如藝術創作、藝術教育、藝術翻譯等拓寬新的視野,提供新的角度和方法,而且對于理清個性鮮明、特色卓異的豐子愷藝術理論在中國20世紀藝術理論的現代化進程中所發揮的獨特作用和理論貢獻,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在豐子愷研究史上,對于豐子愷藝術創作的研究成果較為豐碩,但對于豐子愷藝術理論的系統研究則相對冷僻。豐子愷研究專家陳星曾指出:“一部‘豐子愷研究史’居然百分之七八十的內容是史料的整理。……很少就豐氏思想、文化站位作深入的探討。進入20世紀80年代后,豐子愷研究一度較熱,但研究領域仍未得到應有的拓展。”*陳星《一道消逝的風景——豐子愷藝術思想研究》“序言”,見朱曉江《一道消逝的風景——豐子愷藝術思想研究》,杭州:西泠印社,2001年,第1頁。關于豐子愷藝術理論的研究,少有站在一般藝術理論角度作深入、系統的探討與研究,因而人們對于豐子愷藝術理論的整體概貌和理論貢獻,缺乏應有的了解。顯然這與豐子愷的藝術理論探索和貢獻是不相稱的。因筆者的論域及學力所限,故嘗試從豐子愷藝術比較論的角度入手進行研究,以期從一個側面把握豐子愷的藝術理論貢獻。
豐子愷的藝術比較論主要從三方面展開:一是門類藝術的比較。主要是書法、繪畫、金石、雕塑、建筑、工藝、攝影、音樂、舞蹈、文學、演劇、電影等12種藝術之間的比較。本文摘取豐子愷就繪畫與文學的比較進行展開。二是中外藝術的比較。豐子愷在中外藝術上的比較點主要有工藝、繪畫、建筑等,就藝術技法和藝術風格、藝術精神等層次進行了廣泛、深入的比較,他將橫向比較與歷史研究結合起來,在生動具體的歷史事實中,就中外藝術各自的特征、優勢與局限鞭辟入里地揭示出來,并就中外藝術如何實現相互借鑒與融合的問題提出了獨到見解。三是藝術和道德、宗教、科學的比較。藝術作為一種精神現象或精神活動,與精神領域的其他學科有著割不斷的天然聯系,豐子愷關于藝術和道德、宗教、科學的比較,是放置在一種文化的視野下和跨學科的比較研究中進行的。在展開藝術比較論之前,有必要對豐子愷的藝術自然分類體系和理論貢獻進行介紹。
一、具有現代中國特色的藝術自然分類體系
20世紀30年代流行的8種藝術的分類體系:繪畫、雕塑、建筑、工藝、音樂、文學、舞蹈、演劇。
1935年豐子愷的11種藝術的分類體系(《繪畫概說》):繪畫、雕塑、建筑、工藝、音樂、文學、舞蹈、演劇、電影、書法、照相。
1941年豐子愷的12種藝術的分類體系(《藝術修養基礎》):繪畫、雕塑、建筑、工藝、音樂、文學、舞蹈、演劇、電影、書法、照相、金石。
豐子愷的上述藝術門類劃分法,所采用的是自然主義。從某種意義上說,這種分類法缺乏理論的邏輯性和體系性,更不具備歷史的抽象性,只是一種單純的現象式概述或羅列。但實際上,關于藝術的自然體系的研究,在藝術理論建構、藝術教育、藝術管理等方面均有不可替代的重要意義。就中國現代藝術理論史而言,豐子愷的貢獻是顯著的,其藝術分類的思想初步形成了具有中華民族特色的藝術自然分類體系。豐子愷的自然主義的分類法,在兩方面具有開拓性意義。
一是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1]書法、金石是中國特有的藝術,因此在西方的藝術分類體系中,自然不曾有書法、金石的位置。在對中國的藝術體系進行總結的歷程中,將書法、金石作為獨立的門類藝術列入中國的藝術體系,在20世紀的藝術分類學、藝術理論上,豐子愷是開風氣之先的。豐子愷在參照西方自然藝術體系的基礎上,將書法、金石均當成獨立的門類藝術,放置在與繪畫并列的位置上,這實在是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和歷史意義。書法、金石,不僅對其他門類藝術產生過重大影響,而且對中國文化、民族心理、審美等都有深遠影響,在中國的藝術體系、文化體系中作用巨大,地位顯赫,理應在理論研究中成為基本的門類藝術,否則就不足以體現出藝術自然分類的中華民族固有的本色。
二是富有鮮明的現代色彩。豐子愷不為歷史的傳統所囿,及時將新興的藝術門類吸納到其總結的藝術體系中來,對其進行較全面、系統的分析和研究。在20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藝術理論界,“電影因為新興”,“未被列入藝術之園的部類中”,但在豐子愷的藝術體系總結中,電影是一種基本的門類藝術,并認為“其將來的發展,未可限量”。[2]348,356在豐子愷總結的體系中,攝影是視覺藝術、空間藝術之一種,地位與工藝、建筑、雕刻、書法等相當,同屬基本門類藝術。但在當時,攝影是不是藝術?是否具備作為一種基本門類藝術的資格?爭議頗多(就是現在,針對攝影是否是一種基本門類藝術,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如今攝影作為一種藝術,已成了常識,理論家一般也將其看成是一種基本的門類藝術。但攝影經歷了從“非藝術”到“準藝術”到“藝術”再到“基本門類藝術”的發展歷程。豐子愷將攝影看成一種獨立的門類藝術,也是個漸進的過程,態度也很復雜,而且豐子愷對攝影藝術的價值、功能、地位等的評價不高。在視攝影為“非藝術”階段,豐子愷“奉勸自己會照相的朋友們”,“扶助照相向美術去”,因為他意識到了照相的“美術的意義”[3](1927),同時他的態度又表現得相當猶豫和矛盾,他認為“美術的照相只能算是攝制的藝術,不能視為純正的藝術”,“不能成為正格的藝術”,因為照相“缺乏人的心的活動”[4](1930);在視攝影為“準藝術”階段,豐子愷勸人“以機械時代的一種新美術看待照相”[5](1936),因為照相“具有美術品的資格”[5](1936),豐子愷認為照相“不但求‘像’,又求其‘美’。照得好的,竟同繪畫差不多或另有繪畫所不辦的好處”[6](1935);在視攝影為“藝術”階段,豐子愷卻抱怨照相“究竟太機械的,太不自由,不能充分加入作者的主觀的創作”[7](1941);在視攝影為“獨立門類藝術”階段,豐子愷干脆直截了當地說照相“藝術的價值低淺”[2]353(1943)。
豐子愷的這種藝術體系總結,是對藝術類型理論甚至藝術理論的較為自覺的、全面、系統的總結,較多地帶有藝術學的意義。在中國20世紀的藝術類型學、藝術理論史上具有承前啟后的重要意義。在藝術門類的總結上,豐子愷在半個世紀之前就自覺地意識到將民族特色和時代發展有機地結合起來。
二、藝術門類的比較
豐子愷關于藝術門類的比較,主要是在繪畫、雕塑、建筑、工藝、音樂、文學、舞蹈、戲劇、電影、書法、攝影、金石等12種藝術之間進行。由于豐子愷有著豐富的藝術創作經驗,因此他就各種藝術進行比較時,自然會帶著藝術家的眼光從藝術技法的經驗層面展開。豐子愷在繪畫、文學創作上取得最為突出的成就,為了說明豐子愷作為一個藝術家的藝術比較論特色,現有針對性地選取了他就繪畫和文學兩種藝術的比較。
由于豐子愷在繪畫(以漫畫為主)、文學(以散文為主)上均有豐富的創作經驗,因此他能從藝術創作技法入手來對繪畫與文學進行比較。但同時豐子愷又有深厚的西畫知識背景,因此他的詩畫比較能熟練地借鑒西方的繪畫技法理論,并有意地運用西方繪畫技法理論對中國傳統繪畫和中國民族文學進行比較。例如透視法(豐子愷稱為“遠近法”)和寫生在繪畫與文學上的比較。豐子愷所指的遠近法即透視法,且是西畫中普遍運用的焦點透視法,而非中國繪畫中的散點透視法。豐子愷“發現”“中國的文學合著繪畫的遠近法”,但“中國的繪畫反而不合于遠近法”[8]496,456-468。其所謂的“中國的文學”主要是指古代的詩詞,“中國的繪畫”也主要是指傳統意義上的中國畫。為什么會這樣呢?豐子愷認為詩詞中之所以也存在遠近法,那是因為詩人觀照自然的態度,與畫家是“根本地相同”,只是“表現的工技不同而已”——“畫家用形狀色彩”,“詩人用言語”。用透視法來分析、闡釋詩詞所傳達的意境之真之美,借詩詞的寫景來驗證透視法的原理,《文學中的遠近法》就是專門探討這一問題的。豐子愷用“凡物距離愈遠,其形愈小”、“凡在視線之上的(即比觀察者的眼睛高的)景物,距離愈遠,其在畫面的位置愈低”、“凡在視線之下的(即比觀察者眼睛低的)景物,距離愈遠,其在畫面的位置愈高”、“若兼看視線上下(天與地)兩方,即見其相‘接’,相‘連’”、“平面化”[8]456-468等透視法的系列規律,詳盡、透徹地剖析了大量的詩詞句,當然也用這些詩詞來說明“中國的文學合著繪畫的遠近法”。這既有利于詩畫家的相互借鑒提高,也為人們欣賞類似的詩詞開辟了一個嶄新的角度和異樣的天空。
為說明透視法在寫景詩詞中的廣泛運用,豐子愷羅列了大量的詩詞句作為例證一一進行分析。且看豐子愷的一個分析例句——岑參《登總持圖》中的詩句:
檻外低秦嶺,窗中小渭川。
豐子愷認為這句詩是符合透視規律的。其透視規律有“凡比觀察者的眼睛高的景物,距離愈遠,其在畫面的位置愈低”,“凡物距離愈遠,其形愈小”。依現實邏輯而言,秦嶺的高度怎可能比檻低呢?渭川更是比窗不知大多少千百倍呢?豐子愷由此推測詩人在觀察自然時,采用了與畫家相同的觀察方法,即透視法。因此秦嶺雖然是很高的山且距離很遠,但相對于近在眼前的檻來說,其畫面位置要低于“檻”,“窗雖小而距離近,渭川雖大而距離愈遠,渭川便可納入窗中而猶見小”。從另一角度來說,這些詩句的描寫無疑是符合透視法的。豐子愷認為該詩句之“奇”與“妙處”,就在與這種透視法的運用。其實詩句所描寫的景并非是現實的、真實的自然之景,只是詩人觀察自然時,眼中所看到的真實之景,即眼中之景。豐子愷認為詩人在此處觀察自然時的“觀察要點”是,撤去秦嶺與檻、渭川與窗的距離,將當時眼睛所看到的景物按照眼中的大小“拉近來”放到一塊。如此一來,詩中之景,猶如畫中之景。特別是“窗中小渭川”的描寫,豐子愷認為這好像是詩人將偌大的渭川“使貼在窗上”,“這樣一來,窗框便像畫框,而所見的渭川便是這幅天然畫圖中的川流了”。*此段加注處均引自豐子愷《繪畫與文學》,見《豐子愷文集》第2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460頁。在《文學中的遠近法》一文中,豐子愷共對40多處寫景詩句進行了深入的分析。在這些分析中,豐子愷用畫家的眼光來鑒賞寫景詩句,在寫景詩句中看出透視法來,并用質樸曉暢的語言,將詩句中所運用的抽象的透視法生動、形象地解說出來。
在詩畫結合的關系上,豐子愷認為有兩種結合方式:一種是表面的結合,一種是內面的結合。表面的結合,即“用畫描寫詩文所述的境地或事象”或“在畫上題詩句的款,使詩意與畫義,書法與畫法作成有機的結合”;內面的結合,即“畫的設想,構圖,形狀,色彩的詩化”[9]39,中國畫的特色主要在于此。
三、中西藝術比較
一方面豐子愷以藝術技巧為評價標準。他承認西方藝術在技法上勝過中國藝術,認為西方的工藝、繪畫、雕塑、建筑等在技術性的要素上遠比中國的藝術更為科學、精確,積極倡言中國應向西方學習這些藝術技法。另一方面豐子愷又以藝術的精神意蘊為評價標準。豐子愷明確表示:“藝術不是技巧的事業,而是心靈的事業。”[10]所以,豐子愷認為:從藝術品的思想內容、精神意蘊、內在氣質和外在風采等方面而言,中國藝術要優于西方藝術,“這種二分的評價標準,在豐子愷的藝術思想中,是貫穿始終的”[11]134。
工藝在豐子愷的藝術分類體系中,主要是指實用性工藝,觀賞性的非實用工藝則探討得比較少。且豐子愷所指的實用性工藝多是當時非常普遍使用的家居日用品,如中國的茶碗和西洋的茶杯、中國服裝和洋裝、木屐與皮鞋、八仙椅與西式椅子、毛筆和鋼筆等,即現實生活中隨時隨處所必需的“用具”。豐子愷中西工藝品的比較也主要從上述列舉的家居日用品入手一一進行詳細的對照,他從中西“用具”的形式、目的、用途、審美追求等方面的區別進行了饒有趣味的研究。豐子愷認為西洋工藝品在形式上講究精確、科學,且簡潔明了,在目的用途上舒適、方便、耐用,具有很強的實用性。相比之下,中國工藝品適體的程度遠遠要比西洋工藝品差,因此無論是在實用還是美觀上都顯得有些差距。例如,毛筆和鋼筆在適合人體程度的深淺上,豐子愷認為毛筆從長度、粗度、造型等方面都只是“約略地適合而已”,而鋼筆的長短、粗細、形狀卻是“精密地適合于人的手的形狀而制定的”。值得注意的是,豐子愷不僅贊揚西洋工藝品形式技巧上的精密、科學,而且從審美價值層面對西洋工藝品的形式技巧的精密與科學也持肯定態度。豐子愷認為蘇格拉底關于“凡適合于目的及用途的,就是美的”見解,非常適用于建筑和工藝,并根據西洋工藝比中國工藝更舒服耐用等特征來斷定“西洋工藝實在比中國工藝更美觀”。此外,豐子愷認為工藝品在普及藝術教育于民間的作用方面,無論是中國工藝品還是西洋工藝品都應該是相同的、積極的。由此豐子愷感慨道,中國工藝特別是傳統工藝應向西方學習,認真改良不足之處,其第一要務“須請藝術進工廠,改良工藝品,使合實用而又美觀,方有美化人生之望”。[12]但他反對一味的模仿,認為應該從美的“適合其目的及用途”的精髓上下功夫,以達到中國工藝“比西洋的工藝更適用更美”的目的。*此段未加注處均引自豐子愷《東西洋的工藝》,見《豐子愷文集》第4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68-376頁。豐子愷關于工藝品的審美評價標準與其所提倡的“人生的藝術”、“藝術的人生”見解是相通的,豐子愷主張藝術與生活相溝通,張揚藝術的目的在于“把創作藝術、鑒賞藝術的態度來運用在人生中,即教人在日常生活中看出藝術的情味來。”[13]226
繪畫的比較,豐子愷采用的是二元分析的思維模式,他將繪畫的比較面主要落實在藝術技法和藝術品的精神內涵兩個層面。在比較兩種繪畫優缺點時,豐子愷得出的結論是:在色彩、線條、構圖等繪畫技法上,西洋畫講究精確、科學、理性、規范、客觀、再現,中國畫則流于主觀、感性、非科學,因此西洋畫勝過中國畫;但就藝術品所傳達的藝術精神內涵而言,中國畫所蘊涵的思想感情較為豐富,審美境界較為超脫,因此中國畫要勝過西洋畫;兩者綜合起來講,又中國畫要略勝一籌,因此豐子愷認為就總體而言中國畫要勝過西洋畫。20世紀初期,藝術界反傳統、學西方的勢頭極為強勁,但豐子愷并沒同流而進,他在評價中西繪畫時,這種直截地批評西方繪畫盛贊中國繪畫的極其明確的價值立場,在當時是相當少見的。
豐子愷在比較中西繪畫價值層面或說藝術精神內涵上的異同點主要概括見表1:

表1 中西繪畫精神層面的比較
四、藝術與道德、宗教、科學的比較
(一)藝術與道德的比較
在豐子愷看來,藝術的主要功能和目的是其“涵養之功”[14]。他認為藝術能幫助人養成健全、完善的人格,使人實現靈魂的自由、精神的超越和人生的解放。因此,在人格的養成上,藝術與道德有異曲同工之妙,在靈魂和精神的自由向度上,藝術與宗教相通,但藝術與科學的關系則基本上是對立的、相抵牾的。
以1937年抗日戰爭為界,由于社會語境的變化和豐子愷本人的關注點所致,豐子愷關于藝術和道德的比較有明顯的區別。為了行文的方便,現將1937年以前稱為前期研究,1937年以后稱為后期研究。
1.前期研究
由于豐子愷在早期對藝術功能的認識基本持內部功能論,即強調藝術之于個體審美體驗、生命價值、精神自由的積極影響和內在作用。因此他關于藝術和道德的關系研究,主要是通過藝術的道德教化功能來體現的。他雖然否認藝術的道德教化功能,但又要求藝術家的人格修養與藝術修養相統一。他對藝術之于道德、宗教、政治、社會等的外在功能較多地持否定態度。他堅決反對藝術工具論。舉繪畫為例,他痛斥“拿繪畫來作政治記載,宗教宣傳,主義鼓吹的手段,使繪畫成為政治、宗教、主義的奴隸,而不成為藝術”的現象“可惡”[9]38。由此可見,在藝術和道德的天平上,豐子愷更傾向于藝術,藝術的教化功能在豐子愷的排斥之列。但在人格修養和藝術修養的關系中,豐子愷認為兩者具有內在的統一性:一方面豐子愷認為人格修養的優劣決定藝術修養的“優劣”,同時藝術修養又反過來影響人格修養,甚至藝術能成就人格。豐子愷認為,雖然狹義的藝術不應承擔道德教化功能,但廣義的藝術卻應有道德教化功能。所謂狹義的藝術即“惟美的純藝術”,是“超越利害的,超越理智的,無關心的”。所謂廣義的藝術即是大眾的藝術,他對廣義的藝術特別是當時深入民間的“花紙兒”和“戲文”兩種藝術的道德教化功能表示了極大的歡迎和贊許。他認為這兩種藝術之所以得到最普遍流行的原因就在于忠孝節義等倫理關系的藝術表述,而藝術形式只是“一種附飾,一種手段、一種加味”*以上未加注均引自豐子愷《深入民間的藝術》,見《豐子愷文集》第3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376-384頁。。
2.后期研究
豐子愷后期藝術功能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外部功能論上,特別強調藝術的現實社會作用。具體到對藝術和道德關系的研究中,特別重視兩者的共性和互動關系。豐子愷認為藝術和道德的共性表現在兩者的目的是相同的。藝術除了消遣、娛樂功能外,在教育、認識上的功能作用與道德是相互統一的。“道德與藝術異途同歸”,它們的目的指向都是為了提高“支配人的全部生活”的精神境界。當然兩者的差異也是顯著的,“道德由于意志,藝術由于感情。故‘立意’做合乎天理的事情,便是‘道德’。‘情愿’做合乎天理的事,便是‘藝術’”,“藝術給人一種美的精神,這精神支配人的全部生活。故直說一句,藝術就是道德,感情的道德”。
豐子愷主要就道德對藝術的影響作用從以下幾方面切入:其一,肯定藝術對社會倫理道德的承載,更加強調藝術的道德功能。他認為“藝術以仁為本”[15],并坦言在太平時代藝術的“陶冶之功與教化之力的偉大”“只是暗示地講”,但在“國家存亡危急之秋,不得不打開來直說”。[16]其二,肯定道德觀,道德實踐對藝術家的人格、心理產生重大的影響。豐子愷認為高尚的道德是做人的首要條件,也是成為藝術家的首要條件,因此藝術家首先要注重道德修行,健全心理,完善人格,“欲為藝術家者,必須先修美德,后習技術;必須美德為重,而技術為輕”。最能概括其德藝關系觀點的是“士先器識而后文藝”、“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17]器識即道德修行、才學識見等素質,文藝,即藝術,兩者在建構士的精神面貌、人生境界上的輕重主次不言而喻。由于豐子愷受儒家思想的熏染和其師李叔同的影響較深,有些研究者認為重德輕文是豐子愷“對藝術家如何處理德與文關系的根本觀點”[18]。其實豐子愷對德藝關系的觀點,不能簡單地以重德輕藝來概括。豐子愷更多地認為德藝(美德和藝術技巧)猶如一個藝術家的兩翼,缺一不可。
(二)藝術與宗教的比較
藝術和宗教,豐子愷形象地將其比喻為他用來剪破“世網”的剪刀[19]。因有藝術和宗教的雙重實踐,豐子愷對藝術和宗教的關系的理解與研究,與別的理論家表現出的顯著差異點就是:豐子愷認為宗教在藝術之上。
豐子愷自己對宗教特別是佛教雖有堅定的“信念”,但尚未上升到“信仰”的層次,他與佛教之間的精神聯系在強度與寬度方面都弱于信仰,雖然對佛教教義的觀念較為信奉,但佛教并不是豐子愷情感和心理世界的全部寄托,因此他最多也只是屬于“信念型”[20]的佛教徒。對豐子愷的這一分析,有助于我們理解豐子愷對于宗教特別是佛教的認識。即豐子愷關于宗教的理解是寬泛意義上的宗教,而且他特別注重對宗教教義、宗教精神的信奉,而對于形式上的要求則不斤斤計較。豐子愷提出著名的人生“三層樓”說:“我以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層:一是物質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靈魂生活。物質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就是宗教。”豐子愷認為人生好比一座三層樓,物質生活、精神生活(學術文藝)、靈魂生活(宗教)是構成人生的三個遞進層次。其中宗教是人生的最高階段和最高理想。作為精神生活之一的藝術處于“衣食”和“宗教”之間,是物質生活和靈魂生活的中介,他認為“藝術的最高點與宗教相通”,藝術向宗教邁進的臺階是精神,因此藝術在精神層面與宗教相通。但豐子愷認為此“三層樓”并不是每個人都能經歷的,而是有的人只能上一層或二層,而三層樓能上去的只有極少數人。另一方面即使是三層樓都上去的人,也不是按從低到高的自然過渡來實現的,而是要靠“人生欲”、勤勉和“腳力”來實現的。豐子愷判斷藝術和宗教高下重輕的主要依據有:宗教有終極關懷,宗教解決“道”“德”“器識”問題,而藝術僅是技術層面的問題。他認為藝術只是人生“暫時的美景”,而宗教能“追究靈魂的來源,宇宙的根本”。[21]宗教在豐子愷看來是凸顯個體生命的主體性和實現自省的一種途徑和方式。在其他國家特別是西方國家,宗教是人們人生觀的根柢,也是超越個體自我生命的一種途徑和方式,因此往往會將宗教在精神領域的地位奉若至尊。那么一向張揚民族文化傳統和中國藝術精神的豐子愷,何以會在藝術和宗教地位孰高孰低上如此地“西化”或說接近西方呢?顯然這與當時國內特有的社會文化語境和豐子愷自我的文化訴求息息相關。
(三)藝術與科學的比較
關于藝術和科學的比較,豐子愷采用的基本是二元對立的思維方式。他認為藝術和科學之間具有極強的依賴關聯性,但兩者是對立地存在著的。“科學和藝術,是根本各異的對待的兩樣東西”[22]13,豐子愷認為它們各自的領域、性質、功能、特征是截然不同的。領域上的區別,豐子愷認為科學的領域是知的世界,藝術的領域是美的世界,“科學是真的、知的”,“藝術是美的、情的”;[13]225性質上的區別,豐子愷認為“科學是實用的,藝術是享樂的”,“科學是分析的,藝術是理解的”;功能上的區別有,“科學是創造規則的,藝術是探索價值的”,“科學是研究手段的,藝術是研究價值的”,“科學所論的是事物的要素,藝術所論的是事物的意義”;兩者的特征差異在于,“科學是說明的,藝術是鑒賞的”,“科學是理智的、鉆研的、奮斗的,藝術是直觀的、慰安的、享樂的”。*以上未加注處均引自豐子愷《藝術教育的原理》,見《豐子愷文集》第1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第15-16頁。
雖然豐子愷認為藝術和科學是對立存在的“根本各異”的“兩樣東西”,但兩者的社會功能和人生作用同等重要,它們“同是人生修養上所不可偏廢的”[23]。當時由于受科學萬能論的影響,科學對藝術形成了高壓,在人們的意識中,科學應凌駕于藝術之上。一方面豐子愷對科學的作用持非常理性的態度,表現得相當謹慎低調;另一面豐子愷又敏銳地直覺到這種非常態擴張的科學對藝術造成的破壞和戕害,并一一指陳出來。首先他旗幟鮮明地反對科學高居藝術之上的論調,反對將藝術當成科學奴婢的庸俗功利做法。他認為藝術不應是科學的奴仆。其次他將對這種科學萬能論的危害性的批判直接導入到對人的精神生活的關懷。他認為過分強調科學,容易使人的精神生活陷入偏枯,“人民變了機械的枯燥的生活”,“變成了不完全的殘廢人,不可稱為真正的完全的人”。[22]15-16豐子愷認識到科學的過分擴張將壓抑、束縛、窒息人的精神生活,嚴重削弱精神生活的空間和向度。最后他認為科學實用精神嚴重破壞了藝術精神。豐子愷慨嘆到:“一向認為超越物質與科學,反對物質與科學,而居于至上地位的‘藝術’,現在變成唯物的、科學的規范內部事象,而被用唯物的、科學的態度與約束來待遇了”,“這唯物的科學主義,正是毀壞藝術,使藝術從內部解體,使‘藝術’不成為‘藝術的’。”[24]遺憾的是在探討藝術和科學問題時,豐子愷并未就忽視科學的危害性作研究。顯然在探討科學和藝術作為人的精神活動在整個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時,豐子愷的天平更多地傾向于藝術。有學者認為豐子愷討論科學與藝術問題的最初思想動機與總綱,是來自“對主體性失落的警惕”,其關于科學和藝術問題的對待考察,“目的乃在探討或強調人的精神世界在整個世界中的地位與作用”。[11]31,35
豐子愷關于科學和藝術問題的對待考察,不僅“探討或強調人的精神世界在整個世界中的地位與作用”,同時還強調藝術的獨立性,彰顯藝術在人的精神領域的獨特地位和作用。為此,豐子愷的考察途徑也是多方面的,他從藝術和科學、藝術和道德、藝術和宗教等方面精神領域的對照考察入手來強調藝術之于人的精神世界的巨大作用。因此豐子愷關于科學和藝術問題的考察,不能孤立地看待,應該將他關于藝術和道德、藝術和宗教、藝術和哲學等問題的考察綜合起來系統看待。如果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來反思豐子愷當年關于藝術和科學、道德、宗教、哲學等之間的關系,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豐子愷是將藝術放置在廣闊的文化視野中來定位藝術的,藝術在豐子愷看來,是文化視野中的一極,而且是極為重要的一極,它對人的精神生活所起的巨大作用同道德、宗教、科學、哲學等一樣重要,正是它們的合力,共同建構了人的精神世界,豐富了人的多方面的精神生活需求。劉海斌在《豐子愷藝術生活中的邊緣化傾向》一文中認為,豐子愷在“五四”以來普遍倡導科學、民主二元的價值結構秩序之外,又增加了一維——藝術,從而建立了一個三足鼎立的穩固價值體系,“由于堅持藝術做價值世界一維構成的獨立性,豐子愷擺脫了單純的民主、科學論者對于藝術居高臨下的俯視心態及把藝術當成兩者附庸的功利做法”。劉海斌還認為豐子愷當時所從事的藝術教育普及工作,“是一項邊緣性的工作,同時又是一項偉大的工作。”[25]正是基于對當時藝術教育狀況、藝術作用和地位的現實的清醒認識,豐子愷一方面大力倡導藝術教育,希望通過在民眾中推廣、普及藝術教育的實踐來發揮藝術之于人的直接或間接作用;另一方面他還通過藝術和道德、宗教、科學等的比較分析的理論工作來強調藝術的獨特作用和藝術地位上的獨立性,這既是當時的時代任務使然,也與豐子愷低調、諸事不盲目跟隨潮流的“邊緣性”做法有關。同時這種“邊緣性”也使得他就藝術的地位、作用而言,不至于走向另一極端——藝術至上論。
五、結 語
豐子愷的藝術比較研究總能立足于中國藝術的立場,從民族特色著眼來進行,以達到張揚中國藝術優秀傳統的目的。同時豐子愷在進行藝術比較研究時,又能持包容、開放的心態,對西方各種藝術的多方面優長也有充分認識。在比較研究中,他還就如何融合中西藝術以發展中國藝術、促進西方藝術和世界藝術提出了富有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從20世紀藝術理論史的角度來說,其理論探索上的最大貢獻在于促使中國的藝術理論從古典轉向現代。20世紀初,中國的藝術理論建設較為薄弱,傳統的理論顯得滯后,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西方的理論譯著在當時還很少見。豐子愷在翻譯大量日本、西方藝術理論著作的同時,結合中國的民族特色,融合民族古典理論和西方理論,形成其相對完備的具有現代意義的藝術理論。其中有很多的探索,都是豐子愷在對照分析的基礎上完成的,其藝術比較論既為其藝術理論的建構產生積極影響,同時也為中國現代藝術理論的形成、發展作出了積極的貢獻。
豐子愷關于藝術的比較研究是其藝術理論的一種重要研究方式,也是構成豐子愷藝術理論的一個組成部分。同時它也為我們了解、把握豐子愷藝術理論提供了一個獨特的研究視角和途徑、方式。通過對豐子愷在上述三方面藝術比較研究上的梳理和總結,筆者認為其比較研究上的得與失與其所處的社會、時代有關,也與豐子愷理論自身的局限性有關。
[1] 李心峰.現代藝術學導論[M].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5:177.
[2] 豐子愷.藝術的園地[M]//豐子愷文集:第4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3] 豐子愷.美術的照相[M]//豐子愷文集:第1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73,68.
[4] 豐子愷.從梅花說到美[M]//豐子愷文集:第2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560.
[5] 豐子愷.照相與繪畫[M]//豐子愷文集:第3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339.
[6] 豐子愷.繪畫概說[M]//豐子愷文集:第3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121.
[7] 豐子愷.藝術修養基礎[M]//豐子愷文集:第4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82.
[8] 豐子愷.繪畫與文學[M]//豐子愷文集:第2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9] 豐子愷.中國畫的特色[M]//豐子愷文集:第1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10] 豐子愷.西洋畫的看法[M]//豐子愷文集:第1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84.
[11] 朱曉江.一道消逝的風景——豐子愷藝術思想研究[M].杭州:西泠印社,2001.
[12] 豐子愷.工藝術[M]//豐子愷文集:第4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50.
[13] 豐子愷.關于學校中的藝術科——讀《教育藝術論》[M]//豐子愷文集:第2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14] 豐子愷.桂林藝術講話之三[M]//豐子愷文集:第4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23.
[15] 豐子愷.桂林藝術講話之一[M]//豐子愷文集:第4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17.
[16] 豐子愷.藝術必能建國[M]//豐子愷文集:第4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30.
[17] 豐子愷.先器識而后文藝[M]//豐子愷文集:第6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533.
[18] 徐型.先器識而后文藝——略論豐子愷的重德輕文文藝觀[J].南通師專學報,1995,11(4):27-32.
[19] 豐子愷.緣緣堂隨筆·剪網[M]//豐子愷文集:第5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95.
[20] 譚桂林.20世紀中國文學與佛學[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109.
[21] 豐子愷.我與弘一法師[M]//豐子愷文集:第6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2:398-402.
[22] 豐子愷.藝術教育的原理[M]//豐子愷文集:第1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23] 豐子愷.關于兒童教育[M]//豐子愷文集:第3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253.
[24] 豐子愷.西洋美術史[M]//豐子愷文集:第1卷.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361-362.
[25] 劉海斌.豐子愷藝術生活中的邊緣化傾向[G]//朱曉江.豐子愷論.杭州:西泠印社,2000:191.
(責任編輯:劉 晨)
A Comparative Study of Feng Zikai′s Art
DENG You-nu
(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Press, Beijing 100125, China)
Given the special role that Feng Zikai′s artistic theory has played in the process of the modernization of Chinese 20th century art theory, it helps to determine the contours of Feng′s theoretic contribution to sort out, classify and summarize his theories comparing the art genres, Chinese and foreign arts, art and morality, religion and science and etc.
Feng Zikai; art theory; art comparison
2017-03-16
鄧友女(1975—),女,江西贛州人,碩士,中國文聯出版社學術分社總監、副編審,主要從事藝術學類的學術圖書出版研究。
J03
A
2095-0012(2017)03-007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