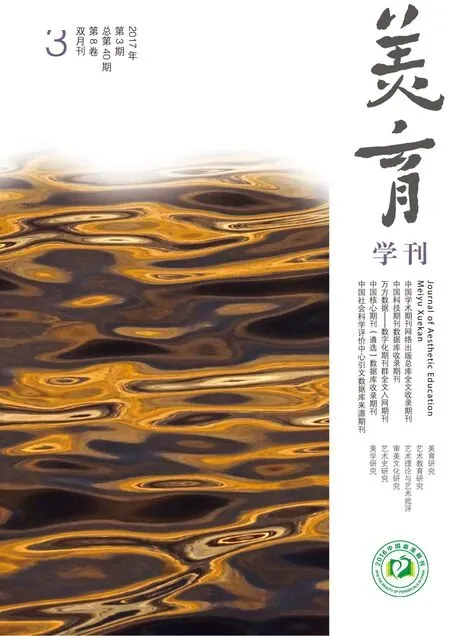蕭公弼與中國現代美育的早期開拓
譚玉龍
(重慶郵電大學 傳媒藝術學院,重慶 400065)
?
蕭公弼與中國現代美育的早期開拓
譚玉龍
(重慶郵電大學 傳媒藝術學院,重慶 400065)
蕭公弼與王國維、蔡元培、魯迅、梁啟超一樣,為中國美育的現代轉型與早期開拓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他在《美學·概論》中,一方面明確區分了“好色(美)”與“好淫”,揭示出了“好色”是人的天性,而“好淫”則是純粹的感官享樂與肉體欲望的滿足,所以他倡導“色而不淫”的審美觀;另一方面,他提出“重內而輕外”的命題,因為“內美”是藝術作品的內在意蘊,能給人持久的美感,同時還具有道德意味。此外,蕭公弼推崇“忘美”之境,它不是一種刻意為之的道德境界,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審美境界,這種審美境界指向道德之善,它是真善美的融合為一。
美育;色而不淫;重內而輕外;忘美之境
盡管早在先秦時期,我國傳統教育思想中就存在“禮樂教化”的美育思想,但直至清末民初,美育才被真正置入教育理念之中,成為與德育、智育、體育并行的一種教育。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中國古典型美育向現代型美育轉型的時期。王國維、蔡元培、魯迅、梁啟超等為美育的轉型及其宣傳推廣作出了巨大貢獻,為現代美育理論的構建奠定了基礎。此外,蕭公弼也同樣值得我們重視。他在“五四”以前,與其他美學家、美育家一樣,倡導重視美育的現實功能,并從自己的立場出發,提出了具有時代意義的美育觀點,以提升當時中國人的精神境界。蕭公弼,雖生卒年月不詳、表字不詳,但根據他1915年前后發表的論文看,他的落款為“四川工業專修學校正科電科一年級生”[1-2]。可見,蕭公弼于1915年左右就讀大學一年級,那么他大致應出生于19世紀末,年齡與朱光潛、宗白華先生相仿佛。此外,據《寸心》雜志,他為該雜志的編輯,也曾與有“蜀中大儒”之譽的彭舉(1887—1966)在成都創辦《世界觀》雜志。所以,蕭公弼很有可能是一位川籍學者。[3]蕭公弼的美育思想見于其《美學·概論》,該作連載于《寸心》雜志(1917年),是中國近現代美學史上最早以“美學概論”為名的論作。《美學·概論》分為《美學之概念及問題》《美學之發達及學說》《發生的生物學的美學》以及《美學之要義及其地位》,加上正文前面的“序”,共五部分。此作試圖全面介紹西方從古到今具有代表性的美學家及其美學理論,如柏拉圖、康德、席勒、叔本華、哈奇生、立普斯等。除此之外,在《美學·概論》中,他還花了大量的筆墨闡述自己關于“忘美”之境,“淫與色”“內美與外美”以及音樂藝術等的美學理論,蕭氏深刻而獨特的美育思想正蘊于其中。
一、“好色而不淫”
好美惡丑與維持生命、傳宗接代一樣都是人的天性。所以,蕭氏云:“目欲窮靡曼之色,耳欲娛聲色之好,口欲極豢芻之美,行欲有輿馬之奉”都是“人情之常,無足異者”。[4]640同時,人的審美觀念也是從這些好美惡丑的天性中生發出來的。另外,“美”在蕭公弼看來具有重要的作用,美的藝術“可卜國家文野”,制作精良的工藝品“可瞰民品優劣”,“美”甚至是動物、植物得以生存與發展的必要保障——“物以美觀而保族,花以香艷而存種”[4]640-641。可見,“美”在蕭公弼的美學思想中占有核心地位,同時,對“美”的追求也成為蕭氏美育思想的出發點。
《孟子·告子上》曰:“食色,性也。”[5]而“色”在蕭氏筆下卻被創造性地發揮為“美”。他說:“蓋美感為人之天性,則好色者亦人之天性也。”[4]661另外,蕭公弼在《美學之發達及學說》中介紹了達爾文的理論,如:“達爾文于其《物競篇》,謂物類之欲保其種也,則雄者常具美麗之羽毛,嫵媚之態度,以誘惑雌者,使其親己,以達其傳種之目的。至于植物,則開美麗鮮艷之花,發芬芳濃郁之香,以引誘蜂蝶,使為媒介,而蕃衍其種焉。”[4]645雖然達爾文理論的科學性值得探討,但是蕭公弼借用此理論足以說明人的“好色”(即“好美”)之情“出于天性,而關于物之生存競爭者大矣”[4]645。
基于此,蕭公弼反對金圣嘆的“人未有不好色者,人好色未有不淫者也”[4]660的觀點。因為金圣嘆雖然是“絕世之聰明才子”,但是“竟將色、淫二字,混為一談”[4]660。在蕭公弼看來:“好色者,美的本質也。好淫者,美的玩賞也。好色者,精神之快感也。好淫者,肉體之欲望也。”[4]661“好色”即追求、喜好“美”,這是人的天性,也是審美活動的本質,人們通過這種追求“美”的審美活動獲得的是一種精神上的審美愉悅。而“好淫”則是純粹的肉體欲望滿足的玩賞活動。“好色”不等于“好淫”。所以,他認為金圣嘆“思想簡單,未入審美高尚領域”[4]661。
曾繁仁先生認為:“審美需要雖是人類的一種美好的感情要求,但如果不引導也有可能走向歧途,變成對某種怪異的‘美’的追求,甚至發展到反面,以丑為‘美’,以生理快感的發泄為‘美’。”[6]而蕭公弼在當時的社會中就發現了這種情況,青年男女的審美需要未得到正確的引導而“色”“淫”不分,他說:“余觀我國近日之社會美術之缺乏,制造之簡陋,已不寒而栗。乃其最者,無行文人,恒喜舞文弄墨,以艷情小說蠱惑當時。”[4]641當時的藝術家“舞文弄墨”,創造“艷情小說”就是一種“色”“淫”不分,以“淫”為“色”的現象。這讓當時的“青年男女之忽于審美,而有以餔其毒也”[4]641。因此,蕭公弼反對“色而淫”,倡導一種“好色而不淫”的審美觀。
蕭氏還借用佛教理論來闡明之:“夫好色而不淫者,是以真如熏無明。故此身常覺清凈,獲自在樂。色而淫者,是以無明熏真如。故此身愛染貪著,受諸種苦報。”[4]641這是佛學中非常有名的“熏習”說。“好色”但“不淫”是用真如熏無明,“好色”而“淫”是無明熏真如。我們怎樣理解這句話呢?在佛學中,“真如”指真如不虛和如常不變,它是宇宙萬物的本體和本然真實,是佛教修行者所要追求的境界。“無明”則是“愚癡”,是一種具有分別心的世俗的認識,修行者就是要鈍除“無明”而求“真如”。“熏習”就如干凈的衣服不香不臭,本來沒有什么味道,但被人穿過后,就會帶上身體的味道,如果身體有臭味,則衣服就會帶上臭味,如果身體是香的,則衣服也就變香了。“真如”本身是“非染”的,“無明”是“染”的。當真如被無明熏習后,則產生業識和妄心,業識、妄心又復熏真如后,則妄念起。“色”好比真如,“淫”好比無明。人天性“好色”,但不一定有淫念,但當“好色”之天性被淫念所熏習后,“色”才會著上淫之色彩,即“好色而淫”。人如果持這種態度,則“快感不生,失美學之真諦者也”。“好色而不淫”則是“以真如熏無明”,用“真如”去熏習“無明”就會讓“無明則滅,無明滅故,心相不起。心不起故,境界相滅”[4]661。也就說,如果人們懷著一顆“真如”之心去印照外界之色或感染邪淫之妄念,即以真如熏無明,一切邪淫之念都會滅絕,而得“涅槃樂”。從審美的角度講,就是讓人不要用功利的態度和充滿欲望的念頭去玩賞對象,這樣就“常覺清凈,獲自在樂”,獲得一種審美的愉悅。
蕭公弼認為如果不明“好色”與“好淫”的區別,則會讓“我國青年男女,審美失當,沉迷聲色,縱欲敗度,致荒時廢事,淫亂之俗,日熾區夏,種既衰微,國且不國也”[4]662。所以,蕭公弼倡“色而不淫”而抑“色而淫”是讓青年男女樹立正確的審美觀,不要把低俗的肉體欲望滿足當作是高雅的審美愉悅,否則青年男女的身心都會受到傷害,甚至國家的興亡也會受此影響。
要言之,蕭公弼認為,“好色”是人的天性,是審美的本質;“好淫”則是人好色之天性受到邪淫之念的熏染而進入與審美相悖的欲望滿足之路。所以,人未有不好色者,但好色不一定淫。蔡元培先生也注意到這個問題,他說:“美色,人之所好也;對希臘之裸像決不敢作龍陽之想。”[7]46也就是說,人們到底是“好美”還是“好淫”關鍵是看人懷著一種怎樣的態度去觀照對象。蕭公弼倡導青年男女“好色而不淫”,不要“色而淫”,因為“色而不淫,提斯警悟,乃如高尚審美之領域,而有無窮快樂者也”,而“色而淫者,斷未有不精神委憊,戕賊厥身者,此又與美之原則相背馳者也”[4]662。
二、“重內而輕外”
“好色”即好“美”,是人的天性,是動植物得以生存、繁衍以及社會發展進步的保障。而“淫”則落入了肉體欲望的滿足與享樂,是一種“龍陽之想”,根本就不是審美。所以,蕭公弼倡導一種“色而不淫”的審美觀,反對那種“色而淫”的低俗觀念。但是,在蕭氏的美育思想中,并不是所有的“美”(“色”)都值得人們去“好”,因為“美”還要分為“內部之美”和“外部之美”,簡稱“內美”與“外美”。
蕭公弼說:“外部之美,則假于外物,托于色相,意覺美觀,緣生愛戀,是此美為自外部發生,是謂‘外美’。若理性自適,意志修潔,天君泰然,良知愉快而感美者,是此美自內部發生,名曰‘內美’。”[4]664外物的形式、色彩等引起人們感官上的愉悅,這種物就具有“外美”,而“內美”就是人們理智把握的對象,能讓人們的心情舒適,喚起人們的良知,它不是來自事物的外部,而是來自事物的內部,即“內部之美,精神之快感也,在我而已。外部之美,形式之美,求在外者也”[4]664。所以,我們可將兩者分別看作形式之美與內容之美。
蕭公弼倡導人們追求“內美”,而不要沉溺于“外美”,即要“重內而輕外”(《美學之要義及其地位》)。他說:“外美之至,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皆物之儻來寄者也。內美則良知瑩然,心不蔽物,自適自樂,無人而不自得焉。”[4]664事物的“外美”來不可止,去不可留,因為它們是寄托在事物的形式中的,而“內美”則讓人們的內心明快,心情自然愉悅,人只要想獲得這種美感就可以得到。蕭公弼進一步講:“內部之美,其感快強,為時永久,外部之美,物有不足,則煩惱以生,其痛苦有異尋常萬倍者。”[4]664在他看來,“內美”才是真正的美,永恒的美,感染力也極強,而“外美”由于托于物的形式,物稍有不足則“外美”受損,人就會產生煩惱,不僅不能獲得美感,反而感覺不快,十分痛苦。
蕭公弼倡導人們要善于捕捉、欣賞“內美”,藝術家也要創造具有“內美”的藝術作品。他說:“彼詩文者,特詞章家意志之寄托耳!無聲音笑貌以悅耳,無美曼婀娜以悅目,然千載之下,使人讀之,或拍案叫絕,或感慨欷歔,或長言吟誦,或手舞足蹈,樂而忘倦者,何也?以其能激發人之感情、思想、內美作用故也。”[4]664詩歌等文學作品雖然沒有悅耳、悅目的形式之美,但是千年以后人們讀了后,卻可以拍案叫絕,感慨萬千,獲得審美愉悅,這是因為詩歌等文學作品是作家思想情感的寄托。而寓于詩歌之中的作家的思想情感就是“內美”,它能激發讀者的思想、情感,從而讓讀者獲得持久的美感。雕刻藝術和繪畫藝術也是這樣,當人們欣賞完雕刻或繪畫后,“暇時默念,亦常能激發人之記憶及想象活動,以思惟該對象,使美之快感情益臻強度,饒有興味,而感情緣以深厚矣”[4]664。這就是說,人們在想象中玩味、思維的不是雕刻或繪畫藝術的外形,而是它們的內在意蘊,給人以美感的也不是藝術的外形,而是內在意蘊,藝術作品的內在意蘊就是“內美”,“內美能滿足吾人知的機能要求,而起美之快感”[4]664。因此,藝術家不能只注重藝術作品的“外美”,還要重視其“內美”,欣賞者也應該欣賞藝術的“內美”,而不應只求感官享樂的“外美”,因為“外美”是有限的、短暫的,只是感官的滿足,而藝術作品的內容或內在意蘊則是永恒的,能給人以持久的美感。藝術作品的“內美”是“自理性而發,非純恃感官知覺故也”(《美學之要義及其地位》)。
蕭公弼認為:“美與善,人類最高尚之生活。”[8]可見,蕭公弼的“美”是不脫離“善”的,是融合了道德之“善”的美。“內美”,即“善—美”。因而蕭公弼十分推崇儒家的圣人,因為他們身上就體現出了“內美”。他說:“孔子疏食曲肱,原憲甕牖繩樞,聲出金石,樂在其中也。”[4]664粗茶淡飯,以肘臂為枕頭,家境貧寒,住處簡陋等都不會讓孔子、子思等人灰心喪氣,反而他們還“樂在其中”。在蕭公弼看來,孔子、子思等體現出的正是一種“內美”。另外,蕭公弼引周敦頤稱顏回的話說:“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4]664顏回不因自己生活貧困而憂愁,反而還自得其樂。同時,顏回追求的不是“富貴人之所愛”的東西,而是追求“天地間至貴至愛”,獲得的是一種“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則一,處一則化而齊。”[4]659這種顏回所達到的無論貧富貴賤都“處一”的境界就是一種至美的境界。因為這些儒家圣人們追求的不是功名利祿的“外美”,而是一種內在道德、心性修養的“內美”。
蕭公弼觀察到,當時的藝術家和觀眾就有“重外而輕內”的傾向,他說:“吾觀我國今日聽劇家,每喜聞妖淫之聲,而評劇家亦多為倚艷之辭,而演劇者之不學無術,昧于音樂之道,教化之義。”[4]665“妖淫之聲”“倚艷之辭”等都是藝術家或欣賞者過分追求“外美”的結果。這種過分重視“外美”而忽視“內美”的“妖聲絕辭”等造成了“國且不國”的嚴重后果。因為這種藝術不僅失于教化,而且讓青年男女更加浮躁,沉溺于聲色之享樂中。所以,蕭公弼不僅強調藝術家或欣賞者要“重內而輕外”,同時還倡導當時的青年男女要以此為自己的審美標準和審美理想,即“我青年男女同胞之審美也,須具此胸襟氣概,然后能不沈于聲色貨利,不淫于富貴功名,而能以美利利天下矣”[4]641。此“以美利利天下”乃蕭公弼美育思想之最終指向與目的。
三、“忘美”之境
蕭公弼明確區分了“好色(美)”與“好淫”,讓當時的青年男女不要以純粹的欲望滿足為審美。而“美”又分為“內美”與“外美”,藝術家要以創造“內美”為己任,欣賞者也要觀“內美”,因為“內美”不僅是藝術作品的內在意蘊,還是圣人的高尚道德情操的體現。但是,蕭公弼的美育思想中的最高境界并不是追求“內美”揚棄“外美”,或者是取“色”去“淫”,而是一種“忘美”的境界。
蕭公弼在《美學·概論》的開篇就講:“惟太上忘美,其次知美,下焉者欲而已。”[4]660他在《美學之要義及其地位》中也說:“復因根器智慧之不同,而有太上、知之、縱欲三種之差別。”[4]657可見,蕭公弼的美育思想中將審美分為了三個層次——忘美、知美和縱欲。
王國維曾說:“美術之為物,欲者不觀,觀者不欲。”[9]5這說明,人如果充滿“欲”是不可能對藝術作品進行審美觀照的,同理,進行審美觀照的人也不可能帶有“欲”。王國維將這種“欲”稱作“眩惑”。“眩惑”就讓“吾人自純粹知識而出,而復歸于生活之欲”[9]6。王國維之“欲”或“眩惑”其實與蕭公弼筆下的“欲”或“縱欲”相通,即蕭公弼所反對的“好淫”,它是一種“阿私所好,或醉生夢死,其去禽獸也幾希”。“欲”就是一種無精神性的純粹肉體欲望的滿足與享樂,這與禽獸沒有分別。在《發生的生物學的美學》中,蕭公弼說:“今之青年男女,誤于審美正鵠,迷戀姿色之美,沉溺肉體之欲,以致耗精疲神,戕賊厥身,年始及壯,躬若老耄。”[4]647-648這就是“縱欲”或“好淫”的真實寫照。所以,這種“欲”其實根本就不是審美——“烏足以語于美哉”。
“知美”就是一般人所達到的境界。蕭公弼倡導人們要好“色(美)”去“淫”以及“重內而輕外”,其實就是“知美”之境。這種境界“察物之媸妍,辯理之是非”。也就說,人有善惡美丑真假之分別,知道去追求真善美而丟棄假丑惡。這種“知美”讓人們具有分辨美丑的能力,確實讓社會取得了一定的進步,因為如果“媸妍同觀,精粗齊等,是茅茨土階之制,必無改于今矣,飲血茹毛之風,必相沿而不革矣”[4]646。但是蕭公弼認為,人如果有了“知美”的觀念后,就會心生欲念去追求美好的東西,即“故吾人觀珍異則思把玩,視好花則擬攀折,見奇鳥則欲牢籠,遇美人則懷繾綣”[4]647。人們因為追求美好的東西,就會發生爭斗,而且還會讓自己“快感與不快感之情生”[4]641。因為,對于美好的東西,人們“得之則喜,失之則郁”。所以,在蕭公弼的美育思想中,這種“知美”只能排在第二個層次。
筆者曾撰文指出,蕭公弼的《美學·概論》“借用佛教理論闡發了他自己的美學觀點,如忘美之境、美與丑、淫與色、內美與外美等,其論述特點是以佛釋美”[10]。具體來講,蕭公弼是站在大乘佛學的角度,推崇一種“忘美”之境。佛教認為人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接觸外界后產生的色、聲、嗅、味、觸、法(“六塵”)不僅是虛假的,而且還刺激人們產生欲望,增加人的無明。佛教把“六根”“六塵”稱為色或相,或色相。色相就是虛相、假相。佛教的最高境界就是求得涅槃,證得佛果。而要達到這一境界,首先就要否定自我,否定外物,否定宇宙間的一切。蕭公弼引用《金剛經》的話講:“無人相,無我相,無眾生相”[4]641。“人”“我”以及“眾生”都被否定了,哪里還有什么美與丑?這就是“夫相之不存,何有于美”?緊接著,蕭公弼用《大乘起信論》的話講:“一切諸法,以心為主,從妄念起,凡所分別,皆分別自心,心不見心,無相可得”[4]641,美與丑、善與惡都是一種“法”,這種“法”是因人的妄念和分別心而產生的。蕭公弼所提倡的是一種“人我兩忘,法執雙融”(《〈美學·概論〉序》)、“思慮寂然,嗜欲不萌”(《美之要義及其地位》)的態度,人們褪去了妄念,消除了分別心,那么美與不美都已經不存在了——“美丑之態,無由發現”,這就是一種“忘美”的境界。
蕭公弼美育思想的最高境界是“忘美”之境,而這種“忘美”之境并不是要人們不分美丑或是去美求丑。一方面,“忘美”之境需要以“知美”為基礎,因為“知美”讓人們區分了“色”(美)與“淫”(丑)、“內美”與“外美”。另一方面,“忘美”之境又需要超越“知美”,因為“知美”會讓人們心生欲念去追求美、色,而在追求過程中會產生情感上的煩惱,甚至是爭斗。“忘美”之境就是在基于“知美”又超越之的過程中,打破美丑的界限,讓人自然而然地處于高尚的道德修養之境界。“忘美”之境不是一種刻意為之的道德境界,而是一種發自內心的審美境界,而這種審美境界指向道德之善,它是真善美的融合為一,也就是蔡元培先生說的一種“脫離一切現象世界相對之感情,而為渾然之美感”[7]5。
四、結 語
蕭公弼是繼王國維、梁啟超、蔡元培等之后,又一位為“美學在中國”作出了重要貢獻的學者,其《美學·概論》不僅“對中國美學具有重要的學科建構意義”[11],還對中國現代美育理論的早期建構與拓展具有重要的意義,并對我們當下的美育研究發揮著啟示作用。首先,蕭公弼美育觀點的提出是以當時社會現實和藝術風貌為基礎的。據蕭氏描述,民國建立后,由于政治劇變,一些“色而淫”的藝術作品充斥著社會,青年男女的審美觀隨之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一股追求欲望滿足、肉體享樂的思潮興起,所以蕭氏倡導“好色而不淫”的審美觀以糾時風。其次,蕭公弼的美育思想立足于中華傳統文化。綜觀蕭氏美育思想,他雖然吸收和借鑒了西方美學,但其思想精髓是儒家文化,同時借以佛學而申發,其“重內而輕外”的美育思想就具有儒家倫理道德教化思想的深刻烙印。最后,蕭公弼點明了美育的最終目標是提升人的境界,所以對于蕭氏而言,美育之學即境界之學。美育不止于藝術創作之教育,也不止于正確的審美觀的培養,而是通過這些教育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實現個人的自由全面的發展,從“以美利利個人”到“以美利利天下”。總之,蕭公弼是一位中國近現代美學史以及美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學者,他與王國維、蔡元培、魯迅、梁啟超一起,為中國美育的現代轉型與理論的早期開拓作出了應有的貢獻,他的美育觀念以及方法論值得我們重視與借鑒。
[1] 蕭公弼.讀康德人心能力論書后[J].學生雜志,1915(6):25-27.
[2] 蕭公弼.釋我[J].學生雜志,1915(3):7-10.
[3] 譚玉龍,朱志榮.論蕭公弼的美學研究方法——兼論其在中國近現代美學史上的地位[J].四川師范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1):109-115.
[4] 葉朗.中國歷代美學文庫·近代卷:下[G].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
[5] 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M]//阮元,校刻.十三經注疏.北京:中華書局,1980:2748.
[6] 曾繁仁.走向二十一世紀的審美教育[M].西安:陜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82.
[7] 高平叔.蔡元培美育論集[M].長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8] 蕭公弼.大戰爭后之新文明[J].學生雜志,1916(3):109-113.
[9] 王國維.王國維文學論著三種[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1.
[10] 譚玉龍.蕭公弼:被遺忘的近代美學學人[J].重慶科技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4):143-144,147.
[11] 黃雁鴻.晚清時期美學在中國的發展歷程與早期留學生[J].人文雜志,2008(5):19-23.
(責任編輯:紫 嫣)
XIAO Gongbi and Early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 Education
TAN Yu-long
(Institute of Media and Art,Chongq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Chongqing 400065, China)
XIAO Gongbi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Chinese modern aesthetics, whoseIntroductiontoAestheticscontains his peculiar and deep thoughts on aesthetic education. For one thing, he differentiates Haose and Haoyin and points out that the former is a human instinct and the latter is the pursuit of sensual pleasure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physical desire. So he advocates the former over the latter. For another thing, He praises the notion of aesthetic education of Zhongnei and Qingwai, because Zhongnei is the inner meaning of arts which can give people an abiding aesthetic feeling and moral meanings. Besides, he calls for the realm of Wangmei, which is not a deliberate realm of morality but an aesthetic realm from the bottom of people′s hearts. It leads to morality and is the mixture of the true, the good and the beautiful.
aesthetic education; Haose instead of Haoyin; Zhongnei and Qingwai; the realm of Wangmei
2017-02-07
譚玉龍(1986—),男,四川樂山人,文學博士,重慶郵電大學傳媒藝術學院講師,主要從事中國美學研究。
G40-014
A
2095-0012(2017)03-004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