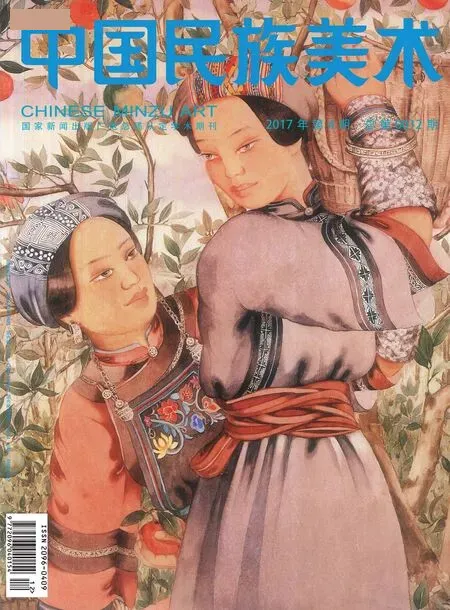青海、西藏地區(qū)民族風(fēng)情寫生見聞
文/圖:王 康

王康中央民族大學(xué)國畫系研究生
藏民族因其生活環(huán)境以及風(fēng)俗文化的獨(dú)特性,一直以來都是中國人物畫家比較喜歡描繪的題材。為了創(chuàng)作出具有生活深度和藝術(shù)價(jià)值的民族題材作品,進(jìn)行實(shí)地考察就顯得尤為重要。只有近距離接觸藏民,體驗(yàn)藏族生活,才能不斷地從生活里發(fā)現(xiàn)美,獲取新鮮的繪畫靈感,為繪畫注入新的活力。中央民族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是我國培養(yǎng)少數(shù)民族美術(shù)人才的國家級(jí)重點(diǎn)高校,民族題材創(chuàng)作在美術(shù)學(xué)院一直是教師教學(xué)和學(xué)生創(chuàng)作的重點(diǎn)。筆者作為中央民族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國畫專業(yè)碩士研究生,本著“從生活中來,到生活中去”的藝術(shù)創(chuàng)作理念,和同學(xué)一起遠(yuǎn)赴西部藏區(qū)進(jìn)行了為期22天的寫生調(diào)研實(shí)踐活動(dòng)。
此次寫生之初,我們先和專業(yè)老師進(jìn)行溝通,將考察地點(diǎn)定在青海省貴南縣以及西藏拉薩市,并針對這兩個(gè)地區(qū)做了一些必要的行程攻略、計(jì)劃,以確保下鄉(xiāng)人員的人身安全和行程安排能夠順利展開。
一、青海貴南縣民族風(fēng)情寫生見聞
貴南縣地處海南藏族自治州的東南部,是典型的以藏族為主的少數(shù)民族聚集區(qū)。在這里我們一共駐留了兩周的時(shí)間,分別去了貴南縣城綜合市場、茫拉鄉(xiāng)、塔秀寺、魯倉寺、文昌廟、森多鄉(xiāng)六個(gè)藏民聚集較多以及藏文化比較原生態(tài)的考察點(diǎn),并針對他們當(dāng)?shù)氐慕ㄖL(fēng)景、服飾、民俗文化等方面進(jìn)行寫生和考察。在貴南縣我們借住在魯倉寺仁愛活佛修建的仁愛智明孤兒學(xué)校里,在這里我們?yōu)檫@里的孩子講了一節(jié)國畫課,希望我們所學(xué)到的知識(shí),能夠?yàn)樗麄兊膬?nèi)心世界多增添一份色彩。我們在貴南通過近距離和藏民進(jìn)行交流,對貴南縣當(dāng)?shù)夭刈逦幕⒚耧L(fēng)民俗有了大致的了解,為我們下一步寫生作了準(zhǔn)備。同時(shí)我們也用手里的速寫本,進(jìn)行了大量寫生,借此加深對藏族各方面的認(rèn)識(shí)。
用繪畫表現(xiàn)藏族題材,藏族人的面貌特征和服飾特征,是區(qū)別于其他民族的兩個(gè)重要的視覺因素。在兩周的時(shí)間里,我們白天出門去寫生、搜集資料,晚上回來就用手機(jī)搜索老一輩畫家的速寫作品觀看,并和自己白天畫的畫進(jìn)行對比學(xué)習(xí),以求在深入生活的同時(shí),畫技也能得到磨煉、提高。就如吳冠中所說:“你一定要穿著大師的拖鞋走一走,然后把拖鞋扔了,在穿和脫的過程中,你就會(huì)找到自己。”在人物形體刻和服飾的表現(xiàn)畫上,我們借鑒學(xué)習(xí)了顧生岳、方增先、陳丹青等畫家的作品,這些藝術(shù)家在藝術(shù)創(chuàng)作生涯中都曾深入藏族地區(qū)進(jìn)行寫生考察,作品技法高超,概括精準(zhǔn),對藏族人的體貌特征把握得十分到位,讓筆者受益良多。藏袍的表現(xiàn)也是另一個(gè)重點(diǎn),藏族人夏季穿著單薄的藏袍或僧衣,他們單薄寬大的衣服看上去和中國古代的長袍大袖服裝有一定相似之處,很適合表現(xiàn)線條的穿插美、疏密美,因此在這方面我們又特意找了元代永樂宮壁畫、明代陳老蓮的《博古葉子》以及當(dāng)代工筆畫家何家英的作品進(jìn)行分析研究,借此提高自己把控形體的能力,同時(shí)也使畫面線條組織安排的能力得到加強(qiáng)。

王康和茫拉鄉(xiāng)念經(jīng)法會(huì)現(xiàn)場的藏族孩子合影 2017年

魯倉寺師傅在畫藏族紋飾

王康在孤兒院給孩子們畫畫

2017年王康在魯倉寺畫速寫

塔秀寺先巴尖措師傅示范藏族僧衣的穿法1

塔秀寺先巴尖措師傅示范藏族僧衣的穿法2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寫生我們還遇到了塔秀寺一年一度舉辦的寺院運(yùn)動(dòng)會(huì)的。運(yùn)動(dòng)會(huì)上,除了常規(guī)流行比賽項(xiàng)目,還有很多他們根據(jù)藏地氣候、地貌,自創(chuàng)的節(jié)目,這也讓我們看到了一個(gè)藏地寺廟與時(shí)俱進(jìn)的一面。期間,我和寺廟里的師傅們一起玩,一起吃飯,用畫筆和相機(jī)記錄了很多珍貴的瞬間,這些資料作為了解藏族同胞的第一手信息,是在校園里每天畫畫所見不到的,它們顯得那么新鮮、有活力,具有濃厚的生活氣息。雖然現(xiàn)在塔秀生活水平還不到三四線城市的水準(zhǔn),但是每個(gè)人的臉上都是平和的、幸福的、滿足的,這種氣氛無形中感染了我,讓我越來越體會(huì)到寫生對于藝術(shù)創(chuàng)作的意義。藝術(shù)創(chuàng)作需要情感基礎(chǔ),這些情感,都是來自于生活,就像畫家華君武所說:“畫家創(chuàng)作猶如戀愛,要先有感情才能結(jié)婚,結(jié)婚才能生孩子。”而反觀現(xiàn)在很多人物畫家,都是通過在網(wǎng)上找照片,進(jìn)行拼湊制作,因?yàn)槿鄙賹?shí)地考察和體驗(yàn),畫面無法注入作者對內(nèi)容題材的情感沖動(dòng),導(dǎo)致最后的作品,像是一件工業(yè)產(chǎn)品一般,情感冰冷,既無法觸動(dòng)畫家自己,也無法打動(dòng)別人。藝術(shù)來源于生活,光有技術(shù),無法成就自己,成就畫作存在的永恒意義。
二、拉薩市民族風(fēng)情寫生見聞
寫生實(shí)踐的第二站為西藏拉薩市,在雪頓節(jié)期間重點(diǎn)參觀考察了哲蚌寺。
雪頓節(jié)一般在陽歷8月21日,也即藏歷六月三十日開始。“雪”在藏語中為酸奶的意思,“頓”表示“宴”“吃”的意思,“雪頓”即酸奶宴會(huì)。拉薩雪頓節(jié)起源于公元11世紀(jì)中,是藏族一個(gè)重要的節(jié)日。在雪頓節(jié)期間,拉薩市有規(guī)模盛大的曬佛儀式,以及藏戲表演、羅布林卡狂歡等活動(dòng)故亦稱為“曬佛節(jié)”其中第一天的曬佛儀式則最為隆重和最具代表性。
哲蚌寺是雪頓節(jié)舉行曬佛儀式的主要寺廟之一,規(guī)模最是盛大,這里除了曬佛,還有地道的藏戲表演。此次演出,藏戲表演者們身著傳統(tǒng)藏戲服裝進(jìn)行了幾大段不同內(nèi)容和不同形式的演出,藏戲有別于東部漢族各地方戲種,語言、服飾、道具、形式以藏文化為根基,帶有濃濃的藏族特色,內(nèi)容上也以表現(xiàn)藏族生活文化為主。在表演過程中,舞蹈編排或氣勢開張,震撼人心,或肅穆靜止,氣壓全場,唱戲者時(shí)而引吭高歌,時(shí)而行走沉吟,舞蹈動(dòng)作不時(shí)穿插期間,甩袖、旋轉(zhuǎn)、交叉舞蹈等,引領(lǐng)著每一位觀看者的心情跟著整個(gè)戲曲的節(jié)奏跌宕起伏,動(dòng)作優(yōu)美流暢,充滿了張力,這充分體現(xiàn)出了藏族是一個(gè)能歌善舞的民族,也強(qiáng)烈地震撼了筆者的內(nèi)心。通過觀看這次演出,筆者聯(lián)想到了已故人物畫家李伯安的著名作品《走出巴顏喀拉》,厚重闊達(dá)的畫面,在表現(xiàn)藏族日常生活以及精神生活的深度上,可以稱得上是典范之作。其中的第八部分內(nèi)容表現(xiàn)的就是我這次觀看的藏戲。李伯安在創(chuàng)作上,通過多次深入寫生考察,將藏戲的精神和自己的觀看感受融合,用畫筆寫出了自己心中的藏戲,這不是原搬照抄現(xiàn)實(shí)的藏戲情節(jié),而是畫家在心性流露的基礎(chǔ)上進(jìn)行的藝術(shù)升華。吳冠中曾說:“藝術(shù)發(fā)自心靈與靈感,心靈與靈感無處買賣。藝術(shù)家本無職業(yè),最重要的是思想——感情。”這次觀看藏戲,熱烈、生動(dòng)的舞蹈打動(dòng)著人心,讓筆者本人對西藏的愛,也無形中從表面滲入了內(nèi)心。

塔秀寺運(yùn)動(dòng)會(huì)中場休息

哲蚌寺曬大佛現(xiàn)場

哲蚌寺藏戲表演
這次下鄉(xiāng)寫生考察,筆者得到的并不只有手頭功夫的提高,伴隨的還有眼界的開闊,胸襟的豁達(dá)。沒有技術(shù)畫不成創(chuàng)作,沒有氣度畫不好創(chuàng)作,而雪域高原高山大河帶給每一位藝術(shù)家的都是全面的震撼和洗滌。就像20世紀(jì)80年代轟動(dòng)畫壇的陳丹青畫的《西藏組畫》一樣,半年的寫生帶給畫家的不只是作品的成功,多年后面對自己的這組畫,他感慨地說道:三十多年前我既不曾意識(shí)到這些,也根本不想它,只是自顧自地畫,日后,紐約的漫長生涯將我的過去逐漸推遠(yuǎn)、隔斷,新世紀(jì)回國再看這些小畫,當(dāng)年假想的所謂“歐洲”美學(xué)消失了,像是很久以前讀過的翻譯小說,忘了情節(jié),忘了當(dāng)初何以為之動(dòng)容。舊作卻是歷歷在目,以每一個(gè)細(xì)節(jié)提醒我:這是我年輕時(shí)代在拉薩畫的畫:既不是蘇聯(lián),也不是法國,我終于明白過來,倘若沒有畫中一個(gè)個(gè)美麗的西藏男女賞我激情與能量,我不可能畫出這批畫。

走出巴顏喀拉之八 藏戲 李伯安 紙本國畫 18800cm X12150cm 1998年

辯經(jīng) 王康 紙本速寫 29.5cm x 14.8cm 2017年

茫拉鄉(xiāng)念經(jīng)現(xiàn)場 王康 紙本速寫 39cm x 14.8cm 2017年

藏族僧人 王康 紙本速寫14.8cm x 29.7cm 2017年

先巴尖措 蘇泉 紙本速寫 25.3cm x 35cm 2017年
三、寫生總結(jié)
下鄉(xiāng)寫生實(shí)踐,和當(dāng)?shù)夭孛翊虺梢黄苤匾诨ハ嘧鹬亍⒂押媒涣鞯幕A(chǔ)上,再去實(shí)踐寫生,才能更深入地了解他們的生活、風(fēng)俗,獲取到第一手的原始資料。這次自發(fā)的藏區(qū)寫生之行,共歷時(shí)22天,大量、集中的速寫訓(xùn)練,加上新環(huán)境的感染,讓我對寫生有了一個(gè)新的認(rèn)識(shí)。寫生不僅僅只是對所見到的人物進(jìn)行一個(gè)單純的“日記”式的描繪,還涉及所處的環(huán)境、道具、畫家當(dāng)時(shí)的心情以及繪畫的狀態(tài)、畫面取舍和構(gòu)圖等多方面的能力,它是對畫家繪畫能力從內(nèi)到外的立體式的考核和鍛煉。這次寫生還使自己對藏族文化方面的認(rèn)識(shí)以及知識(shí)儲(chǔ)備都有了一個(gè)全新的改觀和提升,讓自己以后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可以更加全面立體地去看待“藏族”這個(gè)繪畫題材。藝術(shù)創(chuàng)作離不開技術(shù),更離不開真切的感受,實(shí)地考察走訪所得到的感受和靈感以及在實(shí)地考察中看到、聽到、聯(lián)想到的一切,對一名畫家來說都是不可復(fù)制的精神財(cái)富。深入生活,用寫生帶動(dòng)創(chuàng)作,不僅僅只是對繪畫技術(shù)的訓(xùn)練,還有各地方豐富的傳統(tǒng)文化給畫家?guī)淼撵`魂的洗禮,這些都會(huì)讓畫家更深刻地感受生活之美。
- 中國民族美術(shù)的其它文章
- 中國民族美術(shù)
- 金源文物的一縷燦爛輝光—金源地區(qū)出土的兩件鎏金文物賞析
- 六十年特色辦學(xué)一甲子春華秋實(shí)—內(nèi)蒙古藝術(shù)學(xué)院建校60周年美術(shù)教育及美術(shù)創(chuàng)作述評(píng)
- 專業(yè)突出 特色發(fā)展—關(guān)于中央民族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民族美術(shù)教育”問題的專訪
- 綜合培養(yǎng)、復(fù)合多元
——中央民族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美術(shù)教育專業(yè)的成長歷程與教學(xué)特色 - 探析包裝設(shè)計(jì)中的蒙古族元素—以內(nèi)蒙古地區(qū)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