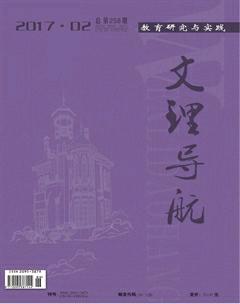深入靈魂的熱愛
李若曈
“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往事如水東流,仍知的誠然已經不多。能夠清晰記得的,依然還有那婉轉吟唱著的女聲。悠揚的古曲領著一個懵懂年幼的我,就那樣走進了絢爛的詩詞世界。
南唐后主的《虞美人》,是我真正接觸的第一首詞。太白之《靜夜思》、子美之《絕句》,樂天之《賦得古原草送別》……在我與這首小令邂逅之前,早已熟記這些人人能誦的詩歌,但此前的吟誦,于我不過是咀嚼些枯燥無味的字眼而已,其中的韻味與深意卻不得而知。而當五六歲的我聽罷這一首《虞美人》,卻無故郁悶起來,好像隱隱知道這些字句的背后是一抔無盡感傷的淚水。李后主的愁腸,如一把啟蒙的鑰匙,帶我領略了詩歌詞曲迷人的魅力。自此,它們便漸漸成為我深入靈魂的熱愛,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后來上了小學,在老師的督促下,教室里人人都捧著一本《小學生必背古詩詞》。老師說,每背過一首,就可以找班干部檢查,并且在詩歌的頁眉上獎勵一朵小紅花。這樣每到學期末,班里同學都要比比誰背得最多。同學們都不甘示弱,而我總是那個最最積極的身影,時時刻刻追著學習委員背詩,惹得她忍無可忍。我確乎是這樣成為班里的“古詩詞背誦大王”的。后來“大王們”進行了詩詞擂臺賽,誰也不服輸。在最后關頭,我靈光乍現,用一句老嫗能懂的“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成功擊潰了對決的實力選手。再后來的畫面,便是拿著獎狀站在講臺前自信地微笑著的我。
后來在同學們還糾結于詩詞本后面的長詩時,那被我早已翻爛的《小學生必背古詩詞》已經被收拾進書柜,取而代之的是一本《初中生必背古詩詞》。四年級的時候已然沒有了評比活動,而我依然堅持吟誦著我所熱愛的詩詞。民歌《木蘭辭》、孟德之《龜雖壽》、《觀滄海》?這些或洋溢民風或氣勢磅礴的文字,同年幼的時光一起深深烙印在心上。那些融入濃情的語言,漸漸地與我的身心結合,如今竟這樣密不可分。上了初中以后,老師沒有再要求課本之外的詩詞背誦,那兩本必背詩詞,也成了閑時翻閱的回憶。當時的我更愿意去讀一讀《宋詞三百首》,以及一些有關詩詞的書籍。熟悉網絡之后,我開始嘗試自己作詩。那時詩雖然已經讀過不少,但我對聲調格律依然一竅不通,寫出的也不過是些不成章的散句。如今再讀那些稚嫩的詩句,每每忍俊不禁。可是正是由于我的無知,才敢于在臥虎藏龍的詩詞論壇上發表拙作,懵懵懂懂地闖進了更加深邃的詩詞大門。
后來再讀人詩,讀己詩,請教前輩批評,自己揣摩字句。如此積累經驗,加之對創作方法的學習?一年有余的錘煉,使我相較于此前那個無知大膽的初生牛犢,已有了很大的進步。我也能著手作一作律詩、填一填詞譜了。
現在,我依然熱愛詩詞,我愛它就如同我熱愛生活。我品讀那些愈久愈香的文字,如同閑暇時光品味一杯經年醇酒;我作抒情懷景的詩詞,如同以生活為酒曲,學前人釀一壺小酒,自斟自飲,自娛自樂。我以心情入筆,以靈魂為伴,做屬于自己的春秋大夢。
翻開一頁宋詞,在迷人的字句里尋一座青山,游一湖綠水,體會千千萬萬種情懷。讓自己的靈與肉,融進古典的光陰。而你所必需的唯一途徑,便是深入靈魂的熱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