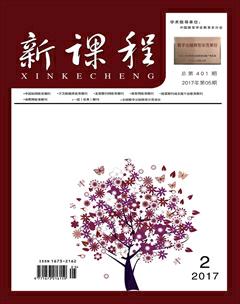面對留守兒童:“快”和“慢”的調控不可或缺
李利平
摘 要:走進留守兒童的內心,需要“快”,也需要“慢”,關鍵就在于教師在這種“快”與“慢”的調控中,是否真正走進了留守兒童的內心,是否以一種喚醒和解放的力量參與了他們的光合作用?無論快慢,都應該從基于留守兒童,體貼留守兒童,扎根于留守兒童真正的內心出發,真正為留守兒童打下學習、精神和健康的底子。
關鍵詞:留守兒童;快與慢;兒童視角
不可否認,近年來留守兒童的心理健康問題進一步加劇:焦慮、畏難、自卑、膽小、敏感、孤僻、壓抑、敵對、失望、不安、孤立……一些留守兒童家長重養輕教、重智輕德、重物質輕精神、重管教輕溝通——“成人總是習慣于以自己的感受判斷兒童的感受,置換兒童的體驗,最終改寫了兒童的真實處境。”那么,如何剝離和剔除這些粗糙的東西,讓留守兒童的生命更敞亮呢?一些教育的先行者,通過改善師生關系,在“快”和“慢”的調控中,走進了孩子的心靈深處,一起參與了留守兒童的生命成長,將“特別的愛獻給了特別的你”。
所謂“快”,是指教師要快速進入留守兒童的內心。比如,新接一個班,或者新轉來一個留守兒童,第一時間就應當記住留守兒童學生的姓名,了解他們的性格、愛好、特長以及可能的“短板”……一周后就應該建立比較全面的“留守兒童成長記錄袋”。更重要的是,教師要快速了解留守兒童的過去,把現在和過去“藕斷絲連”的地方做對比,從而做出準確而細微的甄別、診斷和梳理。在此基礎上,立即和這些孩子的家長取得聯系,協商并制定“留守兒童”之教育方案。
【案例一】
樊某,父母親都到南方打工,留下她和爺爺生活,家境比較貧苦。由于爺爺和她幾乎不怎么交流,但又嚴格限制她和鄰居玩耍,所以孩子從小就顯得內向,不愛說話。平時上課她幾乎都低著頭,不敢舉手,不敢看老師,不敢說話,一旦讓她說話就顯得特別緊張,語無倫次,結結巴巴。下課時,其他學生在操場做游戲,盡情釋放自己,唯有她,默默無語,獨自坐在教室里或者站在一旁觀看。
我了解這一情況后,立即和她的爺爺取得聯系,多渠道、全方位地向她的爺爺普及家庭教育知識,端正其家庭教育的方向,樹立為國教子的正確觀念,掌握科學的教育方法。同時,立即和其他任課教師達成共識,形成教育合力,快速給予留守兒童溫暖和愛,共同為留守兒童營造良好的教育氛圍。上課時多關注這個特殊的孩子,課余時間如何讓這個孩子融入其他孩子的游戲和玩耍中,讓教育的更多陽光頻頻播灑在留守兒童的頭頂。
事實證明,有些事是不能等的,好的教育就是在惡性循環還未開始之前,就在留守兒童的心田播下“愛、責任、尊嚴”等精神層面的種子,就給予他們實實在在的“正能量”,就首先在觀念、心態、情感方面積極轉變,使之轉向一個更活潑、更靈活、更高效的方向,正所謂:“經驗、技術的問題尚可修修補補,思想、觀念的貧血則是一個異常危險的傾向。”面對留守兒童,教師應該及時快速杜絕這種“傾向”,讓留守兒童首先在精神層面上轉入正常的軌道。
所謂“慢”,是指不要急于求成,不要急于對孩子的錯誤或者行為急急忙忙“蓋棺定論”。“慢一些,再慢一些”,通過“慢鏡頭”去觀察、放大、細化留守兒童的問題,從而找到一種開啟他們心靈的密碼,這是走進留守兒童心靈深處最重要的視點之一。
【案例二】
曹某,父母在外地打工,從小由姨媽帶大,上課注意力不集中,喜歡隨意插話,調皮搗蛋,經常起哄,有時還愛做小動作或危險動作,影響他人學習,經常不做或少做作業;至于捉弄同學、打架鬧事則更是他的家常便飯。任課教師和班里的同學都非常厭惡他,不愿與他相處。
面對這樣一個學生,疾風驟雨式的教育肯定不管用。怎么辦?我想,唯有慢下來,耐下心來了解事情的來龍去脈,去進行一點一滴的改進,進行“潤物細無聲”的滲透和影響,才是解決問題的方式之一。想到這一點,我決定不急于處理這個孩子,而是每天陪他一塊兒上操、一塊兒玩耍,一塊兒做作業……盡可能和他做朋友,盡可能通過家訪等多種渠道去了解事情背后“隱形”的真相——所謂的故意搗亂,其實是想通過犯錯引起教師或他人的關注,這種心態叫關注饑渴,是缺乏父愛和母愛引起的……最終,經過三個月的努力,這個孩子終于改變了,不再任性調皮,不再打架鬧事……
可見,當教師或成人慢下來時,以一種“老牛耕地”式的方式進入孩子的內心時,才有可能找到一種更為柔軟、溫潤、靈活的教育方式。正如畢淑敏所說:“別人強加給你的意義,無論它多么正確,如果它不曾進入你的心理結構,它就永遠是身外之物。”
走進留守兒童的內心,需要“快”,也需要“慢”,關鍵就在于教師在這種“快”與“慢”的調控中,是否真正走進了留守兒童的內心,是否以一種喚醒和解放的力量參與了他們的光合作用?無論快慢,都應該從基于留守兒童,體貼留守兒童,扎根于留守兒童真正的內心,真正為留守兒童打下學習、精神和健康的底子。
參考文獻:
[1]林茶居.我們需要什么樣的“減負”[J].教師月刊,2013(4).
[2]張華.教師:做思想的舞者和歌者[J].福建教育(小學版),2013(5).
編輯 孫玲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