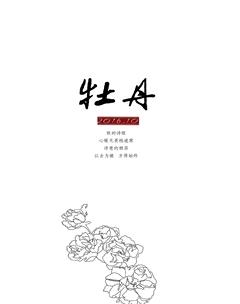水文化與當代江蘇鄉土小說的審美選擇
劉錚
水文化是江蘇傳統地域文化中最根本的代表性文化,水文化影響著江蘇作家尤其是鄉土文學作家的創作追求和審美選擇。一方面,在水文化的滋養下,當代江蘇鄉土小說作家有著較為相似的創作傾向和審美選擇;另一方面,更新發展著的江蘇鄉土文學又不斷為江蘇地域文化注入新的審美內涵。
丹納在《藝術哲學》一書中,明確把地理環境與種族、時代并列,當作決定文學創作的三大基本要素。錢穆先生也說過:“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究其根源,最先還是由于自然環境有分別,而影響其生活方式,再由生活方式影響到文化精神。”地域文化亦非簡單的地理概念,其核心和精髓乃是人文精神。地域文化與一地的人文風貌、人文氣質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同樣影響著一地作家的文學創作和精神氣質。深入研究一地文學、一地作家群體或者一種文化現象,地域文化是相當重要的一種參照。研究文化與文學之間這種雙向互動關系,無論對文化還是對文學都是有益的。
孕育華夏文明的長江和黃河兩大水系在黃海和東海之濱沖積出連綿千里的平原、丘陵、河網、湖泊和大陸架,這使位于長三角地帶、東南沿海地區的江蘇濕潤多雨,水網稠密,地域文化呈多樣風貌。多元文化對江蘇區域人文精神產生了綜合性的影響。江蘇地區不僅有平原文化和山文化,亦有水文化,三者交融共同孕育了江蘇人文精神。江蘇地域文化雖然多樣,但最根本的還是水文化。水本無形,卻隨物賦形,包容萬物,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先。老子也曾說:“上善若水。”水,不僅體現著一種自由自在無拘無束的生命狀態,更具水滴石穿、刀斬不斷的韌性精神,這種文化特點對江蘇文學的影響在于,古往今來生長于這方土地的文人騷客大多以詩意的審美理想作為畢生的創作追求,所謂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地文化孕育一方文學,“這種詩意文化氛圍從古至今繚繞不絕,在它潛移默化的熏染下,江蘇作家的內心深處都或多或少潛藏著一脈文化鄉愁”。另一方面,傳統儒家文化對江南的滲化較之中原為淺,儒家文化中傳統的意識形態,如道德本位、官本位、長者本位等思想,對江蘇作家的影響亦不大,因此江蘇文學,尤其是描寫故土人情的江蘇鄉土文學作品中所表現出的有意或無意對政治的疏離,或是即使碰觸也從不針鋒相對的態度,成為一種饒有意味的文化現象,這一點在江蘇當代鄉土小說創作中表現得尤為明顯。
汪曾祺曾說:“我的家鄉是個水鄉,我是在水面上長大的,耳目之所接,無非是水。水影響了我的性格,也影響了我的作品的風格。”他的鄉土小說創作幾乎全部圍繞著故鄉高郵的民俗風情、景物風貌展開,淡化小說情節,筆下的人物具有濃濃的生活趣味和樸實的民間色彩。汪曾祺不止一次提到:“我寫的是美,是健康的人性,從此之外,別無其他。”《受戒》中作者將故事背景安排在一幅精心描繪的水鄉風景畫里,沒有情節的起承轉合,只描述一個叫明子的小沙彌幫小女孩英子干農活,小英子擺渡送明子去受戒的尋常生活,然而那種似在河水中流淌著的若有若無的干凈純粹的情愫卻感動了無數讀者,這個犯了清規戒律的小和尚雖然觸犯了禁忌,但也正因此獲得了人們的喜愛。《大淖記事》中女人們沒有“規矩”,男人一般隨心隨性地生活,都顯示了作家對自然自在生命狀態的肯定和期待,充滿了詩性文化和自由精神。這是汪曾祺的創作原則使然,他認為好的文學應讓人感受到愛。那么,什么是愛?他說:“愛,是一件非專業的事情,不是本事,不是能力,不是技術,不是商品,不是演出,是花木那樣的生長,有一份對光陰和季節的鐘情和執著。一定要,愛著點什么。它讓我們變得堅韌,寬容,充盈。業余的,愛著。”
高曉聲作為當代江蘇鄉土小說的代表人物,在農民形象的塑造上也頗具特色。他從來沒有旗幟鮮明地發出口號,而是在細微處用筆,細節處顯現,頗有靜水流深的意味。縱觀他的一系列以家鄉蘇南農村生活為題材的小說,都有一個鮮明的共性:以普通農民的生計小事反映農民坎坷命運和時代的大主題。從《李順大造屋》到《漏斗戶主》《揀珍珠》,寫的都是普通農民的日常生活小事,而這看似針頭線腦兒的問題放在歷史長河中卻有著時代和歷史的高度,他的“陳煥生系列”通過對新時期農民陳煥生形象的塑造,成功揭示了思想意識深處的奴性絕非僅靠社會改良或經濟上的翻身就能鏟除。作品以對人性陰暗面的深徹洞察為新文學提供了一個具有典型意義的“新時代阿Q”形象。這種不即不離的姿態,既不是那么決絕地不聞不問,也不那么激情洋溢地投入,這是其背后深厚的地域文化傳統使然。
而這種特色在晚近的江蘇作家范小青、趙本夫、葉兆言、蘇童、荊歌以及畢飛宇等當代江蘇作家身上都有不同程度、形式各異的體現。
以范小青為例,這位來自吳地蘇州的女作家有著與汪曾祺相似的鄉土情結,她說:“我就是被浸染和淹沒在漫長無邊的文化和歷史中,所以,在許多年的寫作中,我筆下的人物和事情,無論如何也離不開這種特定的色彩。”范小青的創作不僅浸潤著吳地水文化的獨特韻味,更在城市化不斷推進的當下書寫著吳文化的精神。從《城市表情》到《女同志》,再到《城鄉簡史》《赤腳醫生萬泉和》,她筆下的人物既有干部、進城的農民工,也有堅守土地的農民,“城里人”和“鄉下人”在小說中相遇,展開一段段故事。《赤腳醫生萬泉和》更是以小見大,以萬泉和這個小小的鄉村赤腳醫生的命運寫出了“一個中國鄉村醫學簡史,更是一個中國江南鄉土社會史與文化史”。在范小青的敘述中我們可以感受到作者的冷靜態度,她始終與敘事客體保持著一定的情感距離,即使是重大歷史事件她也輕描淡寫,有意淡化。這種疏離,正是她追求的一種創作姿態和敘事技巧,也是她在水文化浸染下的一種自然選擇。一方面關心政治,但更關心小人物的命運;一方面淡化政治,但卻緊緊跟隨時代腳步。表面上看似矛盾,但這正是范小青介入現實所采取的獨特的敘事姿態。正如范小青本人所說的那樣:“我是努力把生活化開來,一點一點地寫出來,無論是不是史,無論是什么史,小說應該將這些史放在小說的背后,所以我盡量少寫政治的背景,少寫‘文革,也沒多寫改革,知青和下放干部也都是次要的,都是很快就過去的,只有農民,只有萬泉和和萬人壽,永遠在那里。史在他們身上。”
所謂文化基因,就是決定文化系統傳承與變化的基本因子、基本要素。水是江蘇文化的基因,她溫婉柔美、靈動鮮活,又至柔至剛、剛柔相濟。無論靜水流深還是洶涌澎湃,水是永不止息的,這決定了江蘇鄉土文學是動態的,發展的,也將源源不斷地帶給我們新鮮的閱讀體驗。
(江蘇警官學院)
基金項目:本文為江蘇警官學院院級科研項目“城市化進程中當代江蘇鄉土文學的地域特色呈現研究”(編號:2014SJYSY08)成果;江蘇高校品牌專業建設工程資助項目(T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