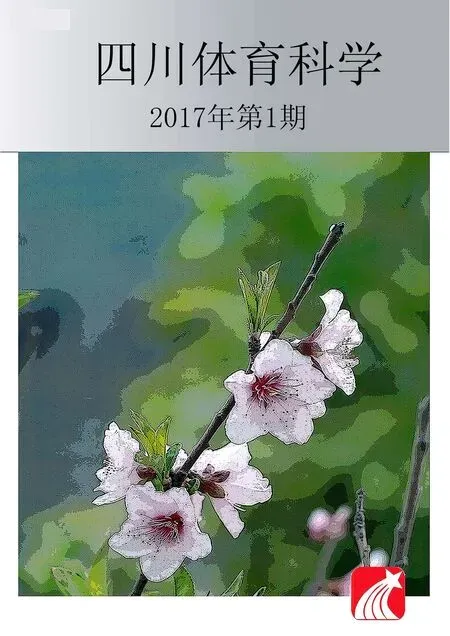近現代以來我國鄉村武術社會結構變遷研究
孫向豪
?
近現代以來我國鄉村武術社會結構變遷研究
孫向豪
近現代以來,西學東漸使我國鄉村社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武術作為鄉村文化的一部分,也發生了很大改變。本研究運用文化學、歷史學、社會學的理論與方法,以重大歷史事件為結點,在界定鄉村武術社會結構的基礎上,分析了鄉村武術生存環境、習練人口、經濟基礎、技術思想等社會構成要素的具體變化,有利于系統認識鄉村武術社會結構的具體變化。
近現代;鄉村;武術;社會結構
宋朝以后,中國武術的發展開始由官方與主導地位逐漸向民間轉移,并在農耕倫理社區中形成了以家族、血緣、師徒、幫派為特征的傳播主體,構成了獨特的社會群體與文化形態,彰顯出有別于其它組織的結構形式。但是,近現代以來,隨著清末民初武舉制退出、中央國術館建立、武術救國論等現象的發生,使鄉村武術社會結構逐漸打破了家族、血緣、師徒等固有模式,開始在清末民初的社會動亂中廣泛向社會傳播,到新中國建立與改革開放,已逐漸突破鄉村走向全國與世界,不僅走出了董海川、郭云深、張文廣、梁以全等一批武術名家,而且出現了一些對武術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重要村落,如陳式太極拳的發源地陳家溝村、塔溝武術學校所在地塔溝村、萇家拳的所在地萇村等。那么,是什么樣的時代背景和因素使鄉村武術文化對近現代以來中國武術的傳承傳播產生重大影響,在這一時代變遷的重大改變中鄉村武術社會結構究竟發生了哪些變化?本研究將運用社會學、歷史學、文化學的理論與方法,以近現代以來的重大歷史事件為結點,對鄉村武術社會結構的變化進行分析。本研究的完成有利于系統認識鄉村武術的變化,分析鄉村武術社會結構變遷的利弊得失,可為中國武術在鄉村社會中的開展提供一種思路和依據。
1 古代鄉村武術的社會結構
社會結構指社會整體的基本構成要素以及它們之間相對穩定的關系[2]。包括環境、人口、組織、經濟、藝術等各要素。基于這種解釋,古代鄉村武術的社會結構,即鄉村武術社會整體的基本構成要素以及它們之間相對穩定的關系。包括鄉村武術賴以生存的社會環境、武術人口、武術組織、武術從業的生存狀況、武術技術與思想等各方面要素,及其所形成和維持的相互關系。在長期的歷史進程中,我國社會形成了以農業為主的超穩定型的社會結構形態,不論是在鄉村還是城市,除了人口的增長外,構成社會整體結構的各要素幾乎沒有發生大的變化,所以黑格爾說“中國歷史從本質上看是沒有歷史的,它只是君主覆滅的一再重復而已。”同樣在近現代以前,構成我國鄉村武術社會結構的各要素也一直生存于超穩定的農耕倫理社區中,生存環境沒有發生過根本性質的變化。武術人口是以鄉村紳士與地方精英構成其主要傳播群體,并依托于家族、血緣、幫派、師徒等倫理關系形成了鄉村武術的組織形式;其經濟來源除了自身的農業耕種外,額外多出了徒弟逢年過節的禮拜、押鏢護院等額外收入,擁有較高的社會威望與良好生存狀況。武術技術與思想在農耕倫理社區的宗法與準宗法環境中,受兵、儒、道、佛、醫等各家思想的影響,形成內容豐富、形式繁多的武術技術體系。
2 近現代以來鄉村武術社會結構的時代背景及其變遷
2.1 清朝末期的社會動亂與鄉村武術社會的變遷
清王朝在經歷康乾盛世之后,長期穩定的社會環境使統治者安于現狀、疏于管理,造成各級統治者日趨腐敗,伴隨而來的是人民賦稅加重、各級剝削增加,使國內階級矛盾日益激化,全國各地反抗斗爭不斷。同時期,以英法為代表新興起的西方國家,正以現代科學技術進行著全球性的殖民擴張,而清王朝的閉關鎖國卻使英法等國家在與我國的經濟貿易中長期處于逆差之勢,由此而拉開了第一次鴉片戰爭的序幕。從嘉慶年間的白蓮教起義到天地會、天理教、捻黨、義和拳等遍及全國的秘密結社,加上二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入侵、甲午戰爭、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等大的社會事件,國內國際兩方面的矛盾進一步加劇了清朝的社會動亂。
在這種社會背景下,鄉村武術社會結構的各方面都發生著相應變化。在社會環境方面,雖然鄉村武術所處的農耕倫理社區沒有發生變化,但是宏觀社會環境的變化卻為鄉村武術提供了一定的傳播空間和機遇;在人口方面,為了鎮壓反抗運動,清朝統治者明令禁止習武活動,使城填的習武活動明顯減少,但在鄉村社會由于地處偏僻、分布較廣,不利于監督和管理,就成為了孕育武力的反抗溫床,是此一時期武術傳播的主要陣地。如影響較廣的義和團運動,本屬鄉團,由梅花拳師趙三多將其改名為義和拳[1],后得到各地教會的廣泛響應,逐漸發展成為義和團。在匪盜猖獗的社會環境中,為了保障人身與財產安全,鄉村居民習武自保,不僅許多民眾自發拜師學拳練武,而且許多教會也吸納了大量的鄉村民眾,使此一時期鄉村武術人口達到鼎盛;在組織方面,雖然清朝末期社會動亂不堪,但基于農耕文明的家族、血緣等社會機制卻沒有發生改變,而且由于教會、幫派等秘密結社的參與,進一步加固了家族、師徒制的組織形式與傳承制度;在經濟方面,雖然此一時期社會動亂,人民難于生計,但鄉村武術習練者較之于其他民眾來說,卻具有經濟與地位的雙重優勢;在技術與思想方面,各教會為了吸引拳眾,打出了“畫符念咒”“降神附體”“刀槍不入”等神秘主義色彩,雖然一方面為武術蒙上了深深地封建迷信烙印,但在另一方面教會林立、各自獨立的現象卻進一步推進了門派與拳種的豐富。
2.2 民國期間的愛國運動與鄉村武術社會變遷
伴隨著西方列強逼迫我國簽訂了一系列不平等條約,我國社會精英開始反思局勢,進行變革圖強。民國期間無論是新文化運動的理論爭鳴,進行科學民主救國,還是國共合作共同抵抗日本帝國主義入侵,社會各界建立了廣泛的愛國同盟。武術也開始在此一時期從政府打壓的俗文化現象,登上與國家命運相關的歷史舞臺,不僅出現了“土洋體育之爭”的理論爭鳴,而且從精武體育會到中央國術館,武術成為了那個時期尚武救國的一種具體實踐和重要思潮。
在這種背景下,我國鄉村武術存在的各方面也發生著相應的變化。在生存環境方面,雖然武術所處的農耕社會生產環境沒有發生變化,但軍閥割據、日本入侵等背景卻使鄉村武術文化的生存環境處于亂世之中,這一方面造成了許多武力盜匪;另一方面也使一批有識之士走出鄉村,投軍從戎加入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英勇對抗。在人口方面,進一步的社會動亂,加劇了社會安保力量的缺失,同時由于尚武精神的提倡,使此一時期鄉村武術的傳播得到了進一步的推廣;在組織方面,民國所建立的一套管理機制使鄉村武術民眾也逐漸加入到其中,如杜心武曾被第一屆國術國考聘為評判員,又如在1928年和1933年舉辦的兩次國術國考中,有許多參賽選手都是來自于鄉村社會,他們通過縣級、省級的層層選撥,最終沖入國考,如張文廣教授;在經濟方面,國家動亂,經濟凋敝,鄉村社會更顯貧乏,此一時期一些鄉村習練者雖然選擇了進入軍隊以改變其農民地位,但就大多數而言其生存狀況堪憂;在技術與思想方面,民國期間中西文化進入了全面沖突與爭論的時代,上演了春秋戰國時代式的百家爭鳴。在這種背景下,土洋體育之爭、科學化的國術、中華新武術等掀起了武術改革的高潮,豐富了武術技術與思想,這雖然沒有在鄉村社會全面普及,但已通過一些鄉村精英開始向鄉村社會逐漸滲透。
2.3 新中國初期的鄉村治理與鄉村武術社會變遷
新中國成立初期由于系統的國家管理體系尚未建立,原來的鄉村管理尚未打破,加之國民黨余力,社會匪亂遺留,使維護社會穩定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首要難題。據統計,自1949年至1950年3月,共發生已遂和未遂的較大的反革命破壞事件253次[3],1956年9月至1957年3月半年時間內,全國發生了少數工人罷工、學生罷課、農民鬧退社鬧缺糧、復員軍人請愿(少數人鬧事)式的群體性事件……在農村也連續發生了鬧社的風潮,如浙江省的農村發生請愿、毆打、哄鬧等事件一千一百多起[4]。在這種背景下,重整鄉村,消除和打擊一切鄉村團體和結社,對其進行徹底性改革就成為了中國共產黨的必然選擇,在這種背景下,帶有濃重家庭、血緣色彩并具有武力性質的群體,成為了改革的必然對象。
在這種背景下,此一時期鄉村武術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巨大改變,表現為農業生產方式打破了原來的小農耕作,轉變為集體耕種,其實質是國家權力在鄉村社會的全面延伸,使原來處于邊緣的、帶有秘密性質的武術傳承,被納入了國家的管控之中。在人口方面,由于國家穩定與管理的需要,開始控制鄉村居民的武術習練,并通過發動文化大革命、國家的統一管理(競技武術的建立)、反四舊等活動逐漸消減鄉村武術人口,使鄉村武術的習練由公開轉為地下,由廣泛傳播轉為私下傳授,造成鄉村武術人口的大量消減;在組織方面,生存環境的變化與現代國家管理制度的延伸,使家族、血緣、幫派等具有宗法與半宗法性質的武術組織與管理在鄉村社會產生了斷裂性轉變,但由于國家經濟、管理方式等方面建設尚未完善,對鄉村武術的直接管理只延伸至縣一級,使鄉村社會的武術組織與管理近乎停滯;在經濟方面,由于整個鄉村社會治理的改變,不僅武術被封為四舊為人拋棄,而且武術習練者還被作為反革命,在鄉村社會慘遭淪落,成為了邊緣人,其生存現狀岌岌可危;在武術技術與思想方面,由于這一時期對武術的管控與打擊,不僅大量武術習練者放棄其技藝,而且大量的武術書籍被燒毀,一些武術拳種在此時期走向消亡。
2.4 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與鄉村武術社會變遷
新中國成立至改革開放前,我國社會面臨著國內重建與國際圍堵的雙重壓力,為了快速建立一個現代化國家,政府不僅通過剪刀差的方式把大量的農業資本集中起來以支持國家工業化建設,而且還通過大躍進、上山下鄉等方式向鄉村轉價,使本已破落的鄉村社會更顯凋敝。一系列事件為改革開放提供了前提,從1978年安徽省鳳陽縣小崗村開始實行“農村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到劃立經濟特區、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明確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的重要組成部分,國家經濟的提升使鄉村經濟得到了發展與緩和。隨著鄉村物質生活的豐富,文化活動重新成為了人們生活的必要內容,鄉村武術活動在此時期,得到了新的復蘇和繁榮。
在此時期,鄉村武術的生存環境重新回到了小家經濟型的農業文明基礎,但由于農業現代化的推進,工業化的生產方式提高了農業生產力與生產價值,同時由于國家工業化、城市化的加快,使鄉村武術的生存環境較之于近現代以前有了根本性改變。在武術人口方面,由于文革導致的文化生活貧乏,致使此一時期的武術活動受到了熱烈追捧,如電影《少林寺》的上演,使十里八村的居民爭相觀看,許多少年因此而開始了自己的習武生涯,以至從20世紀80年代至21世紀初,我國各地鄉村出現了大大小小的武術學校,有研究顯示,2001“河南省已注冊武校有421所”[5];“除西藏自治區外幾乎所有省、市、自治區、直轄市、縣都有民辦武術學校……僅登封就有武術學校80余所。”[6]使鄉村地區的武術人口得到了快速提升;在組織方面,鄉村改造使原有的家族、宗法、師徒等得到限制,在改革后雖然有了一些回轉,但由于其生存環境的改變,已不能等同于古代鄉村社會的組織管理,而國家對武術的管理依然停留于縣一級單位;在經濟方面,由于武術技術可作為鄉村武術習練者的職業選擇,使鄉村武術從事者比起其它村民具有一些額外收入,作為師傅與藝人又具有良好的社會地位,生存狀況較好;在技術與思想方面,各種形式的武術在鄉村社會廣泛傳播,大大小小的武術拳種重新回到人們的視野,傳統文化的闡釋、現代科學的解釋,加上一些不法分子的利用,使鄉村武術技術與思想在此一時期表現出了混亂的局面。
2.5 新世紀的繁榮穩定與鄉村武術社會變遷
改革開放后我國經濟的快速增長,不僅使人們的物質文化生活得到了滿足,而且國家地位也有了大幅度的提升,同時隨著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舉辦奧運會、提出文化軟實力、以工業反哺農業等系列事件,國家大環境的繁榮穩定為我國鄉村社會的發展提供了良好基礎。國家開始出臺一系列政策推動三農發展,如農業稅的取消,國家對農村電力、交通、通訊等基礎設置的投入,支農惠農補貼,引導農民工合理就業等事件使鄉村社會的發展呈現繁榮之勢。在這種背景下鄉村武術的發展也呈現出了新的態勢。
在生存環境方面,農業現代化的推進使生產力與生產方式進一步改善,工業化的經營使農業生產價值進一步提升,城市化的推進使大量農村勞動力走出鄉村等變化,使延續2 000多年的農耕倫理社區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鄉村武術的生存環境發生了徹底改變;在人口方面,國家工業化、城市化、農業現代建設的步步推進,使鄉村武術習練者失去了傳統農業的生存空間,外出務工的需求,使學習一門專業技術成為了人們滿足經濟提升的必然選擇,武術人口在此一時期開始大量消減,以登封為例2001年還有80余所武術學校,2012年只剩下了43所,武術學校人數也大量下降。另外,在此一時期隨著國家提出文化軟實力建設,一些地區開始將武術納入中小學教育;在組織方面,隨著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提出,鄉村地區的武術拳種開始受到重視,被納入到當地文化管理部門的視野之內,傳承人的確立、科學研究的推進,使師徒、門派等傳統武術社團出現了一定的復蘇,但除個別開展較好的地區外,國家對鄉村武術的管理還依然停留于縣一級單位;在經濟方面,對于大部分習武者來說,在經濟方面并沒有得到具體實惠,而對于一些武術大師人、傳承人而言,其生存狀況與社會地位有較高的提升;在武術技術與思想方面,雖然現代文明使傳統武術技術與思想的生存空間遭受到了擠壓,但隨著文化尋根、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傳統文化復興等宏觀環境的變化,使鄉村武術技術與思想開始追求自己的現代化之路,尋求適合于現代社會的生存與傳播方式。
3 結 語
近現代以來,中西兩大文明的碰撞與沖突,使中國2000余年來的農耕文明社會發生了徹底的改變,在這種背景下中國鄉村社會結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不僅以家族、血緣、宗法為基礎的社會組織被打破,而且以小農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生產方式也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在這種背景下,武術在鄉村社會的生存空間發生了徹底改變,使鄉村武術社會結構發生了系列變化。本研究依據社會學理論將鄉村武術社會結構劃分為生存環境、人口數量、組織管理、經濟基礎、技術思想5個方面的內容,并按照歷史結點的劃分,分別對清朝末期的社會動亂、民國期間的愛國運動、新中國成立后的鄉村治理、改革開放的經濟發展、新世紀的繁榮穩定幾個階段的鄉村武術社會變遷進行了分析。總體來說,以西方為主的、重商主義的現代生活方式已經在中國社會全面推進,使原有的鄉村武術社會結構被徹底打破,鄉村武術社會必須根據時代的要求,進行各方面的改進重組,以應對現代生活方式在鄉村社會的進一步滲透,為自己爭取更多的生存空間。
[1]吳增基.現代社會學[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02:51.
[2]李伯欽,李肇翔.中國通史[M].南京:鳳凰出版社,2012,09:236.
[3]柳隨年,吳群敢.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簡史1949-1983[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85,05:43.
[4] 薄一波.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M].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08:700.
[5]姚麗華.河南省武術學校現狀與對策研究[D].河南大學,2001.
[6]金 龍.登封市民辦武術學校課程設置現狀調查研究[D].河南大學,2008.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Social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Wushu in Recent Years
SUN Xianghao
In modern times, Western learning to China's rural society earth shaking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martial arts as a part of rural culture, also has a corresponding change. In this study, the use of cultural science, history, sociology theory and method, to major historical events as nodes, on the basis of defining social structure of rural martial arts, analyzes the rural Wushu survival environment, practicing character, economic foundation, technical thought and social elements of the change, system is conducive 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specific changes in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rural martial arts.
Modern; Rural; Martial arts; Social structure
1007―6891(2017)01―0110―03
10.13932/j.cnki.sctykx.2017.01.23
G85
A
2016-05-23
2016-07-04
河南理工大學社科青年基金項目,項目編號:672605/001/078。
河南理工大學體育學院,河南焦作,454150。
Education College of Hen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Jiaozuo·Henan, 454150,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