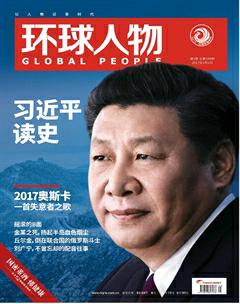奧斯卡為什么這樣“黑”
毛予菲++余馳疆


非裔演員包攬男女配 種族題材占半壁江山
今年的奧斯卡,被提及最多的人是誰?答案是美國總統特朗普。主持人吉米·坎摩爾直接在社交網絡上諷刺他;獲得最佳外語片的伊朗導演阿斯哈·法哈蒂因“禁穆令”不能來領獎,請人代讀感謝信,也不忘抨擊他一番;NASA(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女英雄凱瑟琳·約翰遜的出場,更被視為對特朗普歧視女性言論的反擊。于是,不少媒體稱這屆奧斯卡是“政治色彩最重的一次”。
政治正確并不只在外圍。今年奧斯卡入圍最佳影片的9部作品中,有3部黑人電影;5位非裔演員入圍表演類四大獎,創下新紀錄;最終,《月光男孩》拿下最佳影片,非裔演員包攬最佳男女配角。去年,奧斯卡因為在大獎上沒有一個非裔提名而成為眾矢之的,被大批影人抵制。一年過去,黑人電影大放異彩。這究竟是奧斯卡出于政治正確做出的“友好之舉”,還是黑人電影的全面崛起?或許,只有電影本身才能給出答案。
向王家衛致敬的黑人導演
《月光男孩》拿下最高獎真是一點也不讓人意外。黑人、同性戀、底層生活,這些元素加在一起,注定引人關注。不過,這部電影真正值得稱贊的地方,是導演巴里·詹金斯既沒有強調美國非裔的平權運動,也沒有提及種族問題,而是完全把故事放在了真實的黑人世界里——電影中,幾乎沒有一個白人鏡頭。
影片被分成三部分,分別是非裔男孩喀戎兒時、少年、成年的故事。他在成長中經歷霸凌、母親吸毒、坐牢等,最終慢慢發現自己的真實情感。電影聚焦在喀戎的個人成長上,豐富細膩的人文關懷讓它成為2016年最重要的美國電影之一。
《月光男孩》改編自非裔劇作家塔瑞爾·麥卡尼的舞臺劇。麥卡尼和詹金斯是老鄉,兩人從小在邁阿密的同一個街區長大,母親都有毒癮。上世紀80年代,美國前總統夫人南希·里根發動的“禁毒戰爭”,使得地下毒品買賣越發猖獗。兩個人成長在充滿暴力和毒品的環境中,因此他們稱《月光男孩》就是自己的“半自傳”。在影片剪輯時,詹金斯根本無法看完所有片段,因為電影中那些令人膽戰的畫面,都是他慘痛的過往。
幸而,詹金斯沒有把這部電影拍成苦大仇深的紀實片。電影中,喀戎對性懵懂的探索,毒梟胡安外表與內心劇烈的反差,還有結尾在月光下發著藍光的黑人小孩,都被拍出了令人意想不到的美感。詹金斯自稱是王家衛的粉絲,因此電影的風格也帶著一種腔調,唯美的燈光和鏡頭,都讓它與以往的黑人電影截然不同。《月光男孩》中還有多處向《春光乍泄》《墮落天使》等電影致敬的片段,比如,成年喀戎開車時播放的,就是《春光乍泄》的插曲。
《月光男孩》的確是“正確”的電影,但它更是藝術與深度并存的電影。詹金斯展現了一個沉重、真實的黑人世界,也證明了非裔導演不只是會拍平權與憤怒,他對世界有更深的思考。
摘下看客的有色眼鏡
除了最佳影片,《月光男孩》還收獲了最佳男配角的獎項,得獎者是在影片中飾演胡安的馬赫沙拉·阿里。胡安是個古巴裔毒販,電影開頭就是他訓斥小弟的畫面,全然一副老大做派。但他也有溫柔的一面,比如把被同學欺負的喀戎帶回家,為他做飯,教他游泳,給他講自己的故事。在不到半小時的片段中,阿里將胡安這個兩面性極強的人物詮釋得生動豐滿。
阿里之前也曾在幾部大熱影片中擔任配角,不過只有幾個鏡頭,沒有給觀眾留下深刻印象。真正讓阿里被觀眾熟知的,是風靡全球的“美國宮斗劇”《紙牌屋》。在這部劇中,阿里飾演的雷米·丹頓是個智商極高又充滿魅力的黑人說客。他塑造了一個精明的投機者形象,曾是美國總統的左右手,8年后成為被企業安插在政府的中間人,隨后又轉身投靠富商。
雷米·丹頓“永遠忠于利益”的設定并不討喜,但他一度被粉絲評為“阿里飾演的角色中最有趣的人”,因為他實在是太聰明了。相應地,阿里也開始受到業界認可,斷斷續續獲得艾美獎、英國學院獎等提名。
阿里最初并沒有想過做一名演員。1974年,他出生于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在非裔美國人群體中,阿里的家庭算得上半精英階層,因此他從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從美國圣瑪麗大學畢業后,阿里成了一名籃球運動員。在一次機緣巧合下,他參與演出舞臺劇《勇敢》,隨后便一發不可收拾,成了加州莎士比亞戲劇中心的學徒,又在紐約大學獲得了表演專業碩士學位。
關于自己的黑皮膚,阿里曾做過一次名為《獨立》的反種族歧視演講。“在‘9·11恐怖襲擊后,我發現,自己的名字居然登上了聯邦調查局的觀察名單。這一切只不過因為我是個黑人。”
這個故事倒與今年的熱門影片《隱藏人物》很像,電影中3位非裔女性通過自己的努力沖破了種族偏見,最終在NASA立足。阿里也是如此,從被懷疑到拿下小金人,他用實際行動摘下了看客的有色眼鏡。
曾為自己的卷毛羞愧
最佳女配角可謂今年最沒有懸念的獎項之一,獲得者維奧拉·戴維斯是美國黑人女演員的代表。這座小金人,讓她成為電影史上第一個集托尼、艾美和奧斯卡三大獎項于一身的黑人女星。
在電影《藩籬》中,戴維斯扮演了一名忍氣吞聲的妻子。她接受丈夫的出軌,守護孩子的夢想,卻在家庭矛盾出現后變得狂躁不安,充分展現了上世紀50年代底層黑人女性的心酸。這是戴維斯首次斬獲奧斯卡,卻是第三次入圍。2009年她曾憑借《虐童疑云》提名最佳女配角,2013年又靠《幫助》提名最佳女主角。在這些戴維斯以往的代表作中,“種族問題”都是繞不開的敏感詞。
這也是戴維斯童年的關鍵詞。1965年,她出生于美國北卡羅來納州,父親是馴馬師,母親是一個女仆,一家人生活很貧苦。成名后,戴維斯在幾次公開講話中,都提到了“窮困”“黑人”“非正常家庭”。為擺脫周遭“不友好”的環境,戴維斯報名參加學校的劇團活動,去朱莉亞音樂學院學習戲劇。她愛上了表演,“因為藝術有治愈的力量,成了宣泄的方式”。畢業后,戴維斯開始在百老匯舞臺上跑龍套,雖然演的都是不起眼的小角色,但她在藝術中找到了快樂。
2000年后,戴維斯從百老匯來到了好萊塢,但沒能擺脫膚色問題帶來的困擾,能拿到的有臺詞角色少之又少。好在戴維斯從來不放過任何露面機會。在《虐童疑云》中,她向梅麗爾·斯特里普扮演的老校長哭訴兒子在學校受到排擠,焦慮又憂心。這是戴維斯在電影中僅有的一場戲。所有人都沒想到,這個幾分鐘的鏡頭讓她獲得了當年奧斯卡最佳女配角的提名,一舉揚名好萊塢。
很長一段時間里,戴維斯曾為自己的外表感到“羞愧”,出席公共場合總會戴上假發,因為好萊塢推崇飄逸的直發或者富有彈性的大卷,而不是她那格格不入的小卷毛。直到2013年的奧斯卡頒獎儀式上,她第一次摘下了假發套,頂著一頭卷毛參加了典禮。
戴維斯常常鼓勵同伴:“得不到想要的東西,根本原因是自己從來沒有要求過。區分人類的不是什么膚色,而是機會和努力。”也許,這就是非裔影人在奧斯卡崛起最重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