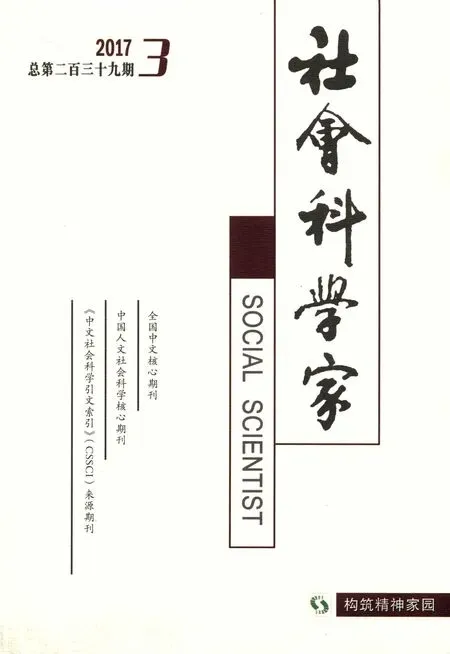論文學(xué)消費(fèi)的物質(zhì)性
張 進(jìn),王 垚
(蘭州大學(xué) 文學(xué)院,甘肅 蘭州 730000)
【文史論叢】
論文學(xué)消費(fèi)的物質(zhì)性
張 進(jìn),王 垚
(蘭州大學(xué) 文學(xué)院,甘肅 蘭州 730000)
文學(xué)消費(fèi)是文學(xué)的物質(zhì)性研究視域下的重要范疇。通過考察文學(xué)作為物的文化傳記,可以看出在大規(guī)模的商品化、貨幣化的消費(fèi)社會(huì),文學(xué)經(jīng)歷了“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的過程。文學(xué)消費(fèi)活動(dòng)發(fā)生在多個(gè)子系統(tǒng)中:一般物性商品的系統(tǒng)、物質(zhì)性“商品符號(hào)”系統(tǒng)以及物質(zhì)性語言符號(hào)系統(tǒng)。文學(xué)接受與文學(xué)消費(fèi)不應(yīng)是高低等級(jí)制的關(guān)系,而是一種“域化”與“解域”的復(fù)雜關(guān)聯(lián)。
文學(xué)消費(fèi);物質(zhì)性;文學(xué)接受
長久以來,文學(xué)被認(rèn)為是精神產(chǎn)物,圍繞文學(xué)的創(chuàng)作、接受等方面強(qiáng)調(diào)文學(xué)精神層面的審美內(nèi)涵與意義的“合法性”似乎毋庸置疑。馬克思的藝術(shù)生產(chǎn)論將文學(xué)藝術(shù)引入經(jīng)濟(jì)學(xué)、社會(huì)學(xué)的領(lǐng)域,指出文學(xué)活動(dòng)是特殊的精神生產(chǎn)的觀念活動(dòng),精神生產(chǎn)是相對于物質(zhì)生產(chǎn)而言的概念。雖然馬克思依然將文學(xué)生產(chǎn)歸于精神的、觀念的實(shí)踐,但他為后來文學(xué)的“物質(zhì)性”研究奠定了基礎(chǔ)。從馬克思到后來的新馬克思主義,再到最近幾十年的消費(fèi)文化、物質(zhì)文化研究,理論家們的視野逐漸從文學(xué)的語言的、話語的、審美的領(lǐng)域轉(zhuǎn)向更為開放的物質(zhì)性的、社會(huì)性的領(lǐng)域,發(fā)掘文學(xué)的語言物質(zhì)性與社會(huì)物質(zhì)性的復(fù)雜關(guān)聯(lián)。
從文學(xué)“反應(yīng)”的角度看,將文學(xué)作品與審美接受這種精神活動(dòng)連接起來,使作品持續(xù)地生成意義的文學(xué)接受論是我國文學(xué)理論界長期認(rèn)可的“合法性”理論。而當(dāng)下社會(huì)轉(zhuǎn)型與文學(xué)理論研究的新轉(zhuǎn)向促使我們考察文學(xué)的物質(zhì)性,反思鮑德里亞描述的“消費(fèi)控制著一切”的消費(fèi)社會(huì),并將文學(xué)消費(fèi)的問題納入文學(xué)理論研究的視域。傳統(tǒng)上認(rèn)為審美是人的精神活動(dòng),“在消費(fèi)社會(huì),審美文化變遷的一個(gè)重要標(biāo)志是:審美活動(dòng)本身變成了消費(fèi)。”[1]文學(xué)消費(fèi)基于“消費(fèi)者”,從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的角度將“創(chuàng)作-作品-接受”的知識(shí)型過渡到“生產(chǎn)-產(chǎn)品-消費(fèi)”知識(shí)型中,產(chǎn)生了文學(xué)研究的新問題和新意義。
一、“消費(fèi)”:觀念的演進(jìn)
英語中消費(fèi)一詞從詞源上看來自拉丁語(consumere),意思是“抓住、利用、完全地接收”,引申出的含義為“耗盡,浪費(fèi),毀滅,耗費(fèi)”。十四世紀(jì),消費(fèi)一詞開始在英語、法語中使用,當(dāng)時(shí)的語境中,消費(fèi)意味著破壞本不應(yīng)該被破壞的東西,具有一定的貶義和消極意義。18世紀(jì),亞當(dāng)·斯密的生產(chǎn)勞動(dòng)學(xué)說將“生產(chǎn)”一詞置于理論言說的中心,伴隨著工業(yè)革命的機(jī)械化生產(chǎn),生產(chǎn)/消費(fèi)逐漸成為一組二元詞。然而,消費(fèi)一詞早期的貶義性在馬克思到法蘭克福學(xué)派都或多或少得到延續(xù)。尤其是后者,在精英主義的立場上對“文化工業(yè)”展開了強(qiáng)烈的批判。
法蘭克福學(xué)派認(rèn)為消費(fèi)者的消費(fèi)活動(dòng)是容易被操控的,是盲從。阿多諾和霍克海默指出:“由于出現(xiàn)了大量的廉價(jià)的系列產(chǎn)品,再加上普遍進(jìn)行欺詐,所以藝術(shù)本身更加具有商業(yè)性質(zhì)了。藝術(shù)今天明確地承認(rèn)自己的獨(dú)立自主性,這不是什么新奇的事,但是藝術(shù)發(fā)誓否認(rèn)自己的獨(dú)立自主性,反以自己變?yōu)橄M(fèi)品而自豪,這卻是令人驚奇的現(xiàn)象。”[2]在標(biāo)準(zhǔn)化的文化工業(yè)生產(chǎn)中,文學(xué)藝術(shù)進(jìn)入到“生產(chǎn)者-生產(chǎn)-產(chǎn)品-消費(fèi)-消費(fèi)者”的關(guān)系中,喪失了其獨(dú)特的光暈(Aura)。在他們看來,消費(fèi)者甚至可以說是這種關(guān)系中的受害者,他們在營銷和廣告策略的誘導(dǎo)下消費(fèi),而這些策略正是資本主義的意識(shí)形態(tài)控制手段。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貢獻(xiàn)是將生產(chǎn)/消費(fèi)的討論從亞當(dāng)·斯密、馬克思以來的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領(lǐng)域引入到文化研究領(lǐng)域。在他們之后,伯明翰學(xué)派接過了旗幟,并且逐漸開始扭轉(zhuǎn)消費(fèi)一詞的消極含義。
與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精英主義不同,伯明翰學(xué)派則將焦點(diǎn)放在了受眾,以大眾這一消費(fèi)主體作為主要研究對象之一。早期的伯明翰學(xué)派還受利維斯主義和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影響,霍加特站在精英主義的立場對商業(yè)化的大眾文化進(jìn)行了批判。到了威廉斯這里,大眾文化的商業(yè)化并沒有遭到反對,但威廉斯認(rèn)為應(yīng)該警惕商業(yè)化愈演愈烈的趨勢。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霍爾成為伯明翰學(xué)派的領(lǐng)軍人物,他的出現(xiàn)將受眾研究引向了新的方向。霍爾在他的著名文章《電視話語的編碼與解碼》中,霍爾提出了著名的三種解碼類型(即主導(dǎo)霸權(quán)地位、協(xié)商符碼、對抗符碼)。霍爾將電視傳播的文化產(chǎn)品看做一個(gè)意義開放的文本,研究在流通和消費(fèi)階段受眾接受的多種可能性,他認(rèn)為消費(fèi)階段受眾主體的能動(dòng)性致使產(chǎn)品文本存在協(xié)商型甚至對抗型的消費(fèi)。霍爾的理論在文化研究領(lǐng)域削弱了消費(fèi)一詞原本的消極含義,消費(fèi)行為不再是被動(dòng)的,破壞的,而意味著可能的主動(dòng)選擇和意義再生。
1970年鮑德里亞的《消費(fèi)社會(huì)》促使“消費(fèi)社會(huì)理論”以及與之相關(guān)的消費(fèi)文化研究成為二十世紀(jì)七十年代以后的顯學(xué)。鮑德里亞將當(dāng)代社會(huì)界定為消費(fèi)社會(huì),與傳統(tǒng)社會(huì)的生產(chǎn)為了滿足生存需要不同,消費(fèi)社會(huì)的生產(chǎn)具有文化的含義。二戰(zhàn)后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建立起新的工業(yè)化社會(huì)(也就是所謂的“后工業(yè)社會(huì)”),技術(shù)的發(fā)展、管理方式的變化、資本運(yùn)作的革新帶來了新的社會(huì)形態(tài)。機(jī)械化生產(chǎn)提高了生產(chǎn)效率,改變了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進(jìn)而導(dǎo)致產(chǎn)能過剩。商品獲得了使用價(jià)值以外的新的價(jià)值。因此,消費(fèi)社會(huì)里消費(fèi)者消費(fèi)的不再僅僅是商品的使用價(jià)值,商品被賦予了符號(hào)意義。鮑德里亞指出:“消費(fèi)的真相在于它并非一種享受功能,而是一種生產(chǎn)功能——并且因此,它和物質(zhì)生產(chǎn)意義并非一種個(gè)體功能,而是即時(shí)且全面的集體功能。”“消費(fèi)是一個(gè)系統(tǒng),它維護(hù)著符號(hào)秩序和組織完整:因此它既是一種道德(一種理想價(jià)值體系),也是一種溝通體系、一種交換結(jié)構(gòu)。”[3]也就是說,鮑德里亞認(rèn)為,消費(fèi)建構(gòu)了我們當(dāng)下社會(huì)的一套編碼系統(tǒng),我們通過這個(gè)編碼系統(tǒng)進(jìn)行交流。馬克思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所闡釋的商品的生產(chǎn)、消費(fèi)模式在消費(fèi)社會(huì)擴(kuò)充為除經(jīng)濟(jì)行為外的文化行為,商品不再只有交換價(jià)值和使用價(jià)值,而被賦予了符號(hào)價(jià)值。鮑德里亞說:“我們處在‘消費(fèi)’控制著整個(gè)生活的境地。”[3]商品作為“物”的功能性、實(shí)用性正在慢慢弱化,而作為“符號(hào)”的文化價(jià)值空前膨脹,這種附加的意義附著在大眾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
可以說一切被賦予意義的“物”都是商品,而參與到意義的散播、增值或解構(gòu)等行為中的人就是消費(fèi)者,這就誕生了與消費(fèi)社會(huì)相融合的消費(fèi)文化。消費(fèi)文化的特征是日常生活在消費(fèi)中有了審美的、藝術(shù)化的意義,而原本具有審美性質(zhì)的藝術(shù)和藝術(shù)品都可以被消費(fèi)。費(fèi)瑟斯通在《消費(fèi)文化與后現(xiàn)代主義》中談到:“使用‘消費(fèi)文化’這個(gè)詞是為了強(qiáng)調(diào),商品世界用其結(jié)構(gòu)化原則對理解當(dāng)代社會(huì)來說具有核心地位,這里有雙重的涵義:首先,就經(jīng)濟(jì)的文化維度而言,符號(hào)化過程與物質(zhì)產(chǎn)品的使用,體現(xiàn)的不僅是實(shí)用價(jià)值,而且還扮演著‘溝通者’的角色;其次,在文化產(chǎn)品的經(jīng)濟(jì)方面,文化產(chǎn)品與商品的供給、需求、資本積累、競爭用壟斷等市場原則一起運(yùn)作于生活方式領(lǐng)域之中。”[4]因此,消費(fèi)品(包括文學(xué)產(chǎn)品)的物質(zhì)性不僅僅指其實(shí)物性,而是實(shí)物性與物性符號(hào)價(jià)值融合于物質(zhì)性的消費(fèi)文化中并不斷參與信息交換、物質(zhì)實(shí)踐的存在狀態(tài)。
20世紀(jì)后期,理論家們開始從各自領(lǐng)域(經(jīng)濟(jì)學(xué)、人類學(xué)、歷史學(xué)、社會(huì)學(xué)、博物學(xué)、文化研究、文學(xué)批評(píng)等)研究消費(fèi),并著重強(qiáng)調(diào)消費(fèi)的積極意義。“消費(fèi)者并不是被動(dòng)的,易被操控的,在他們對物質(zhì)性商品的挪用和改造中展現(xiàn)出了積極的,有創(chuàng)造力的,批判的一面……在這種挪用的過程中,身份被建構(gòu)起來。”[5]包括阿爾君·阿帕杜萊、丹尼爾·米勒、喬納森·弗里德曼在內(nèi)的一大批學(xué)者在他們的著作中從不同的角度談?wù)撓M(fèi)的積極意義,他們希望打破聚集在“消費(fèi)”這個(gè)范疇的固定的貶義性表述和研究范式。丹尼爾·米勒指出自己“不僅僅主張消費(fèi)文化應(yīng)當(dāng)被看作一種正宗的原創(chuàng)性文化,同時(shí)還否定了這種文化一定是個(gè)人主義的、物質(zhì)至上的,或者說資本主義的文化。”[6]大衛(wèi)·格雷伯認(rèn)為比這些不同版本的有關(guān)消費(fèi)的著作中談?wù)摰膯栴}更值得關(guān)注的是與此同時(shí),當(dāng)前的課堂、研討會(huì)、非正式的研究所討論會(huì)中的新的“標(biāo)準(zhǔn)敘述”正在形成。他指出:“從前,我們贊成一種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觀點(diǎn),認(rèn)為生產(chǎn)是歷史的推動(dòng)力和社會(huì)斗爭的合法戰(zhàn)場。另外,我們所能想到的消費(fèi)者需求,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為制造,是廣告商和賣家為了處理掉沒有人真正需要的產(chǎn)品而進(jìn)行操縱的結(jié)果。但最終我們開始認(rèn)識(shí)到這種觀點(diǎn)不僅僅是錯(cuò)誤的而且是極度精英主義和清教徒式的。真正的勞動(dòng)人民在消費(fèi)中發(fā)現(xiàn)他們?nèi)粘I畹臉啡ぁ!盵7]當(dāng)代研究消費(fèi)的學(xué)者傾向于認(rèn)為消費(fèi)者在消費(fèi)過程中是有策略的,是主動(dòng)的,他們創(chuàng)造性和抵抗性的實(shí)踐使產(chǎn)品成為凝聚著特殊價(jià)值、意義、情感、身份的動(dòng)態(tài)物。在這種新型的消費(fèi)觀念下,消費(fèi)者既不是物的掌控者和毀滅者,也不是受制于物的被動(dòng)者,而是處在與物親密糾纏、互相建構(gòu)的多元?jiǎng)討B(tài)的物質(zhì)文化關(guān)系中的一元。
二、文學(xué)作為物的文化傳記
探討文學(xué)消費(fèi)的問題,需要將文學(xué)鑒賞、文學(xué)接受所忽視的文學(xué)作為物的屬性納入考察視野。引入文化的視角,從“物的文化傳記”的維度考察文學(xué)作為商品歷史以及與消費(fèi)的關(guān)系。“引入傳記的概念使我們能夠避免視對象為一系列既定形式中某一結(jié)構(gòu)獲得真實(shí)性的結(jié)果,同時(shí)保證我們關(guān)注物如何具體運(yùn)動(dòng)、如何在多種狀態(tài)之間‘過渡’,以及作為具有時(shí)間性和節(jié)奏性的形態(tài)或連貫行為的物如何受到(自我)管理等問題。”[8]文學(xué)的語言離不開媒介,如果僅僅聚焦于文學(xué)語言的“所指”,而忽略了語言所依賴的媒介的物質(zhì)性和語言本身的物質(zhì)性,則易走向一元化的理論視野。值得一提的是,新世紀(jì)問世的《哥倫比亞中國文學(xué)史》和《劍橋中國文學(xué)史》就打破了以往時(shí)間朝代更替和文類體裁區(qū)分的文學(xué)史編纂體制,在編者看來,“在物質(zhì)條件中的文學(xué)生產(chǎn)與消費(fèi)變遷,較之政治移變更為基礎(chǔ)和重要。”[9]
麥克盧漢的“媒介即訊息”的論斷為研究文學(xué)的物質(zhì)性提供了理論資源,他解釋道:“所謂媒介即是訊息不過是說:任何媒介(即人的任何延伸)對個(gè)人和社會(huì)的任何影響,都是由于新的尺度產(chǎn)生的;我們的任何一種延伸(或曰任何一種新的技術(shù)),都要在我們的事務(wù)中引進(jìn)一種新的尺度。”[10]也就是說,媒介、信息與人的是文化性的能量互動(dòng)關(guān)系,我們需要打破物質(zhì)實(shí)體/精神意識(shí)、形式/內(nèi)容的界限劃分,認(rèn)識(shí)到物質(zhì)性并不等同于物質(zhì)實(shí)體。從媒介的角度引入文學(xué)作為物的社會(huì)傳記,旨在警惕將物質(zhì)性等同于物質(zhì)實(shí)體的偏執(zhí),并揭示文學(xué)所依賴的媒介和文學(xué)作為媒介本身所承載的信息的流動(dòng)。伊戈?duì)枴た破胀蟹颍↖gorKopytoff)在《物的文化傳記》一文中指出:“在文化的視野中,商品的生產(chǎn)也是文化和認(rèn)知的過程:商品不僅僅作為物質(zhì)生產(chǎn)的物,而且被作為一種被文化標(biāo)記的物。”[11]他認(rèn)為在文化的視野考察物的傳記需要?dú)v時(shí)性地從兩種不同規(guī)模的社會(huì)入手。一是小規(guī)模的非商品化社會(huì),一是大規(guī)模的商品化和貨幣化社會(huì)。
“呈現(xiàn)在我們眼前的文學(xué)事實(shí),有三個(gè)重要形態(tài):書籍、讀物、文學(xué)。”[12]這三種形態(tài)界限模糊,而且一旦進(jìn)入文化傳記的考察中則更加難以區(qū)分。也就是說,文本的語言與物質(zhì)意義之間的聯(lián)系是不可避免的。文學(xué)作為“物”必然有載體作為媒介,文學(xué)的發(fā)展伴隨著載體的發(fā)展。不論是口傳、書寫還是印刷,文學(xué)存在于私人化的創(chuàng)造和閱讀、接受領(lǐng)域,同時(shí)也存在于另外一個(gè)生產(chǎn)和消費(fèi)的領(lǐng)域。實(shí)際上,從商品社會(huì)誕生之日起,文學(xué)作品就已經(jīng)開始作為商品流通。
在我國,早在兩漢間,就有相當(dāng)于當(dāng)今書店的“書肆”。揚(yáng)雄《法言·吾子》中就提到了書肆:“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后漢書·王充傳》也有記載說王充“家貧無書,常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通憶。”可見當(dāng)時(shí)圖書的獲得除手抄傳閱外,已經(jīng)可以通過貨幣購買。然而,印刷設(shè)備被開發(fā)之前,文學(xué)并不能作為普遍的商品供大眾消費(fèi)。雕版印刷術(shù)發(fā)明之前,中國古代的文學(xué)作品很大程度上是在小范圍的文人圈里流通,這種流通并不是普遍意義上的“商品流通”。例如引起“洛陽紙貴”的左思的《三都賦》,也只是在權(quán)貴之家競相傳抄。隋唐時(shí)期,雕版印刷術(shù)的發(fā)明和科舉制度的建立促進(jìn)了文學(xué)傳播的繁榮。官方修訂了一批經(jīng)典,并以這些經(jīng)典為綱舉行科舉考試,這就使得圖書的需求量大幅增加。這一時(shí)期佛教的傳播也促進(jìn)了文學(xué)一定程度的商業(yè)化。唐代的書籍交易已頗具規(guī)模,唐傳奇《李娃傳》中就有一段描述買書的情節(jié):“娃命車出游,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jì)費(fèi)百金,盡載以歸。”書肆在唐代尤為發(fā)達(dá),形成了長安、洛陽等圖書交易中心。宋人畢昇發(fā)明了活字印刷術(shù)但并未在當(dāng)時(shí)得到推廣,宋代大力推廣的依舊是雕版印刷。宋代官方大力提倡文治,全國出現(xiàn)大規(guī)模的書籍印刻中心和銷售中心。從此,我國民間文化開始繁榮。元代開始推廣和使用活字印刷,之后通俗文學(xué)開始廣泛傳播。元、明、清時(shí)代戲曲、小說等通俗文學(xué)的興起和繁榮得益于印刷技術(shù)的提高和書籍交易規(guī)模的擴(kuò)大。
雖然印刷技術(shù)在我國誕生,但大規(guī)模的機(jī)械復(fù)制技術(shù)發(fā)明之前,文學(xué)的生產(chǎn)和消費(fèi)是在小規(guī)模的非商品化社會(huì)中進(jìn)行的。不論是以書簡、木板、絹帛還是紙張為載體,在古代封建社會(huì)中文學(xué)作為商品都受制于社會(huì)生產(chǎn)力、經(jīng)濟(jì)規(guī)模、統(tǒng)治者理念、生產(chǎn)技術(shù)等因素。德國人古登堡發(fā)明的活字印刷被認(rèn)為奠定了現(xiàn)代印刷技術(shù)的基礎(chǔ),但當(dāng)時(shí)的印刷技術(shù)離機(jī)械化還很遠(yuǎn)。在小規(guī)模非商品化社會(huì)的各歷史階段,文學(xué)作為商品的身份在交換領(lǐng)域中是確定的,任何與此身份背離的文學(xué)商品在交換領(lǐng)域中往往被“神圣化、孤立、驅(qū)逐”。[11]也就是說,所謂“一代有一代之文學(xué)”,文學(xué)商品的身份被社會(huì)歷史系統(tǒng)所建構(gòu),同時(shí),從這些“小規(guī)模”社會(huì)中考察文學(xué)商品的傳記,我們看到的也是社會(huì)歷史系統(tǒng)本身。
工業(yè)革命帶來的機(jī)械化引發(fā)了巨大的社會(huì)變革。在此之后,現(xiàn)代印刷技術(shù)逐漸發(fā)展成熟,從十九世紀(jì)中期到二戰(zhàn)前后,經(jīng)過近百年的發(fā)展,工業(yè)發(fā)達(dá)國家的印刷業(yè)基本實(shí)現(xiàn)了工業(yè)化。機(jī)械化復(fù)制設(shè)備的大規(guī)模使用是文學(xué)流通的一個(gè)轉(zhuǎn)折點(diǎn)。從此,文學(xué)作品得以大量復(fù)制,文學(xué)的商品性質(zhì)逐漸受到關(guān)注。文學(xué)從此從小規(guī)模的非商品化社會(huì)過渡到了大規(guī)模的商品化社會(huì)。在這種社會(huì)里,物的大規(guī)模的商品化意味著物的交換行為和方式越來越多樣化和復(fù)雜化,而且交換并不意味著消費(fèi)行為的結(jié)束,反而是消費(fèi)過程的開始。文學(xué)也不例外,技術(shù)飛速發(fā)展帶動(dòng)了媒介的更新和增多,這使得原本明確的交換領(lǐng)域變得復(fù)雜而多樣。對文學(xué)作為物的社會(huì)生活傳記的考察從社會(huì)歷史、技術(shù)等領(lǐng)域過渡到多維的文化領(lǐng)域,并把視角聚焦于消費(fèi)文化。“現(xiàn)代社會(huì)中社會(huì)環(huán)境與個(gè)人的品味之間的關(guān)系較之小國寡民的、非貨幣的、前工業(yè)社會(huì)的時(shí)代之中要更為緊密些。”[13]在現(xiàn)代化的工業(yè)社會(huì)里,商品化的文學(xué)與社會(huì)、政治、技術(shù)、傳媒、消費(fèi)者個(gè)人趣味、社會(huì)心理等等因素相互作用,文學(xué)呈現(xiàn)出“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的復(fù)雜的過程性。
大規(guī)模機(jī)械復(fù)制技術(shù)的成熟和經(jīng)濟(jì)體系的完善直接促進(jìn)了文學(xué)的商品化,在消費(fèi)的過程中作為商品的文學(xué)則必然會(huì)發(fā)生“商品的偏移”(阿爾君·阿帕杜萊語),這種偏移也就是文學(xué)的去商品化。所謂偏移(diversions)就是商品脫離了其原本的社會(huì)商品語境,進(jìn)入了意義流動(dòng)、價(jià)值附加、身份建構(gòu)的消費(fèi)文化語境。文學(xué)消費(fèi)將商品化的文學(xué)帶入了更廣闊的文化語境,使文學(xué)從一般的商品化走向特殊化。最直觀的例子即成為收藏品的文學(xué),成為展覽品的文學(xué),成為禮物的文學(xué)等等。交換行為發(fā)生之后,文學(xué)便開始了去商品化過程,不同時(shí)代、不同地域的文化意識(shí)形態(tài)、消費(fèi)者的階層區(qū)分、消費(fèi)者的群體性消費(fèi)心理、消費(fèi)者的個(gè)人趣味互相作用,賦予了文學(xué)更多元的意義和價(jià)值。被消費(fèi)的文學(xué)進(jìn)入了人的日常生活,被人賦予某類特殊意義、價(jià)值、身份的同時(shí)參與了人的身份的建構(gòu),他們通過消費(fèi)某物進(jìn)行自我表達(dá)和評(píng)估,從這種意義上說,消費(fèi)即是文化實(shí)踐。去商品化的偏移路徑終將導(dǎo)致再商品化。走向特殊化的文學(xué)又會(huì)經(jīng)歷再次商品化的過程,去商品化使再商品化成為可能,正如丹尼爾·米勒所說:“一旦貨物不再僅僅被理解為商品,而是看作現(xiàn)代文化的主要成分,消費(fèi)的可能性就出現(xiàn)了。”[14]去商品化過程是意義的再生產(chǎn),并引發(fā)新的消費(fèi)需求,因此重新語境化的文學(xué)便會(huì)經(jīng)歷又一次商品化過程。
三、文學(xué)消費(fèi)的性質(zhì)
文學(xué)家、批評(píng)家們似乎總是想讓我們關(guān)注文學(xué)作品的內(nèi)容和審美意義本身,然而強(qiáng)行將“詞”與“物”剝離開顯然是徒勞。從結(jié)構(gòu)主義語言學(xué)、俄蘇形式主義、英美新批評(píng)等將語言視為“物質(zhì)的東西”到奧斯汀的述行語言的施事功能,再到伊格爾頓的“文學(xué)事件”,文學(xué)的物質(zhì)性成為當(dāng)前文學(xué)理論批評(píng)、物質(zhì)文化研究的重要課題。蒂姆·丹特指出:“消費(fèi)是理解物質(zhì)文化如何塑造而反映社會(huì)形式與過程的一種特定方式。”[15]在消費(fèi)文化領(lǐng)域,文學(xué)消費(fèi)主要有三重性質(zhì)。
(一)消費(fèi)作為一般物性商品的文學(xué)
我們對文學(xué)消費(fèi)的關(guān)注某種程度上是對馬克思“藝術(shù)生產(chǎn)論”的回應(yīng)。在以消費(fèi)為主導(dǎo)的消費(fèi)文化的浸潤下,文學(xué)的商品性質(zhì)得以彰顯。機(jī)械復(fù)制設(shè)備投入使用革新了文學(xué)傳播方式,文學(xué)被大規(guī)模印刷成書籍明碼標(biāo)價(jià)。新媒介的產(chǎn)生更促使文學(xué)成為多種形態(tài)的商品。消費(fèi)者獲得文學(xué)的方式就是消費(fèi)(用貨幣購買),在這種消費(fèi)模式下,一本書和一件衣服并沒有區(qū)別。我們用貨幣消費(fèi)的是完成了的,經(jīng)過印刷、包裝的文學(xué)作品。消費(fèi)作為一般商品的文學(xué),消費(fèi)者可能并不會(huì)進(jìn)入到閱讀階段。文學(xué)作品被生產(chǎn)出來進(jìn)入流通領(lǐng)域,就會(huì)如其他商品一樣產(chǎn)生損耗、積壓或者走俏,這是傳統(tǒng)的物態(tài)商品的共性,文學(xué)作品和其他商品一樣,遵循市場規(guī)律,或高或低于標(biāo)價(jià)出售。
在這種情況下,文學(xué)是普遍意義上的物理性質(zhì)的“物品”,“物品”進(jìn)入商品流通市場從而成為一般性的商品。無論是實(shí)體的書籍、音像制品還是非實(shí)體的電子書、網(wǎng)絡(luò)作品,一旦進(jìn)入“高密度市場”(high-intensitymarket),就進(jìn)入了價(jià)值交換的消費(fèi)領(lǐng)域。如果拋開文學(xué)消費(fèi)的其他性質(zhì),單從購買行為上分析,文學(xué)僅僅作為物體現(xiàn)了消費(fèi)者的購買能力,似乎并不能參與到文化實(shí)踐的社會(huì)關(guān)系網(wǎng)絡(luò)中。然而,文化環(huán)境中的人與物不可能被簡化為純粹經(jīng)濟(jì)上的人與物。威廉·萊斯是這樣描述他所謂的“高密度市場”的:“商品不是簡單的‘客體物’,而是逐步地變得更加不穩(wěn)定,是目的和特征的暫時(shí)性集合,換言之,是高度復(fù)雜的物質(zhì)-符號(hào)的存在物。”[16]消費(fèi)受到文化中多元因素的影響,因此引入文學(xué)消費(fèi)的另外兩重性質(zhì)尤為重要。
(二)消費(fèi)具有物質(zhì)性符號(hào)意義的文學(xué)
文學(xué)在擁有一般商品屬性的同時(shí)被符碼化,在生產(chǎn)-消費(fèi)的過程中,意義不斷地開始生成、附著。鮑德里亞認(rèn)為:“要成為消費(fèi)的對象,物品必須成為符號(hào),也就是外在于一個(gè)它只作意義、指涉的關(guān)系——因此它和這個(gè)具體的關(guān)系之間,存有的是一種任意偶然的和不一致的關(guān)系,而它的合理一致性,也就是它的意義,來自于它和所有其它的符號(hào)——物之間,抽象而系統(tǒng)性的關(guān)系。這時(shí),它便進(jìn)行‘個(gè)性化’,或是進(jìn)入系列之中等等;它被消費(fèi)——但(被消費(fèi)的)不是它的物質(zhì)性,而是它的差異(defference)……被消費(fèi)的東西,永遠(yuǎn)不是物品,而是關(guān)系本身。”[17]鮑德里亞的理論為文學(xué)消費(fèi)的研究開辟了新的視野。鮑德里亞拒絕僅僅將商品理解為實(shí)物,而是將其看做一個(gè)不穩(wěn)定的、漂浮的物質(zhì)性能指領(lǐng)域。鮑德里亞讓我們看到了一個(gè)處在“商品-符號(hào)”系統(tǒng)中的文學(xué)消費(fèi)。在“商品-符號(hào)”系統(tǒng)中,消費(fèi)者消費(fèi)的首先是商品的符號(hào)意義,其次才可能是其實(shí)用意義。
消費(fèi)者通過消費(fèi)進(jìn)行著自我身份的指認(rèn),商品符號(hào)具有的意義附著在消費(fèi)者個(gè)體身上,使之在社會(huì)生活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獲得某種身份上的認(rèn)可。炫耀式消費(fèi)在消費(fèi)社會(huì)更加普遍。例如,有的消費(fèi)者購買大量的文學(xué)作品只為了向他者顯示自己愛讀書的身份,而實(shí)際上并不閱讀;有的消費(fèi)者購買某一特定版本的文學(xué)作品為了收藏,這時(shí),文學(xué)作品作為藝術(shù)藏品體現(xiàn)其價(jià)值,消費(fèi)者通過購買這件商品構(gòu)建了自己收藏家的身份。消費(fèi)者以消費(fèi)文學(xué)獲得某種身份認(rèn)同,追逐暢銷作品如同追逐時(shí)尚潮流一般,因此,在消費(fèi)社會(huì),文學(xué)也是被“時(shí)尚化”的。當(dāng)然,這種“時(shí)尚化”不一定體現(xiàn)在暢銷作品上,那些不受大眾關(guān)注的、市面上并不走俏的文學(xué)作品,被賦予了另一種時(shí)尚化的意義。當(dāng)暢銷文學(xué)被認(rèn)為是主流的時(shí)候,看似非主流的文學(xué)則獲得了抵抗主流的意義。例如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靈夜》等等這樣被認(rèn)為晦澀難懂的文學(xué)作品成為一部分消費(fèi)群體追逐的對象,這些消費(fèi)者將擁有這些作品作為自己區(qū)別于大眾化的高品味的象征,這時(shí)他們消費(fèi)的正是這些文學(xué)作品的“商品-符號(hào)”意義。在“商品-符號(hào)”系統(tǒng)中,消費(fèi)者通過差異性的消費(fèi),形成了象征不同身份、地位、品味的階級(jí)。
(三)消費(fèi)作為物質(zhì)語言符號(hào)的文學(xué)
即便一再強(qiáng)調(diào)當(dāng)代社會(huì)是商品的社會(huì)、消費(fèi)的社會(huì),如果只將文學(xué)作為一般商品和“商品-符號(hào)”進(jìn)行討論顯然有失全面,文學(xué)的語言符號(hào)層面的消費(fèi)同樣值得重視。“閱讀只不過是消費(fèi)的一個(gè)方面,但卻是其最基本的方面。”[18]傳統(tǒng)意義上,進(jìn)入到文本的語言符號(hào)系統(tǒng),就進(jìn)入了文本內(nèi)容的審美層面,也就是文本所謂的“本應(yīng)該”呈現(xiàn)給消費(fèi)者的面目。然而,給文學(xué)文本設(shè)定存在具有“文學(xué)性”這種“邏各斯”屬性是文學(xué)作為一個(gè)獨(dú)立的學(xué)科以來,尤其是從形式主義到接受美學(xué)一直延續(xù)的傳統(tǒng)。進(jìn)入到消費(fèi)話語語境中,文學(xué)的“文學(xué)性”傳統(tǒng)受到了質(zhì)疑與批判。
德·塞托指出消費(fèi)者的閱讀行為如同一種偷獵,消費(fèi)者并不是文本意義的消極體驗(yàn)者和接受者,而是旅行者,“他們在他人的土地上穿梭,在他們并未書寫的田野里過著偷獵式的游牧生活”。[18]也就是說,消費(fèi)者在消費(fèi)關(guān)系中獲得的是主體的身份。在消費(fèi)社會(huì)中,消費(fèi)主體是“去精英主義”的,且擁有對文本意義進(jìn)行解碼和再符碼化的巨大權(quán)力。在大眾消費(fèi)文化中,文學(xué)消費(fèi)具有了新的特性:“挪用”和“重構(gòu)”。一切的對文學(xué)的閱讀、闡釋、再造都是一種消費(fèi)實(shí)踐。文化意義上的挪用是指“占用、盜用”。消費(fèi)社會(huì)體現(xiàn)的是去深度、碎片化、快餐化的消費(fèi)文化,在這種文化語境中,文學(xué)的消費(fèi)也呈現(xiàn)出與文化相同的性質(zhì)。消費(fèi)者對于文學(xué)文本的“挪用”實(shí)現(xiàn)了對文本的再生產(chǎn),完成了意義的重構(gòu)。“挪用”模糊了文學(xué)/非文學(xué)、高雅/通俗、精英/大眾、經(jīng)典/非經(jīng)典、口語/書面之間的界限,將文本意義拓寬到整個(gè)歷史文化的語境中,它作為一種策略、一種操作行為將消費(fèi)者的主體地位加以強(qiáng)化。
首先這種“挪用”體現(xiàn)在對經(jīng)典的祛魅。“祛魅”是原是馬克思·韋伯在論述西方國家宗教化向世俗化社會(huì)發(fā)展的過程時(shí)使用的概念。祛魅的過程也是價(jià)值多元化的過程,那種精英主義的,推崇經(jīng)典文學(xué)的閱讀、欣賞和接受的文學(xué)觀念由于消費(fèi)的滲透而走向瓦解。經(jīng)典文本走下神壇,被去神圣化、去深度化,取而代之的是各種碎片化的“戲說”、“新編”、“戲仿”。其次“挪用”體現(xiàn)在對大眾消費(fèi)訴求的滿足。如果僅僅只挪用經(jīng)典,那么就不能把挪用看作消費(fèi)社會(huì)的專利。從古至今,文學(xué)的“互文性”體現(xiàn)的正是“挪用”的策略。然而,在消費(fèi)社會(huì),這種“挪用”更具大眾化,融合了商業(yè)策略與日常娛樂訴求。于是,從網(wǎng)絡(luò)語言到政策話語,從新聞事件到暢銷小說,從流行歌曲到影視作品,從明星到政客,無一不是被消費(fèi)的文本。這些文本在消費(fèi)文化這張大網(wǎng)中作為一個(gè)個(gè)能指不斷地流動(dòng),不斷地被占有和盜用,不斷地被編碼、解碼、再符碼化。消費(fèi)者作為主體是策略的實(shí)施者,是意義的接受者,也是意義重構(gòu)的生產(chǎn)者。
文學(xué)本身是一個(gè)互文、挪用,接受、再造的物質(zhì)事件過程,這個(gè)過程將文學(xué)文本的意義彌散開來。無論是購買還是閱讀都是消費(fèi)者對這個(gè)事件的參與和銘寫。文學(xué)消費(fèi)的三重性質(zhì)實(shí)質(zhì)上無法徹底區(qū)分和隔離,它們凝聚在文學(xué)事件當(dāng)中,相互關(guān)聯(lián),互為影響。
四、文學(xué)消費(fèi)與文學(xué)接受
談?wù)撐膶W(xué)消費(fèi)的問題是在物質(zhì)文化研究的視野中進(jìn)行的。當(dāng)下物質(zhì)文化研究發(fā)生在許多學(xué)科領(lǐng)域以及跨學(xué)科領(lǐng)域,使得物質(zhì)性這個(gè)概念呈現(xiàn)多樣化和模糊不定的狀態(tài)。《讀者與文本物質(zhì)性》一書中對文本的物質(zhì)性的總結(jié)或許有借鑒意義,文本的物質(zhì)性有四種指向:“(1)文本的解讀要結(jié)合它的物質(zhì)形式;(2)文本和它的互文性副文本可以作為物質(zhì)性意義的證據(jù)閱讀;(3)文本和物質(zhì)形式構(gòu)成意義的關(guān)系;(4)物質(zhì)形式,或者物質(zhì)與思想的闡連關(guān)系,影響著讀者群體和受眾對文本的理解和態(tài)度。”[19]與文學(xué)接受論關(guān)注的文學(xué)的形式與內(nèi)容不同,文學(xué)消費(fèi)論將視角投向了文學(xué)的物質(zhì)性實(shí)體、物質(zhì)性語言以及文本各組成部分之間動(dòng)態(tài)的意義生成關(guān)系等維度。
二十世紀(jì)九十年代初我國開始實(shí)行社會(huì)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商品化、貨幣化的經(jīng)濟(jì)規(guī)模逐漸成型,同時(shí),文化研究成為學(xué)界的顯學(xué)。文學(xué)消費(fèi)的問題開始進(jìn)入學(xué)人的視野。1998年修訂的童慶炳的《文學(xué)理論基礎(chǔ)教程》中對文學(xué)消費(fèi)進(jìn)行了論述,這是國內(nèi)第一次在文學(xué)理論教科書的意義上對文學(xué)消費(fèi)進(jìn)行闡釋。《文學(xué)理論基礎(chǔ)教程》重點(diǎn)借鑒了馬克思主義關(guān)于文學(xué)消費(fèi)的觀點(diǎn),將文學(xué)消費(fèi)的性質(zhì)解釋為既是一般的商品消費(fèi),又是特殊的精神產(chǎn)品消費(fèi)。書中闡釋文學(xué)消費(fèi)、文學(xué)接受、文學(xué)鑒賞三者的關(guān)系時(shí),將文學(xué)消費(fèi)定位為“初級(jí)階段”,文學(xué)接受居中,文學(xué)鑒賞為“最高層次”。可見當(dāng)時(shí)學(xué)界對于文學(xué)消費(fèi)的態(tài)度十分謹(jǐn)慎。這種三層次的等級(jí)制劃分顯然以讀者的審美(陶醉)為最高標(biāo)準(zhǔn),是接受美學(xué)范式指導(dǎo)的結(jié)果。而如果站在文學(xué)消費(fèi)論的立場上,這個(gè)等級(jí)就會(huì)反轉(zhuǎn)過來,使文學(xué)消費(fèi)成為“最高層次”。因?yàn)樵谖膶W(xué)消費(fèi)論的視域下,文學(xué)消費(fèi)的過程中那些處于“文學(xué)性審美”外的因素同樣重要,甚至可能具有更高的價(jià)值。實(shí)際上,從文學(xué)消費(fèi)的性質(zhì)看,只有文學(xué)作為一般商品進(jìn)行交換時(shí),文學(xué)消費(fèi)才是一定意義上的初級(jí)階段,在這個(gè)階段文學(xué)消費(fèi)只涉及貨幣交易層面。然而,交換層面的文學(xué)消費(fèi)不可能被完全隔離出來,因?yàn)樵诮粨Q行為之前,文學(xué)已經(jīng)經(jīng)歷了“商品化-去商品化-再商品化”的過程,并依然處于這個(gè)循環(huán)的系統(tǒng)當(dāng)中,權(quán)力、身份、品味、社會(huì)心理等等復(fù)雜的因素交織其中,這些都很難用等級(jí)制來歸納和解釋。因此,文學(xué)接受與文學(xué)消費(fèi)之間并不是高低等級(jí)關(guān)系,而是一種“域化”(territorialization)與“解域”(deterritorialization)的復(fù)雜關(guān)系。
文學(xué)接受基于“創(chuàng)造-作品-接受”的子系統(tǒng),以讀者為中心,強(qiáng)調(diào)讀者的審美閱讀對文本意義的產(chǎn)生所起的能動(dòng)作用。文學(xué)接受的對象是語言構(gòu)成的文學(xué)作品文本。讀者閱讀文本,從文本中獲得審美感受,激發(fā)文本審美價(jià)值和社會(huì)功能的實(shí)現(xiàn)。讀者作為主體,在審美經(jīng)驗(yàn)基礎(chǔ)上對文本的價(jià)值、屬性或信息進(jìn)行主動(dòng)的選擇、接納或揚(yáng)棄。雖然文學(xué)接受論認(rèn)為文本是開放的,意義延展的,但文學(xué)接受所處的系統(tǒng)相對封閉,它的對象是文學(xué)文本,接受活動(dòng)被局限在文本的語言符號(hào)系統(tǒng)。文學(xué)接受論對于文學(xué)作為“物”的屬性進(jìn)行了有意地忽視,它追求讀者對文本意義的最大化呈現(xiàn),認(rèn)為如果不是讀者的再創(chuàng)造,文本只能是死氣沉沉的物。也就是說,文學(xué)接受看重的依然是文學(xué)的“文學(xué)性”。“通過將讀者‘請進(jìn)’文本之內(nèi),接受美學(xué)瓦解了作者對于文本的‘自主性’。但遺憾的是,讀者從而也被封閉在文本之內(nèi),作品仍然是作者的作品,是經(jīng)由作者的作品。”[20]這種相對封閉的接受活動(dòng),對文學(xué)進(jìn)行著“封疆建域”,使文學(xué)活動(dòng)與人類社會(huì)的其他活動(dòng)領(lǐng)域隔離開來,這就是文學(xué)接受論對文學(xué)的“域化”。
文學(xué)消費(fèi)則傾向多元化的視角,消費(fèi)活動(dòng)發(fā)生在多個(gè)子系統(tǒng)中。這些子系統(tǒng)又同處于社會(huì)物質(zhì)文化的多元巨系統(tǒng)中,相互依存,相互界定,彼此作用。因此,文學(xué)消費(fèi)所關(guān)涉的領(lǐng)域和范圍比文學(xué)接受更為廣闊。相對于文學(xué)接受對文學(xué)“物性”的忽視(甚至蔑視),文學(xué)的“物性”在文學(xué)消費(fèi)這里得到了充分的呈現(xiàn),是物將我們與文化聯(lián)系起來,我們與物形成了一種相互的意義重構(gòu)和情感糾纏。“物不只是我們制造的產(chǎn)品,設(shè)計(jì)來幫助我們滿足基本的本能需求,物也是我們借以表現(xiàn)我們是誰及我們是什么樣的人的表達(dá)方式,而這些也是形塑社會(huì)進(jìn)展的要素。”[15]文學(xué)接受對于閱讀行為的考察傾向于讀者的審美經(jīng)驗(yàn)和藝術(shù)心理以及對文本意義的再創(chuàng)造。而文學(xué)消費(fèi)則在社會(huì)文化系統(tǒng)中考察消費(fèi)者的消費(fèi)行為和對文本意義的再生產(chǎn)。文學(xué)消費(fèi)的主體是消費(fèi)者,消費(fèi)的過程也是物質(zhì)性的文化實(shí)踐的過程,這個(gè)過程與消費(fèi)者的趣味、身份、心理、動(dòng)機(jī)息息相關(guān)。正如埃斯卡皮所說:“讀者是消費(fèi)者,他跟其他各種消費(fèi)者一樣,與其說進(jìn)行判斷,倒不如說受著趣味的擺布,即使事后有能力由果溯因地對自己的趣味加以理性的、頭頭是道的說明。”[12]文學(xué)消費(fèi)論認(rèn)為消費(fèi)者并不絕對規(guī)訓(xùn)于意識(shí)形態(tài)“策略”,“消費(fèi)者的消費(fèi)程序和計(jì)謀將構(gòu)成反規(guī)訓(xùn)的體系”。[18]作為主體的消費(fèi)者在消費(fèi)中對意識(shí)形態(tài)的反規(guī)訓(xùn)、抵抗在文學(xué)消費(fèi)論看來是頗為重要的。讀者不再被認(rèn)為是文學(xué)意義的被動(dòng)接受者,他們是“政治的、建構(gòu)的、決定的、權(quán)威的、參與的和好奇的。受眾可以是書商、收藏者、發(fā)布者……受眾既可以是作者也可以是讀者。”文學(xué)接受看重的依然是文學(xué)的“文學(xué)性”,文學(xué)消費(fèi)論則不再相信所謂的“文學(xué)性”,取而代之的是“社會(huì)性”,或者說“文化性”。我們在物質(zhì)文化的世界里消費(fèi),也消費(fèi)著我們的文化意義,在消費(fèi)過程中意義不斷被編碼、解碼、再符碼化。因此,可以說文學(xué)消費(fèi)論是對文學(xué)接受論的“解域”。
總而言之,文學(xué)消費(fèi)與文學(xué)接受之間,并不僅僅是概念術(shù)語的轉(zhuǎn)變,而是觀念范式的轉(zhuǎn)變。二十世紀(jì)六十年代接受美學(xué)的繁榮將文學(xué)研究帶向了以讀者為中心的維度。當(dāng)文學(xué)研究界在大力談?wù)撐膶W(xué)接受的時(shí)候,文學(xué)消費(fèi)作為新的理論話語在二十世紀(jì)八十年代開始向文學(xué)研究的各個(gè)分支滲透,漸漸引發(fā)了文學(xué)觀念的變革。然而,從文學(xué)接受到文學(xué)消費(fèi)不能僅僅在歷時(shí)性的維度上來把握,這樣容易忽視文學(xué)接受和文學(xué)消費(fèi)之間的“交集”部分,也容易引發(fā)誤解,認(rèn)為文學(xué)消費(fèi)是對文學(xué)接受的替代。因此,談?wù)撐膶W(xué)的物質(zhì)性和文學(xué)的消費(fèi)問題不是對文學(xué)的鑒賞、審美、接受等維度的摒棄,而是指出當(dāng)下文學(xué)理論研究的觀念范式轉(zhuǎn)換的必要性,力圖從物質(zhì)性的、社會(huì)性的、文化性的多元維度考察當(dāng)下文學(xué)本身以及文學(xué)研究的新問題。
[1]余虹.審美文化導(dǎo)論[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146.
[2](德)馬克斯·霍克海默,特奧多·威·阿多諾.洪佩郁,藺月峰.啟蒙辯證法[M].重慶:重慶出版社,1990.148.
[3](法)讓·波德里亞.劉成富,全志鋼.消費(fèi)社會(huì)[M].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0.68.
[4](英)邁克·費(fèi)瑟斯通.劉精明.消費(fèi)文化與后現(xiàn)代主義[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123.
[5]HUGH MACKAY .Consumption and Everyday Life[M].London:Sage,1997.3.
[6](英)丹尼爾·米勒.張松萍.消費(fèi):瘋狂還是理智[M].北京:經(jīng)濟(jì)科學(xué)出版社,2013.72.
[7]DAVID GRAEBER.Consumption[J].Current Anthropology.2011,52(4).490.
[8](英)斯科特·拉什,西莉亞·盧瑞.要新樂.全球文化工業(yè):物的媒介化[M].北京:社會(huì)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10.29.
[9](荷)W.伊維德.關(guān)于中國文學(xué)史中物質(zhì)性的思考[J].上海師范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4(4):101
[10](加)馬歇爾·麥克盧漢.河道寬.理解媒介:論人的延伸[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0.33.
[11]IGOR KOPYTOFF.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Things:Commoditization as Process [A].Arjun Appadurai.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C].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6.64;8.
[12](法)羅貝爾·埃斯卡皮.于沛選.文學(xué)社會(huì)學(xué)[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4.
[13](美)阿爾君·阿帕杜萊.孟悅、羅鋼.商品與價(jià)值的政治[A].物質(zhì)文化讀本[C].北京: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8.23-24.
[14](英)丹尼爾·米勒,費(fèi)文明,朱曉寧.物質(zhì)文化與大眾消費(fèi)[M].南京:江蘇美術(shù)出版社,2010.185.
[15](英)Tim Dant,龔永慧.物質(zhì)文化[M].臺(tái)北:書林出版有限公司,2009.52;20
[16]WILLIAM LEISS.The Limits to Satisfaction:An Essay on The Problem of Needs & Commodities[M].Kingston and Montreal:McGill-Queen’s University Press,1988.82.
[17](法)尚·布希亞.林志明.物體系[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222-223.
[18](法)米歇爾·德·塞托,方琳琳,黃春柳.日常生活實(shí)踐:1.實(shí)踐的藝術(shù)[M].南京: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9.261.
[19]GRAHAM ALLEN,CARRIE GRIFFIN,MARY O’CONNEL.Reading on Audience and Textual Materiality[M].London:Pickering & Chatto,2011.2.
[20]金惠敏.消費(fèi)他者:全球化與資本主義的文化圖景[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14.138.
I03-03
A
1002-3240(2017)03-0132-07
2016-09-07
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xiàng)目“物性詩學(xué)導(dǎo)論”(15FZW027)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yè)務(wù)費(fèi)專項(xiàng)資金資助項(xiàng)目(15LZUJBWYJ007)階段性成果
張進(jìn),蘭州大學(xué)文學(xué)院博士生導(dǎo)師,主要從事文藝?yán)碚摵捅容^詩學(xué)研究;王垚,蘭州大學(xué)文學(xué)院博士生。
[責(zé)任編校:陽玉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