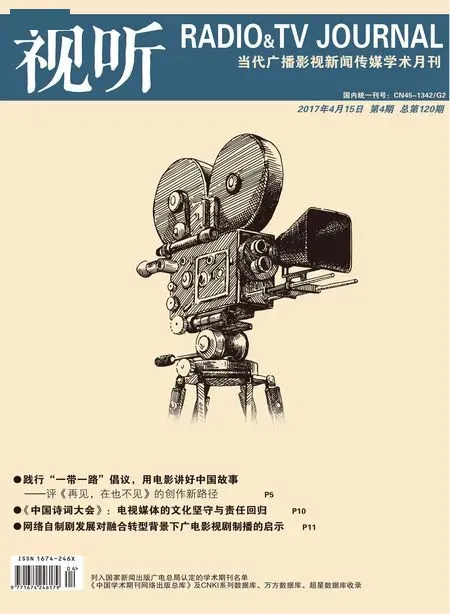基于編碼/解碼理論探析文本生產過程中的霸權性
——以“蕾力CP”事件為例
□譚婷
基于編碼/解碼理論探析文本生產過程中的霸權性
——以“蕾力CP”事件為例
□譚婷
本文聚焦于引發社會廣泛關注的“蕾力CP”事件,以霍爾的編碼/解碼為理論框架,分析編碼者的文本生產過程和受眾在其中的角色。本文認為媒介事件的傳播過程具有霸權性質,它是節目編碼者、自媒體營銷號和部分受眾的一場合謀。當然,并不是所有受眾都是被娛樂麻醉、不知思考的妥協者,在喧囂嘈雜的趨同性聲音中思考者會吶喊出理性的聲音,他們的對抗性思考會對編碼者產生實質性影響。因而受眾既要關注網臺融合背景下由編碼者有意圖主導的罔顧倫理法紀的媒介事件,也需要警惕自我被娛樂消解出的犬儒理性。
“蕾力CP”事件;文本編碼霸權;編碼/解碼;犬儒理性
作為一檔在國內播出系列集數最長的綜藝親子節目,《爸爸去哪兒》自2013年10月11日第一季開播,一直到2016年10月14日,總共播出了四個系列的節目。《爸爸去哪兒》前三季節目是在湖南衛視臺播出,第四季節目從湖南衛視轉戰網絡平臺“芒果TV”播出。與前三季不同的是,本季新增了由明星和普通家庭兒童組合而成的“臨時父子、父女組合”。《爸爸去哪兒》第四季節目基于網絡平臺“芒果TV”播出后,觀看者與節目制作者的互動更加深入,受眾對信息的及時反饋對信息意義的再生產予以影響。其中,萌娃阿拉蕾、實習爸爸董力一度占據熱門話題榜單,成為“蕾力CP”事件。媒介事件的產生依賴于受眾對于“事件”不斷的意義生產和意義建構,而意義的生產和傳播存在著“主導的復雜結構”。本文運用霍爾編碼/解碼理論分析“蕾力CP”事件中編碼者在文本生產過程的霸權性以及文本信息是如何生產出來的。
一、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
在斯圖亞特·霍爾于1980年發表的論文《編碼/解碼》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阿爾都塞與葛蘭西的影子。阿爾都塞的“支配理論”給了霍爾很大啟發,霍爾認為,這一理論突出了“再生產”這一關鍵概念。同時霍爾吸收了葛蘭西的“霸權理論”,霍爾認為,文化領導權和霸權的獲取主要是通過被支配階級和集團的積極贊同來取得。他強調支配并且決定表面現象的深層結構即意識形態,而“傳媒是被結構在統治支配之中”。霍爾用示意圖解讀出了編碼和解碼的符碼并不一定對稱的特征。在他看來,正因為這種失衡狀態的存在,我們才能發現釋碼過程相對于編碼意義的獨立性,也就是說,釋碼行為擁有其專屬的生命與力量,接收者并非“被迫”遵循編碼者的意愿來接收訊息,而是通過對文本進行歧義性或反抗性解讀來抵制意識形態權力及文本的影響力。
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闡述出的文本意義與外部世界緊密相聯,編碼者對于文本意義的整合以及符號化的支配地位與其社會責任密切相關。傳播,包括其各個階段,均非不偏不倚的中立過程,在我們生活的社會里,作為精英的廣播者與受眾之間的傳播過程完全是一種“系統性扭曲”。在編碼與解碼的不對等性背后隱藏著主導話語的控制和軟性意識侵襲,實質是披著綜藝、休閑、娛樂的糖衣在輿論平臺爭奪話語掌控權的編碼意圖。當前網絡環境下編碼者對于文本意義主導地位和意識形態霸權地位的掌握是通過信息以話語形式在傳播交流中占據的特殊位置實現的。行動參與者能夠輕易地觀察到其他參與者的編碼,而參與者的解碼會受其影響,同時行動參與者編制出的話語意義會向其他輿論領域擴散,常常引起其他媒介的關注并形成互動態勢,此時其他媒介同樣對事件進行著編碼與解碼并進一步構建意義。
二、“蕾力CP”事件回顧
《爸爸去哪兒》第四季自開播以來,萌娃阿拉蕾、實習爸爸董力長期占據熱門話題榜單,在快速走紅的同時,大量質疑聲也隨之而來。收看節目的觀眾把這對“父女”解讀為“CP”,同時與“阿拉蕾、董力”相關的微博評論及微信營銷號的軟文呈現出跟風狀態,引發了教育、法律、公安、公益組織等人文社會學科領域工作者的關注。為清晰地呈現這一媒介事件的發展始末,本文選取引發受眾廣泛熱議的節點事件進行回顧。
11月4日13∶00分,@爸爸去哪兒官微發布微博信息“慎重通知!高能預警!請注意!今晚蕾力父女又要虐狗啦?”
11月17日,自媒體“嚴肅八卦”發表了一篇致歉文章,指出此前渲染“蕾力CP”多么有愛,而沒有注意到節目存在的錯誤示范和危險暗示。
11月18日,作為公益組織的官微@女童保護發表目前閱讀量已經達446萬+的文章《一名準媽媽致“爸爸去哪兒”節目組:請停止渲染“董力阿拉蕾CP”!》,文章指出對于兒童防性侵教育而言,節目內容打破了基本底線,充滿了諸多錯誤的示范……因此呼吁有關廣電網信部門及時干預,營造良好的網絡文化環境以保護未成年人。
11與18日,作為當事人之一的董力發表微博表示自己是成年人,懂得把握分寸,一定會尊重阿拉蕾的隱私。對于之前采訪中說要等阿拉蕾長大,董力稱只是玩笑。截止到18號凌晨,#董力阿拉蕾CP爭議#的微博話題閱讀量高達5969.7萬。
11月19日20∶46分,@爸爸去哪兒官微回應:“單純的總是最美好的,《爸爸去哪兒》以親情為本,不支持過了味的過度解讀,也反對一些自媒體營銷號為了博取眼球而無底線的妖魔化言論。”
11月22日9∶51分,@公安部打四黑除四害的官微援引央廣網《真人秀熱炒女童與成人“情侶CP”遭批,專家:有誤導之嫌》的文章,文章中專家認為,節目最大的誤導是讓兒童對“熟人”失去防范意識,而生活中80%被性侵的兒童是熟人作案。
三、“蕾力CP”事件中的霸權性文本生產
(一)“蕾力CP”文本的傳播平臺
只有當媒介信息與其他溝通模式互為補充,媒介沒有被另一種流通范圍更廣的媒介挑戰,媒介吸納并傳播既有價值信念和感知結構時,其影響力最大。《爸爸去哪兒》第四季節目的宣傳力度與以往相比有增無減,節目組有意無意地渲染董力和阿拉蕾“父女間”的“非親情”關系,這種信息輻射于各大有影響力的媒體平臺。在傳統媒體平臺,董力攜阿拉蕾上湖南衛視《快樂大本營》《天天向上》等國內受眾比較廣泛的電視綜藝節目;網絡平臺上,則是在芒果TV首頁醒目宣傳板塊,《芒果撈星聞》特別策劃節目,以及百度貼吧中關于“蕾力CP”“蕾力夫婦”的“戀愛視頻”、同人文已經存在;在社交媒介平臺,如爸爸去哪兒、芒果TV等官方微博、微信平臺進行全媒體宣傳。
格蘭諾維特認為:“強連帶往往形成小圈圈,弱連帶往往會形成一張大網絡。”社交媒體的弱鏈接特性,讓文本信息無處不在,形成了一張巨大的信息網,而受眾從無所不在的媒介文本信息中接收到的不僅僅是簡單的娛樂休閑符號,或者某種口頭形式意義結構的分析,他們接收的更是一個場域,一種社交形式,一種理念意義。
(二)受眾反饋被編碼者預設
霍爾指出,“主流的傳媒理論正確地認識到傳媒在輿論表達方面的作用,但它錯誤地認為,這種一致的輿論原本就存在于社會之中,相反,這種一致的輿論其實是由傳媒生產或者部分生產出來的。”在節目文本創作之初,“爸爸去哪兒”節目組已對受眾的情感傾向度、內容期待度、心理承受度以及對話題的關注度提前進行預設。芒果TV平臺發布的彈幕信息、留言,B站對原創文本的剪輯作品,微信平臺的公眾號文本創作,以及現實的人際交往討論信息都會作為節目組在對節目進行宣傳和后期編輯時的參考信息。
傳播學者尼爾·波茲曼認為:“一種信息傳播的新方式所帶來的社會變遷,絕不止于它所傳遞的內容,其更大的意義在于,它本身定義了某種信息的象征方式、傳播速度、信息來源以及信息存在的語境,從而在更深刻層面上影響著特定時空中的社會關系、結構與文化。”互聯網時代,媒介所具備的共享、合作、群聚等特性使得受眾的意見和心理更容易得到迎合和滿足,編碼者以一種潛藏的方式把受眾希望接收的信息、資訊編碼在銀幕前,把編碼者的意圖與受眾接收文本信息后產生的意圖產生共振。
(三)賦予文本新意義促進再消費
霍爾根據生產、流通、使用及再生產四個階段理論,運用通俗的商品生產理論來描述信息傳播過程的特征,敏銳地抓住了信息傳播的獨特性。霍爾認為:“產品的流通和針對不同觀眾進行的產品分配都是以這一話語形式發生的,話語一旦完成,接著就必須轉譯——改造實踐,如果流通既圓滿又有效果的話,不賦予‘意義’,就不會有消費,如果實踐中沒有講清楚意義,就不會有任何作用。”“蕾力CP”的解讀是在各種不同流通環節當中完成了意義文本的再生產,新的信息生產會促進原有文本意義的再消費。董力和阿拉蕾互動的信息是節目組為了收視率有意識添加的諸如“虐狗”“甜蜜”“CP”等的宣傳文本,于是微信營銷號對這種信息文本注入了更加娛樂化的信息,貼吧和視頻網站則加入成人與兒童戀情的信息。信息構筑的故事線索在不同的解讀版本中根據主導意義進行意圖控制,不同文本信息根據各自脈絡往前發展。
在電視創作環節,主導型文本信息通過專業團隊制作和團隊宣傳無限放大,在第二環節受眾接受“蕾力CP”信息解讀時,依循原有的信息版本,進行再次創作,所有信息都是在原有的范圍內生產、制作、消費和再消費。信息意義的霸權形式通過媒體受益者的加工,讓不符合倫理的事件被認同,產生合意,這種由媒介文本主導、產生不符合社會價值的文本信息投入到更加廣泛的虛擬空間被大眾廣泛消費。
四、結語
新媒體時代,網絡衍生的多種類型亞文化挑戰了傳統倫理道德的底線,從而引發網民廣泛熱議的媒介事件無一例外都具有霸權性,是節目制作者、媒體經營者和節目受眾的合謀。大眾應當時刻警惕這種因形成所謂的共識而被慢慢接受的違背社會倫理道德的觀念。媒體是受眾接觸信息的主要渠道,對社會教育、娛樂的信息傳遞擔負著重要責任,對信息文本具有主導地位和控制權,即使是在社交媒體和自媒體異常興盛的當下,話語權的不平等和信息接受的不對稱仍然廣泛存在。無論是親子節目、選秀節目,還是教育節目、益智節目,收看節目的大眾都要在追求休閑娛樂的同時保持一定的理性,不能過度盲目屈從。盡管新媒體時代話語和傳播方式無法實現人們的生活平等,盡管資源、機遇、權威和權利分配永遠無法平衡,但只要大眾能夠尊重差異,在沖突和競爭的條件下始終保持寬容和克制,社會就能朝著良好的態勢運行。
1.許正林.歐洲傳播思想史[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04):360.
2.羅鋼,劉象愚.文化研究讀本[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01):346.
3.[美]伊萊休·卡茨著.常江譯.媒介研究經典解讀[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01):247.
4.梅梅,何明升.網絡集體行動的意義建構——基于斯圖亞特·霍爾的編碼/解碼理論的分析[J].南京郵電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5(09):24-29.
5.[美]馬克·格蘭諾維特著.羅家德譯.鑲嵌:社會網與經濟行動[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07):191.
6.許正林.歐洲傳播思想史[M].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5(04):360.
(作者單位:西華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