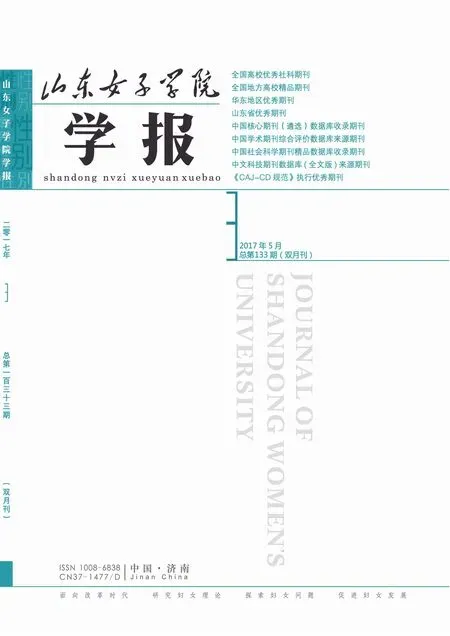性別隔離與男權話語中的權力運作
施文斐
(中國礦業大學銀川學院,寧夏銀川 750000)
?
·性別平等理論研究·
性別隔離與男權話語中的權力運作
施文斐
(中國礦業大學銀川學院,寧夏銀川 750000)
性別隔離發源于古老的女體禁忌,最初僅為出于生命安全憂慮而向特定女性實施的周期性隔離措施。男權話語通過提煉女體禁忌中的歧視“因子”、預設虛構的話語前提以及實施種種話語策略等一系列的話語權力運作,巧妙地將原本保持中立立場的安全保障措施置換為歧視女性、壓迫女性的性別政治工具。而且話語權力運作的隱蔽性,使得性別隔離直至今日仍在社會性別分工、性別角色定位等方面保持著強大的現實干預力,職業性別隔離更可視為傳統性別隔離在現代職場中的變相延伸。明確男權話語于其間的具體運作將有助于我們充分認清性別隔離的本質,以及時至今日仍“經久不衰”的“奧秘”所在,從而對女性解放的現狀保持更為清醒的認識。
性別隔離;女體禁忌;女性劣等論;身體控制;話語權;話語權力
性別隔離,亦即“嚴男女內外之別”的性別空間區域劃分,性別隔離自古有之,《禮記》有云,“禮,始于謹夫婦,為宮室,辨外內。”(《禮記·則》)“辨”,別也,“別的功能是為了要建立秩序”[1](P266),以家內、家外的物理界限將男女兩性各自所應歸屬的空間區域區別開來被認為是社會秩序(禮)得以建立的原初與根基。唯有“男女有別”,而后才能“夫婦有義;夫婦有義,而后父子有親;父子有親,而后君臣有正。”(《禮記·昏義》)性別隔離被賦予的意義遠不止于兩性層面,更被上升到了政治倫理的高度。性別隔離之于秩序,無論是性別秩序還是政治秩序的建立至關重要。
性別隔離對兩性關系格局的影響極其深遠,為世俗觀念所普遍接受的“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易·人·彖》)、“男治外事,女治內事”(司馬光《溫公書儀》卷三《婚儀上》)的社會性別分工,以及在女性性別群體中享有極高認同度的“賢妻良母”的角色定位都與此有著密切關聯。然而,這一以“隔離”(“別”)為重要表征的性別秩序究其實質卻正是產生于針對女性的偏見與歧視,建立于生物差異上的女性劣等論于背后發揮著重要的理論支撐作用。然而,僅有理論支撐是遠遠不夠的,任何“有偏見的態度和歧視行為”的有效實施都必須得到權力的保障。權力首先存在于話語之中,按照后現代主義的觀點,話語即為權力①,“影響和控制話語運動的最根本因素就是權力,而真正具有特殊效應的權力,也是通過話語來執行的”[1](P201)。厘清性別隔離產生的源頭,明確為男權社會所掌控的話語權力于其間的具體運作將有助于我們充分認清性別隔離的本質,對時至今日依然存在著的性別隔離,如職業性別隔離的強大現實干預力保持清醒的認識,從而為女性主體意識的真正覺醒,為女性解放的真正實現鋪平道路。
一、性別隔離的話語探源:女體禁忌與歧視“因子”的提煉
據文化人類學的考察可知,性別隔離早在原始社會即已有之。就其原初動機而言,性別隔離的實施主要是出于對處于經、孕、產等特殊生命期的女性身體(女體)的一種禁忌,伴隨著特殊生命期產生的大量出血(經血、產血)是導致此類女性被隔離對待的重要原因。
著名的文化人類學者詹姆斯·喬治·弗雷澤通過對“德內(美洲)和大多數其他美洲氏族部落”的考察發現,在這些原始部落中,“幾乎沒有任何人像來月經期間的婦女那樣為人們所畏懼”,一旦處于行經期,她就會“立刻被謹慎地同一切異性人們隔開,獨自住在為本村男人或來往行人中的男子看不見的偏僻小屋里”[2](P199),產婦也同樣會“被隔絕起來,直到健康和體力恢復,想象的危險期度過為止。”[2](P200)處于行經期的女性以及產婦之所以被認定為危險的存在而被隔離對待,在相當程度上正是出于對其間大量產生的經血、產血的污穢恐懼,“她們可能會污染她們接觸的任何人和任何東西”[2](P199—P200),為此,即便已被隔離開來,處于行經期的女性也要小心翼翼地“不得觸及任何屬于男人用過的東西或任何獵獲的鳥獸與其他動物的皮肉,以免因此玷污了這些東西”[2](P199)。在一些地區,“婦女坐月子期間丈夫必須隔離八天,不得在家居住”,同樣懼怕的是“受污染”[2](P200)。圍繞著女性特殊生命期的血污恐懼進一步促成了大量迷信的產生,譬如“沾上女人的經血會讓鮮花枯萎、果實腐爛、象牙失去光澤、長劍不再鋒利、狗兒發瘋”等等[3](P90)。在一些地區,人們甚至相信只要此類女性的身影出現即能導致上述災害的發生,而無論是否發生過實際接觸。
正是出于對女性神秘力量的極度困惑、強烈的血污恐懼以及深重的生存憂慮,人們才會普遍相信必須要將處于特殊生命期的女性這一“污染源”與整個社會公共空間隔離開來,通過將其神秘力量盡可能地控制在一個可掌控的范圍內以保障整個社會公共空間的生存安全,以女體禁忌為特征的性別隔離正是在這一樸素的原始認知下逐漸形成的。
這一有關性別隔離的原始認知與古老禁忌在巫術信仰與宗教教律中都得到了繼承與延伸。在記載了利未族的祭司團所應遵奉的一切律例的《利未記》中,就將古老的女體禁忌形成了明確、細致,甚至有些煩瑣的話語表述②,并規定“她潔凈的日子未滿,不可摸圣物,也不可進入圣所”(《圣經·利未記》12:4)[4](P182)。與西方的宗教教律相似,在巫術氛圍濃重的宋人社會中,有著鮮明巫術色彩的醫藥操作中同樣蘊含了對特定女性實施的女體禁忌。這一禁忌不僅如漢唐時期那樣體現在“合藥、用藥之時”,而且還進一步擴大到了“藥物從采摘、收藏、制備,到取拿、服用的全過程”③,女體禁忌也由最初的只針對特定女性擴展到了整個女性群體,“切忌婦人、雞犬見”(朱端章《衛生家寶產科備要》卷六),“忌見喪服、色衣、婦人、貓犬之類”(蘇軾、沈括,《蘇沈內翰良方》),“忌僧尼、婦人、孝子、雞犬,一切厭穢見之”(佚名,《衛濟寶書》卷下),“勿令婦女、小兒、喪孝、產婦及痼疾、六根不具之人及六畜見之”(《太平惠民和劑局方》附《指南總論》上)④之類的話語表述大量充斥于宋人醫書之中,其所傳達的正是唯恐女性尤其是處于特殊生命期的女性的“不潔與污穢”導致藥效失效,并進而危害生命安全的嚴重憂慮。
通過以上對古老禁忌、宗教以及巫術思維下的醫藥操作的簡要考察可知,女體禁忌早在原始社會以及以巫術、宗教為代表的古老意識觀念中即已存在。需明確的一點是,此時的女體禁忌并不必然意味著針對女性群體的性別歧視。誠如上文分析所示,對特定女性實施的周期性隔離措施主要是出于生命安全的考慮,而且,人們相信隔離措施的實施對女性自身也是有益的,否則她們就會“瘦得皮包骨頭”或者“全身就會潰瘍”[2](P542)。性別隔離正是為了保障女性自身以及他人的生命健康而實施的安全保護措施。
但同時不可否認的是,性別隔離中確實已然內含了針對女性這一性別群體的歧視“因子”。“最低的私密的身體過程,能夠賦予最復雜的和形而上學的解釋”[5],將處于特殊生命期的女體視為“不潔與污穢”,其本身就是在進行著善惡、正邪的道德判斷,《利未記》中規定的女性因經血不潔、產血不潔而須獻祭、贖罪的條例清楚地表明了這一點⑤。在古代中國,處于特殊生命期的女性也同樣“不得參與家族祭祀這類嚴肅、莊重的場合,不得接近神龕、祭桌、祭品和巫師,否則的話就會褻瀆祖先的亡靈,是對祖先的不敬。”[1](P94)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女性之所以被加之“不潔與污穢”的道德判斷不是因為別的什么原因,而恰恰是根源于女性自身特有的、先天存在的、無法避免的生理現象。“在父權社會中,女性的生理特征往往被貶低和歪曲為不健全、不潔凈,尤其是行經和生育現象,多半被視為神圣的對立面而加以禁忌。”[6]僅僅因生理差異而成為禁忌,更進而遭到歧視,這完全是一種生物決定論的論調。這樣一種論調在十六、十七世紀曾普遍流行于近代早期西歐社會的“體液學說”中并得到了繼承。這一性別闡釋話語將人體視為“一副容納著體液的皮囊”,“男人性屬熱干,女人則屬冷濕”[3](P82),男女兩性的一切差異,以及由此而產生的一切道德判斷都起源于所謂“體液”的不同。例如當時的學者曾以這一理論解釋過何以女人沉在水里時會面朝下而男人一般面朝上的現象,認為其原因就在于“男人、熱量、光線和上帝之間存在著內在關聯,而女人則與潮濕、陰冷聯系在一起,所以很少會面向天空。”[3](P90)顯然,男性體內的熱干性體液象征著一種陽性的力量,與太陽、熱量、光線保持著某種神秘的內在聯系;而女性體內的冷濕性體液則與陰性的力量非常相似,總是與潮濕、陰冷發生著聯系。這一性別差異上的本質主義傾向更進而取得了宗教層面上的支撐,“女人的本性是造物主創造的陰暗面,她比男人更接近魔鬼,而男人受到的更多的則是上帝的好影響”[3](P89)。從古老的女體禁忌中“提煉”出“不潔與污穢”的歧視“因子”,再將對特定女性的血污恐懼擴展到面向整個女性群體的體液厭惡,最后借由宗教層面上對“上帝”(善)與“魔鬼”(惡)的比附作出“相應的”道德判斷,女性這一性別群體就這樣在男權話語的一系列運作下被無可辯駁地貼上了劣等的標簽。
二、性別隔離的預設話語前提:“不完整的人”與沉默的失語者
通過上一部分的分析可知,古老的女體禁忌雖并不必然意味著針對女性的偏見與歧視,但確實促發于為女性所獨有的生理現象。對女性特殊的生理現象,如月經、生育及經血、產血的困惑與恐懼都是圍繞著為女性所特有的生殖場域而發生的,這一生殖場域的存在無可辯駁地標志了女性的身體與男性的是多么地不同,多么地異質。相較于男性,女性身體所表現出的“異質性”是女性遭到性別歧視的又一重要原因。
這里,顯然有一個預設的假定前提,即“將男性身體定義為標準人類軀體”[7](P8),女性身體由于其自身呈現出的巨大異質性而被視為有缺陷的、不標準的、不完整的,13世紀著名的神學家托馬斯·阿奎那即將女性看作“有缺陷的男人,是由于性交失誤而生下來的男人”[1](P151),是“不完全的人類”[8]。“女性并不被視為獨立的個體……女性是參照男性來定義和區分的”[7](P7),以男性身體為參照,將女性貶低為“不完整的人”這一觀念意識可以一直追溯到神話時代。最初的女性夏娃僅僅是從亞當身上所取的一根肋骨,神出于“那人獨居不好,我要為他造一個配偶幫助他”(《圣經·舊約·創世紀》2:18)[4](P10)的愿望而創造出了夏娃,她的誕生完全取決于男性的需求,不僅在身體上是不完整的,在意志上也同樣是從屬的。這一“神說”話語的運用之于女性從屬性的確立具有重大意義。原型—神話批評的著名學者諾思洛普·弗萊曾就神話與意識形態之間的關系表述過這樣的觀點,即“每種意識形態開始時都就其傳統神話體系中意義重大部分提出自己的認識,并利用這種認識去形成和實施一種社會契約”[9](P30)。依據這一觀點,《圣經》將關于人類始祖的伊甸園神話緊隨于創世紀神話之后,又將女性的“肋骨誕生說”置放于伊甸園神話之始,這一話語策略本身即體現了意識形態領域中的一個重要認知,即性別秩序的建立是與宇宙生成同樣重要的頭等大事,而確立女性的從屬性則是性別秩序得以建立的關鍵。恰如亞當所說的,“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稱她為女人,因為她是從男人身上取出來的”(《圣經·舊約·創世紀》2:23)[4](P10),由男權話語主導的神話完全成為了“一種為了使女性處于從屬地位,并設法將其永遠置于此從屬地位的一系列觀念、偏見、趣味和價值觀系統”⑥。女性的先天缺陷,即身體上的不完整性以及意志上的從屬性都從“神說”話語的權威性中得到了認定。
女性“先天缺陷”的權威認定,或者說女性劣等論的確立之于性別隔離的實施具有重大意義,既是性別隔離的預設前提,又由性別隔離的實施而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由于女性被認定為先天就是有缺陷的、不完整的,因此女性的智力水準乃至于道德品質也就順理成章地遭到了否定。圣保羅曾將男性比作女性的“頭”,“你們作妻子的,當順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順服主。因為丈夫是妻子的頭,如同基督是教會的頭”(《圣經·新約·以弗所書》5:22、23)[4](P357),女性的存在價值僅與“身”等同,而“身”無疑是要服從“頭”,聽從“頭”的意愿的。這一觀點與西方社會慣于將男性與理性、精神相聯系,而將女性與肉體、欲望相聯系這一性別上的二元(靈、肉)對立論完全一致,女性被視為“永遠也不能發育成熟的‘孩子’”,她們“既愚蠢又淺見”,其智力水平永遠只停留在“男性成人和小孩之間”[10]。
正是因為“她”的缺乏頭腦、極端愚蠢,女性被剝奪了于社會公共空間發聲的權力。圣保羅曾要求“婦女在會中要閉口不言,像在圣徒的眾教會一樣,因為不準她們說話。她們總要順服,正如法律所說的。她們若要學什么,可以在家里問自己的丈夫,因為婦女在會中說話原是可恥的”(《圣經·新約·哥林多前書》14:34、35)[4](P311)。于社會公共空間發聲的權力被完全賦予了男性,有資格與神對話的永遠是擁有話語權的亞當,而夏娃僅僅是亞當背后的一個沉默的失語者。作為男權社會中的他者,被剝奪了話語權的女性群體也只能保持沉默,語言中蘊含著的“至高無上的權力與威力”以及“從語言權力與威力中派生出來的暴力”都為男性所獨享[9](P24)。盡管女性有時也會滔滔不絕,“不停地說,嘮嘮叨叨,口腔充滿著聲音,從嘴里發出聲音”,但她說出的話并不具備任何話語權威,僅僅是“talk”,而不是“speak”,“她們實際上并沒有表達,因為她們沒有什么可表達的。”[11]失去了話語權的女性即使在社會公共空間現身,甚至于偶然發聲,但也仍是一種“缺席”,仍是一種“失語”,她的身體與聲音不具任何意義。
恩格斯曾指出:“母權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失敗。”[12]在此基礎上,筆者更進而認為女性話語權的喪失是進入父權制社會后,女性這一性別群體所遭受的又一重大失敗。由于話語權的被剝奪,女性失去了反擊性別歧視的重要途徑,而只能任由掌控了話語權的男性社會擅自界定女性的身體、智力乃至于道德品質。不僅如此,憑借著手中掌控的話語權,女性劣等論被男性社會以各種話語方式反復灌輸給了女性群體,直至內化為女性“自覺”的自我性別體認,“賤妾”“賤婢”之類的自稱無疑是女性劣等論內化成功的體現,反映了女性主體性喪失后的一種低自尊狀態,而“保持女性低自尊對父權力量結構是有利的”[13],譬如,性別隔離的有效實施。
女性劣等論這一話語前提的預設,以及隨之促成的女性話語權的喪失,尤其是女性對自身“劣等性”的自我認同使得性別隔離的實施變得更加暢通無阻。被驅逐出社會公共空間的女性從此失去了從事公眾社會勞動的機會,只能“安心”于“賢妻良母”這一家內角色的扮演,而公眾社會勞動恰恰是獲得“社會性成人身份”的物質基礎。男性社會正是通過將女性排斥于社會公共空間與公眾社會勞動之外的性別隔離,從而否定了“她”的社會性成人身份。女性“被排除出嚴肅的事情和公共事務空間,她們長期以來扎根于家庭空間和與子嗣的生物和社會再生產相關的活動中”[14],“在這個沒有她參與創造的世界上,在這個男人的世界上,她得完全依附于男人的保護,她永遠也不可能成長起來”[15](P84)。長此以往,其結果只能是被局限在家內空間的女性變得愈來愈膚淺、愈來愈幼稚,反而進一步證明了女性的確是一群智力低下、行為可笑的“劣等”生物,“不完整的人”,這一原本純屬虛構的話語前提于此得到了意想不到的“證據”支持。女性劣等論與性別隔離二者之間就此形成了相互促進、彼此轉化的循環呼應,性別隔離存在的合法性得到了證明與鞏固。
三、性別隔離的話語策略:“天使”“妖婦”與身體控制技術
“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禮記·內則》)性別隔離,如僅就話語表層來看,可視為面向男、女兩性實施內、外空間隔離的公平之舉,但誰也無法否認有關性別隔離的種種話語總是針對女性施加了更為詳細、更為瑣碎的身體限制。就其實質而言,性別隔離更多地只是針對女性實施的空間隔離,即通過將女性的身體限制于家內空間的私人領域,借以達到將女性從社會公共空間驅逐出去的目的。性別隔離,或者更明確地說,將女性驅逐出社會公共空間的性別歧視行為,歸根到底,正是對女性身體實施的一種控制。
由于女性被認定為“不完整的人”,更多地僅與身體相關,而缺乏頭腦與理性,因此,男性社會對所謂的“提升女性智力水準”并不抱任何幻想,而僅將關注點更多地投注到對女性身體的控制與馴化上。正如尼采所言,“你到女人那里去?別忘帶你的鞭子!”[16]⑦對于“女性”,這一在身體、智力、道德上都存在著嚴重缺陷的“劣等”生物而言,能使其得到“馴服”的唯一方法也就只有身體控制了。恰如馬戲團的馴獸師訓練動物一樣,男性社會所要做的就是通過“操縱”“塑造”和“規訓”以使女性(或者說女性的身體)學會“服從”和“配合”[17],并通過對女性身體的馴化,在兩性之間建立起一種服從與被服從的關系,使女性的身體“在變得更有用時也變得更順從,或是因順從而變得更有用。”[18]
在男性社會的身體規訓下,“她”的身體不僅被驅除出社會公共空間,而且即使在家庭領域也會受到進一步的“內”“外”限制,如“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內言不出,外言不入。”(《禮記·內則》)“婦人無故,不窺中門。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仆非有繕修,及有大故,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仆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司馬光《溫公書儀》卷三《婚儀上》)除了家內進一步的身體回避外,女性還被要求應有意識地對自己的身體進行控制,如“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寒不敢襲,癢不敢搔。”(禮記·內則》)“不登高,不臨深,不茍訾,不茍笑,立必正方,不傾聽,毋嗷應,毋怠荒。”(《禮記·曲禮》)“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莫窺外壁,莫出外庭……”(《女論語·第一“立身”》)在中世紀那些為新興資產階級女性編寫的關于行為舉止的書籍里,也有類似的一些訓誡,如“走路不要太快,不要猛然回頭,不要晃動肩膀”等等,“不雅的大笑、直視的眼神、胡說八道的舌頭和放肆的步態”[19](P199)等都被視為禁忌。
此類女教書中之于女性身體的種種規訓自然可以被視為對女性儀態舉止的一種“禮儀訓練”,然而正如上文分析所示,這種“禮”的訓練并不是通過提升內在的道德精神來實現的,而更多地僅僅體現為對身體這一“物質”的完美控制。女性身體成為男權話語權力運作的對象與場所,對女性的限制幾乎全部聚焦到了“她”的身體上,女性的存在意義在相當程度上也僅限于“她”的身體。一個服從約束、符合規范、安心于家內空間的身體本身即被視為道德的體現。在中國的古典小說《林蘭香》中,不幸早逝的封建淑女燕夢卿之所以被人們長期懷念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她能對自我身體實施有效的控制,“遇著可喜的事,從不見她大說大笑;遇著可憂的事,也不見她愁眼愁眉。總然身體清爽,從不見她催酒索茶,胡游亂走。就是疾病深沉,也不見她蓬頭垢面,遲起早眠。”(《林蘭香》第三十八回)接受身體控制,尤其是“自覺自愿”地進行自我身體控制就是美德,身體控制的道德化是男權話語權力運作的一個重要策略。
被道德綁架的女性于是只能被困守于家內空間的狹小天地中,這在相當程度上正是男權話語權力作用的結果。然而,單純依靠強權、暴力的壓制必然會引起受壓迫者的反抗,將男權話語中蘊含的權力通過一定的話語策略巧妙地發揮出來無疑更為明智。在眾多的男權話語策略中,“最深層、最隱蔽、最具有欺騙性”的莫過于“神化和歌頌女性”[20](P29)的“母性神話”。它以“一種控制和馴服心靈的縝密溫柔型的權力技術”[21]巧妙地誘導著女性“自覺自愿”地按照男性的愿望需求、男性的價值尺度來形塑自身,而實現母性(包括妻性)的最佳場所無疑是家內空間,實現母性(包括妻性)的角色定位無疑是“賢妻良母”,從而極大地削弱了女性向家外的社會公共空間拓展的動力與愿望。“女性的形象和聲音被邊緣化了,女性只是男性角色的陪襯”[22],成為“具有母性、有社會道德、舉止文雅、鐘愛自己的丈夫和家庭”[19](P73)的“賢妻良母”成為女性生存價值的全部體現,其獨立的主體性因此被取消,豐富的生命需求因此被遮蔽,充分發展的可能性因此被制約,“她的身份就只能是妻子和母親,她自己也不知道她是誰”[15](P18),這一身份危機的產生正是源于身體的受限。
對“賢妻良母”這一角色的神化與“社會不愿把婦女作為完整的人來對待”[15](P284)有著密切關聯。將女性認定為“不完整的人”,是性別隔離預設的話語前提;專注于賢妻良母角色的“母性神話”,是性別隔離實施的話語策略,其共同指向的是使女性“自覺自愿”地留守于家內空間這一直接目的,最終促成的則是性別隔離的完美實現。
在將接受身體規訓、安心于家內空間、專心于角色扮演(“賢妻良母”)的女性美化為“家庭天使”的同時,男權話語更積極地借助于包括通俗小說在內的各種話語形式對那些拒絕被納入性別隔離秩序的女性進行丑化、性化、妖魔化等異質化處理。在中國的古代社會中,女尼、道姑、三姑六婆等游走于社會公共空間的女性其道德品質就總是會遭到男性社會的嚴重質疑,古典小說中寫到的許多犯罪事件,尤其是奸情的發生往往都與此類女性有著直接關聯。其中,男性社會對“三姑六婆”這一特殊女性群體的抨擊最為強烈。她們憑借著女性性別身份的便利而得以出入內宅,熱心于為私情男女暗中撮合以便從中牟利,其頻繁跨越內、外界限的行為使得本應處于封閉狀態的家內空間變得有隙可乘。相較于引誘良家婦女墮落的罪名,對嚴守內、外之別的性別隔離秩序造成的破壞無疑更為嚴重,這也正是這一特殊女性群體遭到男權話語集中攻擊的深層原因所在。諸如“話說三姑六婆,最是人家不可與他往來出入”(《初刻拍案驚奇》第六卷《酒下酒趙尼媼迷花機中機賈秀才報怨》),以及“一句良言須聽取,婦人不可出閨房”(《初刻拍案驚奇》第六卷《酒下酒趙尼媼迷花機中機賈秀才報怨》)、“所以內外之防,不可不嚴也”(《二刻拍案驚奇》第二十五卷《徐茶酒乘鬧劫新人鄭蕊珠鳴冤完舊案》)之類于小說行文間不時穿插的訓誡都可視為男權話語的直接表態。在西方社會中,倡導女性走出家門的女權主義者也同樣遭到了男權話語的妖魔化處理。她們往往被描述為“缺乏幽默感的自私鬼,不修邊幅,刻意把自己打扮成沒有女人味的‘變態狂’,以及整日爭風吃醋、吵吵鬧鬧地爭辯不休的‘潑婦’”,有時甚至會被罵成“妓女”“豬”“淫婦”“巫婆”等等,那些支持或同情女權運動的男性也未能幸免,他們不是被視為“沒有男子漢氣概”的“無用和懦弱之流”“事業上的失敗者或感情上的失意者”,就是被無端地貶低為“陽痿患者”“畸形人”或者“害怕老婆嘮叨的‘氣管炎’患者”⑧。
上述列舉的所有這些具有歧視性、侮辱性的“標簽”無疑是語言暴力的體現,“語言不僅有著它至高無上的權力與威力,同時,更有從語言權力與威力中派生出來的暴力”[9](P24),這一語言暴力更多地只為掌控了話語權的男性社會所獨享,那些被認為破壞或蓄意破壞了性別隔離秩序的女性(有時也包括男性)只能任由男權話語貼上這些“標簽”。標簽策略得到了廣泛而持久的運用,20世紀30年代被稱作“花瓶”的職業女性,民國時期被稱作“交際花”的女記者們等莫不如此。
美化與丑化的并用,促成了女性形象的“天使”與“妖婦”的兩極分化。以是否遵從內、外隔離的性別秩序為界,不是“天使”,就是“妖婦”,非此即彼,幾無回轉的余地。女性形象的刻板化使得“一種使女性壓抑和限制自己的方式”[23]得以創建起來,在“妖婦”標簽的“震懾”下,許多女性都對逾越內、外空間的界限感到深深的恐懼,清代的一些才女甚至有自焚詩稿的舉動,即便僅僅是自己的文字流出家內空間也足以令人憂懼。無論是身體,還是話語,一切“越界”行為都將是不被允許的。然而即便如此,在男性作家書寫的小說文本中也還是客觀地捕捉到了女性渴望一窺家外空間的潛在欲念。在許多中國古典小說,如在章回小說《金瓶梅》《醒世姻緣傳》,話本小說《任君用恣樂深閨楊太尉戲宮館客》(《二刻拍案驚奇》第三十四卷)、《王嬌鸞百年長恨》(《警世通言》第三十四卷)中我們都會發現,為女性所最為熱衷的娛樂項目就是“蕩秋千”,這一象征著沖破封閉空間的意象在當代女性作家瑪格麗特·德拉布爾書寫的具有穿越色彩的小說《紅王妃》(2004)中表現得更加明顯。借著故事的女主人公——18世紀朝鮮李氏王朝洪夫人的幽靈的回憶,描述了那些仿佛過著“幽閉恐怖癥患者的生活”的女人們用盡全身的力量奮力地將秋千高高蕩起,也就是為了“在高高蕩起的時候能瞅一眼高墻之外的風光”[24]。
無論是男性作家的客觀呈現,還是女性作家的主觀書寫,“禁閉”的空間與“逃離”的欲念所反映的正是女性“身”的不自由與“心”的渴望自由。然而,以女性的身份公然出現在社會公共空間勢必又會遭到男權話語的異質化處理,既渴望突破內、外界限,又不愿被貼上“妖婦”標簽的女性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拒絕女性身份而將自己消逝為男人。這種女性身份的消逝不僅止于身體上的女扮男裝,更指的是“丟棄自己作為女性特有的生存方式、體驗方式和言說方式”,而完全以“男性社會已經僵化的、制度化的、理性化的口吻、詞匯、意向和符號去說話”[1](P202),這是女性在這個為男性所操控的世界中獲得話語權的唯一方式,也是將自己消逝成男人的關鍵所在。唯如此,才有可能跳出被局限在家內空間的“女人宿命”,使自己被禁錮、受限制的身體得到真正的自由。在清代的女性彈詞作家書寫的大量故事中,“僭越”著男性話語并在男性社會努力尋求個人發展的男裝麗人們即使最終被識破了女兒身份,也往往拒絕重返家內空間,她們共同的愿望,同時也是這些女性作家們發出的共同聲音,就是“拒絕自己的性別角色,走出閨閣,成為男人”[25]。
四、結語
在男權社會中,話語權完全為男性所操控,其不僅“具有文化符號體系的操作權”,同時也具有“話語理論的創作權和語言意義的解釋權”[1](P202)。話語中的權力,以及衍生而出的強制力、暴力、威懾力都為男權社會所壟斷。由于掌控了話語權,男性社會有權從古老禁忌中任意“提煉”出歧視“因子”并加以發揮,使其成為性別隔離的生物學依據;有權借助“神說”的權威將女性界定為“不完整的人”,從而為性別隔離的實施預設下話語前提;有權運用身體控制的道德化、“母性神話”“妖婦”標簽等各種話語策略使女性“自覺自愿”地將自己的身體限制于家內空間。話語權的掌控賦予了男性社會支配話語權力的權力,男性社會的權力正是通過話語中的一系列的權力運作得以實現的。從提煉生物學依據到預設話語前提,再到種種話語策略的巧妙運用,在性別隔離得以實施的每一個重要環節上都體現著話語權力的強烈干預,性別隔離的完美實現正是男權話語中權力運作下的必然結果。
男權社會雖然掌控了警察、法庭、監獄等一系列暴力機關,或者說一整套權力系統,但話語中的權力運作無疑是最為文明、最為隱蔽的。通過一整套話語操作,話語中蘊含的權力得以以一種“隱性,不容察覺的,甚至是科學的,友好的形式表現出來”[20](P30),使得受其支配者深陷其中卻又難以覺察,“傳統社會性別的角色定型并沒有發生改變,處于弱勢地位的女性變得更加艱難”[26]。時至今日,盡管絕大多數女性已經走出了狹小的家內空間,打破了內、外界限的制約,但即便進入到以現代職場為代表的社會公共空間內,也很難說就沒有繼續遭到性別隔離的隱性禁錮。作為傳統性別隔離在現代職場中的延續,職業性別隔離中所謂的“男性職業”“女性職業”、橫向隔離、縱向隔離,以及那個看不見的玻璃天花板⑨的實際存在都無不在證明著這一點,而且,“對于不同性別類型的職業,職業性別刻板印象普遍存在”[27]。將女性勞動力更多地視為應急的臨時補充,在勞動力過剩的情況下號召“讓女性回家”以保障男性優先就業等諸如此類的職場性別歧視中同樣可以看到傳統社會性別分工(男外女內)與傳統女性角色定位(賢妻良母)的強力影響,而這些又無不與傳統性別隔離有著千絲萬縷的內在關聯。借助于話語權力的隱性運作,而非“鞭子”式的直接暴力,正是性別隔離“經久不衰”的“奧秘”所在。
注釋:
① “話語權”與“話語權力”這兩個概念既彼此關聯,又相互區別。“話語權”,簡而言之,就是說話權、發言權,即說話、發言的權力;“話語權力”則更接近福柯權力話語理論的界定,即話語并不僅僅體現為交際工具的“手段”,更體現為權力這一“目的”,話語本身即內蘊了權力,權力通過話語得以實現。擁有話語權者才有資格支配話語中的權力,而喪失話語權者則與話語中的權力處于絕緣狀態,即使他在說話,他的話也無足輕重,不具任何權力效應。
② 如“女人行經,必污穢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潔凈到晚上。女人在污穢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為不潔凈,所坐的物件也都不潔凈。凡摸她床的,必不潔凈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凡摸她所坐什么物件的,必不潔凈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在女人的床上,或在她坐的物上,若有別的物件,人一摸了,必不潔凈到晚上”(《圣經·舊約·利未記》15:19—23),《圣經》精讀本,香港:牧聲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189頁。“……若有婦人懷孕生男孩,她就不潔凈七天,像在月經污穢的日子不潔凈一樣。……婦人在產血不潔之中,要家居三十三天……”(《圣經·舊約·利未記》12:2、4)《圣經》精讀本,香港:牧聲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182頁。)
③ 參見李貞德的《漢唐之間醫方中的忌見婦人與女體為藥》,轉引自方燕的《巫文化視域下的宋代女性——立足于女性生育、疾病的考察》,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第110~111頁。
④ 以上宋醫藥文獻皆轉引自方燕的《巫文化視域下的宋代女性——立足于女性生育、疾病的考察》,四川大學博士學位論文,2005年,第111頁。
⑤ 關于經血不潔贖罪的條例,“……要取兩只斑鳩或是兩只雛鴿,帶到會幕門口給祭司。祭司要獻一只為贖罪祭,一只為燔祭;因那人血漏不潔,祭司要在耶和華面前為她贖罪”(《圣經·舊約·利未記》15:29、30),《圣經》精讀本,香港:牧聲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190頁)。關于產血不潔贖罪的條例,“滿了潔凈的日子,無論是為男孩,是為女孩,她要把一歲的羊羔為燔祭,一只雛鴿或是一只斑鳩為贖罪祭,帶到會幕門口交給祭司。祭司要獻在耶和華面前,為她贖罪,她的血源就潔凈了……”(《圣經·舊約·利未記》12:6、7)《圣經》精讀本,香港:牧聲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第182頁。)
⑥ 參見林幸謙的《歷史、女性與性別政治:重讀張愛玲》,臺北:麥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0年,第210頁。轉引自林丹婭的《語言的神力:神話隱喻的性別觀》,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年第4期,第27頁。
⑦ “你到女人那里去?別忘帶你的鞭子!”出自尼采的著作《扎拉特斯圖拉如是說》中的《年老的和年輕的女人》一篇。該篇以“我”與一位老婦人之間對話的形式展開,這句話實出于老婦人之口,但完全可視為尼采個人的觀點,正如《扎拉特斯圖拉如是說》托名于扎拉特斯圖拉,但完全可視為“尼采如是說”一樣。
⑧ 與“女權主義者形象的妖魔化”相關的論述參見姚桂桂的《論美國媒體與反女權運動》,《婦女研究論叢》2011年11月第6期,第83頁。
⑨ “玻璃天花板”,意指就個人發展而言,雖然看不見但又實際存在的阻礙。
[1] 賀璋瑢.東西文化經典中的女性與性別研究[M].上海:三聯書店,2013.
[2] [英]詹姆斯·喬治·弗雷澤.金枝——巫術與宗教之研究[M].徐育新,汪培基,張澤石,譯.北京:大眾文藝出版社,1998. [3] [法]羅貝爾·穆尚布萊.魔鬼的歷史[M].張庭芳,譯.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5. [4] 圣經(精讀本)[M].香港:牧聲出版有限公司,2012.[5] [英]菲奧納·鮑伊.宗教人類學導論[M].金澤,何其敏,譯.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51. [6] 楊莉.宗教與婦女的悖相關系[J].宗教學研究,1991,(Z2):49-58. [7] 桑德拉·利普斯茨·班.關于性別不平等爭議的演變:從生物差異到大男子主義制度化[A].[美]瓊·C·克萊斯勒,卡拉·高爾頓,帕特里夏·D·羅澤.女性心理學[C].湯震宇,楊茜,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
[8] 張曉玲.婦女與人權[M].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160. [9] 林丹婭.語言的神力:神話隱喻的性別觀[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4). [10] 袁曦臨.潘多拉的匣子——女性意識的覺醒[M].上海:上海譯文出版社,2005.37.
[11] 劉巖,邱小輕,詹俊峰.女性身份研究讀本[M].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07.140.
[12]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54.
[13] 克里斯特·A·史密斯.女性、體重和體形意象[A].[美]瓊·C·克萊斯勒,卡拉·高爾頓,帕特里夏·D·羅澤.女性心理學[C].湯震宇,楊茜,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73.
[14] [法]皮埃爾·布爾迪厄.男性統治[M].劉暉,譯.深圳:海天出版社,2002.135.
[15] [美]貝蒂·弗里丹.女性的奧秘[M].程錫麟,朱徽,王曉路,譯.哈爾濱:北方文藝出版社,1999.
[16] [德]尼采.扎拉特斯圖拉如是說[M].北京:三聯書店,2007.72.
[17] [法]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監獄的誕生[M].劉北成,楊遠嬰,譯.上海:三聯書店,1999.154.
[18] 陸揚.文化研究概論[M].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151.
[19] [美]蘇珊·布朗米勒.女性特質[M].徐飚,朱萍,譯.南京: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2006.
[20] 楊鳳,田阡.性別政治下的女性發展邊緣化[J].思想戰線,2006,(1).
[21] [美]馬克·赫特爾.變動中的家庭——跨文化的透視[M].宋踐,李茹,等,譯.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8.
[22] 談思嘉.女性神學思想述評[J].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16,(4):9.
[23] 帕特里夏·D·羅澤.針對女性的暴力[A].[美]瓊·C·克萊斯勒,卡拉·高爾頓,帕特里夏·D·羅澤.女性心理學[C].湯震宇,楊茜,譯.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7.242.
[24] [英]瑪格麗特·德拉布爾.紅王妃[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7.51.
[25] 盛志梅.清代女性彈詞中女扮男裝現象論析[J].南開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4,(3):27.
[26] 王蓓敏.“女性發展與性別平等——中德比較研究”研討會綜述[J].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16,(5):50.
[27] 王炳成,王俐,王森.大學生就業性別刻板印象的logistic回歸研究[J].山東女子學院學報,2016,(5):36.
(責任編輯 魯玉玲)
Gender Segregation and Power Operation in Male Discourse
SHI Wen-fei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Yinchuan College, Yinchuan 750000, China)
Gender segregation originated from some ancient taboos about female body, when periodic separation was applied to certain women for safety concerns. Male discourse, by refining the discrimination “factor”, creating fictional presupposition and implementing various discourse strategies, skillfully substitutes the neutral safety measures with sextually political tool of discrimination and oppression. And because its elusiveness, gender segregation is still at work in the gender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dentity. The occupa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 in modern workplace can be regarded as more disguised extension of traditional gender segregation. Awareness of the specific operation of male discourse will help us to 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gender segregation and reveal the “mystery” of its “enduring” nature, and realize the status of women’s liberation.
gender segregation;female body taboo; inferiority of women; body control;right to speak;discourse power
2017-03-07
陜西師范大學優秀博士論文資助項目“性別書寫研究與近世白話小說”(項目編號:2014YB11)
施文斐(1978—),女,中國礦業大學銀川學院中文系講師,陜西師范大學文學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近世白話小說、性別研究。
C913.68
A
1008-6838(2017)03-0008-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