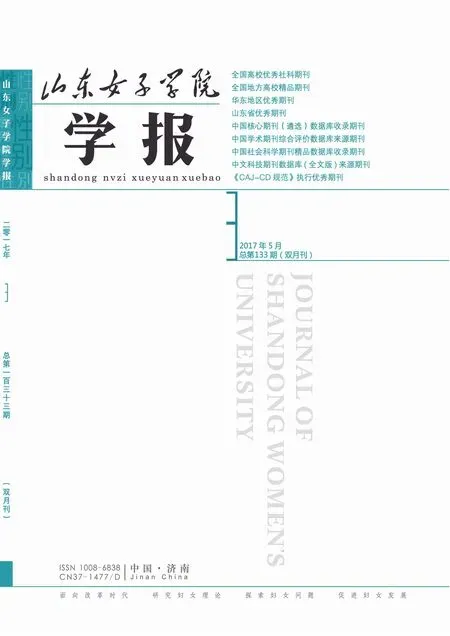家族微信圈的文化傳承及其性別價值
郭淑梅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18)
?
·女性文化研究·
家族微信圈的文化傳承及其性別價值
郭淑梅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黑龍江 哈爾濱 150018)
悄然興起的家族微信圈,在中國家庭中正日益發揮著重要的情感紐帶作用和家族文化傳遞功能。以百年為考察時段發現,家族在中國經歷了農業、工業、信息社會的發展階段,建構著社會形態的基本樣式,見證著人生的悲歡離合。其在培育優秀人才,以及提供家訓、家教、家風等方面的作用不可替代。新中國成立后,社會主義公有制標舉集體主義新風尚,單位兼具了部分家族功能,傳統家族文化漸行漸遠。改革開放后,家族力量得以釋放。尤其近年來,由微信牽引的家族文化的重建,不僅將斷裂的家族脈絡重新紐結起來,而且女性在重建過程中價值凸顯,借助家族微信圈平臺,以個性張揚為特征的性別平等體現得尤為充分。
家族文化變遷;家族微信圈;性別價值
一、家族文化變遷
家族是以姓氏為單位,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親情為依托的人類生活共同體和經濟利益共同體,以維持獨特的文化傳承為旨歸的社會基本細胞。中國是個農業大國,傳統家族在中國社會的形成是以地緣為中心的血緣集合。三世同堂、四世同堂的大家族普遍存在于社會各個階層。正如老舍百萬字的長篇小說《四世同堂》,以宏闊的視野講述北平淪陷時期祁家、錢家、冠家等家族的抗戰與投降的曲折命運,將舊式家族的分崩離析與國家民族命運結合起來,家族在中國具有普遍的認同價值。家族曾經與家風家教的熏陶、社會責任的擔當、傳統技藝的接續,以及文化密碼的傳遞直接相關,是關系到民族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
農業社會中,在以村為單位的社會結構中,以姓氏為核心聚集起的家族可以設祠堂、編族譜,私立族法、族規以懲治逾越者,違者甚至可遭極刑。家族族長對族人具有生殺予奪的權力。即便在城市文化圈中形成的大家族,在地緣圏子規囿下,舊式家族的族規文化的封閉性也制造了許多人間悲劇,這在著名的“五四”作家的文學創作中都有表現。如巴金的“家”三部曲《家》《春》《秋》,寫盡了大家族的沒落和青年人的覺醒,代表了“五四”青年決意沖破舊式家族束縛,走上社會而獲得新生的一種時代風尚。舊式家族在此被表現得沒有任何存在價值,是逆潮流而動的腐敗文化機體。青年人必須沖破牢籠,甚至砸碎家族的鐵鎖鏈,才能換來與大眾一道的新生活。另一位“五四”女作家蕭紅在小說《呼蘭河傳》《家族以外的人》中,把家族中有二伯卑微的下等人身份寫得淋漓盡致。盡管有二伯的輩份高,但經濟地位低下,是寄食于族中富有的弟弟家中的窮親戚、乞食者。因此,農業社會的舊式家族文化經過“五四”時代新文化運動,被作家文人所詬病,令聞者生厭。
但是,在民間口述中,家族文化往往被賦予正面價值,得以數百年地承繼。家史的口耳相傳,使贊頌成為傳承基調。如滿族家族英雄說唱《薩大人傳》[1](P3)是滿族說部中的“包衣烏勒本”,即家史。這部產生于清朝道光年間的家族史,主要流傳于黑龍江省愛輝地區滿族諸姓中。在富察氏家族、關姓、吳姓、楊姓、張姓等家族中公開傳講。一部家族史傳承下來,已有二百七十多年歷史,可見家族文化傳承的生命力。家族史傳唱的初衷,被當作“子弟書”,教育家族內部子孫對祖先產生敬意,弘揚家族精神文化。傳承人富育光對《薩大人傳》高度概括,認為其“是一種講家風,述族史,唱英雄,揚國威的傳承教育的虔誠、肅穆之舉”[1](P4),也是一種尋根問祖不忘源頭的追溯家族偉人的方式。家訓、家教、家風便在這種口耳相傳的家史中,潛移默化、自然而然地成為訓育后人的家族文化范本。另一個家族脈絡傳承人傅英仁的滿族說部《薩布素將軍》,原名《老將軍八十一件事》,主要流傳在黑龍江省寧安市一帶,傅英仁的長輩對他說:“你得把這個故事弄完整了,把它記下來吧。要不然的話,在我這一代人傳不下去,對不起祖宗,也對不起后代子孫”[2](P3)。這部傳承二百多年的家史,同樣凝聚著傅氏家族對祖先黑龍江首任將軍薩布素的敬重,家史的傳遞,目的也是頌揚其業績和愛國精神,以訓育后人。
工業文明的到來,還產生了另一種中西會通的家族文化。20世紀上半葉,西方教育、科技、生活方式沖擊了中國舊式家族,西學東漸,一些有識之士有感于國運衰落,從挨打中覺醒。接受變革思想的家族,都將子女送到海外學習深造,于是“流動性”家族產生了。在此,地緣不再是家族圈核心,分散的家族勢力如同移動的大樹,在不同的地方扎根、發芽、開花、結果。譬如,宋耀如宋氏家族,誕生了在中國現代史上產生過重大影響的“宋氏三姐妹”宋藹齡、宋慶齡、宋美齡,她們的宋氏家族文化具有獨特的政治經濟標識,是中國現代史上具有標志性的與國家命運緊密相關的大家族文化。
工業文明體制的一個顯著特征是資本和勞動力的對抗。工人作為勞動力從農村、山區、小城鎮等小地方涌向燈紅酒綠的大城市,建構起歷史上從未有過的有組織的工人集群。在這個龐大的社會集群中,以工資關系為紐帶的資本家的權力迅速上升,成為主宰工人命運的新型權力。譬如,20世紀上半葉,中東鐵路的建成通車,使哈爾濱成為中國最著名的移民城市。與中東鐵路同時興建的哈爾濱車輛廠,不僅聚集起一大批俄國工人,也吸引了大批“闖關東”的山東、河北移民。“闖關東”大潮使“關里家”①與關外世界,隔成一個家族的兩個世界。俄國工人與故鄉親人也是天各一方。思鄉情緒,也就是對故鄉家人、家族的思念,使哈爾濱大街飄蕩著東正教教堂的鐘聲,也使極樂寺的香火為“闖關東”的移民提供了思鄉的精神慰籍。在此,家族的影響力相對弱化,工人階級以各種組織形式取代了家族集群,并形成了聯合起來的世界性癥候。為向資方爭取過“五一”的國際勞動節的權利,1907年5月14日(俄歷5月1日),哈爾濱車輛廠中俄工人舉行大罷工,成為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工人罷工[3]。這進一步說明,工業文明尤其是工人集群,在生存空間范圍內突破了舊式家族的血緣圈囿,進入了工業社會范疇。
新中國成立后,中國實行全面計劃經濟國策。單位制度人事戶口制度的嚴格管控,使城鄉差別界限凸顯。農村由于地緣關系,在一定的區域內仍然保留著以往家族群體的聚集模式,以同一姓氏或不同姓氏但有姻緣關系的家族共同體,承擔著彼此關聯的責任義務和家族文化傳承。城市由于公有制單位的出現,家族圈子越來越小,民間往來也僅限于居住地相距不遠的親屬來往。遠距離的城鄉之間親戚往來,由于火車、汽車等交通工具以及住宿的不便,而阻礙了交流。保持家族成員聯系的方式,主要由通信、包裹來完成。
在單位制和社區制中,許多問題都可以由“公家”解決處理,如生育、紅白喜事、子女就學、子女工作、子女上山下鄉等涉及個人隱私和家族內部的事務均由個人所就職的單位來解決。生產生活等眾多事務,與家族姓氏關系不大。因此家族文化往往隱退幕后,沉潛入人們的記憶深處。這一時期,由單位制和社區制的集體方式,取代了數千年流傳下來的以姓氏為核心的家族方式。
二、家族文化重建的需要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社會以前所未有的開放包容姿態來擁抱世界。在“全球化”“一帶一路”等大文化語境下,中國與世界各國的政治、經濟、科技、文化交流互動頻繁,地理空間的阻礙,已由飛機、高鐵等交通工具逐漸縮小。在制度上,以身份證制替代戶口制,為人員自由流動提供了先決條件。為獲得更優質的生存條件和生活空間,許多中國人背起行囊,選擇在異國他鄉發展,加入流動遷徙大軍,以致世界各地到處都有中國人的身影。在全國各處,人們隨時都可能遇到故鄉親人。家族成員沖破地域界限,分布在國內外、省內外、市內外,天各一方。許多家族成員只有逢年過節才能團圓相聚。這種地理空間和文化阻隔的差距愈大,家族內部彼此情感需要、精神撫慰的心理需要愈強。
同時,重建家族文化,也是人類進入“地球村”時代產生的一種文化自我保護心理,是由于經濟高速發展中狂拆的村落、城墻、老宅等城鄉改造項目的負面效應,以及區域文化遺產等家族共同記憶消失的影響,而產生的一種身份認同需要。文化之所以能夠存續下來,原因之一即是文化身份的個性化,也即文化的多樣性魅力。家族文化正是具有識別意義的文化身份個性,這些獨特標識吸引著人們回歸故園、了解故人,進而追溯家族史,使中國人重新有了家族意識和家族文化。
目前,雖然中國社會談論“家族”這個詞匯的人越來越少,人們多半以家庭代替家族。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又為渴望大家族生活的人們提供了新的機會。與“80后”“90后”獨生子女相比而言,中國最有資格談論家族的一批人是“50后”“60后”人,這兩個代際出生的人,所處的歷史時期是中國戰后的生育高峰。新中國成立后,中國迎來了除舊布新的建設期,支撐國民經濟發展的不僅是經濟、文化資源,也有人力。在鼓勵生育、學習蘇聯“英雄母親”的號召下,中國母親也最大限度地奉獻了一批寶寶,這一時期的生育高峰使中國社會家庭結構有了獨特的稱謂“多子女家庭”。進入信息社會,文化傳承方面起主導作用的這一批人,擁有接受新事物的極大熱情。他們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文革”、改革開放,是一批精力充沛永不言敗的人。他們上有老,下有小,還有兄弟姐妹,一批同姓氏、同祖籍的人,比較容易形成家族圈子。作為城市家族圈里的長輩,經常會起到文化傳承的主角作用。年輕的后輩則在長輩間的交流互動中,傳承著家族優秀的文化基因,從中汲取集體的力量。
信息社會的到來,尤其是不斷更新換代的技術革命,使家族文化傳承迅速進入一種虛擬社會,得以即時快速傳播。早在改革開放前,人們為解決家族成員分隔兩地、三地,及至國內國外的思念之苦,主要聯絡途徑是電報、通信、郵包、長途電話等。尤其是信件、電報、包裹等實物,寄托著沉甸甸的親情,是家族成員極為珍視的可以看得見摸得著的交流手段。及至出國潮、打工潮的長盛不衰,又使國內外長途電話、手機成為家族成員聯系的主要紐帶,這個紐帶持續了30多年。
進入21世紀,智能手機因其操作簡單容易,圖片和視頻上傳的即時性等優勢得以普及。微信自媒體平臺的廣泛應用,節省了每個家庭大量的電話費支出。由于城市水泥森林的阻隔,家族微信圈以在場的方式,把碎片化的家族重新凝聚起來,使家族人員承擔的家族義務得以明晰,互助互惠理念得以強化。家族微信圈形成了一個可以自給自足的小社會。其互動的主要內容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大事小情,諸如生育、紅白喜事、生病住院、子女升學工作、經商者開業、公職人員升遷、退休人員養生、小家庭集體旅游等,都可以在微信家族圈中公開亮相,以獲得幫助和達成共識。《三亞日報》刊文《家族微信群:幾家歡樂幾家愁》談到家族微信群帶來的利弊。“32歲的阿毅在廣州生活了10年,他的長輩中,奶奶和幾個叔叔生活在老家瓊海,父母兄弟則在海口生活,幾個堂兄弟也都在不同的城市,‘家族微信群對我而言更像一個紐帶,將一大家子人聯系在了一起’”。[4]網友@abc安認為,多年未見的親戚,通過微信圈聊天也親近起來,“既活躍了氣氛,也讓大家族的親切感更濃”[4]。當然,盡管家族微信圈是虛擬空間,但并不是孤立的存在,仍然是社會生活的一部分。線上線下,一些生活問題也會帶入微信圏內。比如,年輕人不喜歡的催婚,在家族微信圈里也會有所表現。網友@小心翠翠認為,家族內的親戚的逼婚讓她非常煩惱,“大姨、二叔,甚至是已婚的表弟,有時聊著聊著,就會突然冒出一句‘什么時候請我們喝喜酒啊’,此話題一出,大家就開始跟著逼問,甚至張羅著介紹對象,沒完沒了”[4]。對于家族微信圈催婚現象,包括各種長輩對年輕人的建議,主要是因其牽涉到親情、家族利益,其他人才會動之以情、曉之以理,或者說話口無遮攔,直抒胸臆。因此,家族微信圈針對個人生活私密性的干涉,仍然是線下家族內部才會發生的事情。
毫無疑問,家族微信圈存在的利弊,均源自正常的家族成員的交往內容。是否加入家族微信圈,還擁有選擇性的自由。譬如,不喜歡催婚的年輕人可以選擇屏蔽,照樣過自己喜歡的日子。總的來說,家族微信圈利大于弊,它通過視頻、發文章圖片、分享網頁、收發紅包、贈送祝福、討論家務事等,既解決了家族成員的思念之苦,又密切了家族成員的親情關系,也傳遞了良好的家訓、家教、家風。同時,在涉及對政治、經濟、文化等國家大事的思考、討論、分析、評價等表達家族成員的社會責任方面,也有其他自媒體無法取代的良性互動優勢。
尤其是中國實行計劃生育國策以后,家庭人口銳減,一些“80后”“90后”年輕人熱衷于家族重建,不僅在家族二代中間建立小型微文化圈,也傾心于充當大家族的時尚教主,在大家族微信圈中發布新的時尚文化信息,成為指導前輩家族成員融入當下社會,接受社會新風尚新文化的一股新生力量。城市家族微信圈的普及,有利于凝聚家族人心,也有利于傳播家族文化,成為當下家庭文化建設中重要的一環。
三、城市家族微信圈的性別價值
城市家族微信圈的興起,是與智能手機等信息技術革命一道而來的一種家族重建熱潮。從性別方面探討,可以發現家族微信圈無形中已成為一條虛擬空間的地道,順利地挖到了性別文化的前沿。以往,可望不可及的話語權成為家族女性唾手可得的大禮包。嚴格意義上講,自媒體女性話語權,由于其普及性的特點,可以稱之為一種互聯網信息技術革命帶來的性別利益分紅。
改革開放以后,中國社會最先擁有話語權的是大批女作家。她們在經歷過一段時間的對社會問題和重大題材的關注后,大都轉向了女性題材,關注女性自身的成長過程,女性家族的命運。她們在作品中試圖回溯女性生命的源頭,探討母系一脈的形成發展,希望能夠獲得女性自身的優秀文化資源,并努力讓這種資源帶給女性力量。如張潔的長篇小說《無字》[5](P14)是一部跨越四代女性生命成長的家族史詩,她將女性家族的命運鑲嵌在中國社會百年風云變幻的歷史畫卷中,并針對“渴望被拯救”的女性姿態,清算男權中心文化對中國女性訓育的成就,以一部女性為中心的母系家族史來回答血緣之愛高于男女情愛的社會性別命題。贊譽者認為其是“無韻的悲歌、無字的歷史”(曾鎮南);批評者認為其是“一個失敗之作,一個憑借著小說的虛構權來泄私憤的文本”(徐岱)。這部受到贊譽和抨擊都十分明顯的小說,曾獲第六屆茅盾文學獎,說明其文學史地位之高。王周生的長篇小說《性別:女》[5](P190)與張潔的《無字》史詩般的敘述不同的是,前者更像是一部社會學心理學案例剖析,體現出作家把社會性別平等理念執著地轉化為藝術形象的良苦用心。其從性別角度切入家族文化史,從一個女性家族對生育和性事的厭惡,透視出女性話語權對女性家族史追溯的重要性和決定性意義。
很長一段時間以來,女作家的文學語言,成為中國性別平等意義上的先鋒符號。林白的《婦女閑聊錄》[5](P215-216)將這種書面語,帶到女性日常生活的瑣碎事件的描寫里,以女性的聲音記錄女性的記憶和感受,是一種口述實錄的寫作方式,接近于微信圈中的碎片化、斷裂式表述。李小江認為,口述對女性生命立場是極為重要的,是“找回和重建女人的歷史,不僅是史學的需要,更是女人找回自我,確立自主、自信的人生的必要基石”[6]。李小江的女性口述對于重建女性文化必要性的論斷,是擁有知識儲備和大量理論積淀的女知識分子對女性史建構的理性思考。
綜上考察的女作家作品案例,其所體現的是作為擁有話語權的知識女性,在女性家族史的建構中所起到的重要支撐作用,以及她們對女性史、女性家族史的貢獻。作為女性群體中的少數精英人物,她們所擁有的話語權無論是在批判傳統男權中心文化方面,還是在建構女性自尊自信等方面,都為歷史留下了可圈可點的業績。
遺憾的是,以往大多數非知識分子女性,對話語權的掌握與運用的機會并不多,她們的話題權充滿局限性,使其無法與女作家性別話語立場的先鋒性和理論價值相提并論。然而,女性對話語權的渴望一直存在,對個人能力的展示欲望一直存在,這在各種類型的女性口述史中都有明確的表現。微信圈作為一種自媒體平臺,恰恰可以提供給男女平等的話語權,這對于渴望表達的女性來說,是個極好的機遇。
家族微信圈由于話語權的自由平等而發展速度迅猛。無論男女老少,都可以在這個平臺上享有信息發布權和話語權。由于是虛擬平臺,彼此不相對視,僅是語言符號交流,性別在此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可以突破面對面的正式交往帶來的嚴肅性,從而自由流暢地進行彼此交流。這種平臺功能至少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分享。在這一功能下,家族成員發布各種信息、新聞都是互相增進感情的手段。贊美往往可以使人變得年輕而有活力。家族人員之間的互相點贊,對某些家族成員精彩人生的褒揚,不僅可以加深彼此感情,還會成為一種動力,推促其向更好的方面成長。二是給予。無論是發布信息,還是廣告話語,抑或展示自家照片等,都需要家族圈成員率先給予支持。不僅是年節時發的微信紅包,可以讓家族人員得到給予的幸福感,就連平時的點贊也可以讓人被滿足感包圍。三是互助。生活中,家族成員不可避免地會遇到難處,每當這時,家族微信圈如同一個調度室,可以迅速地聚集起力量,就連需要資金、醫藥等應急問題,都有可能通過家族微信圏得到解決。
家族微信圈由于沒有入門門坎,操作極為簡單,語言表達也任由個人掌握,為性別平等搭建了以往無法比擬的自主平臺。首先,網絡語言與生俱來的嘻哈風格和口語化,使女性比男性運用得更加自如,一些搞笑的片斷式的吐槽語言沖擊了代表主流正統風格的男性話語。女性在微信圈里,自由舒展地發揮著聰明智慧。有位84歲的老太太在家族微信群“一家親”里搞笑,“微信玩得與時俱進,發過的表情包就有二三十種。今年春節,這位老太發了一封配音樂的賀年信,引來眾人點贊。……不懂網絡語言,卻愛插話,吐槽。商場搞促銷‘秒殺’,她說‘干嗎老是殺殺的,瘆得慌’。”[7]這種搗蛋式的表述,正是女性文化的風格。其次,微信家族平臺與生俱來的熟悉感和抱團意識,使家族女性成員更愿意真實地表露個人行蹤、意圖,由此催生了共同的興趣愛好。旅游、健身、休閑、養生、美食、音樂舞蹈、書法繪畫等信息均可在此平臺發布。相對于家族男性,微信自媒體更多地是女性展示和獲得自信的重要途徑。女性更依賴這個社交平臺,以獲得精神認同。再次,在家族微信圈,長輩女性擁有更大的權力。中國女性由于養育了兒女還要養育孫輩這一特殊的社會分工,她們一般在家族中地位甚高,擁有話語權。她們不僅在微信圈里表達對孩子們的關愛,在圈里嘮叨些家族瑣事,還有掌控家族文化傳承的力量。“佘老太太把微信圈看作是家族成員互相學習、相互促進、共同提高、凈化心靈、傳播真善美等正能量的平臺。”“圈里有人轉發了一個關于男人包養小三小四的段子,雖然只是逗逗樂,佘老太太卻認為有傷大雅,不符合微信圈的輿論導向,因而勒令其立即刪除。”[8]
因此,就家族微信圈來說,以女性比男性更為頻繁地發布信息、堅持嘻哈話語風格、表現強烈的展示欲望以及鮮明的主張家族正能量的傳播等特點,說明以個性張揚為特征的家族微信圈平臺,是一個性別平等體現得最為充分的平臺,也是一個最能體現女性自身價值地位的平臺。
注釋:
① 關里家,指移民到哈爾濱的山東人對家鄉的稱謂。
[1] 富育光,于敏.薩大人傳[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7.
[2] 傅英仁,程迅,王宏剛.薩布素將軍傳[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2007.10.
[3] 張翔,常好禮.黑龍江紅色歷史文化資源研究[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2.3.
[4] 梁麗春.家族微信群:幾家歡樂幾家愁[N].三亞日報,2016-02-24.
[5] 郭淑梅.女性文學景觀與文本批評[M].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13.
[6] 李小江.讓女人自己說話:文化尋蹤[M].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3.7.
[7] 何杲.老人玩微信,有喜也有憂[J].新天地,2016,(9):18.
[8] 劉靜一.“佘太君”坐鎮家族微信圈[J].新天地,2016,(9):17-18.
(責任編輯 趙莉萍)
The Value of Family WeChat Group in Cultural Inheritance
GUO Shu-mei
(Heilongjiang Provincial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Haerbin 150018,China)
Family WeChat group, quietly emerged in recent years, is becoming a significant emotional connection and bridge of cultural inheritance in today’s Chinese families. Over the last century, family has gone through different stages of agricultural, industrial and informational periods, functioned as the basic unit of society and witnessed ups and downs of its members. Nothing could replace the family’s function in cultivation, disciplining and styling Chinese people.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PRC, work unit took part of the family’s function under the call of socialist collectivism, causing the withering of traditional family cultural. After the opening-up and reform, family was functioning again. Up to recent years, the reconstruction of family culture enabled by WeChat not only reunited the scattered family members but foregrounded the status of women. On the platform of family WeChat group, gender equality and individuality have never been more significantly reached.
transition of family culture;family WeChat group; gender value
2017-03-02
郭淑梅(1958—),女,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主要從事女性文學、少數民族文學、區域文化史研究。
G122
A
1008-6838(2017)03-005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