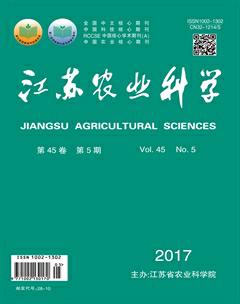貴州省城鎮(zhèn)化進程中耕地保護存在的問題與對策建議
馮應(yīng)斌韓德軍+敖貴艷



摘要:城鎮(zhèn)化是國家或地區(qū)現(xiàn)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傳統(tǒng)發(fā)展方式下的快速城鎮(zhèn)化模式以占用大量耕地為代價,如何在快速城鎮(zhèn)化進程中實現(xiàn)耕地的有效保護,已成為政府和社會各界普遍關(guān)注的重大社會經(jīng)濟問題之一。本研究結(jié)果表明,貴州省城鎮(zhèn)化水平嚴重滯后于全國平均水平,存在著人口城鎮(zhèn)化和土地城鎮(zhèn)化發(fā)展不均衡、城鎮(zhèn)建設(shè)占用耕地數(shù)量與所占比例均呈上升趨勢等凸出問題。優(yōu)質(zhì)耕地空間分布與城市擴展區(qū)、工業(yè)園區(qū)存在空間“重疊”,面臨著壩區(qū)耕地保護與城鎮(zhèn)化、工業(yè)化建設(shè)占用的“兩難困境”。基于此,從設(shè)置耕地保護“規(guī)模紅線”與城鎮(zhèn)用地“擴展紅線”2個方面提出了貴州省快速城鎮(zhèn)化進程中耕地數(shù)量保護的策略與措施;從提升城鎮(zhèn)建設(shè)用地集約利用水平、合理管控農(nóng)村宅基地規(guī)模2個方面明確了貴州省快速城鎮(zhèn)化進程中應(yīng)強調(diào)城鄉(xiāng)建設(shè)用地內(nèi)涵式管控方向。同時,加強壩區(qū)耕地高標準整治,通過土地流轉(zhuǎn)促進規(guī)模經(jīng)營,促進壩區(qū)耕地高效利用;通過合理配置坡耕地種植模式,穩(wěn)步提升坡耕地生態(tài)涵養(yǎng)功能。
關(guān)鍵詞:城鎮(zhèn)化;耕地保護;問題;對策;貴州省
中圖分類號: F321.1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1002-1302(2017)05-0292-05城鎮(zhèn)化過程需要一定的土地保障,城鎮(zhèn)化發(fā)展與耕地保護之間存在著矛盾的對立統(tǒng)一[1]。隨著城鎮(zhèn)化的發(fā)展,耕地數(shù)量減少的幅度呈現(xiàn)出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形變化趨勢[2]。在全國層面,1986—2010年我國城鎮(zhèn)化率每提高1%,建設(shè)占用耕地數(shù)量將增加2.693 4%[3];在省域?qū)用妫?978—2005年湖北省城鎮(zhèn)化率每提高1%,建設(shè)占用耕地數(shù)量將增加1.886 8%[4];在市域?qū)用妫靥帋r溶區(qū)的廣西壯族自治區(qū)河池地區(qū),其1997—2006年耕地總量隨著城鎮(zhèn)化的提高而逐漸減少,城鎮(zhèn)化率每提高1%,耕地總量將下降0.744%[5]。從土地利用空間分布來看,建設(shè)用地和耕地高鄰接度的空間格局,以及城市在空間上的攤餅式發(fā)展是導(dǎo)致城市擴展占用耕地比例大的直接原因[6]。上述研究結(jié)果表明,城鎮(zhèn)化進程不可避免地造成耕地面積減少,如何在快速城鎮(zhèn)化進程中實現(xiàn)耕地的有效保護,已成為政府和社會各界普遍關(guān)注的重大社會經(jīng)濟問題之一。貴州省山多平地少,土地資源尤其是耕地資源匱乏,城鎮(zhèn)化水平低,人口城鎮(zhèn)化率長期位于全國末尾。實施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帶動戰(zhàn)略,成為新時期貴州省加快發(fā)展、實現(xiàn)后發(fā)趕超的重要路徑。然而,在城鎮(zhèn)化進程中同樣面臨著耕地總量減少較快的難題,尤其是耕地質(zhì)量較高的壩區(qū)耕地持續(xù)減少[7-8]。本研究在分析貴州省城鎮(zhèn)化發(fā)展歷程、耕地面積變化的基礎(chǔ)上,診斷貴州省城鎮(zhèn)化進程中耕地保護面臨的特殊困境,借鑒相關(guān)成功經(jīng)驗,重構(gòu)貴州省城鎮(zhèn)化進程中的耕地保護策略,破解“城鎮(zhèn)化快速發(fā)展導(dǎo)致耕地大規(guī)模減少”的資源詛咒,為貴州省在加速城鎮(zhèn)化進程中有效保護耕地提供政策建議。
1貴州省城鎮(zhèn)化進程及其耕地保護的主要問題
1.1貴州省城鎮(zhèn)化進程及其特征
1952—1999年間,貴州省總?cè)丝趶? 489.90萬人增長至3 710.06萬人,非農(nóng)業(yè)人口從118.95萬人增長至528.78萬人,非農(nóng)業(yè)人口比例從7.23%增長至14.35%。2000年以來,貴州省人口城鎮(zhèn)化率從24.01%增長至2014年的 40.01%,年均增長1.07百分點,實現(xiàn)了較快增長(表1)。橫向?qū)Ρ葋砜矗F州省與全國人口城鎮(zhèn)化率的差距從2006年的16.79百分點縮小至2014年的14.76百分點;與西部地區(qū)的差距從8.14百分點縮小至7.36百分點;與西南地區(qū)的差距從6.35百分點縮小至5.81百分點(圖1)。西部地區(qū)包括內(nèi)蒙古自治區(qū)、新疆維吾爾自治區(qū)、青海省、寧夏回族自治區(qū)、甘肅[CM(25]省、陜西省、四川省、重慶市、貴州省、云南省、西藏
]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等12個省、直轄市、自治區(qū);西南地區(qū)包括四川省、重慶市、貴州省、云南省、西藏自治區(qū)、廣西壯族自治區(qū)等6個省、直轄市、自治區(qū)。雖然2000年以來貴州省人口城鎮(zhèn)化率與全國、西部地區(qū)、[JP3]西南地區(qū)的差距均呈縮小趨勢,但總體上仍處于較低水平,與全國平均水平、西部地區(qū)、西南地區(qū)分別相差15、8、6百分點左右,長期處于全國末尾,后發(fā)趕超壓力較大。[JP]
與人口城鎮(zhèn)化相對應(yīng)的土地城鎮(zhèn)化是指土地從非城鎮(zhèn)狀態(tài)向城鎮(zhèn)狀態(tài)轉(zhuǎn)變的過程,以城鎮(zhèn)建設(shè)用地與城鄉(xiāng)建設(shè)用地的比例來度量土地城鎮(zhèn)化水平[9]。從人口城鎮(zhèn)化與土地城鎮(zhèn)化相互協(xié)調(diào)關(guān)系來看,貴州省土地城鎮(zhèn)化率從2000年的7.39%增長至2014年的27.19%,年均增長1.32百分點,其增長速度快于人口城鎮(zhèn)化。2000—2014年間,貴州省城鎮(zhèn)人口年均增長率為3.03%,同期城鎮(zhèn)建設(shè)用地年均增長率為10.75%,導(dǎo)致該時段內(nèi)貴州省城鎮(zhèn)建設(shè)用地增長彈性系數(shù)達到3.55,遠大于其合理比值1.12[10]。其中,2006—2010年(“十一五”時期)貴州省城鎮(zhèn)建設(shè)用地年均增長率達到 19.80%。一方面是由于該時段內(nèi)貴州省正大力發(fā)展工業(yè)園區(qū)建設(shè),城鎮(zhèn)建設(shè)用地需求量較大。另一方面是由于2009年之前的城鎮(zhèn)建設(shè)用地數(shù)據(jù)來源于第1次全國土地詳查基礎(chǔ)上的年度變更匯總,數(shù)據(jù)精度不高,導(dǎo)致2009年之前的城鎮(zhèn)建設(shè)用地數(shù)據(jù)比實際情況偏小;2009年之后的城鎮(zhèn)建設(shè)用地數(shù)據(jù)來源于第2次全國土地大調(diào)查基礎(chǔ)上的年度變更匯總,導(dǎo)致該時段內(nèi)城鎮(zhèn)建設(shè)用地增長幅度較大。2011—2014年(“十二五”時期)貴州省城鎮(zhèn)建設(shè)用地年均增長率為 7.59%,仍為城鎮(zhèn)人口年均增長率的2倍以上,表明貴州省土地城鎮(zhèn)化速度快于人口城鎮(zhèn)化,城鎮(zhèn)用地擴張與人口增長不協(xié)調(diào),城鎮(zhèn)用地規(guī)模擴張過快。
受貴州省特殊自然地理條件的限制,貴州省耕地質(zhì)量總體較低。《貴州省耕地質(zhì)量等級調(diào)查與評定》成果顯示,2011年全省耕地平均質(zhì)量等別為11.30等(共分為15等,值越大代表耕地質(zhì)量越差)。其中,7~10等別(優(yōu)等、高等)耕地數(shù)量占全省總量的25.75%,11~12等別(中等)耕地占 57.58%,13~15等別(低等)耕地占16.67%,貴州省耕地質(zhì)量等別總體偏低。由2009年貴州省坡度耕地面積統(tǒng)計(表3)可知,貴州省平坡度6°以下耕地面積僅占17.02%,坡度6°~15°之間的緩坡耕地面積占35.62%,>15°~25°之間的陡坡耕地面積占29.42%,需逐步退耕還林、退耕還草的25°以上耕地面積占17.94%,即貴州省15°以下的緩坡耕地僅占52.64%。水田、水澆地面積占耕地總面積的28.43%,旱地占71.57%。其中,15°以下水田占水田總面積的72.53%,15°以下水澆地占88.03%,15°以下旱地占44.69%。這進一步表明了貴州省耕地保護存在著破碎化程度高、坡度大、宜農(nóng)用地少、后備資源開發(fā)難度較大等特點。
由2000—2014年耕地面積、人均耕地面積、城鎮(zhèn)化率的變化趨勢(圖2、圖3)可知,除“十五”期間外,該時段內(nèi)貴州省耕地總量與城鎮(zhèn)化率之間并不存在簡單的線性關(guān)系,即耕地總量并未隨著城鎮(zhèn)化率的不斷提高而持續(xù)減少, 而人均耕地面
[FL)]
[FK(W7][HT6H][STHZ][JZ]表32009年貴州省分坡度耕地面積統(tǒng)計[HTSS][STBZ]
[HJ*5][BG(!][BHDFG3,WK6,WK48,WK6W]類型[ZB(][BHDWG1*2,WK12。4W]6°以下6°~15°>15°~25°25°以上
[BHDWG1*2,WK7,WK5,WK7,WK5,WK7,WK5,WK7,WK5W][XXZSX*2-ZSX11*2]面積(萬hm2)比例(%)[XXZSX*2-ZSX11*2]面積(萬hm2)比例(%)[XXZSX*2-ZSX11*2]面積(萬hm2)比例(%)[XXZSX*2-ZSX11*2]面積(萬hm2)比例(%)合計(萬hm2)
[BHDG1*2,WK6ZQ1*2,WK7DW,WK5,WK7DW,WK5,WK7DW,WK5DW,WK7DW,WK5DW,WK6DWW]水田43.8634.1249.3738.4124.4319.0110.878.46128.53
[BHDW]水澆地0.6150.610.4537.420.129.760.032.211.21
[BH]旱地33.2010.17112.7034.52109.6733.5970.9621.72326.53
[BH]耕地77.6717.02162.5235.62134.2229.4281.8617.94456.27[HT][HJ][BG)F][FK)]
[FL(2K2]
[FK(W11][TPFYB2.tif][FK)]
[FK(W11][TPFYB3.tif][FK)]
積自2006年以來呈不斷增長的趨勢。存在以下3個因素,即該時段內(nèi)貴州省城鎮(zhèn)化水平尚處于“S”形曲線的初期階段,建設(shè)占用耕地數(shù)量相對較少;該時段內(nèi)國家日益重視耕地保護和土地整治工作,土地整治新增耕地對建設(shè)占用起著較強的“沖抵”作用;隨著農(nóng)村人口大量向省外流動以及統(tǒng)計口徑因素,自2006年以來貴州省常住人口規(guī)模變動較小。
由2010—2014年國務(wù)院和貴州省人民政府批準的各類項目占用耕地數(shù)量(表4)可知,該時段貴州省依法批準的各類項目占用耕地面積呈先增加、后快速減少的變化過程。其中,城鎮(zhèn)建設(shè)占用耕地數(shù)量由2010年的29.18 km2增長至2014年的51.57 km2,其比例由27.06%上升至62.37%。工業(yè)園區(qū)建設(shè)占用耕地數(shù)量除2011、2012年較大外,2010、2013、2014年均保持在10~13 km2之間,其所占比例為13%左右。交通水利能源等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占用耕地數(shù)量呈持續(xù)下降趨勢,由2010年的63.04 km2持續(xù)下降至2014年的 16.43 km2,所占比例由58.48%下降至19.88%,表明隨著貴州省以高速公路、鐵路、水利樞紐、能源開發(fā)等為代表的基礎(chǔ)設(shè)施不斷完善,基礎(chǔ)設(shè)施建設(shè)占用耕地數(shù)量將呈下降趨勢。與此同時,農(nóng)村宅基地占用耕地數(shù)量及所占比例均呈上升趨勢,表明隨著農(nóng)村危房改造、生態(tài)移民等民生工程的持續(xù)推進和農(nóng)民收入水平的不斷提高,貴州省農(nóng)村建房占用耕地數(shù)量進入了持續(xù)上升期。[FL)]
貴州省2010—2014年經(jīng)國務(wù)院和省級人民政府依法批準的各類建設(shè)項目占用耕地數(shù)量與城鎮(zhèn)化率之間并未存在協(xié)整關(guān)系,即穩(wěn)定的比例關(guān)系,但城鎮(zhèn)建設(shè)、農(nóng)村宅基地占用耕地數(shù)量與所占比例均呈上升趨勢。如何有效控制城鎮(zhèn)建設(shè)、園區(qū)開發(fā)、農(nóng)民建房占用耕地尤其是壩區(qū)優(yōu)質(zhì)耕地(坡度小于6°),將是貴州省快速城鎮(zhèn)化進程中耕地保護亟需解決的特殊問題。
1.3貴州省快速城鎮(zhèn)化背景下耕地保護面臨的特殊困境
從建設(shè)用地適宜性評價指標體系來看[11],坡度作為衡量建設(shè)用地開發(fā)經(jīng)濟性的重要地形因子之一,坡度在6°以下為開發(fā)經(jīng)濟性優(yōu)良區(qū)域,6°~15°為開發(fā)經(jīng)濟性較好區(qū)域,>15°~25°為開發(fā)經(jīng)濟性一般區(qū)域,25°以上為開發(fā)經(jīng)濟性較差區(qū)域。從建設(shè)用地適宜性偏好來看,貴州省15°以下耕地(占總面積的52.64%)成為建設(shè)占用的“優(yōu)先對象”。通過查閱貴州省47個666.67 hm2大壩所在位置及其所在縣城(集鎮(zhèn))的城市規(guī)劃范圍、工業(yè)園區(qū)規(guī)劃范圍等基礎(chǔ)資料,在此基礎(chǔ)上對貴州省47個666.67 hm2大壩與其所在地城市(鎮(zhèn))規(guī)劃、工業(yè)園區(qū)規(guī)劃的“空間匹配”程度,并綜合考慮2005—2011年間壩區(qū)6°以下耕地面積減少數(shù)量等因素,進而得出壩區(qū)耕地保護壓力指數(shù)等級賦值(最高為5星,星級越高代表壩區(qū)耕地保護壓力越大)。結(jié)果顯示,7個666.67 hm2大壩耕地保護壓力指數(shù)為4星等級,15個666.67 hm2大壩為3星等級,22個666.67 hm2大壩為2星等級,3個666.67 hm2大壩為1星等級。貴州省耕地保護壓力指數(shù)等級為3~4星的666.67 hm2大壩中,2011年坡度在6°以下的耕地面積所占比例達到 54.51%,而2005—2011年間6°以下耕地面積凈減少 60.79 km2,占666.67 hm2大壩總減少量的80%左右(表5)。這進一步表明貴州省47個666.67 hm2大壩中有接近50%數(shù)量(22個)、超過50%面積比例(54.51%)的66667 hm2大壩在空間分布上與城市擴展區(qū)、工業(yè)園區(qū)存在空間“重疊”,面臨著壩區(qū)耕地保護與城鎮(zhèn)化、工業(yè)化建設(shè)占用“兩難困境”。
2貴州省城鎮(zhèn)化進程中耕地保護策略選擇
2.1實施“空間錯位”開發(fā)模式
當前貴州省城鎮(zhèn)化尚處于初級階段,國家加大耕地占補平衡和土地整治工作力度。從全省范圍來看,貴州省耕地數(shù)量保護受到城鎮(zhèn)化、工業(yè)化的“沖擊”總體可控;但受到貴州省山地多、平壩少的特殊自然地理條件制約,城鎮(zhèn)、工業(yè)園區(qū)主要分布在地勢相對平緩的壩區(qū)。貴州省快速城鎮(zhèn)化過程中對壩區(qū)耕地尤其是6°以下的優(yōu)質(zhì)耕地占用較為凸出,必須實行城鎮(zhèn)、工業(yè)園區(qū)與壩區(qū)耕地“空間錯位”開發(fā)模式。(1)在城鎮(zhèn)、工業(yè)園區(qū)空間擴展布局形態(tài)上,盡量避開壩區(qū)成片耕地,主要通過帶狀交通線路形成組團式、串聯(lián)型空間格局。借鑒英國等西方國家的城市綠化帶政策,將壩區(qū)成片耕地作為環(huán)繞城鎮(zhèn)、工業(yè)園區(qū)的綠化帶,并細化作為城鎮(zhèn)、工業(yè)園區(qū)綠化帶的壩區(qū)耕地用途管制政策。(2)劃定耕地保護尤其是壩區(qū)耕地“規(guī)模紅線”,守住壩區(qū)耕地保護規(guī)模底線。在現(xiàn)行永久性基本農(nóng)田劃定基礎(chǔ)上,進一步明確壩區(qū)耕地“規(guī)模紅線”,并作為審批城鎮(zhèn)規(guī)劃、工業(yè)園區(qū)規(guī)劃的前置要件之一。(3)設(shè)置城鎮(zhèn)、工業(yè)園區(qū)“擴展紅線”,控制城鎮(zhèn)開發(fā)邊界。貴州省除貴陽市、遵義市等少數(shù)城市外并無嚴格意義上的大城市,但鑒于貴州省壩區(qū)耕地與城鎮(zhèn)分布空間高度匹配的現(xiàn)實困境,以及貴州省分散、串聯(lián)型城鎮(zhèn)體系格局,在總結(jié)貴陽市等地級市開發(fā)邊界劃定試點經(jīng)驗基礎(chǔ)上,進一步推廣到全省尤其是666.67、333.33 hm2大壩周邊城鎮(zhèn),對現(xiàn)階段保護壩區(qū)優(yōu)質(zhì)耕地仍不失為一個剛性約束。
2.2提升城鎮(zhèn)建設(shè)用地集約利用水平
目前,在國家層面上,已于2014年9月1日起施行了《節(jié)約集約利用土地規(guī)定》。在省域?qū)用嫔希轿魇∪嗣裾k公廳印發(fā)了《山西省建設(shè)用地節(jié)約集約利用考核辦法》(晉政辦發(fā)[2013]98號文件),明確考核設(shè)置了億元固定資產(chǎn)投資消耗新增建設(shè)用地量、億元固定資產(chǎn)投資消耗新增用地下降率、億元GDP消耗建設(shè)用地量、億元GDP耗地下降率、億元財政收入消耗建設(shè)用地量、億元財政收入耗地下降率等億元投入與產(chǎn)出的耗地指標;遼寧省建立了省、市、縣三級億元GDP耗地評估制度,采取年度考核、定期通報、強化約束等手段對耗地量高的地區(qū)進行“黃牌”警告。在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十二五”規(guī)劃中,將耕地保有量、單位GDP能源消耗降低等資源環(huán)境指標作為約束性納入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主要指標,接受人大監(jiān)督。將單位GDP耗地量及其相關(guān)指標納入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指標體系,像節(jié)能減排指標一樣作為各級政府經(jīng)濟社會發(fā)展的重要考核指標之一。
2.3激勵存量閑置宅基地有序退出
結(jié)合當前貴州省正在實施的易地扶貧搬遷工程、農(nóng)村危舊房改造、城鄉(xiāng)建設(shè)用地增減掛鉤等工作,在充分借鑒浙江省建設(shè)用地計劃指標跨區(qū)域交易、江蘇省萬頃良田整治、重慶市地票交易等農(nóng)村宅基地市場化運作經(jīng)驗教訓(xùn)的基礎(chǔ)上,出臺貴州省農(nóng)村宅基地退出補償價格構(gòu)成及其測算辦法,按照自愿有償原則,通過經(jīng)濟杠桿激勵農(nóng)村存量宅基地有序退出。
2.4強化壩區(qū)優(yōu)質(zhì)耕地高效利用
發(fā)達國家的發(fā)展歷程表明,在工業(yè)化和城鎮(zhèn)化過程中,農(nóng)業(yè)勞動力的損失是導(dǎo)致耕地撂荒的重要原因。土地流轉(zhuǎn)能否緩解耕地撂荒是社會各界普遍關(guān)注的課題。現(xiàn)有研究成果表明[12],土地流轉(zhuǎn)可減少優(yōu)等耕作條件的耕地撂荒,通過完善土地租賃市場化程度,有助于減少或降低耕地撂荒現(xiàn)行的發(fā)生,可避免優(yōu)等耕作條件的耕地浪費。從耕地適度規(guī)模經(jīng)營實踐經(jīng)驗來看,山地丘陵區(qū)農(nóng)戶適度規(guī)模經(jīng)濟規(guī)模為 1.33 hm2 左右,種植大戶為6.67~13.33 hm2,示范規(guī)模為33.33~66.67 hm2,而生產(chǎn)基地或產(chǎn)業(yè)帶規(guī)模一般在 666.67 hm2 以上。根據(jù)貴州省耕地資源分布狀況,在山區(qū),不便于機械化大規(guī)模種植,應(yīng)鼓勵種植大戶和專業(yè)合作社形式流轉(zhuǎn)耕地進行規(guī)模化經(jīng)營;在壩區(qū),在防止一些工商資本到農(nóng)村介入土地流轉(zhuǎn)后搞非農(nóng)建設(shè)、影響耕地保護和糧食生產(chǎn)等問題的基礎(chǔ)上,通過典型示范,推動土地流轉(zhuǎn)規(guī)范有序進行,適度引入專業(yè)合作社、城市工商資本進行規(guī)模化經(jīng)營,提高壩區(qū)耕地產(chǎn)出效益,更好地利用壩區(qū)耕地。
2.5合理配置坡耕地生態(tài)化種植模式
立足貴州省坡耕地比例大、水土流失嚴重等實際情況,結(jié)合貴州省山地立體農(nóng)業(yè)特征,在15°以上尤其是25°以上的坡耕地區(qū)域,因地制宜種植中藥材、茶葉、核桃等經(jīng)濟作物。將沒有破壞耕作層并易于調(diào)整種植結(jié)構(gòu)的經(jīng)果作物種植土地作為可調(diào)整耕地,仍納入耕地保有量目標范疇。擴大坡耕地經(jīng)果作物種植面積,增加坡耕地經(jīng)濟產(chǎn)出效益,倡導(dǎo)坡耕地生態(tài)化種植模式,實現(xiàn)坡耕地生態(tài)化保護。
3貴州省城鎮(zhèn)化進程中耕地保護政策建議
3.1制定耕地占補質(zhì)量等級折算辦法
當前貴州省實施了更為嚴格的“占優(yōu)補優(yōu)”耕地占補平衡政策,即占水田補水田,占旱地補旱地。但從貴州省耕地資源特征以及后備資源稟賦來看,不同坡度、坡向、高程等自然因子的水田和旱地,其質(zhì)量和產(chǎn)出水平差異較大。按照習(xí)近平總書記“堅決防止耕地占補平衡中出現(xiàn)的補充數(shù)量不到位、補充質(zhì)量不到位問題,堅決防止占多補少、占優(yōu)補劣、占水田補旱地的現(xiàn)象”指示精神,貴州省耕地占補平衡管理政策應(yīng)以耕地產(chǎn)能核算為前提,以耕地質(zhì)量等級為基礎(chǔ),探索制定更為完善的耕地占補質(zhì)量等別折算辦法。如占用0.066 hm2優(yōu)等、高等別耕地(水田、水澆地、旱地),需對應(yīng)補充多少中等、低等別耕地(水田、水澆地、旱地)。確保貴州省耕地總地力(產(chǎn)能)達到較為穩(wěn)定的水平,為貴州省糧食安全提供耕地保障。
3.2適度提高產(chǎn)業(yè)用地經(jīng)濟門檻
產(chǎn)業(yè)目錄是我國加快轉(zhuǎn)變經(jīng)濟發(fā)展方式、推動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調(diào)整和優(yōu)化升級、完善和發(fā)展現(xiàn)代產(chǎn)業(yè)體系的重要手段。上海市、廣州市、深圳市、江西省等省市分別結(jié)合自身實際情況制定了用地指南或用地標準。在國家層面上,《節(jié)約集約利用土地規(guī)定》(國土資源部令第61號)第十五條明確提出國家實行建設(shè)項目用地標準控制制度,并鼓勵地方國土資源主管部門根據(jù)本地實際情況制定和實施更加節(jié)約集約的地方性建設(shè)項目用地控制標準。根據(jù)貴州省各類開發(fā)區(qū)(國家級和省級新區(qū)、綜合保稅區(qū)、經(jīng)濟開發(fā)區(qū)、高新區(qū)等)的性質(zhì)、功能、開發(fā)程度、主導(dǎo)產(chǎn)業(yè),分門別類地細化產(chǎn)業(yè)目錄和用地標準,提高各類產(chǎn)業(yè)用地經(jīng)濟門檻,有效約束各類開發(fā)區(qū)土地閑置、低效利用問題。
3.3嚴格控制新增宅基地規(guī)模
目前正在實施的《貴州省土地管理條例》僅對戶均宅基地面積進行了簡單規(guī)定,如城市郊區(qū)、壩區(qū)不超過130 m2,丘陵地區(qū)不超過170 m2,山區(qū)、牧區(qū)不超過200 m2。尚未出臺有關(guān)農(nóng)村宅基地的管理辦法,[JP2]且未對院壩用地、其他附屬用地進行硬性規(guī)定。現(xiàn)行單純以人均用地標準測算的農(nóng)戶宅基地標準管制模式已不適應(yīng)貴州省山地特色新型城鎮(zhèn)化建設(shè)的相關(guān)要求。在體現(xiàn)宅基地福利功能屬性的基礎(chǔ)上,以人均用地標準控制農(nóng)戶宅基地總規(guī)模,根據(jù)農(nóng)戶分化類型及其宅基地的主導(dǎo)用途和功能(居住、養(yǎng)殖生產(chǎn)等),進一步明確其宅基地內(nèi)部用地結(jié)構(gòu)比例浮動范圍(居住用地比例、養(yǎng)殖生產(chǎn)用地比例、院壩等附屬設(shè)施用地比例等)、房屋層數(shù)、容積率、建筑密度、建筑風貌等指標[13],形成農(nóng)村聚居(新農(nóng)村建設(shè)點)、散居農(nóng)戶宅基地用地管制細則,嚴格控制新增宅基地規(guī)模。[JP]
3.4高標準整治壩區(qū)耕地
農(nóng)村土地整治作為改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條件、增強農(nóng)業(yè)基礎(chǔ)設(shè)施抵御災(zāi)害能力的重要手段,在提高耕地質(zhì)量和產(chǎn)出效益方面取得顯著成效,促進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營專業(yè)化、標準化、規(guī)模化、集約化,為助推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夯實基礎(chǔ)。圍繞高產(chǎn)、優(yōu)質(zhì)、高效、生態(tài)、安全的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發(fā)展目標,推動以產(chǎn)業(yè)化經(jīng)營為重要技術(shù)路徑的農(nóng)業(yè)現(xiàn)代化發(fā)展。以適應(yīng)壩區(qū)現(xiàn)代農(nóng)業(yè)發(fā)展要求為目標導(dǎo)向,按照增強糧食綜合生產(chǎn)能力、提升農(nóng)業(yè)基礎(chǔ)設(shè)施水平、轉(zhuǎn)變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方式、改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結(jié)構(gòu)的基本原則,從整治重點、工程標準、運作方式等方面構(gòu)建與之相匹配的土地整治模式。在工程配套層面,按照“生產(chǎn)提高、生態(tài)運行、生活改善”的總體要求,根據(jù)糧油、瓜果、蔬菜等不同農(nóng)作物產(chǎn)業(yè)鏈需求,從技術(shù)方案、建設(shè)模式、建設(shè)標準、規(guī)程規(guī)范等方面對土地平整與集中、灌溉與排水、田間道路與農(nóng)田林網(wǎng)、土壤改良與培育、農(nóng)業(yè)機械化耕作與配套、農(nóng)作物種植與管護等工程技術(shù)進行集成,提升農(nóng)業(yè)機械化生產(chǎn)水平和經(jīng)營效益,促進農(nóng)民增收[14]。
3.5整合多渠道支農(nóng)資金
在倡導(dǎo)坡耕地生態(tài)化種植模式的前提下,將中草藥、茶葉、核桃、精品水果等經(jīng)果作物種植納入產(chǎn)業(yè)扶貧項目,整合產(chǎn)業(yè)扶貧資金,重點打造,進行典型示范。同時,使核桃、果樹等郁閉度較大的喬木類以及覆蓋度較大的灌木類經(jīng)果作物享受退耕還林資金支持。通過整合多種渠道支農(nóng)資金,助推坡耕地生態(tài)化高效利用。
4結(jié)論
城鎮(zhèn)化是國家或地區(qū)現(xiàn)代化水平的重要標志,也是人類走向文明不可逾越的歷史階段。貴州省城鎮(zhèn)化作為西部城鎮(zhèn)化、中國城鎮(zhèn)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水平嚴重滯后于全國平均水平。近年來貴州省城鎮(zhèn)化發(fā)展迅速,取得了較大突破,但仍存在人口城鎮(zhèn)化與土地城鎮(zhèn)化發(fā)展不均衡、城鎮(zhèn)建設(shè)占用耕地數(shù)量與所占比例均呈上升趨勢等問題。尤其在城鎮(zhèn)化過程中,貴州省47個666.67 hm2大壩中有接近50%數(shù)量(22個)、超過50%面積比例(54.51%)的666.67 hm2大壩在空間分布上與城市擴展區(qū)、工業(yè)園區(qū)存在空間“重疊”,面臨著壩區(qū)耕地保護與城鎮(zhèn)化、工業(yè)化建設(shè)占用“兩難困境”。基于此,本研究從設(shè)置耕地保護“規(guī)模紅線”、城鎮(zhèn)用地“擴展紅線”2個方面提出了貴州省快速城鎮(zhèn)化進程中耕地數(shù)量保護的策略與措施,從提升城鎮(zhèn)建設(shè)用地集約利用水平、合理管控農(nóng)村宅基地規(guī)模2個方面明確了貴州省快速城鎮(zhèn)化進程中應(yīng)強調(diào)城鄉(xiāng)建設(shè)用地內(nèi)涵式管控方向。同時,加強壩區(qū)耕地高標準整治,通過土地流轉(zhuǎn)促進規(guī)模經(jīng)營,促進壩區(qū)耕地高效利用,并通過合理配置坡耕地種植模式穩(wěn)步提升坡耕地生態(tài)涵養(yǎng)功能。
參考文獻:
[1]宋戈,吳次芳,王楊. 城鎮(zhèn)化發(fā)展與耕地保護關(guān)系研究[J]. 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問題,2006(1):64-67.
[2]李丹,劉友兆. 城市化發(fā)展與耕地變動的關(guān)系研究[J]. 經(jīng)濟縱橫,2003(1):46-50.
[3]鄧榮榮,吳燕,詹晶. 我國建設(shè)占用耕地數(shù)量與城鎮(zhèn)化水平的相互關(guān)系——基于VAR模型的實證[J]. 西北人口,2012,33(6):89-94,102.
[4]胡偉艷,張安錄. 人口城鎮(zhèn)化與農(nóng)地非農(nóng)化的因果關(guān)系——以湖北省為例[J]. 中國土地科學(xué),2008,22(6):30-35.
[5]吳玉鳴,馮仁勇. 巖溶區(qū)城鎮(zhèn)化與耕地資源動態(tài)變化的面板數(shù)據(jù)分析——以廣西河池地區(qū)為例[J]. 資源科學(xué),2010,32(5):985-991.
[6]談明洪,李秀彬,呂昌河. 20世紀90年代中國大中城市建設(shè)用地擴張及其對耕地的占用[J]. 中國科學(xué):D輯,2004,34(12):1157-1165.
[7]王永平,張瑜,黃海燕. 貴州快速城鎮(zhèn)化進程中的土地問題與對策[J]. 貴州農(nóng)業(yè)科學(xué),2011,39(12):243-247.
[8]姚原溫,李陽兵,金昭貴,等. 貴州省大壩土地利用變化及驅(qū)動力分析[J]. 長江流域資源與環(huán)境,2014,23(1):67-74.
[9]李昕,文婧,林堅. 土地城鎮(zhèn)化及相關(guān)問題研究綜述[J]. 地理科學(xué)進展,2012,31(8):1042-1049.[ZK)]
[10]蕭篤寧. 城市化進程與土地資源的可持續(xù)利用[J]. 云南地理環(huán)境研究,1997,9(1):34-39.
[11]齊增湘,廖建軍,徐衛(wèi)華,等. 基于GIS的秦嶺山區(qū)聚落用地適宜性評價[J]. 生態(tài)學(xué)報,2015,35(4):1274-1283.
[12]邵景安,張仕超,李秀彬. 山區(qū)土地流轉(zhuǎn)對緩解耕地撂荒的作用[J]. 地理學(xué)報,2015,70(4):636-649.
[13]馮應(yīng)斌,楊慶媛. 丘陵地區(qū)村域居民點演變過程及調(diào)控策略研究[M]. 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06:154-155.
[14]馮應(yīng)斌,楊慶媛. 轉(zhuǎn)型期中國農(nóng)村土地綜合整治重點領(lǐng)域與基本方向[J]. 農(nóng)業(yè)工程學(xué)報,2014,30(1):175-1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