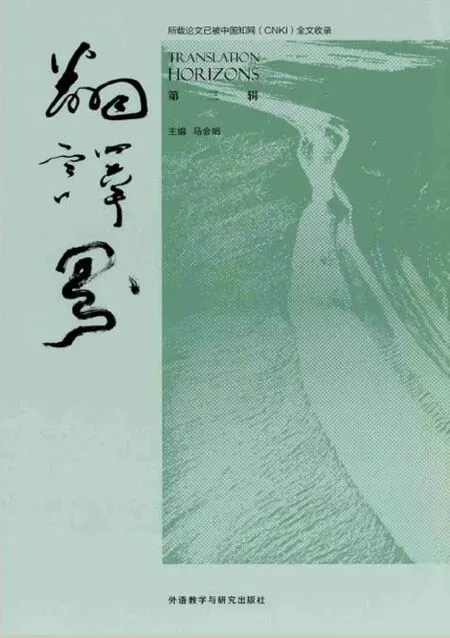口譯者與歷史的締造*
管興忠 張思雨 譯
北京語言大學
口譯者與歷史的締造*
管興忠 張思雨 譯
北京語言大學
本文摘譯自讓·德利爾(Jean Delisle)與朱迪斯·伍茲沃斯(Judith Woodsworth)主編的《歷史上的譯者》(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一書第九章,講述了口譯史、口譯培訓和口譯研究方法。摘譯部分主要介紹了從交替傳譯到同聲傳譯的口譯模式轉變、從巴黎和會到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審判相關重大歷史時刻及相關口譯員,以及探索新大陸時期為歐洲探險家充當翻譯的兩位女性:瑪麗娜夫人(Do?a Marina)和在梅里韋瑟·劉易斯(Meriwether Lewis)與威廉·克拉克(William Clark)遠征隊中擔任口譯的薩卡加維亞(Sacajawea)。
《歷史上的譯者》;口譯史;同聲傳譯;交替傳譯
歷史上的口譯員,無論活躍在哪個領域,他們既是歷史事件的見證者,也因為參與其中而成為歷史的締造者。如果沒有口譯員,無論是民族和國家關系,還是跨越語言和文化障礙的交流活動,都會有很大不同。
口譯員無法像翻譯家那樣給世人留下永恒的遺產,杜蘊德(Andrew Dawrant)如是認為。杜蘊德是唯一一位母語為英語、為聯合國提供漢語口譯的專家。這位加拿大人通過看電視、上課、在中式點心店當服務生掌握了漢語,后來曾為國家首相、外交官、公司首席執行官、諾貝爾獎獲得者提供口譯服務。身為世界頂級的漢英口譯員,杜蘊德可謂是個“奇跡般的人物”。然而,他覺得:
(作為口譯員,)我注定只不過是21世紀初中西關系史上一個有趣的旁注而已……如果你翻譯了《戰爭與和平》,而且譯得足夠好,你的譯作會在一代又一代的讀者中流傳,但我們不會留下什么遺產。我們的工作曇花一現,是空氣中流動的語言。(Hoffman, 2011)
口頭語言稍縱即逝。這一特性導致了口譯及口譯研究的“少數化”傾向(Cronin, 2002: 46)。若想了解口譯員的過去,我們往往要借助于他們的書信、日記、回憶錄、自傳等材料,但這些文獻涉及口譯活動本身的內容僅是東鱗西爪式的只言片語而已。由于缺乏可靠的書面記錄,一些空白可能永遠都無法填補。縱使文獻資料充足,口語表達本身依然很難通過“書寫或印刷等外化翻譯形式”給予充分的解釋,因此邁克爾·克羅寧(Cronin,2002)建議通過“權力、文化、性別、種族等范疇”來開展口譯研究。
多數情況下,口譯員及其工作成果都無法載入史冊,因為史書記載的都是些重大事件、杰出人士或者豐功偉績。此外,書面文字的主導地位使得筆譯員更可能受到歷史學家的青睞。口譯員的社會階層同樣解釋了他們在歷史上的位置;他們具有民族和文化上的雜合性,而且多為婦女、奴隸或出身次等社會階層的成員,比如生活在英屬印度的基督徒、亞美尼亞人和猶太人(Roditi, 1982: 6)。他們通常是那些無家可歸或生活動蕩之人(比如遭綁架之人、沖突摩擦或政治劇變的受害者),在經歷跨文化的過程中逐漸習得第二語言,成為雙語或多語人士,進而開始從事口譯。盡管這些人作為文化中間人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但歷代書吏、編年史家和史學家作為甄選史書內容的決策者,顯然不愿意給予口譯員應有的一席之地。因此,關于口譯員的秘聞軼事只能經由說書人或作家口筆相傳,內容也就隨著一次又一次的傳播逐漸走樣。其中最極端的例子大概非薩卡加維亞(Sacajawea,約1788-1812?)莫屬,關于她的故事我們會在后文予以介紹。
口譯史研究起步雖然相對較晚,但已經挖掘出許多新的線索。早在公元前3000年,埃及就出現了表示“口譯員”和“口譯”的象形文字(Gardiner,1969)。英格里德·克魯茲(Ingrid Kurz, 1986: 218-219)詳細記錄了經典作品中出現的與口譯相關的內容,比如李維(Livy)的著作中有五處提到口譯,此外在愷撒、西塞羅、奧拉斯·格留斯(Aulus Gellius)、賀拉斯、普林尼、塞勒斯特(Sallust)及瓦勒里烏斯·馬克西穆斯(Valerius Maximus)的作品中也均有提及。漢斯·弗米爾(Hans J. Vermeer)的研究也顯示,古希臘、古羅馬和中世紀文獻中均明確或間接提及口譯(1992: 168-174)。例如,他通過研究色諾芬的《遠征記》推斷出希臘人和波斯人在談判時都會帶著自己的口譯員。
歷史發展到一定階段,總會出現某種通用語,以方便講不同語言的人進行溝通。這里特別要指出的是拉丁語。拉丁語不僅曾經用于宗教、科學、文學,在17世紀以前還是歐洲各國的外交語言。在某種程度上,意大利語和法語也在歐洲起過類似的作用。阿拉伯語在非洲,英語、法語、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在其各自的殖民地亦是如此。然而,這些語言主要在特定的地理區域或社會團體中使用。軍隊、商人、探險家或傳教士一旦離開通用語的使用范圍,就需要口譯員的幫助。比如,羅馬人在管理被征服領土、在帝國邊境開疆拓土時都離不開口譯員的參與(Van Hoof, 1962; Roditi,1982: 2)。
在晚期拉丁語和中世紀阿拉伯語文獻中,我們經常可以看到關于口譯的記載。在中世紀,人們對口譯員的需求不斷增長,該職業也逐漸得到認可,比如法國史學家記載了十字軍東征期間的口譯活動。文藝復興時期,人文主義激發了人們對外語的興趣,加之歐洲人開始了探索、征服和建立帝國的征程,口譯員顯得越來越重要。人們在威尼斯共和國的貿易檔案以及從中世紀晚期到17、18世紀的外交檔案中均發現了有關口譯的記載(Roditi,1982)。隨著越來越多國家的誕生,各國語言隨之發展,需要口譯員的情況變得愈發常見,書籍文獻中也愈發明確地提及口譯員的工作。政治家、外交官的回憶錄和信件等原始資料中均包含有寶貴的信息,口譯員們也為我們留下了極具價值的回憶錄。
歷史上,無論關于口譯的記載如何不連貫、如何支離破碎,有資料足以證明有口譯員將畢生獻給了口譯事業,有的則是順應形勢所需走上了口譯的道路。不管是他們選擇了口譯,還是口譯選擇了他們,口譯員都為塑造歷史做出了貢獻。在深入探究他們取得的功績之前,我們首先來簡單看一下古往今來的口譯模式,以揭示口譯與某些重大歷史時刻的關聯。
口譯形式和方法的演變
在現代社會,我們對科技早已習以為常。對于那些有機會頭戴耳機參加國際會議,或者在電視上看過世界各國領導人自由交談的人來說,同聲傳譯(以下簡稱“同傳”)早已是見怪不怪,甚至被理所當然地視為一項技術成就,與個人的努力似乎沒有多大關系。事實上,口譯一直以來都是一項極為復雜且要求嚴苛的活動,而且具有多種多樣的功能和形式。
在引入專門的同傳設備前,口譯以交替傳譯(以下簡稱“交傳”)為主。交傳需要譯員先聽取一段相對較長的話,通常還需同時做筆記,然后用另一種語言復述聽到的內容。翻譯的內容長短不一,筆記的形式也多種多樣。
1920年的巴黎和會以及后續的多邊會議無疑是交傳歷史上最輝煌的時刻之一。不過具有諷刺意味的是,也正是在巴黎,法語失去了作為外交語言的優勢地位。這一變化經歷了一場“語言大戰”。由于一戰的戰勝國聚集在法國,會議又由法國總理克列孟梭主持,英國和美國便認為應該對會議的語言做些調整。于是,英語和法語同時成為會議的官方語言,會議文件也用這兩種語言起草。瑪格麗特·麥克米蘭(Margaret MacMillan)對這場關于語言的爭論做了如下總結:
法國人要求把法語作為唯一官方語言,最明顯的理由是法語比英語更準確,更能體現細微的差別。法國人認為,幾個世紀以來法語一直是國際交流和外交語言,而英國人和美國人則認為法語正逐漸被英語取代。英國首相勞合·喬治雖然一直說自己后悔沒有學好法語(他幾乎完全不懂),但他指出當時有超過1億7千多萬人使用英語,因此英語不能享有與法語平等的地位似乎是荒謬的。意大利人則說,那樣的話,為什么不把意大利語也算上[……]勞合·喬治反駁道,那樣的話,為何不把日語也算上?對于這場論戰,英語和法語都聽不懂的日本代表唯有保持沉默。令法國官員驚訝的是,克列孟梭最終讓步了。(2002:55-56)
這場發生在更大規模戰爭(一戰)之后的特殊戰爭最終導致了法語地位的下降,并為多語種在國際組織中的使用敞開了大門,使得口筆譯員的工作成為必須(Baigorri-Jalón, 2004: 12-16)。
在巴黎和會以及后續的國際磋商中,不少譯技精湛的譯員承擔了口譯工作。巴黎和會上的12名口譯員中,好幾位成為了口譯界的先驅,其中以保羅·芒圖(Paul Mantoux, 1877-1956)和古斯塔夫·亨利·卡梅林克(Gustave Henri Camerlynck, 1870-1929)最為有名(Roland, 1999: 121)。另外,當時的譯員還包括1941年創立日內瓦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的安東尼·威爾曼(Antoine Velleman, 1875 -1962)。讓·艾赫貝爾(Jean Herbert, 1897-1980)成為國際聯盟杰出的交傳譯員,后在紐約聯合國總部擔任首席口譯員。其他譯員還有羅伯特·康菲諾(Robert Con fi no, 1903-1969)、安德烈·卡明科(André Kaminker, 約1877-約1961) 以及其弟弟喬治·卡明科(George Kaminker, 約 1890-約 1969)。
西班牙作家、外交家薩爾瓦多·德·馬達里亞加(Salvador de Madariaga, 1886-1978)時任國際聯盟西班牙代表團團長,他曾提到一位“天使般”的夫人,言語中充滿欽佩:“她能做到聽完英語、法語或意大利語的講話后,不借助筆記,用其他任意兩種語言完美復述出講話人的內容。”他認為,具有此種能力的譯員最適合做大會口譯,而那些適應更短一些講話和應答機敏的口譯員更適合為各委員會翻譯,至于“老練、對政治敏感的譯員”則適合在理事會做口譯(Madariaga, 1974: 107)。拜戈里·哈隆(Baigorri-Jalón, 2004: 92; 116)指出,馬達里亞加提到的“天使般”的夫人指的就是英國作家、口譯員奧莉維亞·羅塞蒂·阿格雷斯蒂(Olivia Rossetti Agresti)。阿格雷斯蒂來自藝術家、作家輩出的羅塞蒂家族,叔叔是集藝術家、作家、翻譯身份于一身的但丁·加百利·羅塞蒂(Dante Gabriel Rossetti)。阿格雷斯蒂投身無政府主義政治,后來加入意大利法西斯陣營。
即使所處時代不同,工作環境各異,歷史上有許多交傳譯員因其復述大段內容和準確翻譯的能力而受到贊譽。從16世紀為征服者科爾特斯(Cortés)擔任口譯的瑪麗娜夫人(約1500-約1530)到20世紀為美國總統提供口譯的弗農·沃爾特斯(Vernon Walters, 1917-2002),無不如此。
尤金·多爾曼(Eugen Dollmann, 1900-1985)曾擔任二戰軸心國的口譯員。他在回憶錄中分享了一次別樣的口譯經歷——為希特勒做口譯。希特勒的演講地點在戶外,聽眾是來自墨索里尼當局的青年組織成員,約有一千人。原計劃較為簡短的講話最終卻持續了半個多小時。多爾曼當時還尚未掌握筆記技巧,他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一場意大利語講話,與希特勒的演講內容根本毫無關系”,但沒想到的是,竟然收獲了現場雷鳴般的掌聲(Dollmann, 1967: 13)。
但在有些情況下,口譯員則必須進行逐句翻譯。比如在結束美西戰爭的1898年巴黎和會上,代表們便要求亞瑟·弗格森(Arthur Ferguson,1859-1908)一句一句地將仍處于起草階段的合約進行口譯(Morgan, 1965:104)。
人們經常提起這樣一個問題:口譯員到底應該在何種程度上再現講話人的用詞和語調?巴黎和會上為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擔任口譯的斯蒂芬·邦斯爾(Stephen Bonsal)上校主張譯員應對講話人的用詞、語氣做出一定的調整。據傳,巴黎和會四巨頭之一曾要求邦斯爾向“阿拉伯的勞倫斯”(托馬斯·愛德華·勞倫斯,Thomas Edward Lawrence,1888-1935)提議參照芒圖的先例,“淡化國王費薩爾(Faisal)的講話中言辭激烈的成分,以防冒犯權勢人物”。芒圖曾開此先河,“在翻譯時淡化了民族主義發言人慷慨激昂的講話中過于尖銳的內容”。但勞倫斯表示拒絕:
他也許是對的,但恕我難以從命。我是一名翻譯,我只負責翻譯。費薩爾國王的勇士們扛著阿拉伯的旗幟,跨越無垠的沙漠,從圣城麥加前往圣城耶路撒冷、大馬士革以及更遠的地方。費薩爾國王是代表成千上萬在長期斗爭中犧牲的勇士發言,是他們臨終之言的傳信人。國王不能更改遺言的內容,我也不能淡化他的語氣。(Bonsal, 1946: 33-34)
然而,一些曾有幸見證勞倫斯口譯風格的人感覺他也并非總是能夠達到自己所說的高標準(Keynes, 1949)。也有傳言說,費薩爾“身著鑲金白袍,腰佩半月彎刀[……]只是在那里背誦《古蘭經》,勞倫斯則在一旁即興發揮”(MacMillan, 2002: 391)。這樣的軼事不勝枚舉,其中有些說法有著可靠的來源,有些則被夸大了。
盡管交傳有時被認為非常費時,但也不乏擁護者。口譯員兼理論家達妮卡·塞萊斯科維奇(Danica Seleskovitch, 1921-2001)便認為交傳可以使討論的主題更為集中,因為參會者有額外的時間用來思考。她還提出,“交傳實際上是省時的”(1978: 124-125)。持這一觀點的其實不止塞萊斯科維奇。比如,曾參加圣雷默會議(San Remo Conference)的英國首相勞合·喬治及其他代表也曾表示,與直接發言相比,有口譯員在場會讓磋商變得更加容易,因為每次停頓都為思考提供了時間(Riddell, 1933: 189)。
另外,所謂的“耳語傳譯”——即譯員在聽眾耳邊低聲翻譯——也有著幾百年的歷史。1747年9月14日,譯員在格洛高耶穌學院舉行的文藝演出現場用德語向普魯士國王腓特烈二世口譯拉丁文詩歌時使用的正是這種翻譯方式(Barthel, 1982: 143)。如今,在僅有一兩人不懂會議語言的場合,耳語傳譯仍然不失為一種高效的翻譯形式。
盡管交傳有著各種各樣的優點,但仍然被認為過于繁瑣,特別是涉及兩種以上語言的時候。在國際聯盟時代,人們就已經找到了解決方案。當時的IBM公司專門為同聲傳譯開發了一套由耳機和麥克風組成的特殊設備,通過該設備即可實現口譯員與發言人同時講話。這套設備后來由三個美國人——商人愛德華·法林(Edward Filene)、電機工程師戈登·芬利(Gordon Finlay)和IBM公司總裁托馬斯·沃森(Thomas Watson)——推廣到國際聯盟。僅通過一個旋鈕即可選擇任意的工作語言,在當時看來不啻一項技術上的奇跡,但因接線量巨大,整個系統實際上存在許多技術問題。位于日內瓦的國際勞工局是國際聯盟中唯一決定采用該設備的機構。1927年,國際勞工大會在日內瓦召開,法林–芬利–IBM系統首次和交傳結合使用。同聲傳譯用于會議翻譯則始于1935年在列寧格勒召開的第15屆國際生理學會議。在會議上,諾貝爾生理學獎獲得者伊萬·巴甫洛夫致開幕辭,他的演說內容通過同聲傳譯由俄語譯為英、法、德三種語言(Van Hoof, 1962: 19-20)。但在二戰爆發前幾年,隨著國聯影響力的下降,同聲傳譯也暫時退出了國際交往的舞臺。
直到1944年,IBM的同傳設備才在費城的一場會議上再次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然而,當時的工作條件非常不理想。口譯員坐在位于講話人講臺正下方的地下室里,頭頂上方不時傳來嘈雜的腳步聲,再加上二十年前的設備老化陳舊,運轉不靈,翻譯極為困難(Roditi, 1982: 10)。盡管交傳的諸多不足已經為人所知,但在誕生了《聯合國憲章》的1945年舊金山會議上,采用的仍然是交傳,而非同傳。
同聲傳譯東山再起,是在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上。二戰結束以后,同盟國成立國際軍事法庭,于1945年11月至次年10月對軸心國領導人的戰爭罪行進行了數十次軍事審判。盟軍一方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接受審判的戰犯主要是德國納粹頭目。仲裁法庭使用英語、法語、俄語和德語。由于紐倫堡審判不僅牽扯到當事國,更涉及全世界的利益(Conot,1983),時機成熟,同聲傳譯重出江湖。
利昂·多斯特(Léon Dostert, 1904-1971)上校是紐倫堡審判口筆譯服務的主要負責人。這位出生于法國的美國人有著非凡的組織能力,他招募的口譯員除了日內瓦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的老師和學生,還有在家庭環境和戰爭影響下掌握多門語言的人。在所有口譯員中,只有愛德華·羅迪特(édouard Roditi, 1910-1992)和哈康·薛瓦利埃(Haakon Chevalier, 1902-1985)有同傳經歷。兼具詩人、藝術評論家和翻譯家多重角色的羅迪特生于巴黎,父母是美國人,他曾在不同的文化中生活過,精通多門語言。舍瓦雷于1929至1946年在加州大學教法語,翻譯過司湯達、馬爾羅和阿拉貢等法國知名作家的作品。多斯特的口譯團隊不得不在極其困難的條件下進行各個主題的翻譯1。盡管如此,同傳這一全新的口譯方式似乎是未來的發展方向。后來,加拿大人安東尼·皮隆(Antoine Pilon)對同傳系統進行了完善。這位前皇家空軍轟炸機飛行員、音頻工程師設計了一套將麥克風和耳機連接在一起的復雜線路網絡,最終使得當時的同傳設備變得方便實用(Delisle, 1990: 335)。
二戰結束后,聯合國應運而生。國際聯盟使用英、法、西三種語言,聯合國則有六種工作語言。隨著語言數量的增加,對口譯的要求也愈發復雜。聯合國官員目睹了全新的口譯設備的工作效率后立即與多斯特上校簽訂了合同,授意他組建一支同傳團隊。1947年,團隊在倫敦舉行的關稅與貿易大會上正式亮相(Roditi, 1982: 15)。1947年11月15日,聯合國通過第152號決議,規定同聲傳譯作為一項永久性服務,可替代交替傳譯或者與交替傳譯同時使用。
第152號決議實際上標志著交傳在聯合國大會上的終結,盡管交傳仍不乏輝煌時刻。《外交實踐指南》第五版的主編保羅·戈爾–布思勛爵(Lord Paul Gore-Booth)曾講過這樣一樁軼事:“秘魯著名政治家、演說家費爾南多·貝朗德(Fernando Belaúnde)在聯合國大會上用西班牙語發表了一段長篇講話,知名譯員卡明科兄弟之一負責譯成法語。譯者在翻譯時再現了講話人的每項重要內容、每次顯著的停頓、每處生動的語調,甚至每個鮮明的手勢,并且期間完全不借助任何筆記。當他坐下時,現場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Satow, 1979: 511n)。
盡管一開始同傳遭到了前國際聯盟那些經驗豐富的譯員的反對,但是到了1950年,同傳已經完全獲得了認可,設備也得到了進一步的改進。雖然交傳仍在繼續使用,尤其在法庭和社區口譯中,但是同傳借助先進的技術得到了很大的提升,在全世界大多數政府間機構里、多語會議上,都能見到同傳譯員的身影。
在過去,不少成功的口譯員純粹是因為偶然才進入這個行業,比如羅迪特。他在火車上遇到了時任魏瑪共和國外交部口譯員的漢斯·雅各布(Hans Jacob)。在雅各布的勸說下,羅迪特去日內瓦參加了翻譯考試,并走上了口譯之路(Roditi, 1978)。類似的例子還有杜蘊德。他在飛機上偶遇了20世紀80年代至90年代加拿大頂級的漢語口譯員讓·杜瓦爾(Jean Duval),從此找到了自己的使命(Hoffman, 2011: F7)。
隨著國際關系在政治、經濟、文化和科學等領域發生巨大的變化,對口譯員及譯員培訓項目的需求也開始激增。19世紀后半葉,工業革命引發了諸如鐵路、電信等領域的國際組織的崛起。到19世紀末,全球已有超過1400種專業會議(Van Hoof, 1962: 15)。隨著社會流動性的增大,許多國際會議中也有了各國專家和外交官的身影,但他們所受的教育卻不包括外語培訓,于是大量的專業譯員開始出現在國際機構,提供交傳服務。
直到近代,“口譯員是天生的,而非后天的”這一觀點依舊很普遍。各種語言培訓有著悠久的歷史,但針對口譯技巧的培訓卻是20世紀早期才出現的。不少國家的外交部也開始組織考試選拔人才,以滿足外交口譯的需求。據相關文獻資料顯示,美國國務院1904年的人事檔案中有“實習口譯員”的記錄,英國和德國也都設立有專門的語言服務機構。盡管如此,當時的口譯員學習口譯主要是通過實踐,依靠在工作中反復摸索,課程也多局限于雇主提供的培訓項目。大學里有別于一般語言和文學專業、針對口譯人才培養的項目則是從20世紀40年代才開始設立的。日內瓦大學于1941年開設了口譯課程,維也納大學始于1943年,美因茨大學蓋默斯海姆翻譯學院始于1946年,薩爾大學始于1948年,喬治城大學始于1949年,海德堡大學始于1950年。此后,翻譯學院的數量才開始有所增長2。20世紀70年代,隨著歐洲共同體(今歐盟前身)的擴張,其翻譯語言組合的數量也在成倍增長。同傳專用設備的引入也是推動口譯職業發展和職業訓練的一個主要因素。此外,技術上的改善可以方便監測學生的學習進展、分析譯員的表現,甚至還可以快速獲取專業術語。
和筆譯的情形類似,正規口譯訓練的發展也推動了口譯作為一個研究領域的出現,也就是說,要制定出一套理論原則來指導口譯的教學,或對口譯進行觀察和描述。此外,同筆譯員一樣,口譯員也開始思考他們的發展歷史以及自身在宗教、文化和政治團體機構中發揮的多重作用。
探索與征服
除了宗教,歐洲人從舊大陸前往新大陸探險還伴隨著拓展貿易、獲取權力、擴張領土等目的。歐洲人同美洲土著居民接觸必然要涉及溝通交流、文化交際、商業交往、征服占領、紛爭解決,此時口譯員便顯得尤為重要。直到近幾年,才有研究從多個角度詳細介紹這些所謂“文化掮客”或“文化中間人”的復雜人生3。
瑪麗娜夫人4,又作瑪琳辛(Malintzin)或瑪琳齊(la Malinche),是為新世界征服者、侵略者和發現者提供口譯服務的最杰出的土著譯員之一。無論是在當時的記錄中,還是在后人撰寫的歷史資料里,她都被視為“征服過程中的關鍵人物之一”(Madariaga, 1942: 117)。
盡管不止一處有記載提到瑪麗娜,科爾特斯本人對她卻很少提及。在科爾特斯寫給查理五世的五封長信中的第二封僅僅把她稱作“印第安婦女”(MacNutt, 1977: 217),只在描述1524年洪都拉斯遠征的第五封信中提到了她的名字(MacNutt, 1977: 273)。
關于瑪麗娜的生平至今尚有爭議,她何時去世至今仍不清楚。但我們知道的是,她出生于1505年左右,有著高貴的血統,父親是墨西哥夸察夸爾科斯地區(Coatzacoalcos)的酋長,但在她兒時就已去世。母親后來改嫁,為新丈夫生下一子,于是瑪麗娜就被賣給了瑪雅商人。瑪麗娜的早年經歷頗有幾分神秘色彩,這可能是由于她本人的原因所致(Herren, 1992:37)。她可能經過多次轉手才最終和其他十九名奴隸一起被送給科爾特斯和他在塔巴斯科的屬下(Díaz del Castillo, 1983: 58)。科爾特斯為這些女奴安排受洗后,把她們當作禮物送給了自己的手下。瑪麗娜既會阿茲特克語,又會瑪雅語,前者是她的母語,后者是她在和塔巴斯科人生活期間學會的。據說,她學西班牙語的速度很快,不過究竟有多快只能靠推測。年僅14歲的瑪麗娜因美貌與聰慧格外引人注目,科爾特斯便又將她送給了一位顯赫的紳士阿隆索·埃爾南德斯·波托卡雷羅(Alonso Hernández Puertocarrero)。波托卡雷羅回到西班牙后,瑪麗娜成了科爾特斯的情婦,為他育有一子。在運氣不佳的洪都拉斯遠征中,科爾特斯又把瑪麗娜轉手給了胡安·哈拉米略(Juan Jaramillo),以便回到西班牙后與社會地位更高的女子結婚(Díaz del Castillo, 1983; Greenblatt, 1991)。
作為科爾特斯的“口舌”和“耳朵”,瑪麗娜握有很大的權力,但人們對她的評價卻是褒貶不一,有人稱她為救世主,也有人視她為賣國賊(Greenblatt, 1991: 143)。墨西哥獨立后,瑪麗娜被指控為“雜種的娘、賣國賊”(Mirandé & Enríquez, 1979: 24),但是女權主義學者卻為她“正名”,以贊許的態度把她視為未來多元文化社會的先驅(Del Castillo,1977; Mirandé & Enríquez, 1979; Alarcón, 1981)。
在美國,薩卡加維亞是一位非常有名的人物。她在梅里韋瑟·劉易斯與威廉·克拉克的遠征隊中擔任翻譯。從1804年至1806年,遠征隊跋涉四千英里抵達太平洋。薩卡加維亞年幼時便被希達察族人(Hidatsa)掠走,后被賣給法裔加拿大翻譯、皮毛販子圖桑特·夏博諾(Toussaint Charbonneau)為妻(另一說法是賭博時贏取)。劉易斯與克拉克的遠征隊雇傭夏博諾為翻譯,薩卡加維亞也一同前往。她組織口譯員幫助遠征隊同內茲佩爾塞人(Nez Percés)等原住民交流,尤其在與自己的部族肖肖尼族(Shoshone)溝通時,發揮了極為重要的作用。肖肖尼部族為遠征隊提供了馬匹。劉易斯在日志中稱薩卡加維亞為“夏博諾的妻子”或者“臭娘們兒(squaw)”——后者在印第安阿爾貢金語中含有貶義,意為“妓女”,印第安人和白人用這個詞指代印第安婦女(Butter fi eld, 2010)。然而,劉易斯和克拉克對薩卡加維亞的多重身份變得越來越欣賞。薩卡加維亞不僅是遠征隊的語言、文化和地理向導,作為一名帶著孩子的婦女,她還是和平的象征,讓充滿敵意的印第安部族認為探險隊的使命是和平的。
史料顯示,薩卡加維亞于1812年患熱病去世。然而在一些記錄中,由于她被簡單地稱為“夏博諾的妻子”,而夏博諾又有好幾個妻子,因此很難確認死去的是否是她。另據其部族口述史顯示,薩卡加維亞最后又回到了自己的部族生活,于1884年在懷俄明州風河印第安人保護區去世。后一種說法經由懷俄明大學一位教授于1933年撰寫的傳記流傳開來,并隨著各地人們為她樹碑而廣為傳播(Butter fi eld, 2010)。薩卡加維亞的故事是一個關于口譯員的極端例子。她的身份和忠誠都有兩面性,甚至連生平都流傳著兩個不同的版本。
口譯是最有人情味的活動,是一種直接、即時、高度個人化的行為,需要譯員在不同個體間進行溝通,還要符合他們所處的文化位置的政治形勢。因此,口譯史必然會有很多問題懸而未決,這不僅是因為有關口譯過程的文字記錄匱乏,還因為口譯必然涉及意識形態沖突、忠誠的兩面性以及復雜的權力關系。
現有的書面及口頭資料盡管并不充分,但仍能幫助我們追溯歷史上口譯活動的蛛絲馬跡。在這一過程中不斷涌現的各種問題尚未得到完美的解答,特別是涉及年代更為久遠的問題時更是如此。不過同筆譯一樣,口譯在20世紀后期也羽翼漸豐,口譯職業的地位得以提升,從20世紀50年代起建立的各類口譯協會推動了口譯職業道德標準和專業準則的制定。此外,培訓課程、專業協會、研究出版、口譯史的撰寫等等舉措無不令作為藝術和科學的口譯得以進一步發展。過去二三十年間出現的文化轉向、后殖民轉向、權力轉向等翻譯理論研究也促成人們重新定位口譯的某些焦點問題,并對口譯復雜性有了更為深入的認識。
注釋
1. 關于參與紐倫堡審判口譯員的更多信息,請參閱Baigorri-Jalón(2004)一書第五章。
2. 關于建立口譯學校的信息來自1985版Guide des établissements proposant des cours en interprétation de conférence,國際會議口譯協會(AIIC)出版。在1993年11月的版本中,AIIC列了26所口譯學校。截至2004年,學校已增至178所。2011年后,這一數字有望繼續增加(www.aiic.net/schools)。據最新數據顯示,AIIC擁有來自101個國家2965位從事專業會議口譯的會員,涉及51種語言(www.aiic.net/database/,2011年11月訪問)。
3. 在眾多的研究方法中,“底層社會”的歷史以及關于庶民和后殖民的研究為移民和混合民族研究帶來了新的啟示。關于口譯員相關研究,可參見Karttunen(1994),Szasz(1994),Cronin(2002)和 Luca(1999, 2004)。
4. 其原名為Malinalli Tenépal,在洗禮時賜名“Marina(瑪麗娜)”。西班牙人出于對她貴族身份的尊重,尊稱她為“Do?a(夫人)”。科爾特斯的手下,甚至是科爾特斯本人,都未被尊稱為“Don(先生)”。印第安人則稱她為“Malintzin(瑪琳辛)”。這個名字是從“Marina”衍生而來的(墨西哥人不知道中間“r”這個音,便用“l”模仿其發音),名字中的后綴“-tzin”則是等級或貴族的標志。她喜歡這個和她主人名字一樣的特別稱呼,因為印第安人開始把科爾特斯的名字也稱作“Malintzin”。“Malintzin”在西班牙語中的對應稱呼是“Malinche”(瑪琳齊) (Madariaga, 1942: 151-152; Del Castillo, 1977: 146n)。
Alarcón, N. (1981). Chicana’s feminist literature: a re-vision through Malintzin / or Malintzin: Putting fl esh back on the object. In Anzaldúa, G. & Moraga, C. (Eds.),The bridge called my back: Writings by radical woman of color (pp.182-190).New York: Kitchen Table.
Baigorri-Jalón, J. (2004). De Paris à Nuremberg: naissance de l’interprétation de conference.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Barthel, M. (1982). Die jesuiten. Düsseldorf & Vienna: Econ Verlag.
Bonsal, S. (1946). Suitors and supplicants: The little nations at Versailles. New York:Prentice-Hall.
Butter fi eld, B. (2010). Sacagawea: From captive to expedition interpreter to great American legend. Retrieved Oct. 2011 fromhttp://www.bonniebutter fi eld.com/NativeAmericans.html
Conot, R. E. (1983). Justice at Nuremberg. New York: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Cronin, M. (2002). The empire talks back: Orality, heteronomy, and the cultural turn in interpretation studies. In Tymoczko, M. & Gentzler, E. (Eds.), Translation and power (pp. 45-62). Amherst & Bost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Delisle, J. (1990). Les alchimistes des langues: La Societe des traducteurs du Quebec, 1940-1990.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Delisle, J. & Woodsworth, J. (2012). Translators through histor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Del Castillo, A. R. (1977). Malintzin Tenépal: A preliminary look into a newperspective. In Sánchez, R. & Cruz, R. M. (Eds.), Essays on la Mujer (pp. 2-27).Los Angeles: Chicano Studies Center Publicatio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Díaz del Castillo, B. (1983). Historia Verdadera de la Conquista de la Nueva Espa?a. Mexico: Editorial Porrua S.A.
Dollmann, E. (1967). The interpreters, memoirs of Doktor Eugen Dollmann. London:Hutchinson.
Gardiner, A. H. (1969). Egyptian grammar, being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hieroglyphs (3rd ed.).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eenblatt, S. (1991). Marvelous possess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Herren, R. (1992). Do?a Marina, la Malinche. Barcelona: Planeta.
Hoffman, A. (2011). Need to talk to China? Go through him. The Globe and Mail(Toronto, Canada), August 27, pp. F6-7.
Karttunen, F. E. (1994). Between worlds: Interpreters, guides and survivor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Keynes, J. M. (1949). Two memoirs. (Dr. Melchior: A defeated enemy & my early beliefs) (2nd ed.). New York & London: Augustus M. Kelley & Rupert Hart-Davis.
Kurz, I. (1986). Dolmetschen im alten rom. Babel, 32 (4): 215-220.
Luca, F. X. (1999). Re-“interpreting” the role of the cultural broker in the conquest of La Florida. Retrieved Mar, 2011 fromhttp://www.kislakfoundation.org/prize/199901.html
Luca, F. X. (2004). Re-“interpreting” the conquest: European and Amerindian translators and go-betweens in the colonization of the Americas, 1492-1675(doctoral dissertation).
MacMillan, M. (2002). Paris 1919: 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 New York:Random House.
MacNutt, F. A. (Ed.). (1977). Fernando Cortes: His fi ve letters of relations to the emperor Charles V. Glorieta, NM: Rio Grande Press.
Madariaga, S. (1942). Hernan Cortés conqueror of Mexico. London: Hodder &Stoughton Ltd.
Madariaga, S. (1974). Morning without noon: Memoirs. Farnborough, England:Saxon House.
Mirandé, A. & Enríquez, E. (1979). La Chicana: The Mexican-American woman.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Morgan, H. W. (Ed.). (1965). Making peace with Spain: The diary of Whitelaw Reid,September-December 1898.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Riddell, G. (1933). Lord Riddell’s intimate diary of the peace conference and after,1918-1923. London: Victor Gollancz Ltd.
Roditi, é. (1978). How I became a conference interpreter. 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Roditi, é. (1982). Interpreting: Its history in a nutshell. Washington, D.C.:Georgetown University.
Roland, R. A. (1999). Interpreters as diplomats: A diplomatic history of the role of interpreters in world politics. Ottawa: University of Ottawa Press.
Satow, E. M. (1979). Guide to diplomatic practice. London: Longmans.
Seleskovitch, D. (1978). Interpreting for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Problems of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Washington, D.C.: Pen & Booth.
Szasz, M. C. (Ed.). (1994). Between Indian and white worlds: The cultural broker.Norman: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Van Hoof, H. (1962). Théorie et pratique de l’interprétation avec application particulière au fran?ais et à l’anglais. Munich: Max Hueber Verlag.
Vermeer, H. J. (1992). Skizzen zu einer geschichte der translation. Frankfurt/M.:Verlag für interkulturelle Kommunikation.
(責任編輯 蔣劍峰)
* 本成果獲北京語言大學校級科研項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專項資金)資助,項目編號為16HQ03。正文和注釋有刪節。
管興忠,博士,北京語言大學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翻譯學。
張思雨,北京語言大學高級翻譯學院研究生。
譯者電子信箱:管興忠guanxingzhong@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