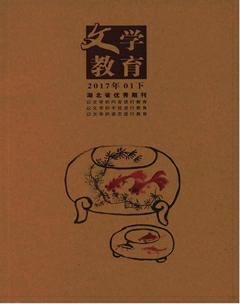法國文壇的風流才女喬治·桑
藍泰凱
喬治·桑(1804-1876年)是法國近代文學史上最出色的女作家之一,也是世界最著名的女作家之一。她文思敏捷,感情豐富,有著驚人的創作才能,以多產著稱于世。米雪爾·雷維版的《喬治·桑全集》就多達105卷,作品以小說為主,也有戲劇、散文、童話、政論及大量書簡。陀思妥耶夫斯基贊譽喬治·桑是一位“從精力和才華來說簡直是獨一無二”的作家。其文學成就使她毫無愧色地躋身于巴爾扎克、雨果、司湯達、福樓拜和左拉等一批享譽世界的偉大作家之林。然而,喬治·桑卻因個人的感情生活而受到時人的攻擊,后來也常被人非議,甚至把她說成是那種水性楊花的女人,其形象被嚴重毀損。
喬治·桑原名奧羅爾·杜邦,她的童年和成年后的婚姻都非常不幸。父親出身名門望族,是拿破侖帝國時期的一位高級軍官,在她4歲時墮馬而亡。母親出身微賤,是一個舞女。祖母是一個很有見識、但很專橫的貴族。母親一直為祖母所鄙視和不容。婆媳之間長期不和,難以相處,母親只得撇下幼小的女兒,離開諾昂,只身前往巴黎獨自謀生。奧羅爾從此便由祖母撫養。她在祖母的教育和指導下,學習拉丁文、音樂、繪畫和各種自然科學,表現出了驚人的稟賦。奧羅爾13歲那年,由于對母親的同情而遭到祖母的懲罰,把她送進了巴黎的修道院,在那里過了兩年多孤寂凄苦的生活。1820年2月,祖母由于年邁體虛,自覺不久人世,便把她接回昂諾。在修道院里,奧羅爾養成了勤學好思的習慣,并對文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所以一回到諾昂,便如饑似渴地讀書,從亞里斯多德、維吉爾、但丁到莎士比亞、拜倫、夏多布里昂,她都廣泛涉獵,尤其是盧梭的作品使她著迷。“盧梭對于自然的理解和崇拜,對于上帝的信仰,對于平等的信念和熱愛,對于所謂文明社會的藐視——這一切都和她的天性產生了共鳴,而且仿佛預先占有了沉睡在她靈魂里的各種感情”(勃蘭兌斯《法國的浪漫派》,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年,158。)。她成了盧梭的忠實信徒,從此在自由、平等、博愛的啟蒙思想的哺育下成長,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
奧羅爾16歲時,祖母去世。她繼承了豐厚的遺產,但她對財富卻十分淡然,而是把精力投入到閱讀大量書籍之中。1822年9月,也就是奧羅爾侶歲那年,她同卡西米爾·杜德望男爵結婚。杜德望是一個生活放蕩、荒淫無度、粗俗平庸,終日在外吃喝玩樂、事業上毫無進取之心、既不能理解妻子而又丈夫氣派十足的鄉村紳士,不久便把家產揮霍殆盡。這個俗不可耐的男人,正如海涅在《呂特莉亞》中所描繪的那樣,他“會使心靈深邃的女子不寒而栗,使她產生恐懼和逃走的愿望”。兩人由于志趣的不同,氣質的殊異,感情上漸漸有了隔閡,摩擦和爭吵不斷發生,終于使共同生活的基礎破壞無遺。奧羅爾決心從不幸的婚姻中解脫出來。1825年,她開始與杜德望分居(1835年正式離婚)。為了生計,她搞過翻譯,做過縫紉,畫過裝飾畫。她為此耗費了許多時間和精力,而且損傷了眼睛。然而,奧羅爾的志趣還是在寫作。她對自己的創作才能充滿信心,她說:“我善于分析人類的感情,刻畫某些人物的性格特點,熱愛大自然……我對于鄉野的風土人情有一種非常親切的感情。就憑著這些,我完全可以動手去創作。”1831年初,奧羅爾懷著這種強烈的愿望來到巴黎,開始了她的創作生涯。
1831年的巴黎,剛剛經歷了七月革命的風暴,摧毀了查理十世的專制統治,自由空氣十分活躍,喬裝改扮風靡一時。奧羅爾為了顯示自己的放任無羈,與眾不同,她身穿灰色粗呢哨卡式禮服,系著一條毛料大領帶,腳蹬一雙長筒靴,嘴上叼著煙斗,從巴黎的這一端走到另一端。她的“腳下踩著冰塊,肩上落滿雪花,雙手插在衣袋里,有時候肚子里還空空如也,但腦子里卻充滿了夢想、樂曲、色彩、人形、光明和幽靈”。
在巴黎,奧羅爾住在一間小閣樓里,生活十分清苦,經常饑腸轆轆。眼前的處境,對她來說最迫切的需要就是掙錢。恰恰在這最困難的時候,她認識了青年小說家于勒·桑多(1811-1883年),并與之產生了戀情,兩人合作寫了一部長篇小說《羅絲與布朗什》,作者署名為“于勒·桑”,于1831年12月在巴黎出版。當時凡是署有這個名字的書都相當暢銷,于是另一個出版商要求他們也用“于勒·桑”的署名再創作一部小說。奧羅爾拿出了早在諾昂寫好的《印典娜》。因這部小說純屬出自她一人的手筆,于勒·桑多拒絕分享這個勞動成果,不同意再署“于勒·桑”的名字。為了既照顧出版商的利益,也尊重于勒·桑多的意見,經過反復考慮,采取了一個折中的辦法,把“桑多”的“桑”字保留下來,以表示紀念此前兩人的合作;再起一個只屬于奧羅爾的名字。“喬治”好似“貝利人”(“貝利”是奧羅爾的家鄉)的同義詞。從此,“喬治·桑”的筆名便出現在法國的文壇上。
1833年8月,喬治·桑在一次宴會上結識了浪漫派詩人繆塞(1810-1857年)。繆塞的才華贏得大他6歲的喬治·桑的青睞。兩人的關系日漸親密,同年12月到意大利旅游。繆塞出身貴族之家,是父母的寵兒,嬌生慣養,生活放蕩,意志薄弱,尤其是他的懷疑和嫉妒使喬治·桑難以忍受,兩人的感情逐漸破裂,相處兩年多后終于分道揚鑣。1836年秋,在李斯特的音樂沙龍里,喬治·桑與波蘭作曲家肖邦(1810-1849年)相識。那時的喬治·桑已30多歲,是一個有兩個孩子、飽經滄桑的中年婦女。起初,肖邦對喬治·桑并無好感,認為她缺少女性誘人的姿色。但是,經過多次接觸之后,肖邦終于為喬治·桑的才情所征服。據安德烈·莫魯瓦的《喬治·桑傳》記載,肖邦曾多次寫信給喬治·桑,信中說:“奧羅爾,我愿拜倒在你的裙下,我愛你的一切,也愿把我的一切獻給你。”從此,彼此傾慕。從1837年開始同居,經常往返于巴黎和諾昂之間,形影不離,共同生活了10年之久。最后,因生活情趣、思想見解和政治原則的不同而于1848年3月徹底分手了。翌年5月,肖邦病逝。
此外,喬治·桑結識的男性朋友還有文學批評家圣·勃夫(1804-1869年)、布朗舍(1808-1857年)、思想家拉莫耐(1782-1854年)、空想社會主義者皮埃爾·勒魯(1797-1871年)、匈牙利作曲家李斯特(1811-1886年)等。喬治·桑同異性朋友頻繁無羈的交往如同走馬燈一樣,風流韻事時有傳聞。而且,在愛情觀念上,她敢于講真話,坦率地表白自己對靈與肉的需求。她說:“誰失去了心靈,誰就失去了一切,失身于人而保存了靈魂,這樣倒還好一些。”對于激情和本能的抑制或輕蔑,在她看來也是做作和虛偽的。她尖銳地指出,“如果只執著于精神愛,硬要把精神和肉體分離,其結果必然是建立修道院和妓院”。她甚至謳歌男女之歡是“世界上最神圣、最值得尊敬的事”,“是宇宙生活中最嚴肅、最崇高的行為”(郭珊寶《法國近代小說概觀》,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年,96.)。對于喬治·桑的上述種種言行,時人多有訾議和微詞,也遭到社會上千奇百怪的評說。一些西方評論家在談及喬治·桑的時候,避而不談這些男性朋友對她的思想和創作所產生的有益影響,以及她對他們的影響,而是過分夸大、渲染她的私生活的小節這一面,因而對喬治·桑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偏見。更有甚者,把喬治·桑貶損為“不規矩的女人”,辱罵她是“賣弄風情的壞女人”,等等。最為惡毒的是把肖邦的英年早逝歸咎于喬治·桑的縱欲所造成的。這些非議和中傷,嚴重毀損了喬治·桑的形象。為此,我國著名法國文學專家羅大岡教授在其《天生的小說家》中為喬治·桑鳴不平,他說,人們偏偏看不到喬治·桑“畢生最早的一個戀人是小說,最后一個戀人仍是小說。她的一生無數的戀人和情夫中,感情最純潔的戀人是小說”。
下面,讓我們來看看喬治·桑和她的朋友們是怎樣看待他們之間的交往的。喬治·桑說:“我結識了知識淵博的朋友,也聆聽了明智通達的勸戒”,“是我的朋友們把我帶進了一個感情的和精神的世界,這里才是我真正的生活史中的一個最基本的組成部分,也即是我的思想與智慧的發展過程。我深深地相信,我的心靈里之所以具有并保持著一點點好的東西,全是由于同其他人交往的結果。”事實也的確如此。于勒·桑多是她文學生涯中的第一個指導者,她從他那兒學到了一些寫作技巧。她愛過、也幫助過于勒·桑多。世人公論,“桑多的一切成就都應歸功于喬治·桑”。
在同繆塞的關系中,“這兩個天才在一場熱戀的升華過程中你影響了我,我也影響了你”,他們“是藝術天國里的亞當和夏娃。他們相遇了,共享了知識之樹的果實”。最后,雖然“他走他的路,她也走她的路。但他們已不再是從前的老樣子。他們現在產生的作品比起他們相遇以前產生的作品卻迥然不同了”(勃蘭兌斯《法國的浪漫派》,142)。事情正是這樣:喬治·桑的胸懷坦蕩、仁慈善良,以及對理想的熱烈追求,使繆塞變得誠實和成熟,摒棄了年輕時的浮華和幼稚的傲慢,成了一個熱情的青春的詩人。他在同喬治·桑分手后懷著感激的心情說道:“我愿為你修建一個祭壇,即使用我的骨頭……自豪吧!我偉大的、正直的喬治·桑,你把一個孩子變成為一個堂堂的男子漢。”這正是比他大6歲的喬治·桑的成熟氣質對他所產生的影響的結果。同時,喬治·桑也從繆塞的身上感染了男子漢的氣概,從此脫掉了她的男式服飾,還原了一個真正的女人。
在同肖邦相處的10年中,喬治·桑從這位偉大的音樂家身上汲取了許多美好的東西:
“他的高尚的性情,他的無私的胸懷,他的自豪感,當然還有他的傲慢,他厭惡一切低級趣味的虛榮心和所有的狂妄吹噓,他待人接物真誠可靠,為人處世精細周到。”所有這一切使他成為她“一個既嚴肅正經,又可親可愛的朋友”。肖邦的許多傳世之作,如《F小調狂想曲》、《波蘭狂想曲》、《F小調奏鳴曲》等,正是兩個天才所播下的愛情種子所結出的碩果。對此,肖邦也承認,是喬治·桑的才情引發了他的音樂創作的靈感,使他攀上了音樂創作的頂峰。肖邦體弱多病,喬治·桑總是“懷著深沉的母愛忠實地陪伴著他”,把他當做自己的“大孩子”一樣精心護理;在性生活上,她強制他節欲,甚至要他徹底禁欲,以利于他恢復健康,能夠集中精力從事創作。對于肖邦來說,喬治·桑可算得是“一位偉大的奉獻者”。肖邦逝世后,人們告訴她,“他一直到生命的最后時刻都在呼喚她,懷念她,而且像兒子對母親那樣對她充滿深情”。可見那種把肖邦的英年早逝歸咎于喬治·桑的縱欲所致完全是無稽之談和蓄意中傷。
毋庸諱言,喬治·桑并不是一個完人。作為一位熱烈追求自由的女性,她的某些言行,尤其是與眾多異性朋友不拘小節、過于頻繁的交往,在當時看起來確實有些驚世駭俗,背離世俗的傳統軌道,但她決不是傳說中的那種水性楊花的女人,而是一個懷有堅定信念的理想主義者。她的浪漫激情是從長期被壓抑的性格中進發出來的火花。正如她自己所說:“為了生活,我必須要有一個明確的、堅定的信念,即為某個人、某種東西而生存,或為某些人、某種思想而生存。我從童年時代起就自然而然產生了這種對于信念的需要,這是環境使然,也是感情不斷受到壓抑的結果。”而且,在喬治·桑的性格中,主要方面還是真誠坦率、明斷果敢、善良博愛,對弱小者的苦難和命運的深切關注和同情,以及對美好理想的孜孜不倦地追求。
晚年,喬治·桑在諾昂鄉間過著遠離塵囂的田園生活,仍然保持著樂觀的心態和創作熱情,完成了長達上百萬字的《我的生活史》等作品。1876年春,青少年時期患上的肝病、胃病復發,并日益惡化。同年6月8日清晨,喬治·桑在諾昂鄉間邸宅與世長辭,享年73歲。在諾昂,為她豎立了雕像,設立了“喬治·桑博物館”。喬治·桑的作品被列入法國進步文化遺產之列,一直為世界廣大讀者所喜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