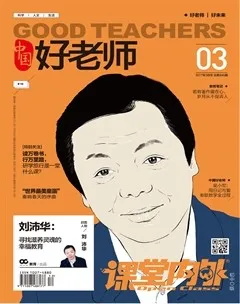別讓“假語文”來擾亂教學規(guī)律
教育部前新聞發(fā)言人王旭明和幾位志同道合者近年提出了“假語文”的概念。王旭明說:“從理論上來說,假語文就是違反語文教學規(guī)律的現(xiàn)象。”
《斑羚飛渡》是動物小說家沈石溪的小說。小說描寫一群被逼至絕境的斑羚,為了贏得種群的生存機會,用犧牲一半挽救另一半的方法擺脫困境。
網(wǎng)上有個語文教師講解《斑羚飛渡》的教學課件,印證了王旭明的說法。這個課件為“思考”做了這樣的定向:“從這群斑羚的身上,我們看到羚羊具有什么樣的精神?團結合作,舍己為人,自我犧牲,視死如歸。”這一課件接著又給“主題探討”作了這樣的導航:“面對種群的滅絕,這群進退維谷的斑羚有著一種為了種族的生存而甘于自我犧牲的崇高精神,它們的智慧、才能、膽識,特別是從容鎮(zhèn)定,舍己為人的情操,可貴的整體精神,為自己、也為人類唱響了一曲悲壯的生命贊歌,放射出燦爛無比的人生光彩。”
團結合作,舍己為人,自我犧牲,視死如歸,崇高精神,生命贊歌,燦爛無比,人生光彩……這種大而空泛的語言,一直循環(huán)重播于我們的耳際,已經(jīng)把我們的耳膜磨出繭來。從小學到大學,從課堂到社會,只要有“先進人物”和“英雄壯舉”出現(xiàn),幾乎都會有這些詞語與之對應。
《斑羚飛渡》所描述的斑羚“無私奉獻精神”是虛構的。作者也許為了“弘揚崇高精神”而設計了斑羚“舍己為人”的場景,這符合我們作家概念先行的創(chuàng)作特點。
實際上,無論是動物還是人物,還真有這種利他精神。英國生物社會學家道金斯在《自私的基因》的著作中,實證地研究考察生物行為的內(nèi)在驅力,他發(fā)現(xiàn)“自私的基因”并沒有道德意識。自然界中的利它行為,不能用簡單地用“奉獻精神”來歸納,而是涉及復雜的算計:在種群競爭中,那些具有群體意識和自我犧牲行為的群體,將更有競爭力。
而在我們許多人眼里,利他行為似乎毫無潛在的利己動機,一些好人好像都是“毫不利己,專門利人”的。這種排除任何利己算計來理解利他行為,在道金斯這樣的生物社會學家看來是膚淺的。
然而更為蒼白的是我們的教學語言。接受心理學告訴我們,空泛僵化的語言是最有效力的催眠藥。在單一的傳播環(huán)境中,這種催眠藥或許能起到誘導作用;但在多源的傳播環(huán)境里,語言催眠藥的唯一作用,是關閉人們的接受大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