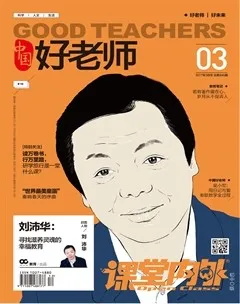語文是柔軟的
語文是什么?問題很大,答案也很多。
余秋雨先生在《我的文化山河》中寫道:“再宏偉的史詩也留不住,只剩下與之相關的無言山河。陸游說:‘細雨騎驢入劍門。’劍門是權力地圖的千古雄關,但消解它的,只是雨,只是驢。史詩也會變成文字存之于世。顧炎武說:‘常將《漢書》掛牛角。’煌煌漢代,也就這么晃蕩在牛角上了。那牛,正走在深秋黃昏的山道間。陸游、顧炎武他們在旅行中讓人間的大事變小、變軟、變輕,這頗合我意。歷史是山河鑄造的,連山河都可以隨腳而過,那歷史就更不在話下了。”
我恰恰以為這就是對“語文是什么”最好的解答。“劍門”“漢書”都是很政治、歷史的意象,可是“細雨騎驢”“牛角”卻將它們變成了很語文的意境。語文就是一門將“硬”的事物變柔軟的學科。
語文是柔軟的。既是強調語文學科的文學性,更是強調語文學科的思維性。一提到理科,就想到邏輯性、理性;而文科,特別是語文,一定會說是感性。說到感性,不少人就會對“語文的柔軟”產生抗拒心理,總以為感性是人性格的敏感,像林黛玉,動不動就哭。其實,語文的感性是語文學科的思維方式,不是性格心態。
語文的柔軟是思維的柔軟
語文的柔軟是一種思維的方式,是學語文的人必備的語文意識。
現實中,我們普通的表達是不夠語文的。例如,介紹重慶的火鍋,不夠語文的表達是這樣的:說到重慶,你一定會想到火鍋吧!火鍋現吃現燙,辣咸鮮;火鍋又分成麻辣鍋和鴛鴦鍋;典型的火鍋食材包括各種肉類、海鮮類、蔬菜類、豆制品類、菌菇類、蛋類制品等;重慶的火鍋店到處都是,品牌也很多,有小天鵝、德莊、劉一手等;到了重慶,不吃火鍋等于沒來重慶,我愛火鍋。雖然現實表達不完全相同,但表達效果是差不多的。這是介紹性的文字,不是很語文的文字。
可如果有語文意識的人來表達這段文字,他會想辦法把生硬的事物柔軟化。說到火鍋,他第一想到的是唐代白居易的《問劉十九》詩“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不是科普火鍋,而是把火鍋詩意化,火鍋是白居易的詩,是一種生活情趣。
他會這樣來表達火鍋:“自然而然,我喜歡上火鍋。上海人餐桌上潔凈小碟里的糕點印證著他們的精致;西北人粗糙的大瓷碗反映著他們的豪邁;山城人火辣辣的火鍋卻孕育著我們的溫情。那紅藍藍的灶爐上架著一口銀色的鍋,鍋里正歡笑地冒著泡泡,煙霧繚繞在火鍋店里,一群男人正光著膀子在喝酒,一群女人火紅的嘴唇正發出光亮,小孩的叫嚷聲、男人的劃拳聲、女人的瑯瑯笑聲,熱鬧得如同剛煮開的白水,一下鬧騰。這樣的世界雖然嘈雜,卻蘊含著溫情。在冰冷快節奏的城市里,生活得孤獨寂寞的我喜歡上了這種看似“粗魯”的吃飯方式,在這個不起眼的凡常之處,我找到了久違的情誼和家庭的溫馨。”
不是說哪種文字更高明,只是表達的目的有差異。當我們需要作文的時候,當我們需要很語文的時候,我們要能有足夠的意識來完成我們的表達。
語文的柔軟是視域的柔軟
語文是為了更好地表達。同樣的話題,因為語文視域的差異,而產生的表達效果是不同的。
朱自清先生的《荷塘月色》在結尾處引用了梁元帝的《采蓮賦》和南朝樂府的《西洲曲》,其妙處是使現實的荷塘月色一下從時間和空間上被拉遠、拉大了,仿佛人一下穿越了千年,在歷史和文學的某處,在荷塘邊聽采蓮的悠揚的歌,也許能聽出柳永《望海潮》里的味道,也許看到夢中的“江南”,使人回味無窮。朱自清先生的語文視域是極其廣袤的,當然,也更印證了語文的柔軟。
我的學生曾經寫過一個命題作文——《青青草色勝庭花》。命題的核心,是要寫清楚,普通的小草怎么就勝過、超過了嬌艷的庭花。絕大多數學生都是從贊美平凡的偉大處立意的,這當然可以,但正如路走的人多了,便略顯尋常了。獨有一個孩子,受到川端康成《花未眠》的影響,寫作視域上升到新的高度,從審美、尋美的角度來深化命題:人們都是渴望美的,都以為精心呵護那種植在庭院里的花就是得到了自然美,可直到有一天,來到了內蒙古的青青草原上,看到了那漫天的青青草色,體會到小草那“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精神,才發現了真正的自然美原來在這里。與大眾的立意相比,這樣的視域可以讓我們的表達更精彩,更有味道,更語文。
記得有這樣一個說法:同樣一棵樹,詩人看見,它是一首詩;畫家看見,它是一幅畫;歷史學家看見,它是一段歲月;生物學家看見,它是一門科學。
語文要有語文的視域。一個事物,在語文人的眼里,它應是柔軟的。
語文的柔軟是文字的柔軟
語文柔軟的基石是語言文字的柔軟。這是毋庸置疑的,因為這是語文學科最基本的要求。“語文教學要注重語言的積累、感悟和運用,注重基本技能的訓練,給學生打下扎實的語文基礎。同時要注重開發學生的創造潛能,促進學生的持續發展。”《語文課程標準》如是說。
當然,我們要特別注意文字的柔軟性。例如,“岑寂”和“寂靜”是一個意思,但“穿越岑寂的歷史碎片”就是比“穿越寂靜的歷史碎片”更有文學的味道;“斯”和“這”是一個意思,但“斯人獨憔悴”就是比“這個人很憔悴”更有文學的意境。
文字的柔軟還包含意象的柔軟。正如,讀流沙河先生的《就是那一只蟋蟀》,“想起雕竹做籠,想起呼燈籬落,想起月餅,想起桂花,想起滿腹珍珠的石榴果,想起故園飛黃葉,想起野塘剩殘荷,想起雁南飛,想起田間一堆堆的草垛”,這些柔軟的意象既勾起我們的情思,又將我們帶入到一個很中國很古典很意境的世界里。語文是應該這樣柔軟的。
語文是柔軟的,不是說語文只有柔軟,也不是說我們的性格要細膩敏感。語文的柔軟指的是思維,是視域,是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