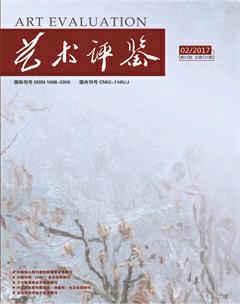隱喻的“流變”
張熙
摘要:耿占春先生在《隱喻的極限》一文指出,人類通過語言中“空間方位的隱喻” “物的隱喻”,以及“結構性活動的隱喻”來感知未知世界,這是隱喻的極限。本文從藝術史的角度進一步提出,早在語言誕生之前,人類就通過感官直覺的“隱喻”對未知世界展開想象,隨著人類時間觀念與空間觀念的轉變,這種直覺的“隱喻”方式發生了變化,這一變化直接體現在不同時期人類的藝術作品中。
關鍵詞:隱喻 極限 流變 時間 空間
中圖分類號:J0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8-3359(2017)03-0064-03
從藝術史的角度來看,隱喻沒有“極限”,隱喻在“流變”。
首先要明確的是,在耿占春先生及其著作中提到的“隱喻”是一種隱蔽的、人類直觀體驗與存在之間的類比關系,而非簡單的修辭學概念。耿先生將其大體歸納為“空間方位的隱喻”“物的隱喻”,以及“結構性活動的隱喻”。比如,“高”“低”原本是肉體對空間的知覺經驗,卻被人類用于觸知“高明”“高興”或者“低落”“低沉”等精神狀態;再比如,我們用進攻、防守、反擊等一系列屬于戰爭的詞匯來類比辯論、比賽等競爭機制。換句話說,相似體驗通過日常語言系統被人下意識的挪用并構建為個體衡量世界的尺度,從而據此設定出人與世界的關系。[1]
筆者認為,這個看似自洽的邏輯其實并不能涵蓋“隱喻”誕生以來的全部歷史。作為詩人的耿先生把注意力更多的集中在語言學的范疇,探求用“已知”類比并認識“未知”的隱喻的“極限”。但筆者認為,用感官體驗“隱喻”未知世界早在語言誕生之前就已經出現在人類的行為中,出現在如今被我們定義為藝術活動的表達系統里。
十幾萬年前繪制于阿爾塔米拉洞穴深處的公牛,且不管它究竟是獻給神的祭品還是對狩獵活動的祝禱,值得注意的是,尚未產生藝術自覺的原始先祖爬進極其狹窄曲折的洞穴繪制了這些圖像。這一行為本身,已經構成了藝術史閥域中的“隱喻”:對于原始人類來說,黑暗所帶來的恐怖、神秘、不可預測是切身的感官體驗,正如不可感知的“神”一樣,因此,與神的交流一定要發生并留存在漆黑的、人跡罕至的洞穴深處。這一邏輯同樣出現在幾百年前的閃族人中。繪制于南非龍山山脈懸崖峭壁上的大角斑羚究竟有什么含義尚待討論,但可以肯定的是,這些隱藏在常人難以企及的高度的圖像一定是對神秘力量的獻禮。因為對于閃族人來說,懸崖與神力同樣不可征服,所以與神的對話只能存在于目力難及的高處。
由此可見,在人類漫長的歷史進程中,“隱喻”是一個極其復雜的表達系統,它隨著諸多因素的影響而孕育出各種樣態。筆者認為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人類時間觀念和空間觀念的轉變。
一、時間觀念與空間觀念的轉變及相應的隱喻形式的流變
不管是古典社會還是現代社會,始終貫穿著時間和空間的概念,但人對二者的側重卻因時代的不同而大相徑庭:古典時期的人更習慣于空間性的隱喻,而現代社會則更傾向于時間性的隱喻。
在古典社會,生命被視作空間的存在,向上的靈魂和向下的肉體構成了信仰的兩元。生存就是靈魂引導肉身不斷趨向理想世界的過程。同時,時間作為一種節奏和循環,作為萬物生死、四季輪回的潛在規則,僅僅是一種大致的感覺。
近代以后,隨著宗教改革的世俗化、科學革命的標準化以及國家力量的增強。時間從古典時期模糊的節奏變成精準的、可以無限分割的線性計量單位。整個社會都圍繞著一種速度邏輯爭分奪秒的運轉,“時間焦慮”取代“上升的渴望”支配著人對自身的定位。這種時空觀念的變化影響著人的認知方式,也改變了“隱喻”的語法結構:
1.空間隱喻方式的轉變
隨著先驗的、自上而下、追求神性的層級秩序被近代開疆辟土的國家力量所取代,藝術語言出現了相應的變化。其中最為典型的是對透視法的祛魅和近代風景畫的興起。
為什么古典藝術對創造視錯覺的透視法有特別的鐘愛呢?其目的無關“像與不像”或“是否寫實”,而在于利用其錯視性打通現實空間與神圣空間,使其互為延展,使觀者能夠因立于畫前而真實的感受到來自神性的光輝。因此,《圣三位一體》《最后的晚餐》《創世紀》等古典作品中準確的透視關系和單純靜穆的古希臘雕塑、高聳入云的哥特式教堂具有相同的隱喻邏輯——通過視覺真實表達理念的真實,藝術手法作為一種“隱喻”,是兼具理念與表象的介質,是神與人相遇的場所,是精神超度肉身的階梯。
然而,隨著世俗欲望的膨脹,神圣信仰日漸稀薄。透視法被科學主義求真、求實的自然觀祛魅,淪為一種遵從于畫家個人意志的技法選擇。17世紀左右,在英雄主義的神話風景和阿卡迪亞的田園牧歌之外,一種為了滿足“土地想象”而專門制作的風景畫獨立出來:它可能是一處自然風光,同時悄悄的用畫面深處的古堡標明金主對畫中一切的所有權;也可能是一處人文景觀,同時用理想化的構圖勾勒出時人心目中城市秩序的藍本。總之,風景畫的“獨立”,隱喻了近代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中人們對土地空間,或者說“橫向”空間的渴望。正如今人所說,世界變成了“平的”。
2.時間隱喻方式的轉變
近代以來孕育出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比喻:時間就是金錢。“花了”“節省”“浪費”“剩余”等原本用于衡量金錢的詞匯被用以表現“時間”的珍貴性,這充分體現了利潤導向的工業化社會“用最短耗時獲取最大收益”的根本訴求。
那么,近代由資本驅使的時間機器對人的操控是如何隱喻在藝術表達中的呢?其統一的特點是,從表現對象到構圖方式的選擇,都呈現出一種難以被明確辨識的運動性。基于時間的動感文化傾向于描繪那些易逝的小景、易被遺忘的小人物。這種與時間的對陣并非濫觴自印象派藝術,而早在那些表現塵世歡愉的荷蘭風俗畫中就已初露端倪。即便是最為宏觀、壯美,最具歷史性的大教堂,在以時間為潛在導向的畫筆下,也只剩輪廓模糊的一瞥或軀體不全的一角。
反觀以空間隱喻為主導的古典藝術,平衡、明確、和諧、完整的靜力學原則被奉為終極法則。其中,最能體現這一審美傾向的是反復出現的金字塔構圖:將部分秩序化的匯聚于中心的支點,既滿足了有機統一的審美理想又符合了三位一體的神性召喚,堪稱古典美的典型范式。與此同時,作為敘事線索的時間被隱匿于空間之中,用以完成對情節的建構。以《最后的晚餐》為例,從耶穌宣布被出賣的消息,到各門徒做出反應,這樣一個時間性的段落被達·芬奇有序的排布于同一空間中,從而提示著觀者對潛在文本的記憶。
由此可見,在狹義的語言學范疇之外,基于時空觀念的“隱喻”以最為直觀的視覺形式呈現在不同時代的藝術作品中,與相應的藝術理念互相交織、互為因果。那么,這些暗藏于藝術語言背后的隱喻形式構成了哪些藝術風格的流變呢?筆者認為,宏大主題的缺失與自我意志的彰顯是現當代藝術與古典藝術的最大區別。
二、源自宏大命題的悲劇文化與源自精巧細節的快感文化
“悲劇”不等于“憂郁”,“快感”不等于“歡愉”。美學領域的“悲劇”往往通過其“悲劇性”而指向關乎命運的宏大主題;“快感”則通過其“感官性”指向關乎趣味的細節設置。通過前文對視覺隱喻形式的梳理可以發現,古典藝術更側重于借用宏大命題給背負原罪的人以靈魂的拷問,而近現代藝術更傾向于用精巧的細節設置帶給肉體感官以情緒的宣泄。
古典藝術崇尚一些經典的悲劇范式:俄狄浦斯逃不掉弒父娶母的命運悲劇,安提戈涅要直面城邦與家族沖突的社會悲劇,哈姆雷特要承擔糾結于生命價值的性格悲劇。不同的情節設定體現了肉身與理念在不同層面的遭遇,這種激蕩的碰撞在拉奧孔因痛苦而扭曲的肢體上、在賀拉斯兄弟立下誓言的瞬間、在布魯特斯忍痛放棄兒子和薩賓婦女決定挺身而出的時刻一再重現。藝術借此完成對人靈魂的凈化。
近代以后,隨著市場法則和商品關系的確立,以洛可可為代表的快感文化泛濫起來。它表現為通過精妙的細節設置來滿足人對趣味的需求:來自異域的裝飾紋樣、身著華服的自我扮演成為藝術的表現對象。曾經對經典范式的遵守在此時變為對“創新”的一味追求。對藝術概念的重構進行的如火如荼,能被公認的成果卻少之又少,藝術的概念被消解重構,以至越來越多的人相信藝術即將死亡。
從以悲劇的宏大命題隱喻神性追求的經典范式,到以消解經典來隱喻個人追求的當代范式,體現了不同時代人們對藝術的認識的轉變,這種轉變并不需要專門撰史記錄,它超越語言和文字,隱藏在不同時代人們的藝術選擇中。
三、從“光輝的流溢”到“意志的滿足”
古典藝術遵從于柏拉圖“光輝流溢”的美:神性、至善的“太一”流入混沌,使物質取得整一的形式。可見,美并非源自物體本身,而來自于至高無上的神。物質分享到神流溢出的理念而產生美。如前文所說,這種美體現為平衡、明確、和諧、完整,如同古希臘雕塑一般,不僅整體是美的,各部分也是美的。并且在其縱向層級中,精神之美要高于物質之美。
從文藝復興高揚人性、理性的旗幟開始,到18世紀的啟蒙運動,一套基于肉體經驗的對世界的理解方式被建立起來。比如,現代市場分析之父亞當·史密斯在《道德情感論》中就嘗試將美德和罪惡轉變為一種喜歡或抵制的情緒反應。這種將理性價值代入身體直覺的感官哲學,嘗試根據人的自身原則來確立意義的合法性[2]。
相應的,現代意義中的美也由自上而下的“流溢”變成了人對沖動和欲望的滿足,即叔本華所謂的“生命意志”的實現。如果說“流溢”指向“富足”,那么“欲望”則指向“匱乏”。“意志論”背后隱喻的是現代人特有的孤獨與無力。
因此,筆者認為我們應該關注隱喻的“流變”多于發掘它的“極限”,因為我們從來不缺乏對詞匯和語法的創新沖動,我們缺乏的是在整體視域下安置這種沖動,讓它棲居在肉身與靈魂的和諧統一中,并使其超越、飛升的能力。
參考文獻:
[1]星座學術文叢編委會編.流亡與棲居·星座學術文叢[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
[2][英]特里·伊格爾頓.美學意識形態[M].王杰,付德根,麥永雄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