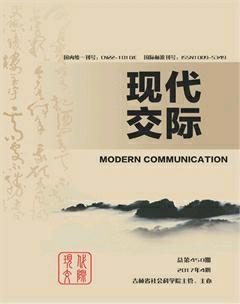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川籍女兵述論
楊友紅
摘要:在時局和社會背景、家庭背景、自身選擇等多方合力之下,四川一部分受過新式教育、有著進步思想的女青年于1926年考入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她們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其入伍經歷具有曲折性和迫切性,其主體意識強烈。她們為國民革命作出了巨大貢獻。研究其入伍經歷、探究其家國情懷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關鍵詞:川籍女兵 生平事跡 特點
中圖分類號:K26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9-5349(2017)04-0195-02
1926年,黃埔軍校武漢分校首招女生,各地女性爭相報名,錄取人數尤以兩湖、四川為甚。“女狀元”陳德蕓、“民族英雄”趙一曼、“廣州起義”的游曦、“民國少將”胡蘭畦等皆來自四川。關于黃埔女兵,學界早有關注,如,《大革命時代的黃埔女兵》《黃埔軍校武漢分校女生隊歷史真相述論》等,相關研究多側重對女兵事跡的敘述,但缺乏對女性從軍背景和特點的探討。本文在現有的文獻資料基礎上,以陳德蕓、胡蘭畦、游曦、趙一曼等川籍女兵為主要考察對象,分析其時代背景、敘述其生平事跡、總結其顯著特征和思想,以追憶黃埔女兵的家國情懷。
一、川籍女性從軍之時代語境
辛亥革命后,民智漸開,民族主義思潮十分活躍。川籍女性便在國民革命浪潮、新思想、婦女解放運動、急劇變遷的時局和社會背景等多重因素的合力下積極從軍,譜寫了女性從軍的華麗篇章。
(1)國民革命發展的需要。國共合作前夕,孫中山公開承認:“俄國革命六年,其成績既如此偉大;吾國革命十二余年,成績無甚可述”[1],關鍵在于黨缺乏組織,缺少革命精神和鞏固基礎。鑒于此,孫中山決定效法俄人,以黨治國,吸納共產黨人,擴大群眾影響,遂接受了共產國際代表“容共”的建議。最終,在各方合力下,國民黨于1924年召開了“一大”,確立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并改組國民黨,國共合作開始。是年五月,即創辦了“親愛精誠”的“黃埔軍校”,以“創造革命軍,來挽救中國的危亡”[2]。無疑,國共合作伊始,軍隊的政工干部、宣傳人員稀缺。隨著國民革命的推進,各地黨、政、軍紛紛要求派政工人員,開展工運和農運,發展群眾,指導軍隊,尤以北伐后為甚。可見,政工干部、宣傳人員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國民革命的發展,同時,國民革命的發展又為擅長開展工農運動等政工宣傳的女性從軍創造了條件。
(2)新思想、婦女解放運動的推動。隨著民族主義的高漲,西方女權學說、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李大釗、陳獨秀等一批致力于婦女解放的志士投身民族解放運動。他們在開展工人等群眾運的同時,積極宣傳婦女解放思想。吳玉章、惲代英等進一步在川內利用《新青年》《女界鐘》等革命刊物強烈抨擊封建綱常禮教,傳播女性解放思想,使得一部分女性認識到要取得經濟的獨立女性就必須拿起武器推翻舊制度。1925年3月,《中國軍人》刊發了《軍人與婦女》一文,指出打倒列強軍閥“匹婦亦有責”,女性應“其速武裝完成國民革命,以追取應得之平等自由,以洗女界之舊污,發揚女權,以追求人類最高之幸福”[3]。這些思想引領越來越多的女士投身于革命運動中,使“女子從軍”和“男女同校”的呼聲愈烈。1920年代,婦女解放運動早已融入民族革命運動之中,婦女參與社會政治生活的訴求已勢不可擋。
(3)政局變動等其他原因的影響。1926年7月,國民革命軍北伐,10月10日,攻克武昌,16日即開始籌備武漢分校,10月22日,蔣介石致電張靜江、譚延闿,力主遷都武漢。[4]隨著北伐的順利進行,女子從軍的呼聲已達到空前的高度。1926年11月2日,蔣介石電請中央黨部政治會議將本校政治科移設武昌,并女生百名。同時,為限制蔣集權,國民黨左派領袖和鮑羅廷等共產黨人于1926年11月中旬先行前往武漢召開臨時聯席會議,改選了黨政軍領導機制,強調維護“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政策[5],譚平山、吳玉章、林伯渠等共產黨人再度進入黨政領導核心。此時,劉湘鑒于形勢,宣布易幟,支持北伐。隨即,《新蜀報》登載了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武漢分校招取第六期政治科女學生的通知。
(4)此外,家學氛圍、家庭民族氣節和親友思想的熏染,敢于和舊思想決裂的勇氣與刻苦學習的精神也是重要的原因。她們多從小喜讀《木蘭辭》等愛國的詩歌,這既為其打下進入女子高校的基礎,又煉造了其堅韌的性格與不屈的精神。她們或是重慶女二師、川南師范、重慶中法大學等女子高校的佼佼者,或是已經開展革命運動的現今知識分子,在其求學過程中全都主動或被動地受到先進知識分子的引導。
二、川籍女兵生平事跡簡述
1927年年初,30名川籍女生通過初試,乘劉湘所包招商局“其春”號客輪沿江東下,經萬縣于云陽靠岸,游覽張飛廟,齊誦諸葛亮的《出師表》以明志。船到宜昌,換乘“快利”號輪順利到達武漢。后在武昌兩湖書院進行復試。其中,陳德蕓、趙一曼、游曦、胡蘭畦四人頗具代表性。
(1)“女狀元”陳德蕓。陳德蕓(1908—1985),四川涪陵人。1924年8月,考入重慶女二師。在蕭楚女等人的影響下,參加學生運動,并于1925年由游曦介紹入團。1926年12月,更名為陳德蕓,報考“黃埔軍校”,以“女狀元”身份進入武漢分校。其間經惲代英介紹,與武漢軍事委員會作戰科副科長劉騫相識,結下良緣。[6]寧漢分裂后,隨夫居南京,多次以國民政府高級將領眷屬的身份掩護共產黨人和民主人士,并勸導丈夫投誠。新中國成立后,陳德蕓在家義務參加掃盲教育工作,服務社會,彰顯其軍人的品質。1985年9月13日,病卒于成都。[7]
(2)民國少將胡蘭畦。胡蘭畦(1901—1994),出生于四川成都北門內醬園公所街一戶頗負名望的“反清世家”。1925年3月,與陳夢云結婚。次年3月,隨夫前往廣州,結識了周恩來、何香凝等人,旋入中央黨部婦女部工作。1926年秋,回川領導婦女運動,組織成立了合川婦女聯合會。不久,考入黃埔軍校。1929年,胡蘭畦被蔣介石點名驅逐,先后前往德國、蘇聯。1936年回國后,擔任何香凝的政治秘書。[8]抗戰期間,任上海戰地服務團團長和軍委會的少將指導員。后曾一度被劃為“右派”。平反后,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四川省政協常委、中國作家協會會員,1981年受聘為四川省文史研究館館員。1994年在北京結束了她曲折、幽遠、坎坷的一生。
(3)“廣州起義”的游曦。游曦(1908—1927),原名游傳玉,四川巴縣人,家境貧寒,父母靠織土布、毛巾為生。1922年秋,考入重慶女二師,次年6月,因深受蕭楚女其啟發,積極投身社會活動,并加入共青團,改名游曦。1925年冬,轉入重慶中法大學,不久即轉為中共黨員,并擔任黨支部委員和中法大學共青團支部書記。1926年年初,投身婦女解放運動,籌備成立重慶市婦聯。期間,曾創辦磁器口女校,并建立了工會組織。[9]1926年,游曦考入黃埔軍校,并積極從事革命活動。次年5月,隨軍西征,出色完成各種任務。“七一五”事件后,游曦遵照黨的指示,團結了鄭梅仙、廖德璋等30多位女同志留在教導團,隨軍南下并參加了“廣州起義”。后因與部隊失去聯系,不及撤退而壯烈犧牲,年僅19歲。
(4)民族英雄趙一曼。趙一曼(1905—1936),四川宜賓人。趙一曼在姐夫鄭佑之的幫助下,于1923年冬加入共青團。1926年冬,進入黃埔軍校。次年春轉為黨員,積極開展農民運動。“四一二”事件后隨軍西征。“七一五”事件后,被派往蘇聯學習,并與陳邦達相戀、結婚。回國后,先后在宜昌、哈爾濱等地從事黨的地下工作,并擔任東北抗日聯軍第三軍第二團政委,于1936年8月被捕就義。其一生恰如其詩《濱江抒懷》所言:“誓志為國不為家,涉江渡海走天涯。男兒豈是全都好,女子緣何分外差?一世忠貞興故國,滿腔熱血沃中華。白山黑水除敵寇,笑看旌旗紅似花!”
從進入軍校到同年七月女生隊提前畢業,黃埔女兵們既接受政治軍事訓練又參與社會政治活動,歷經反帝,反蔣,西征夏斗寅、楊森等重大事件。“七一五”事件后,武漢國共分裂,除少數國民黨右派外,她們或如游曦堅持隨軍作戰,或如陳德蕓回鄉組織工運、農運等革命活動,或如趙一曼被派到蘇聯等國外繼續學習、斗爭,或如胡蘭畦留在白區從事革命斗爭。雖選擇各異,但無疑的是,軍校的學習煉造了她們不怕苦累的精神,堅定了她們的信仰,升華了她們的家國情懷。
三、川籍女性從軍的特點
(1)要求迫切,過程曲折,信仰堅定。在民國初年社會封建勢力仍很強大的背景下,女子上學、從軍無不體現與舊社會決裂的決心和勇氣,無不體現過程的艱苦曲折。四川籍女兵從軍無不表現出立刻實現男女平等、民族解放的心理。在遭受挫折時,甚至用性命來證明與詮釋。在當時,若“學校不認其是學生”而被送回,家庭亦不認其為女兒。[10]據載,到武漢復試的30名四川籍女生中有二人落榜,其一名為柯銀珠的女生,因落榜而氣死,其憂世激憤,可以想見。女性解放運動的過程是艱難曲折的,身在其中的她們所受苦痛更甚。她們敢于突破舊有綱常,追求平等、自由、民主,不畏艱難困苦和堅定理想信念的精神品質當為今人品鑒。
(2)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把個人的命運與團隊、組織、國家,乃至世界的命運連結,具有強烈的家國情懷是其最為突出的特點。愛情作為生命的重要部分,因志趣相異、革命斗爭需要成為特殊時代的獨特記憶。1923年6月,蕭楚女到游曦所在的重慶女二師任教,二人成為了革命情侶。最終,他們的英骨在珠江找到了歸宿,得以相聚。作為“女狀元”的陳德蕓,經惲代英介紹與時任武漢軍委會的軍官劉騫結成伉儷,并多次以國民黨高級將領家屬為名保護革命志士,還為四川和平解放作了相當的貢獻。趙一曼與陳邦達相戀,后經組織批準,舉行了婚禮,但因革命的需要,二人卻常年分隔兩地。尤值一提的是,1938年初,胡蘭畦率領服務團來到南昌與十年未見的陳毅定下了白首之盟,后陳毅又致信胡蘭畦說:“馬革裹尸是壯烈犧牲;從容就義是沉默犧牲,為了革命,我們就吃下這杯苦酒吧。假如我們三年內不能結合,就各人自由,互不干涉。”后因革命形勢的變化,二人最終未能走在一起。無疑,當她們了解到婦女壓迫的根源是社會制度后,其潛在的民族氣節便顯現出來,為個人或女性的權利,民族、國家、世界的解放和發展而獻身。
(3)具有強烈的主動性。她們并不是在民族解放的浪潮中作為被賦予、被解放的對象,相反,她們一直在積極主動探索和追求自身、他人和國家的解放和發展,極具擔當精神和責任意識。她們主動向先進的知識分子、集體和組織靠攏,有強烈的自我意識和權利意識逐漸,她們既順應著婦女、民族解放的潮流,又主動推動著婦女、民族的解放運動。無論是在女校、軍校還是日后的革命中,她們都主動地跟上革命潮流,并推動著婦女、民族的解放,影響著一代又一代的后來人。
誠然,正是在家庭背景、時局和社會背景、個人品質追求等多方歷史與現實合力之下,鑄就了這樣一批有著強烈的家國情懷、主體意識且經歷很是曲折的巾幗英雄。可以看到,從巴蜀之地到夢寐武漢再到大江南北,最后天上人間,陳德蕓、胡蘭畦、游曦、趙一曼等黃埔學子歷家國之難、流離之苦,而民族氣節不喪,理想信仰不改,著實難能可貴。這些精神不僅僅是歷史的記憶,更是歷史的傳承。她們所崇尚的精神、所代表的文化、所堅持的信仰是整個國家整個民族永不該消失的傳承。逝者雖逝,精神猶存。
參考文獻:
[1]楊奎松.國名黨的“聯共”與“反共”[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8:25.
[2]陳以沛等.黃埔軍校史料[M].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4:47.
[3]洪筠.軍人與婦女[J].中國軍人,1925(3).
[4]楊天石.關于孫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J].近代史研究,2000(1).
[5]張武.國民政府遷都武漢[J].武漢建設,2014(6).
[6]陳德蕓.回憶黃埔軍校武漢分校與趙一曼烈士[J].武漢文史資料,1983(6).
[7]劉運勇.白云山房叢稿[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1:273.
[8]胡蘭畦.胡蘭畦回憶錄[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273.
[9]尹凌.游曦與磁器口女校[J].紅巖春秋,2002(5).
[10]謝冰瑩著.一個女兵的自傳[M].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13:89.
責任編輯:楊國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