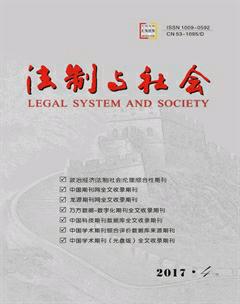論保護優先原則的理論基礎
摘 要 保護優先原則作為環境法基本原則于2014年寫入新《環境保護法》,但新法并未對該原則給予進一步明示,也未有官方解釋出臺。本文對該原則的理論基礎進行了論述,認為可持續發展、環境權、環境正義及環境倫理分別是該原則的社會目標基礎、公民權利基礎、法律價值基礎及環境道德基礎,希冀為該原則的進一步研究奠定理論基礎。
關鍵詞 保護優先 環境權 環境正義 環境倫理
作者簡介:苗振華,黑龍江大學法學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環境法。
中圖分類號:D922.6 文獻標識碼: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7.04.273
2014年新修訂的《環保法》(2014)第五條確立了環境法的基本原則,其中之一即為保護優先原則,這是新中國成立后我國環境立法上首次將基本原則以條文形式明確規定在環境保護領域的基本法中 。環境法基本原則是人類在處理環境問題時的所產生和發展的,它以自然生態規律及人類社會秩序為基礎,以人類社會的可持續發展為實現目標,保護優先原則作為環境法的基本原則之一,其產生必然需要一定的理論基礎作為支撐,現作如下分析。
一、社會目標基礎——可持續發展
發展是人類社會前進的方向,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 ED)于1987年向聯合國大會提交了《我們共同的未來》研究報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 。1992年在里約熱內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大會重申了1972年6月16日在斯德哥爾摩通過的《人類環境宣言》,通過了《里約環境與發展宣言》和《21世紀議程》,前者是進行全球環境與發展領域合作的框架性文件,后者是全球范圍開展可持續發展的行動計劃,各國政府代表在此簽署了包括聯合國《氣候變化發框架公約》在內的一系列國際文件與公約,對可持續發展給予了極大的關注與承認。隨后,我國于1994年7月發布了《中國21世紀議程》,是我國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的行動綱領。可持續發展是從環境與資源的角度,提出了人類長期發展的戰略模式,它涉及經濟、社會、文化、技術及環境等人類社會發展的多個方面。可持續發展鼓勵經濟增長,維持資源環境的永續利用及良好的生態,其發展目標是促進社會的全面進步。
2001年7月1 日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同志在“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八十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上指出,在處理經濟發展同人口、資源、環境的關系時,要堅持實施可持續發展戰略 。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屆三中全會在《中共中央關于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中確定了科學發展觀的概念 。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志于2004年3月在“中央人口資源環境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中進一步明確了科學發展觀的深刻內涵,就是要可持續的發展 。從中可見,科學發展觀就是可持續發展在中國的進一步闡釋,增加了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內涵 ,其關注的范圍與可持續發展的范圍一致,涉及環境、經濟與人類社會發展等方面。
2007年10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錦濤同志在中共十七大的報告中提出,將生態文明建設 作為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斗目標的要求之一,并要求全社會應當牢固樹立生態文明觀。在隨后的中共十七屆四中、五中、六中全會上均提出了生態文明建設的要求。2012年11月的中共十八大報告提出要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要求,提出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等五位一體建設的總體布局,……把生態文明建設放在突出地位,將其融入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各方面建設的全過程,建設美麗中國,從而實現中華民族永續發展 。可見,生態文明建設的目的就是實現環境資源的可持續發展,是科學發展觀或可持續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
根據《環保法》(2014)第一條的規定,“保護和改善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就是為了“生態文明建設”,為了實現環境領域的可持續發展,而環境領域的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就是“促進經濟與社會的可持續發展”,這是由環境資源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所決定的。因此,保護優先原則作為環境法的基本原則之一,通過保障環境資源可持續的實現,從而最終達到保障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目標。
二、公民權利基礎——環境權
對環境權問題的探討始于1960年聯邦德國一位醫生提出的有關“原子廢物拋入北海”的案件 。隨后,有關環境權的理論問題便在美國和日本迅速展開了研究。1982年蔡守秋老師發表的《環境權初探》,開啟了我國對環境權理論研究的熱潮,涉及環境權的性質、主體、客體、內容等方面,大體形成了三個研究流派,即廣義環境權論、公民環境權論和狹義環境權論 ,但并沒有形成一致的認識。從國內外的司法實踐來看,不管法律對環境權有無規定,法院幾乎都否認了環境權可以作為提起訴訟的請求權。
故此,有必要從環境權的客體來重新認識環境權。從《環保法》(2014)第二條對環境所下的定義可知,環境要素作為環境法保護的對象是用來保障人類生存和發展的物質基礎,因此,人類為了生存和發展有從各環境要素中獲取利益以維持生命并進一步發展的權利。可以認為,環境權是公民為了生存和發展而享有環境利益的權利。從環境權的行使來看,對環境利益的享有一旦完成,便完成了對環境利益的擁有,但享有并不等同于民法上對物行使的所有權,因為公民個人對環境利益的享有并不包括占有、收益、處分這些屬于所有權的權能。《憲法》(2004)第九條規定了自然資源的全民所有權(即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權。這就否認了公民個人對自然資源的所有權,但這并不妨礙公民個人基于生存與發展而享有的從這些非公民個人所有的自然資源中獲取其所產生的環境利益。可以說公民不必基于所有權便可享有環境權。同時,《憲法》(2004)在第二十六條規定了國家在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生態環境及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等方面的義務或職權,這便賦予了公民獲取環境利益的權利,而環境利益就表現為良好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另外,對于作為環境要素的自然資源本身的利用,則應當由物權法的相關規定去調整。根據憲法基本權利主要是公民個人針對公權力(如國家)所享有的權利這一特征,可以將環境權歸為憲法中公民的基本權利范圍內,這樣便使得國家的環保義務有了權利的來源 ,同時也與《憲法》(2004)第二十六條構成了權利義務理論邏輯上的閉合。另外,作為環境權所保護的環境利益本身具有豐富的內容,如果對某一環境利益的享有受到妨礙,就以具有復合性特征的環境權受侵害為起訴理由,就會顯得起訴理由不具體、含混模糊,導致法院無法對被侵害的具體利益進行認定并予以保護。當然作為憲法基本權利的環境權所含的各單項環境利益的享有權應當由具體的部門法予以保護,但由于環境利益的內容豐富且對部分環境利益的享有所需達到的保護程度不好界定,使得部門法對相關環境利益的保護缺失,這一問題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以解決環境權的保護問題。
環境權所保護的環境利益是公民個人生存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作為憲法基本權利的環境權除了為國家設定環境保護的義務外,也為相關環境立法提供了依據。因此,具有憲法基本權利的環境權是環境基法中保護優先原則的權利基礎。
三、法律價值基礎——環境正義
正義是社會制度的首要價值 。所謂正義就是以平等對待平等的人們,其現實要求同等情況同等對待 。環境正義產生于20世紀80年代美國北卡羅萊納州的華倫郡事件 所導致的環境運動,該運動主要表現了公眾對環境負擔分配問題的抗議,反應了人與人之間社會關系的失調,這同時也是環境問題惡化的重要原因。美國環境保護署(EPA)認為環境正義就是指在環境法律、法規和政策的制定、貫徹和實施等方面,全體公民無論種族、膚色、民族和收入的差異,都應當得到公平的對待和有效的參與 。有學者認為,環境正義是指在環保領域,在分配環境保護成果、環境風險和負擔的承擔時,法律和執行法律的政府應當無歧視地對待每一位公民或群體 。因此,從環境正義問題的產生及其相關定義來看,環境正義強調的是環境利益與環境負擔的公平分配問題。可見主張環境正義的主體是人,而環境正義所分配的對象是環境利益和環境負擔。因此,從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環境正義問題涉及代內正義與代際正義,而從代內正義看,環境正義又涉及不同地區的環境利益與負擔的分配。
在代內正義中,強調環境利益與環境負擔在全體公民或群體之間平等的分配,當弱勢群體的環境利益與強勢群體 的環境利益發生沖突時,應當優先保護弱勢群體的環境利益,與此相對的是,應當給強勢群體分配更多的環境負擔,以保護弱勢群體的所享有的環境利益,達到雙方公平分配環境利益與環境負擔的狀態。同時,既要實現本國范圍內不同地區的環境正義,又要實現國際范圍內不同國家之間的環境正義。國內環境正義主要涉及因種族、民族、收入、地域等因素而引起的環境公正問題。國際上的環境正義涉及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環境資源的超低價購買或以其他方式進行的不符合該環境資源應有價值的占有。在代際正義中,就是關涉當代人與后代人之間對于環境利益與環境負擔的公平分配問題,這更多關注的是人類自身的可持續發展。當代人在享有環境利益的同時,必須相應地承擔保護環境的義務,以此來保證后代人對良好環境利益的享有權。
權利理論要求一個社會中的所有人都必須得到同等的關心和對待,使所有的人都必須成為政治社會的真正平等的成員 。故此,在通過行使環境權而享有環境利益的同時,應當充分考慮代內成員的環境利益與環境負擔的分配及代際之間的分配,以保證環境法所保護的環境利益能夠公平分配,并永續利用,使得社會的所有成員都能平等的享有環境權。保護優先原則作為環境法的基本原則,其作用就是通過保障公民公平且可持續的享有環境利益,來保護公民環境權的實現。在此意義上,可以說環境正義作為環境法的價值基礎,同樣也是保護優先原則所追求的價值。另外,有學者認為環境正義還包括人與自然之間的環境正義 或種際公平 ,但從法律的調整對象角度來說,法律調整的是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環境正義作為法律所追求的價值,此處的環境正義不應當包括人與自然之間的環境利益與環境負擔的分配,而這只能屬于環境倫理方面的問題。
四、環境道德基礎——環境倫理
20世紀中期,由于新工業革命的興起,環境問題成為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面臨的社會問題,但到20世紀后期,由于國際經濟往來密切,使環境問題演變為全球性問題,引發了人們對人與自然關系的反思,環境倫理學也隨之產生并發展。環境問題的本質是人與環境關系的失調 ,環境法作為平衡這種失調的重要手段之一,如果缺乏環境倫理道德的支持,則將不可能實現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最終目標。環境倫理學的發展經歷了從“人類中心主義”到“生態中心主義”的發展過程。
傳統的“人類中心主義”與近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治地位的確立有很大關系,其核心論點就是征服自然、主宰自然,擺脫自然對人的奴役 。在這種環境倫理觀念的指引下,人類毫無節制的利用環境資源,使得自然資源日益枯竭和環境問題不斷惡化。隨后這種不惜以犧牲環境為代價來換取人類幸福的環境倫理觀念受到質疑挑戰,使與之觀念相反的“生態中心主義”倫理觀應運而生。生態中心主義一種整體主義倫理學,將倫理關懷的范圍從人類擴展至整個生態系統、自然過程以及其他自然存在物 。生態中心主義以奧爾多·利奧波德的土地倫理學、阿恩·納斯的深層生態學、羅爾斯頓的自然價值論等角度闡述了把道德義務擴展至整個地球的理由。然而生態中心主義僅從“純自然主義”的角度關注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而忽視了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以及人的主體性質,這不利于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實現。因此,為了防止絕對的“生態中心主義”傾向,有學者提出了一種新型人類中心主義,即生態人類中心主義,它是對傳統“人類中心主義”進行批判的基礎上,堅持以人為人,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新人類中心主義。可以說生態人類中心主義包含兩個方面:一是以人的生存與發展為目的,二是為了這個目的的實現而堅持生態中心主義中所強調的人與自然作為整體的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