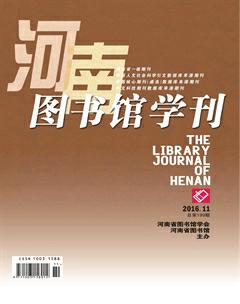從古今圖書分類目錄(法)列類沿革探“儒家文化”之地位
馬光華 王淼 李莉 孫玉玲
關(guān)鍵詞:漢未央宮;獨(dú)尊儒術(shù);《七略》;《直齋書錄解題》;“語(yǔ)孟類”;儒家文化;“列于首”
摘要:文章探討了“四書五經(jīng)”在分類目錄中的列類沿革,宋代產(chǎn)生雛形:二書——“語(yǔ)孟類”;明代“四書”成型:“四書類”;到清代成了名正的“四書五經(jīng)”:“四書類”“五經(jīng)總義類”;當(dāng)代的《中圖法》中,“四書”依然保持:“儒家”——“四書”“孔子”(“五經(jīng)”已各入其類)。應(yīng)當(dāng)說(shuō),“五經(jīng)”在我國(guó)第一部分類目錄《七略》中已列在“六藝略”中,此乃目錄學(xué)、分類學(xué)史上的又一新觀點(diǎn)。
從西漢劉向、劉歆父子所著《別錄》《七略》之“六分法”到《中經(jīng)新簿》《隋書經(jīng)籍志》等,又到清代的“四庫(kù)全書總目”之“四分法”之目錄,經(jīng)筆者閱讀及研究后認(rèn)為:第一,這些分類目錄始終起著目錄及分類法的兩種作用。“分類法在我國(guó)有著悠久的歷史。還在公元前7年的時(shí)候,我國(guó)就有了第一部分類法即劉歆的《七略》”。第二,從西漢之《七略》,直到清朝的《四庫(kù)全書總目》,一直延續(xù)到今天的國(guó)家標(biāo)準(zhǔn)(GB)《中圖法》,始終把儒家文化(孔子及其弟子之著作及研究)“列為首”或“單獨(dú)列類”,將“儒家文化及孔子研究”“列為首”源于漢武帝的“獨(dú)尊儒術(shù)”之治國(guó)思想。“我國(guó)古代的書目是在封建社會(huì)中產(chǎn)生的,它們都是以儒家思想作為指導(dǎo)的學(xué)術(shù)文化的反映”。筆者認(rèn)為:我國(guó)的圖書目錄及分類發(fā)展史,也是一部文化史及學(xué)術(shù)史。筆者探討了“四書五經(jīng)”在分類目錄中的列類沿革:宋代產(chǎn)生雛形:二書——“語(yǔ)孟類”;到清代成了名正的“四書五經(jīng)”:“四書類”“五經(jīng)總義類”,此乃目錄學(xué)、分類學(xué)史上又一新觀點(diǎn);民國(guó)以后,也始終將“儒家文化及孔子研究”單獨(dú)列類,且當(dāng)代國(guó)標(biāo)(GB)《中圖法》中,依然保持了“B222.1四書”類,“五經(jīng)”已各人其類。下面分別對(duì)若干個(gè)時(shí)代的典型分類目錄(法)進(jìn)行探討、論述。
1.漢未央宮承明殿:“獨(dú)尊儒術(shù)”的提出與最終實(shí)施
1.1“獨(dú)尊儒術(shù)”的提出
西漢政權(quán)建立后,采取了“與民休息”的政策,從皇帝到太后及諸大臣,信奉“黃老之學(xué)”,推崇道家文化,出現(xiàn)了“文景之治”。漢武帝執(zhí)政后,為強(qiáng)化思想統(tǒng)治,征集各類治國(guó)方略及思想。董仲舒(公元前179-前104)在未央宮向皇帝提出了“獨(dú)尊儒術(shù)”。“未央宮……正殿前修了一座承明殿,……殿左側(cè),站著幾個(gè)書生模樣的年輕人和一位四十歲左右的中年人,這中年人就是名揚(yáng)天下的大儒——董仲舒。……董仲舒環(huán)視了一下四周的大臣,提高了嗓門說(shuō):依愚民之見(jiàn),要統(tǒng)一全國(guó)人民的思想必須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
1.2尊崇“道學(xué)”與“儒學(xué)”之爭(zhēng),“獨(dú)尊儒術(shù)”的艱難實(shí)施
侯外廬先生認(rèn)為:尊崇“道學(xué)”與“儒學(xué)”存在著一個(gè)先后且斗爭(zhēng)的過(guò)程,“獨(dú)尊儒術(shù)”被漢武帝采納后,并非一帆風(fēng)順,盡管最終被實(shí)施,但歷經(jīng)周折:“在漢初文景武三世,儒道爭(zhēng)霸相當(dāng)厲害,……文景雖立博士,但并不甚好儒,……直到武帝初,和竇太后斗爭(zhēng),……立出法度,所謂‘天下靡然鄉(xiāng)風(fēng)矣”。“武帝元封時(shí)代,罷黜百家,‘法度確立,……由這時(shí)起到宣帝的石渠閣稱制臨決,‘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隨時(shí)抑揚(yáng),……是以五經(jīng)乖析,儒學(xué)寢衰”。
1.3筆者的新觀點(diǎn)及論文支撐此觀點(diǎn)
真正“定儒學(xué)為一尊”時(shí),應(yīng)當(dāng)是漢成帝時(shí)期,這僅為筆者之觀點(diǎn),體現(xiàn)在分類目錄《七略》的列類上,且有文章支撐。“漢武帝雖然采納了董仲舒的建議,……獨(dú)尊儒術(shù),立五經(jīng)博士,并大規(guī)模地征集文獻(xiàn),……真正精通《詩(shī)》《書》,崇尚儒學(xué)的是漢成帝,……一方面使謁者陳農(nóng)求遺書于天下,……韶光祿大夫劉向校經(jīng)傳、諸子、詩(shī)賦……”。
綜上所述,董仲舒向漢武帝推崇自己的主張:“推明孔氏,抑黜百家”(《漢書·董仲舒?zhèn)鳌罚浣ㄗh被采納后,歷經(jīng)周折得以實(shí)施,但初期較為艱難,“暢通之時(shí)”應(yīng)當(dāng)在漢成帝時(shí)期。
2.漢天祿閣:《別錄》《七略》的編撰及列類——對(duì)儒家文化的重視
同樣在漢未央宮之“天祿閣”——西漢國(guó)家圖書檔案館,西漢學(xué)者劉向、劉歆父子在上述“漢成帝重視及支持”背景下,“奉漢成帝之命——‘詔”,對(duì)其中的圖書檔案進(jìn)行了分類整理:“漢成帝和平三年(公元前26),詔向領(lǐng)校中五經(jīng)秘書于天祿閣……”,先后編出了我國(guó)第一部分類目錄:《別錄》《七略》。在《七略》的分類中,采取了“六分法”,因受漢武帝采納董仲舒“罷黜百家,獨(dú)尊儒術(shù)”的治國(guó)思想的影響,加之漢成帝對(duì)儒家文化的重視,將孔子整理的“六藝”(又稱六經(jīng))及所編著的《論語(yǔ)》“列為首”,稱之“六藝略”,將儒學(xué)列為“諸子略”之首。
《七略》即輯略、六藝略、諸子略、詩(shī)賦略、兵書略、數(shù)術(shù)略和方技略。輯略分總論及分論,以下為六大內(nèi)容分類法:六藝略分易、書、詩(shī)、禮、樂(lè)、春秋、論語(yǔ)、孝經(jīng)、小學(xué)九種。諸子略分儒、道、陰陽(yáng)、法、名、墨、縱橫、雜、農(nóng)、說(shuō)十種。從《七略》分類目錄中可看出:①將孔子所整理的“六藝”(又稱六經(jīng))及所著《論語(yǔ)》“列為首”,可見(jiàn)對(duì)儒家文化創(chuàng)始人孑L子及其所著、所整理的著作的重視。“東洋五千多年歷史中,縱有很多偉賢,唯孔子最占理想的極高地位。祖述憲章,刪正六經(jīng)六藝,為往圣繼絕學(xué),為萬(wàn)世開太平……其遺書,有《論語(yǔ)》七篇”。②將“儒家”列為“諸子略”中的首類,又可見(jiàn)對(duì)儒家文化的重視。③將道家僅列于儒家之后,依然保持了西漢初年文、景皇帝及竇太后等對(duì)道家思想(無(wú)為)的重視(與民休息):“漢代初期,鑒于秦朝用法術(shù)而迅速滅亡的歷史教訓(xùn),采用了經(jīng)過(guò)改造后的道家學(xué)說(shuō)——黃老之學(xué)作為治理國(guó)家的指導(dǎo)思想,……許多人信奉黃老之學(xué)”。
3.《七略》之后的《漢志》《隋志》《中經(jīng)新簿》等目錄,依然將“儒家文化”列于首
《七略》之后又編撰的《漢書藝文志》《七錄》《七志》等的“六分法”“七分法”中,依然均按《七略》之列類方法,可見(jiàn)對(duì)孔子及儒家文化的重視之延續(xù)。《中經(jīng)新簿》已開創(chuàng)了我國(guó)四部分類法(目錄)的先河,定型后以“甲、乙、丙、丁”(后改“經(jīng)、史、子、集”)四部分類,延續(xù)了一千多年。在四部分類法中,也始終將孔子所整理的“六藝”及所著《論語(yǔ)》“列于首”,“儒家”列為“子部之首”。《隋書》為史學(xué)之經(jīng)典之作,其“經(jīng)籍志”為圖書分類目錄,也為“四分法”。在該四部分類目錄中,依然將孑L子整理的“六藝”(又稱六經(jīng))及所著《論語(yǔ)》“列于首”,并將儒學(xué)(儒家)列于子部之首。
4.宋代的《直齋書錄解題》——“語(yǔ)孟類”:“四書”之雛形的誕生
在現(xiàn)存宋代私藏目錄中,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最為晚出。其“經(jīng)部”包含易類、書類、詩(shī)類、禮類、春秋類、經(jīng)解類、語(yǔ)孟類、孝經(jīng)類、小學(xué)類……,“子部”包含儒家類、道家類……。這部目錄之類目排列中,依然保持了“孔子整理的文獻(xiàn)六經(jīng)中的五經(jīng),(“樂(lè)”經(jīng)已丟失)”“列為首”——“經(jīng)部”及“儒家類”在子部“列為首”,此也反映了宋代依然是“儒家文化為主導(dǎo)地位”,“宋代統(tǒng)治者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思想文化發(fā)展政策……倡導(dǎo)尊儒讀經(jīng),復(fù)興維護(hù)專治統(tǒng)治的儒學(xué)”。陳振孫之書目是對(duì)“儒家文化”的又一創(chuàng)新點(diǎn):“在53類中,僅類目有分合、增創(chuàng)、復(fù)立的語(yǔ)孟、小學(xué)、起居注……”,其中,“語(yǔ)孟”即為《論語(yǔ)》《孟子》,為“四書”中“二書”,同時(shí)也將“孔孟”連到了一起,由此可見(jiàn),宋代對(duì)儒家文化有了“升華的列類”,已出現(xiàn)了四書的雛形“二書”(語(yǔ)孟類)。
5.千余年來(lái)的“四部分類法”均將“儒家”列于首
除上述幾部各朝代的經(jīng)典目錄外,其他的《古今書錄》《新唐書·藝文志》《崇文總目》《文獻(xiàn)通考》直至清朝等歷朝歷代的圖書分類目錄(法)中,均將孔子整理的“六經(jīng)”及所著《論語(yǔ)》列為首(經(jīng)部),并將儒家(儒學(xué))列為子部之首。由此可見(jiàn),儒家文化及儒學(xué)從漢代至近代約兩千年來(lái),在中國(guó)文化、學(xué)術(shù)、目錄史(分類史)上的地位始終“列于首”!
6.清朝《四庫(kù)全書總目》及《鄭堂讀書記》中“儒家文化”的列類
《四庫(kù)全書總目》中的“經(jīng)部”包括易類、書類、詩(shī)類、禮類、春秋類、孝經(jīng)類、五經(jīng)總義類、四書類等。從清朝的《四庫(kù)全書總目》列類中可看出以下特點(diǎn):①依然將孔子所整理的“六藝”列為經(jīng)部之首,而將《論語(yǔ)》列于“四書類”中。②將“五經(jīng)”也列專類即“五經(jīng)總義類”。③將《論語(yǔ)》列為“四書類”,在前朝的《明史·藝文志》中,已經(jīng)開始了此列類法即“四書類”。④“四書五經(jīng)”在清代目錄中出現(xiàn),并已成為一個(gè)學(xué)術(shù)代名詞且延續(xù)多年。⑤將孔子列為史部中傳記類之首,而在圣賢之后才列“名人”,可見(jiàn)清朝已將孔子提到了“名人之上的圣賢”。清朝還有一部較為重要的目錄,即周中孚所作《鄭堂讀書記》,其經(jīng)部包含易類、孝經(jīng)類、五經(jīng)總義類、禮類、樂(lè)類、詩(shī)類、書類、春秋類、四書類、小學(xué)類。《鄭堂讀書記》中的列類,更將《四書五經(jīng)》名正列類,均在目錄之首——經(jīng)部。上述清朝兩部著名分類目錄之列類方法體現(xiàn)了清朝順治、康熙、雍正、乾隆等幾位皇帝對(duì)孔子及儒家文化與著作的贊譽(yù)及尊崇。雍正曾指出,“若無(wú)孔子之教,則人將忽于天秩天敘之徑……”“乾隆皇帝可謂始終不渝地大力提倡經(jīng)學(xué)……”。
7.民國(guó)及當(dāng)代的分類法,仍將“孔子及儒學(xué)”單獨(dú)列類
民國(guó)時(shí)期,誕生了何日章、袁涌進(jìn)及皮高品等所編的多部分類法,較為著名的為1929年劉國(guó)鈞所編的《中國(guó)圖書分類法》,其中,將“孔子及儒家”單獨(dú)列類:“121.2”。當(dāng)代全國(guó)通用的國(guó)家標(biāo)準(zhǔn)《中國(guó)圖書館分類法》,采用了“字母與數(shù)字混合制”的分類號(hào),依然將孔子及儒家文化研究單獨(dú)列類:哲學(xué)與宗教(B)-中國(guó)哲學(xué)(B2)-儒家(B222)-四書(B222.1)-孔子(B222.2)。上述《中國(guó)圖書館分類法》也將“四書”及“孔子”在“儒家”大類下又單獨(dú)細(xì)分列類,“四書”在明代目錄《明史·藝文志》中早已單獨(dú)列類,“四書類”“五經(jīng)”已各入其類,可見(jiàn)目錄學(xué)及分類學(xué)史的列類沿革對(duì)儒家經(jīng)典著作的重視。
8.結(jié)語(yǔ)
筆者經(jīng)綜合分析研究后認(rèn)為,在我國(guó)兩千余年的分類目錄(分類法)列類沿革中,孔子及儒家文化的地位始終不變,均被“列為首”,可見(jiàn)其重要地位。筆者也探討了“四書五經(jīng)”在分類目錄中的列類沿革:宋代產(chǎn)生雛形二書——“語(yǔ)孟類”,明代“四書”成型即“四書類”,清代成了名正的“四書五經(jīng)”即“四書類”“五經(jīng)總義類”,在當(dāng)代《中國(guó)圖書分類法》中依然保持了獨(dú)到地位,“四書”“五經(jīng)”已各人其類。應(yīng)當(dāng)說(shuō):“五經(jīng)”早在我國(guó)第一部分類目錄《七略》中已列在“六藝略”中,“六藝”即為“六經(jīng)”(包含“五經(jīng)”),此乃目錄學(xué)、分類學(xué)史上又一新觀點(diǎn)。“古典目錄學(xué)所呈現(xiàn)的學(xué)術(shù)格局,并不僅僅是對(duì)既有書籍從內(nèi)容上進(jìn)行歸納的結(jié)果……同時(shí)也是目錄制定者或其時(shí)代的學(xué)術(shù)理想的體現(xiàn)”。同時(shí),筆者認(rèn)為:漢未央宮、石渠閣、天祿閣等,應(yīng)成為當(dāng)代儒家及道家等思想文化、圖書館學(xué)、檔案學(xué)、目錄學(xué)的專業(yè)教育及研究基地。
——兼談歐美游客儒家文化認(rèn)知狀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