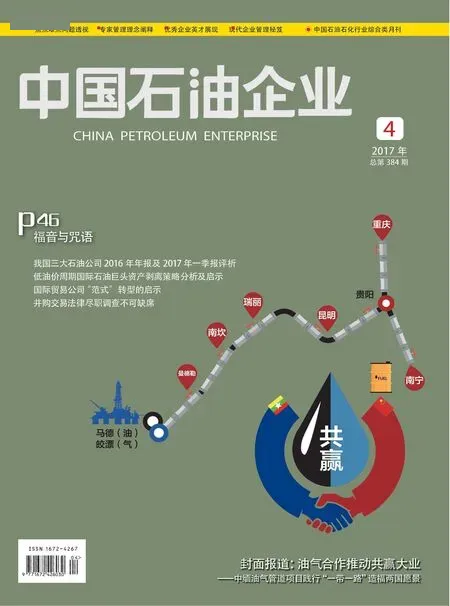“能源獨立”與“資源詛咒”
“能源獨立”與“資源詛咒”
特朗普因何如此不待見環保?以至于非要置之死地而后快。有些人甚至從作為商人的特朗普經歷環保部門種種“刁難”的角度,解釋作為總統的他因而進行“挾私報復”。這或許是其中的因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作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必須要在環境優先和能源效率優先之間做出選擇。這是一場難以兼顧的、非此即彼的選擇,而特朗普選擇了后者。
美國兩黨有關氣候的博弈由來已久,成為了一場口水拉力賽。2001年3月,布什政府就曾以“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將會影響美國經濟發展”為借口,拒絕簽署旨在全球范圍內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京都議定書》。2010年,民主黨提議的減少二氧化碳排放量和準許企業交易碳排放指標的法案,也被共和黨占多數的參議院成功阻攔。因而,特朗普政府在環境選項上的態度,更多的是兩黨博弈在此消彼長中的延續。特朗普在美國總統大選第二場辯論電視直播中曾表示:“我們在毀滅能源行業,環保署太嚴厲了,讓能源行業沒有生意可做。”
“能源獨立”是特朗普的重要能源政策主張。特朗普計劃通過擴大以煤炭、石油和天然氣為代表的化石能源的生產與出口來實現能源自給自足。
“能源獨立”概念并非特朗普發明創造。早在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機期間,尼克松政府便提出“能源獨立計劃”,以后受到歷屆政府支持,旨在加快國內能源開發,希望依靠自身力量滿足國家能源需求。特朗普政府能源政策“創新”之處在于,其“能源獨立”邏輯是建立在惠及民生之上的。可以進一步理解為,要恢復美國曾有過的石油開釆業輝煌,增加美國石油工人就業崗位。可見,當下特朗普提出的能源獨立已不僅僅是歷屆政府為了不被中東產油國綁架那種單純的“政治問題”,而是更多關系到美國民眾就業與生存的“民生問題”。僅從這一點就可以明顯地感到,以往歷屆建制派的政客由于受到各種利益牽制,只能說但不能做的美國能源獨立問題,很有可能在特朗普時代在民粹思潮的裹挾下有極大的改變。特朗普稱,頁巖油氣產業可在未來7年內為美國增加200萬個就業崗位,開放聯邦所屬化石能源開發可創造28萬個就業崗位,Keystone XL管道項目將創造4.2萬個就業崗位。此外,油氣產業的發展從總體上可每年創造40萬個就業崗位。
由于美國一次能源中只有油氣需要大量進口,提高油氣獨立便成為美國“能源獨立”的重心。頁巖革命已使美國“能源獨立”在奧巴馬期間邁出重要一步。EIA統計數據顯示,2016年美國原油進口量為700萬桶/日,占消費比重從70%降至40%,從歐佩克進口量也從70%降至30%。而隨著特朗普放松油氣監管及開放聯邦土地等利好,這一進程還會加快。但利好化石能源政策并不意味著油氣鉆探活動大幅提升,目前很多封閉的聯邦土地位于偏遠地區,需要大量勘探作業和基礎設施投入,而美國私有土地已足夠滿足絕大多數油氣公司至少十幾年的鉆探計劃,尤其是在目前國際油價低迷背景下,油企大規模開采油氣積極性并不高。因而特朗普若想在短期內實現“能源獨立”和復興,難度很大,但其一系列政策變化會對美國乃至全球能源市場產生深遠影響。

從另一個角度看,“能源獨立”也不意味著“讓美國變得更加偉大”,相反,能源對外依存度降低到一定程度上,預示著美國經濟活力減弱和綜合實力衰退。放眼世界,緬甸、朝鮮、委內瑞拉、尼日利亞等國家早已實現能源自給自足,但卻無法擺脫貧困,而韓國、日本、新加坡等能源匱乏國家卻選擇了“相互依賴”,極大地繁榮了本國經濟。迪拜油氣富集,因選擇了開放貿易,在過去幾十年其經濟實現爆發式增長。事實上,在過去100多年里,美國能源消費隨著經濟增長而增長。1913-2013年,美國在石油進口增加300倍的同時,經濟產出也增長了300倍。與世界能源聯系的削弱,或許能減少美國外交上受到的掣肘,但也意味著美國與世界經濟聯系削弱,與世界經濟相互依賴程度降低。也許這在一定程度增加了美國能源供應的安全度,但經濟乃至國家安全則面臨更大的風險和威脅。
資源富集程度與財富富集程度永遠不是同步的,自然資源既會撒播福音,也會帶來“詛咒”。國際能源署研究結果顯示,從1960年到2000年,資源貧乏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以人均GDP衡量)比資源豐富的國家高2-3倍。在另一項被經常引用的研究中,薩克斯(Sachs)和華納(Warner)于1997年研究了95個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記錄,發現了以自然資源為基礎(礦產品和燃料能源產品等)的國家,其出口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明顯的負相關。“資源詛咒”背后發生機制很清晰:資源貧乏的經濟體在嚴酷的壓力下不得不放棄“消耗式”增長,而是通過技術和制度創新,走上新型經濟發展道路。而資源豐富的經濟體則過度依賴“抽血式”增長,反而使其工業退化,產品失去競爭力。
美國人熱衷于“能源獨立”,也突出反映了美國在相對衰落過程中孤立主義和保護主義的抬頭。“9·11”后,“能源獨立”成為美國擺脫中東獨裁政權、打擊恐怖主義的代名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