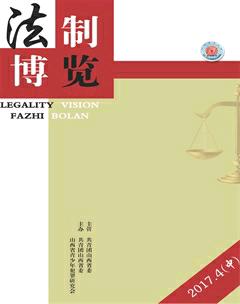論法律實踐中的程序正義問題
摘要:我國的文化傳統長期以來重結果,輕程序,所帶來的后果之一便是直接造成了程序正義和事實正義之間的對立和沖突。筆者嘗試分析程序正義的概念以及如何落實程序正義,兩者發生沖突時應該遵循哪些原則并論及兩者關系對我國法制建設的影響,如果能對讀者有所啟迪,本文目的便已達成。
關鍵詞:程序正義;實體正義;平衡兩個正義沖突
中圖分類號:D926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7)11-0108-02
作者簡介:賀軍杰(1982-),男,漢族,河北石家莊人,河北師范大學法政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在讀,研究方向:刑法學。
一、程序正義的概念
程序正義,是法律界經常涉及或者談論的術語,它其實源自英美法系一個很早的格言:“正義不僅要得以實現,而且應該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如果需要對程序正義制定一個規范的概念,筆者認為有必要先搞清什么是“程序”。程序是一系列動作的執行過程的描述,簡單地說,程序指什么樣的人,在什么時間、什么地點、通過什么樣的方式,按照什么樣的步驟完成一件事。為了更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筆者列舉一個例子來求證它如何實現。幾個人在森林里迷了路,他們饑腸轆轆,手頭只有一塊蛋糕得以分享。我們假設讓一位個頭高大,有力氣的成員切蛋糕,他肯定會把最大的一塊分給自己,但是別的人可能會餓死;如果讓他們當中的領導切蛋糕,他也會依仗自己的地位多分蛋糕,看來這些辦法行不通,如何才能讓蛋糕分得合理又不會產生爭議呢?最好的辦法是讓分蛋糕的人最后取蛋糕,這樣分蛋糕的人不會謀私。我們可以把這種分蛋糕的方式稱作程序,參與者切實遵守了這種方式,我們可以認定它實現了程序正義。又譬如幾個人賭博,我要問的是,如何判斷這個結果是正義的?無論是幾個人贏錢,一個人輸錢還是一個人贏錢,幾個人輸錢都不能證明賭博結果的正義。那我們只能從打牌的過程去觀察它,如果大家默認接受的游戲規則沒有偏向任何一方而且被嚴格遵守,我們就可以說這個過程公平公正,程序正義自然得以實現[1];反之,如果有人倒花房子或者偷窺別人的底牌,這個過程就會存在問題,自然在結果上也談不上正義了。以上兩個事例說明一個道理:程序正義有利于結果正義的實現,現在我們把程序正義引入司法審判領域,顯而易見,對于司法部門來說,僅僅做到最終判決的公平公正是不夠的,關鍵是審理過程是否做到了公開、公平和公正,如果它做到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稱其為程序正義。
二、程序正義優先于結果正義
在一定程度上,結果正義并不能保證程序的合法性。比如我國民眾耳熟能詳的戲劇《鍘包勉》,包勉是包公的侄子,因為貪污賑災公款而被包公斬殺。從法律人的角度看,包拯和包勉存在親戚關聯,和案件當事人存在利害關系的人并不適合充當法官,包拯的判案過程首先違背了程序規則,沒有做到程序正義,但并不能說這個結果是錯誤的。當然,程序正義并不必然導致結果正義,蓋其原因,乃是我們想要實現完全的結果正義是做不到的。人類沒有時光機器,也不具有上帝視角,緣于人類社會的現實復雜性和人類認識技術的局限性,人們不可能完全重現過去發生的事情[2],所以法律人常說的法律事實更多是一種最大程度符合客觀事實特征的“事實”。另外,無論多么理想的法律最終需要依靠人去執行,而適用法律的司法人員不可能不犯錯誤,無論是案件的當事人,還是審理案件的法官,他們對于法律規定和法律事實的理解總是存在差異,這一切都決定了司法審判并不存在一個人人接受的正義標準。
筆者認為,如果我們按照字母表從先到后的順序對兩個正義進行排列,程序正義的優先性應該在結果正義的前面,筆者有充足的理由證明這一點:首先,在一個法治國家,秩序是一種重要的價值,按照法律規定的程序和步驟去執行法律有益于良好秩序的形成。穩定的、需要自我維持的系統需要程序正義,遵守程序是為了確保整個國家的有序運行和長治久安,保障整個國家的核心利益比追求個案的結果正義顯得更為重要。
其次,法律的價值不僅在于被制定和頒布,更在于這種法律被信仰和遵守。如果某個案件的審理過程很公正公平,即便最后案件的判決錯誤,它仍然會給人民留下法律公正的印象;反之,如果某個案件的判決結果合乎正義,但因為在審理中沒有保障被告人應有的訴訟權利,缺失程序正義,人們則會懷疑法官枉法裁判以及判決的公正。所以,我們從“兩害相權取其輕,兩利相權取其重”的原則出發,應該更重視程序正義。
再者,法律的本質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后盾,使用暴力抑制和懲罰暴力。為了防止政府公權力的濫用并株連無辜的旁人,必須對公權力的使用進行限制和約束,而程序正義正是為了保證這種處理惡的力量不至于滋生和濫用。在辛普森殺妻案中,在上帝都知道辛普森是殺妻兇手的情況下,因為檢方提供的證據存在瑕疵,法院最終以證據不足為名判決被告無罪[3]。該案例充分體現了美國司法實踐中重程序優于實體的原則,而究其根源,還在于對法律而言,懲罰犯罪,維護正義固然是其價值的一面,但法律還是自由、平等和人權的象征。我們假設把匡扶社會正義的任務交給了一群正直無私而又無所不能的警察,國家授權他們可以運用一切他們認為適合的手段實現結果正義,那么你的家庭因為情報需要就會被竊聽,他們會非法闖入你的家中進行搜查,暫時對你實施強制措施等,這種對正義的追求卻以全體公民被迫忍受自身的權利被侵犯作為代價,筆者認為,為了司法正義而犧牲全體公民的福祉絕不是立法者當初的認識和目的。
最后,筆者想強調的是,程序正義有利于結果正義的實現。兩個“正義”不存在非此即彼的對立關系,程序正義也許并不一定會導致結果正義,但是程序正義的嚴格遵守,能夠盡最大可能實現一個相對公平合理的結果;換言之,嚴格遵守程序正義所帶來的最壞結果不過是放縱犯罪,但如果程序正義被執法人員無視,它可能帶來冤枉好人的惡果。在法律界我們制定和適用法律的底線是“寧可放縱壞人,也不能讓好人蒙冤”,正如培根所說的那樣:“一次不公正的審判,其惡勝過犯罪十倍,因為犯罪不過是污染了河流,而不公正的審判則是污染了水源”[4],不公的審判過程會導致人們對法律信仰的喪失,而法律的生命就在于信仰。
三、兩個正義原則的協調和處理
現在我們已經討論了程序原則的重要性,并且得出結論,程序正義優先于結果正義,但是如果兩者之間發生沖突,我們需要舍棄結果正義去保障程序正義嗎?哲學家告訴我們,世界上的事物豐富多彩,由此延伸為任何事情必須特殊問題特殊處理。例如,刑警大隊接到線報,房某正在自家住所里聚眾吸毒,情況緊急,值班刑警小李和小趙出警執行任務,由于行事倉促沒來及申請和辦理搜查證,但是根據我國法律規定,司法人員搜查人身和他人住宅,需要出示搜查證。假設警察最終在房某住宅查獲了毒品,程序正義的違反是否一定會導致結果正義的失效?綜合各國的司法實踐,程序正義和結果正義可以進行權衡取舍,法律的目的在于公眾的福利,輕微的程序正義的損害應該讓位于公共秩序和道德風尚的正義。我們再看另外一種情況,警察用刑訊逼供的手段取得了犯罪嫌疑人的口供,并最終依賴口供破獲了案件,但是這種辦案方式對程序正義的損害太大,如果法律對這種違法行為視而不見,其結果可能會放縱執法人員濫用權力,所以結果正義必須被犧牲,被告人的口供不能作為證據予以采納,對于公務人員刑訊行為,上級部門應該予以處理。
也許讀者會問到一個問題,一個殘疾人因為沒有攜帶殘疾證件而被乘務員拒絕乘車優惠,乘務員的行為符合國家和地方有關規定,但是殘疾人沒有手也是事實,筆者想類似這種程序正義和結果正義發生沖突的情形應該比較常見。筆者的意見是,當實體狀態不確定時,即沒有證人和確鑿的證據證明當事人的主張,裁判人員應該堅持程序正義優于實體正義,因為程序正義可以最大程度的發現客觀事實,實現實體正義;但如果實體狀態很明確,乘務員從外觀上可以判斷殘疾人的身體狀況,那么應該堅持實體,后補正程序。
還有一種不得不予以重視的情況,程序正義完全依附于實體正義,在這種關系中,程序并不具備獨立價值,而只具有促進實體目的實現的工具價值和保障價值,比如某個國家的政府制定了一部排斥少數民族選舉資格和擇業權利的法律,因為這部法律的目的是為了放縱壞人,懲罰好人,在沒有絲毫實體正義的前提下,執行標準被制定的越嚴格,它的惡性就越重,此時談論程序正義優于實體正義是十分荒謬的。
四、結語
在我國的文化傳統里,為了追求最后結果的正確,程序可以被視為可有可無,為了實體正義可以犧牲程序正義。改革開放后,我國加強了和西方國家的交流,逐漸認識到:法律的目的在于保障公共利益,在實體正義難以完美實現的情況下,遵守程序規則至少不會導致最壞的結果。程序正義雖然可能造成某些個案結果的不正義,但它會在更廣大的基數上實現總體正義;而且,結果正義是潛在的無法明確感知,而程序正義則是看得見的正義。如果司法部門不能做到程序的公正公開,那么人民無法感受到法律的公正就不會真正信服法律,而法治國家的建立正是以確立法律在人民心中的信仰為前提的。
當然,實體正義才是絕對正義,只是因為人類社會的復雜性,實體正義在有些情形下難以達成罷了。事實上,在社會生活的大多數事例中,兼顧程序正義和結果正義是常態,而在一些極端的案例中,因為程序正義和結果正義發生沖突,應該采用一系列平衡和估量的原則去判定,關于這一點,上文已經提及,不再累述。
[參考文獻]
[1][美]羅爾斯.正義論[M].何懷宏,何包鋼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67-70.
[2][美]波斯納.法理學問題[M].蘇力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4:277.
[3]許玉鎮,劉小楠.辛普森涉嫌殺妻案的法理學思考[J].河北法學,1999(01).
[4][美]培根.培根論說文集[M].水天同譯.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1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