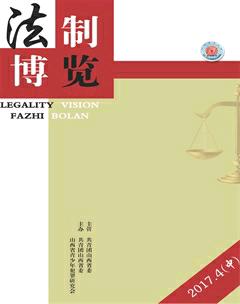論“職業打假”存在的法律意義
摘要:一直以來,“職業打假人”的存在面臨著巨大爭議,“職業打假人”的法律地位,也被畫上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在一些人眼中,這些人以打假為職業、有的甚至以獲利為目標,缺乏道義基礎,“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還要索賠,是敲詐勒索;但是,也有人認為,只要商家販售的商品質量的確存在問題,“職業打假”就有存在的理由。要保障市場健康有序、杜絕假貨泛濫,必須依靠政府職能部門,既建立起方便消費者維權的便捷通道,更要通過完善法律、嚴格執法,提高違法成本,形成制假售假者心中不敢踏入的“雷池”。
關鍵詞:生活消費;法律依據;行政立法;營利性
中圖分類號:D922.294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2095-4379-(2017)11-0175-02
作者簡介:姜玉(1967-),女,吉林長春人,吉林司法警官職業學院,教授,研究方向:律師實務。
2016年8月5日,國家工商總局發布《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征求意見稿)》,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引起爭議的莫過于第二條有關條例適用對象的規定,其對《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適用對象進行了界定: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條例保護,但是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以營利為目的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行為不適用本條例。這項有關“適用對象”的界定,也被認為是所謂的“職業打假人”將不再受消法保護。
“職業打假”是近年來頗受社會關注的現象,更有王海、劉艷清等長期從事此項活動者將之作為一種職業,進行公司式運作,“職業打假”飽受爭議。就法律對“職業打假”的約束而言,相比于“新消法”第二條,意見稿的最大差異在于后半句,前者的“本法未作規定的,受其他有關法律、法規保護”,看似含混卻對“生活消費需求”之外的消費行為提供了法律保護空間,而后者則變成了意圖明顯的限定性排除,所以才會引起有關“職業打假”的聯想式解讀。
一、“職業打假”的法律依據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是1994年1月1日起施行的,其中“退一賠一”的規定造就了以王海為代表的中國首批職業打假人。而消法中對消費者的定義,也經常成為商家拒絕對“職業打假人”進行賠償的理由。有些法官認為職業打假非為生活需要不受消法保護,而另一些法官則認為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獲利為合法利益,應受法律保護。
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明確指出“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是傾向于支持“職業打假人”知假買假的。近幾年法院的相關判決明顯都傾向于支持“職業打假人”。在此項《規定》出臺前,我國法律對于“知假買假”并無明確規定。而這一司法解釋,無疑給了近些年來不斷壯大的民間職業打假群體一柄“尚方寶劍”。
近三年來,全國消費維權訴訟案件在呈倍增趨勢。以北京朝陽區人民法院為例,據媒體報道,在2014年3月15日新消法實施后,朝陽區人民法院當年受理涉消費者買賣合同糾紛案496件,較上年的受理量增長了10.3倍,其中網購糾紛增長了4倍,大部分的功勞都源自“知假買假”的特殊消費者。受理的這些案件中,涉及食品領域的案件達256件,占案件總數近六成。這是因為,原告依據新消法的3倍賠償規定和食品安全法的10倍賠償規定,可以獲得懲罰性賠償。在這幾百件消費維權案件中,只有一名原告是律師,其他的均為職業打假人,其中韋某一人在朝陽區人民法院就提起92起訴訟,大多涉及食品領域。
二、《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實施條例(征求意見稿)》違背了行政立法的基本原則
此次的征求意見稿由國家工商總局牽頭起草,但“實施條例”的最終發布者將是國務院,屬行政法規。行政法規是行政機關將抽象法律進一步具體化的產物,因此在我國法律位階中是低于法律的規范性文件,且在行政立法原則上也必須符合上位法的規定精神。根據2014年3月15實施的“新消法”第二條,“消費者為生活消費需要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其權益受本法保護;本法未作規定的,受其他有關法律、法規保護”。而意見稿中有關“金融消費者以外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組織以營利為目的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行為不適用本條例”,則很容易造成誤讀,即把“職業打假”排除在條例保護之外,又把金融消費者包含其中,然而兩者都屬“營利為目的”,為何又“厚此薄彼”?
三、“職業打假”存在的社會意義
目前全國各類市場主體已經超過八千萬戶,而40萬工商和市場監管執法人員中,能到監管一線的有多少?絕大多數案件都是靠舉報人調查取證,對于洪水般的欺詐行為而言,工商市場監管部門的執法力量顯然遠遠不夠。職業打假者只要不是進行消費欺詐,他們的打假活動,對社會的整體效果是有益的。否定職業打假的合法性,受益最大的群體就是制假者、銷假者,會使假冒偽劣商品繼續泛濫,對社會不利。“職業打假”能夠在長時間內存在,并非法律縱容的結果,而是客觀上說明在這個共治格局中,很多環節還沒有真正把職責落到實處。天下無假,才不會有“知假買假”。
從現實來考慮,根據最高人民法院2013年發布的《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的司法解釋,“知假買假”至少在食品藥品糾紛中已經得到法律保護。同時,大量“職業打假”的勝訴案例表明,所謂的“營利性”消費行為舉證爭議非常多,只能由法官根據具體案件進行裁定,而不應該由行政機關進行非此即彼的限定。另外,至于具體到任何一起“職業打假”案件中,打假人是否有敲詐勒索商家行為,也完全可以通過訴訟雙方舉證,由司法裁決。由是觀之,即便是為了具體化一部法律,但行政立法,特別是進行基本概念界定和闡述原則時,也未必總是越詳細越好,該交給法律的就不妨留給法律。
如果執法部門因為嫌職業打假者“太煩”,就一再對其設限,甚至將職業打假人排除在賠償范圍外,那只會損害消費者利益,卻讓制假售假者松了口氣,等于變相鼓勵制售假冒偽劣商品的行為,只會讓目前本已嚴重的商品質量問題雪上加霜。即便真的出現有些官員擔心的“競買假冒偽劣商品潮”,也不是什么壞事。真正該擔心的也是假冒偽劣商品的經營者,而不應該是消費者。相反,大多數消費者是樂于見到這一局面的。如果假冒偽劣商品的生產商、經營者不因生產和銷售假冒偽劣商品而付出高昂代價,血本無歸甚至傾家蕩產,此類商品怎么會減少呢?真正要限制的是借用打假的名義,對守法的經營者進行敲詐、欺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