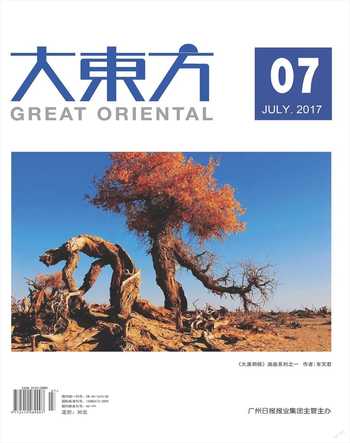論李煜后期詞中的思家念鄉
摘 要 以亡國被俘為界可將李煜的詞分為前后兩期,李煜后期詞大多以表達去國懷鄉、亡國被俘的憂愁之感為主。本文主要在爬梳李煜后期詞的基礎上,探討李煜后期詞中表達的思家念鄉。
關鍵詞 李煜;思家念鄉;后期詞
李煜后期詞共14 首。在亡國被俘后,李煜淪為階下囚,在宋朝廷備受壓迫、毫無自尊。由晚唐國主淪為北宋俘虜,李煜經歷了由奢入儉、由甜到苦的急轉折。人生經歷過大起大落的人,都會用極其悲觀的眼光看世界,李煜的作品確實有其他人所沒有的境界,這種境界能讓讀者從各種不同的角度去體會與其一致的情感。在整個歷史背景、生活狀態的巨大落差和壓抑屈辱的心情變化下,他詞作的情感基調和色彩風格也似乎完成了水從沸點到零點的巨變,完全跳脫了以往的靡靡之音,而著重突出孤獨者的自白。
李煜在汴梁過了兩年的囚徒生活,這使他的地位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白衣紗帽待罪于明德樓下,聽任兩朝天子對其命運的擺布。他在寫給金陵舊宮人的信中說: “此中日夕只以淚洗面”,“時悔殺了潘佑和李平”,屈辱、悔恨和傷感可想而知。也許此刻,李煜才真正感悟到什么是殘酷的政治、無常的人生。對往昔生活的回顧,對故國江山的眷戀,對過去錯誤的追悔,對人生自由的渴望,詞人把這一切都寫入詞中,使他這一時期的詞具有一種無比感人的藝術魅力。
《烏夜啼》:林花謝了春紅,太匆匆,無奈朝來寒雨晚來風。胭脂淚,留人醉,幾時重? 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
李煜將人生的無限悵恨寄寓在暮春殘景的描繪之中,面對被凄風寒雨晝夜摧殘的杏花紅蕊而感到無可奈何。詞人家亡國破,因而敏感于眼前季節時序之變化,花之處境亦人之處境,無力護花亦即無力護國之語意雙關。祖父辛苦開創的南唐基業毀于己手,回首往事更是寸斷肝腸,這綿綿的愁思和悔恨有如東逝的流水,無窮無盡。
《浪淘沙》:簾外雨潺潺,春意闌珊,羅衾不耐五更寒。夢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貪歡。獨自莫憑欄,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流水落花春去也,天上人間。
李煜將苦澀凄涼滲入到簾外的殘春景象,痛苦的囚徒生活和夢境的片刻歡娛,又折射出詞人思念故國的感傷情緒,只有在夢境中,詞人才會忘記自己是個階下之囚,才會貪戀那片刻的歡娛。淚眼登樓,無限江山,別時容易見時難,詞人朝思暮想的故國,如今已如流水落花般隨春而去,今昔生活的境遇,真有如天上人間的輪回。詞人在夢與現實的對照中,理出了血淚浸透的情絲,感嘆那逝去的人生經歷。
《相見歡》:無言獨上西樓,月如鉤。寂寞梧桐深院鎖清秋。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別是一般滋味在心頭。
凄涼的秋夜,詞人愁緒難遣,獨自默默登樓。那隨風飄落的梧桐葉和頭上那彎新月,又勾起詞人多少愁苦與悲傷。“無言”,揭示了詞人內心深處隱藏的多少不能與人傾吐的孤寂與悔恨,“鎖”字又寫出了環境的死寂,此種意象與“鳳閣龍樓連霄漢,玉樹瓊枝作煙蘿”形成鮮明的對照。面對此景,這位昔日的南唐國主心中又涌動著怎樣的離愁別緒,是追憶“笙簫吹斷水云閑,重按霓裳歌遍徹”的富貴榮華,還是痛悔“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奏別離歌”的生離死別。這諸多的愁恨哽咽于詞人的心頭難以排遣,有如那裹縛全身“剪不斷,理還亂”的亂絲,不可超脫、不可回味。
李煜雖身為臣虜,但心靈是高貴的。當高貴的心靈一再受到傷害、侮辱甚或摧殘時,他不再掩飾了,選擇用他那顆特有的詩心來抗爭,任故國之思和亡國之恨奔涌其間。
《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時了,往事知多少?小樓昨夜又東風,故國不堪回首明月中。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問君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
全詞通篇以問答的形式,描繪出詞人悲恨相續的心理過程。春花秋月是人生中難得的良辰美景,本應令人欣喜,但對日夕以淚洗面的囚徒來說,已了無意趣。越是良辰美景,越能誘發他對痛苦往事的回憶,越是回憶往事,越會帶給他無窮無盡的精神折磨。“何時了”三字雖問得離奇,卻表明了詞人對生命決絕的心態。接著他從囚徒的狹小天地聯想到故國,“不堪回首”便是滴血之語。李煜觸景生情,一任故國之思和亡國屈辱之恨,如江水般涌泄,從春花秋月到小樓東風,從雕欄玉砌到朱顏改變,幾乎每一個字都浸透了詞人孤獨絕望泣血之心,反映了人類悲憫的共同情感。李煜的詞,真實地反映了他一生的生活和情感經歷,尤其是他后期抒寫故國之思、亡國之恨的作品,充滿了感傷主義情懷和悲劇色彩。詞人以寫實筆法,恢復自己被扭曲了的人性和尊嚴,歷歷悲歡,字字血淚,是詞人被俘后屈辱生活的真實畫卷。李煜詞中所表現出來的人生愁苦和悔恨,不僅是一種個人的情緒和感觸,更是用血淚書寫成的不朽的生命篇章。正因為它反映了對人生毀滅的普遍深沉的挽歌式情調和悲劇性精神,具有悲憫的深刻普遍性,才得以在歷代讀者的心中產生巨大的共鳴。
李煜在寫其愁恨時借助了許多載體,再加上其真摯情感,使原來抽象的愁恨變得具體可感,且造語新穎、奇特,頗能感人。“恰似一江春水向東流”,以一江春水喻愁,且九字一口氣傾吐而出,更顯示了浩蕩不盡的愁思。王國維認為此句可以作李煜詞的評語,可謂恰當之至。“自是人生長恨水長東”,“水長東”是永恒的自然現象,“人生長恨”則是主觀思想,兩者對比則道出了人生的失落感、藐小感、悲劇感。“離恨恰似春草,更行更遠還生”更是新奇,春天一到,小草蓬勃生長,而愁也似春草一樣滋長的速度快,彌漫的范圍廣。“剪不斷,理還亂,是離愁”,用一種具體的動作方式描繪了離愁雜而多、雜而亂、理不清的無序狀態。俞平伯說:“‘別是一般滋味也是離愁。剪不斷,理還亂,還可形狀,這卻說不出,是更深一層的寫法”。總之,李煜借用具體事物,使愁具體化,這愁中錯綜交織著國破之痛、離散之恨,有歡娛不在,也有追悔莫及,有物是人非之感,更有自然永恒、人生難測的嘆息。
參考文獻
[1]朱歡歡.論李煜悼亡詩的情感內涵[J].遼寧教育行政學院學報,2013,1.
[2]張國軍.李煜后期詞的感傷情懷[J].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2014(3).
[3]王力.悲劇人生鑄偉詞——李煜后期詞的美學特質[J].語文教學通,2011(3).
作者簡介:陳奇(1993-),女,山東濱州人,聊城大學文學院15級研究生秘書學專業研究生,研究方向為現代文秘與應用寫作。
(作者單位:聊城大學文學院15級研究生秘書學專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