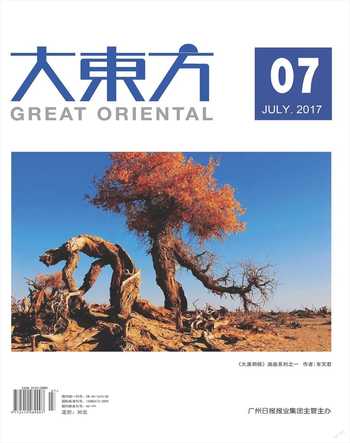論平面設(shè)計民族化表現(xiàn)中意象的構(gòu)思與表達
一、圖形符號的意象
(1)形意結(jié)合的傳統(tǒng)。《周易》提出“圣人立象以盡意”的觀點,意思是以形象直觀的語言來表達那些難以意會和言傳的思想情感。相對于畢加索曾經(jīng)把公牛圖像符號不斷地提煉、簡約化來說,《韓非子·解老》中的描述一樣很有意思:“人希見其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案其圖,以想其生也,故諸人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這段話的大意是說,人很少見到活象,而常常是得到了死象的骨路,依據(jù)死象骨髓的模樣想象活象的樣子。后來人們把所有意想的東西都叫做“象”。其實,由大象的骨路去想象大象,是由提煉后的主干形象部分逆向地推演、復(fù)原原型對象。畢竟,骨豁才是構(gòu)成和決定對象形體的主要部分。這其中雖然主要論述了 “意”與”象”的關(guān)系,但也與畢加索在素描中不斷地舍棄公牛的非特征部分,而逐漸突出特征部分的過程十分相似。
后來,三國時期魏國的王弼在《周易略例》中也說:“言者所以明象,得象而忘言;象者所以存意,得意而忘象。”這樣卻是突出了“意”的訴求目標超越表現(xiàn)手段的情形。“意”既不同于表述作用的“言”,又不同于具有物質(zhì)形態(tài)的“象”,它是超越虛擬概念和有限物象的一種境界,是一種含有無限情思和豐富內(nèi)涵的“象”。
(2)文圖對應(yīng)的表達。作為古老的象形文字的變種,漢字源于原始的、近乎再現(xiàn)對象原型的圖畫符號。例如,“日” “月” “水” “火” “山” “川” “馬” “牛”等漢字,在篆字之前的形態(tài)幾乎是客觀對象的形象再現(xiàn)。比如在山十于安陽的《祭祀狩獵涂朱牛骨刻辭》的甲骨文上,“囚”字是一側(cè)身站立的人被置于方框形的牢籠中;“馬”字是勾勒了馬的大致輪廓,馬腿用直線來畫出,而馬頭、軀干和尾巴則用曲線來描摹;但是兩個“車”字是從俯視角度看到的車輛形狀,彼此架構(gòu)略有差別。
從設(shè)計主題出發(fā)而生成設(shè)計理念,版面語匯通過象征等間接表達手法,把信息進行解讀和編碼,然后再尋找典型的傳統(tǒng)圖形元素,并進行二度創(chuàng)作和組織。如此,只要能確定作品的意象,就能通過版面語言去表現(xiàn)。可見,民族化表現(xiàn)的設(shè)計語言的生成過程,是一個多層次的意象主導(dǎo)、符號轉(zhuǎn)換、編碼再現(xiàn)和秩序化的過程。也就是說,它是從設(shè)計主題出發(fā),深化對主題的理解,找尋與主題對應(yīng)的傳統(tǒng)觀念和視覺符號。民族化設(shè)計表現(xiàn)的過程,可以說是一個多層次的符號轉(zhuǎn)換、編碼的過程。
二、版面構(gòu)成的意象
(1)情思的串聯(lián)。版面上意象是圖形符號經(jīng)過創(chuàng)作主體獨特的審美活動而組合出來的,是物化的藝術(shù)形象。可以說,“意”是無形的、抽象的,是隱含在圖像背后的,就像融入水中的鹽,無形而有味。在一個版面中,人們看得見的是一定幅面中的構(gòu)成要素,審視的是“象”,而經(jīng)過品味后得到的是“意”。
一方面,傳統(tǒng)的意象觀與現(xiàn)代設(shè)計語言相結(jié)合,形成了傳統(tǒng)文化意蘊的設(shè)計意象。平面設(shè)計中的設(shè)計意象,是把以視覺體驗形式出現(xiàn)的幻象當(dāng)作情意的載體,然后再對語言形象進行串聯(lián)、呼應(yīng)。但這并不是簡單的形式層面上的處理。也不是簡單地對原型對象進行概括、抽象,而是根據(jù)設(shè)計的需要在形式語言中尋找對應(yīng)的元素符號,并借以構(gòu)筑設(shè)計意象。另一方面,版面情思通過意象符號的象征去傳達某種主觀感受、觀念。意象符號的外在形式表現(xiàn)為符號元素,是可以具體感觸的形象,是與構(gòu)成版面所需要的點、線、面等相對應(yīng)的抽象的形式要素。表面上,這些抽象的形式要素作用于人的感官,會帶來不同的感覺。實際上,作品特有的寓意在知覺作用后,便形成體現(xiàn)版面內(nèi)涵的某種指示。可見,視覺語匯只有與作品的寓意結(jié)合,形成版面中的意象,才使其超越可視的符號元素的形式,而彰顯版面意蘊的獨特性。
(2)虛空的活泛。平面設(shè)計中的各種圖形符號常作為意象的載體出現(xiàn)在畫面中,傳達內(nèi)在的、隱性的一些含義,引發(fā)觀者的某種聯(lián)想。一般而言,圖形元素是版面的主體部分,平面設(shè)計是以圖形元素傳達信息、觀念的。由于設(shè)計作品往往需要在短時間內(nèi)引起觀眾的注意,給人們留下深刻的印象。如果僅靠可視化語言往往顯得單調(diào)乏味,因此應(yīng)恰當(dāng)?shù)剡\用“虛”與“實”的對比,形成情境,以追求更好的藝術(shù)效果。在圖形元素中,除去植物、動物和景物圖形圖像等一些常見的具象表現(xiàn)形式外,還有一類特殊的意象表現(xiàn)形式,即空白意象。
視覺心理也需要意猶未盡的省略處理。有時候版面中的空白處理就如同文學(xué)作品中的省略部分一樣,雖不列舉,戛然而止,卻能夠造成受眾在視覺和心理上的沉思。可見,空白已是組成形象的有機部分,是形象的延續(xù)與衍生,是提示形象具有不可知的神秘一面,它可引發(fā)更多的聯(lián)想和想象。平面設(shè)計中的空白,相當(dāng)于一種“神秘空間”,能夠隨著不同主體內(nèi)容演變成其對立互補的神秘一面。同時,它還是版面中無處不在的一種“氣場”。版面中各構(gòu)成要素,正是被這種無形的“氣場”協(xié)調(diào)地統(tǒng)一在某種氛圍和風(fēng)格里,互相關(guān)聯(lián),表現(xiàn)出一種完整性和系統(tǒng)性。可以認為,只要巧妙地運用空白這一構(gòu)成要素,活躍版面氣氛,就可以讓空白成為氣質(zhì)營造中最突出、最重要的部分。
(3)意興的生成。語言的生動帶來興趣的激發(fā),形象的豐富帶來情意的勃興。就風(fēng)格特點而言,后現(xiàn)代主義設(shè)計是對現(xiàn)代主義設(shè)計的一種修正,是化簡約、乏味為一種裝飾性發(fā)展,主張以裝飾性手法來達到視覺的豐富,顛倒了內(nèi)容與形式的從屬次序,反而將形式置于創(chuàng)作的核心位置,可見它推崇的是視覺刺激的傳達方式,帶來的也是多樣化的淹沒主題的方式。如果不是出于形式主義的考慮,如果不考慮到意興生成的需要,民族化表現(xiàn)就不必合理地運用傳統(tǒng)繪畫中的節(jié)奏營造方式與裝飾語言,追求中國傳統(tǒng)藝術(shù)的意象表現(xiàn),追求“言有盡而意無窮”的意境,以體現(xiàn)民族化表現(xiàn)的設(shè)計觀念。可見,意象手法可以結(jié)合構(gòu)成語言,民族化表現(xiàn)的理念也可以在現(xiàn)代設(shè)計的體系里得到實踐應(yīng)用。
作為信息傳播的發(fā)起方,設(shè)計方通過符號系統(tǒng)傳達信息,社會受眾作為信息接收端在信息讀取中理解、認知這些圖形語言,即進行解碼、讀取信息的心理活動,領(lǐng)會作品意象,參與作品想象。在這過程中,平面設(shè)計的表層意義是根據(jù)圖形、字體和顏色等形象語言直觀表達的屬性,形成平面媒介的版面形象,比如版面的大小、文字的容易辨認程度等,是一種技術(shù)性的功能主義傳達。
朱秀婷(1989-),女,聊城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15級研究生,專業(yè)為藝術(shù)設(shè)計,研究方向為視覺傳達設(shè)計。
(作者單位:聊城大學(xué)美術(shù)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