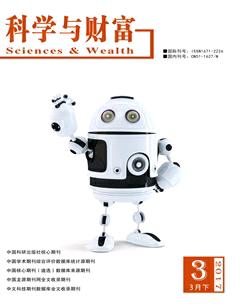城中村的死與生
金希 高珊玥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的發展,我國正經歷著高速的城市化進程,相應帶來的是大批的外來人口流入城市,城市用地面積不斷增加,外圍逐漸擴張。然而,這種急功近利式的空間擴展導致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城中村的出現。本文旨在通過實地走訪,調查北京一典型的城中村一一朝陽區東壩鄉,深入了解長居在城中村的當地人和暫居在此的外來人員的生活,以探究城中村在當下社會中存在的意義(主要為積極意義),進而討論城中村真的要徹底鏟除嗎這一現實問題,以及提出我認為合理的整改方案。
關鍵詞:城中村;共同體;流動人口;正功能;利益
一.研究問題
城中村現狀
筆者幾次深入到東壩鄉,見到了許多以前從沒見過的景象。值得一提的首先就是公用現象。在城中村里,很多東西都是公用的,公用的衛生間,公用的廚房,公用的水池,公共的浴池等等,因為公用,衛生條件就很難保證,人們對于公用的東西往往持有事不關己的態度,認為自己沒有義務去愛護或者收拾清理一個本不屬于自己的東西,這也就是那些公共衛生間,水池臟亂的主要原因。
另一點另筆者感觸頗深的是城中村的違建現象,在東壩鄉,大多數建筑都屬于違規建造,都是當地村民自己建成的平房或二層小樓,小樓里兼并出大大小小的屋子以便出租,通過收取外來流動人口的租金來維持自己的日常生活。因為屬于違建,大量的房屋建造未經規劃,造成了房屋與房屋之間密集擁擠的現象,更甚之處在于,很多房屋存在著安全隱患,說是危樓都不為過。這樣的居住環境嚴重地影響著租客的生命安全,然而低廉的租金對于沒有雄厚經濟基礎的外來流動人口可以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以至于可以不顧安危居住于此。
二.文獻綜述
(一)理論視角
Slum視角下的城中村
(1)Slum視角
Slum一詞翻譯過來即貧民窟,該名詞由國外學者于十九世紀二十年代首先提出,而聯合國針對貧民窟一詞給出的定義是,最惡劣的住房條件、最不衛生的環境、犯罪率和吸毒盛行的窮人避難所。可見,貧民窟是一個和正直、健康毫不相干的地方。
(2)國外的slum與國內的城中村
今天,我國的城中村就好比國外人眼中的貧民窟,兩者有著極為相似的地方,同時,又存在著些許的不同。國外的貧民窟大多數以拖家帶口的形式存在,而不同于貧民窟較為單一的組成形式,我國的城中村現狀更為復雜。我國的城中村中居住著兩種不同類型的群體,一是當地的原住居民,二是外來的流動人口。當地的原住居民多數以家庭為單位去組織開展生活,且這種家庭的輻射范圍較大,涉及到更多親人的參與,社會整合力極強。不同于當地原住居民以家庭為單位的居住形式,外來的流動人口更傾向于獨立居住,且流動性較大,這一群體正是造成城中村臟亂不堪,治安混亂的主要原因。
(二)經驗研究——“浙江村”的古今
城中村問題歷來是學者們熱議的話題,其在北京存在已久,最早進入廣大學者眼中的城中村即“浙江村”。所謂“浙江村”,是指從八十年代初開始,以浙江溫州人為主的外地人,陸續來到豐臺區南苑鄉的時村、果園村一帶,租住當地居民和農民房屋,在京城經商,從而形成較固定的活動區域。對于“浙江村”這一發展模式,不少學者都做了相應的探討,社會學家鄉項飆在《“浙江村”——中國農民進入城市的一種獨特方式》一文中,將“浙江村”定義為一個以聚居為基礎的產業加工基地,將村民融入城市的過程看作是不斷尋找市場與開拓市場的過程。不僅如此,作者更認為,“浙江村”在和北京的交往,依存不斷發展的同時,逐漸形成了日益復雜的自我服務體系,這種自我服務體系不僅不會成為北京城市的負擔,相反地,會進一步帶動北京城市的發展。可見,“浙江村”這片北京特有的土地,最早的城中村之一,無論是存在之初,還是在當下社會,都對北京城市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其正功能遠遠超出其最初“臟亂差”的負功能。可見,城中村的存在有其歷史必然性。
(三)研究設計
在本篇文章的展開中,筆者首先從探討城中村形成的原因入手,分析在原住民的利益驅動和城鄉二元體制兩種不同因素促使下形成的城中村,以及針對不同原因前人提出的不同整改方案,并對其方案進行合理的否定,進而從正反兩個方面對于城中村做出功能分析,以提出新的有別于前人的整改方案。在研究方法上,筆者主要采取了訪談法,深入到朝陽區東壩鄉進行實地的調查與訪談,目的在于通過當地外來流動人口的視角來證實城中村存在的積極意義,最終在政府,當地原住民以及外來流動人口三個利益相關者之間尋求利益的平衡與最大化。
三.城中村的功能分析
(一)城中村的正功能
1.緩解城市住房供需矛盾
在筆者看來,城中村首要的正功能就是緩解城市供需矛盾,簡單來說,就是為外來流動人口提供保障其基本生活的住所。眾所周知,北京的房價節節攀升,已經遠遠地超出了普通百姓的經濟承受能力,更是剛步入社會的大學生所不能承擔的,恰巧城中村的存在為那些懷揣夢想的北漂青年提供了施展空間。
2.為當地原住民提供經濟收入和就業機會
研究中不難發現,城中村中的原住民文化程度較低,身體素質較差,相應帶來的就是競爭力較弱,那么,城中村的土地自然成為其保障生活的僅有籌碼。原住民在城中村的土地上建造幾層小樓,兼并出許多屋子以供出租,從中謀取生活的資本。這也不失為對于農民失去耕地的另一種補償方式。
(二)城中村的負功能
城中村的負功能一直是以往學者主要探討的問題,也是他們主張推土機式鏟除城中村的有力證據,在前文城中村現狀一節中筆者也有所提及,例如城中村的環境臟亂,街道擁擠,違規建筑隨處可見,社會治安嚴峻,管理薄弱等等,在這里就不做贅述了。
四.結論——尋找利益的平衡點
曾有位學者說到,城中村的本質是不同利益相關者之間利益協調合約的再安排,而城中村的改造本質上是為各利益相關者有效地創造價值,即滿足利益相關者多維的利益需求。針對前文中筆者做的城中村的功能分析,結合該學者說的話,筆者的理解,對于城中村這一問題,不應該鏟除,而是改造,而這一改造也并不能僅僅地考慮原住民和當地政府的利益,進行簡單的推土機式的鏟除,還要考慮到居住在此的外來流動人口的相關利益,尋找到三者利益的平衡點。城中村存在有其歷史必然性以及特殊的意義,然而時代在進步,城市在繼續擴展,朝陽區東壩鄉這一城中村必然會淹沒在時代的洪流中,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不同于之前學者提及的弊端重重的貨幣安置和就業安置,也不同于歷時較久的城鄉體制改革,在我看來,對于朝陽區東壩鄉等類似的城中村改造應采取開發性措施,也就是在該地區開發新的項目,招商引資,同時又劃分出居住區域,不破壞成中村原有的社會承載力,這一點在筆者看來是極其重要的,畢竟前文中也說到了無論是外來流動人口還是長居于此的本地居民,對于城中村的居住功能依賴是非常大的。以上討論,簡言之,城中村存在有其積極意義,不可能也不能完全鏟除,能做的,就是在最大程度地保存其居住功能的基礎上進行相應的功能區域改造,以順應廣大切身利益群體的利益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