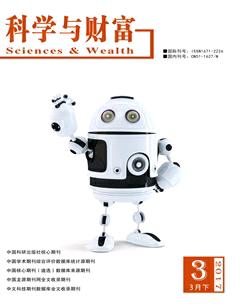從制度經濟學中解讀改革開放
彭鵬
摘要:中國的改革開放是二十世紀以來人類最偉大的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的成就之一,中國因為改革開放而帶來的長達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一直受到諸多國內外學者的關注,很多人都嘗試以不同的視角來解釋產生這一現象的原因,本文則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希冀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產生的高速發展做出合理的解釋。
關鍵詞:特殊利益集團;改革開放;經濟增長;制度變遷
一、社會利益分配機制的變革
“特殊利益集團”是經濟學家奧爾森在其著作《國家的興衰》一書中提出的,作者在書中提到:“特殊利益集團”的多少和其分布范圍的廣泛程度影響到整個國家的長期經濟增長的效率,并且對國家的長期高速發展具有決定性的作用。關于特殊利益集團對于國家經濟發展的阻礙,奧爾森總結出兩點原因:一是降低了社會總體效率或者總體收入,同時加劇了國家政治生活中的分歧;二是無形中提高了國家管理和統治的復雜性,并且會改變社會演進的發展方向。
對于特殊利益集團的認識,我們可以從歷史上的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和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經濟發張中得到佐證。
早期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發展,前后長達百年。但是隨著資本主義國家在十九世紀中葉先后進入了壟斷資本主義時代,這些壟斷寡頭不僅控制國家的經濟,還越來越多的開始干預國家的政治。在隨后多年的經濟發展過程中,大量的反壟斷法案都是西方各國政府保證社會利益分配盡可能的公正而做出的努力,這也使得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避免了相當程度的發展停滯與危機。
與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相反的,拉丁美洲經歷了二十世紀六十和七十年代的經濟高速增長后,發展逐漸減慢甚至陷入停滯,社會也進入長期的動蕩和不安,因此被稱之為“拉美現象”。拉美現象實質上證明一旦開始形成特殊利益集團,隨著社會和經濟發展的深入,這些利益集團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必將干預正常經濟秩序,而國家和社會也因此產生政治分歧和社會動蕩。
按照奧爾森的經濟學觀點,當前中國的改革開放之所以使中國經濟快速發展三十多年,很大程度上源自中國尚未產生或者尚未發展成熟真正的特殊利益集團,原因有三:一則新中國的體制在客觀上難以形成真正的特殊利益集團;二則建國后的社會主義改造客觀上消除了產生特殊利益集團的條件;三則中國的改革開放畢竟只進行了三十多年,目前還沒有到出現真正特殊利益集團的時間年限。
與特殊集團利益相對的,是社會共榮利益。奧爾森認為:“所謂的社會共榮利益,是指如果某位理性追求自身利益的所有個人或所有某個擁有相對凝聚力或紀律的組織能夠獲得該社會所有產出增長額中的相當的部分,則該個人或組織在此社會中便擁有一種共榮利益。這種共榮利益給所涉及到的所有個人以激勵,誘導他們去關心并努力提高全社會的生產率。”社會共榮利益某種程度就是人民共同利益,因此中國的改革開放的成就,很大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中國實現了全社會的人民利益的共存與共享。
二、社會準入秩序的變革
諾斯認為人類社會先后形成過三種不同的社會秩序,它們分別是:原始社會秩序、有限準入秩序、開放準入秩序。有限準入秩序通過限制進入產生租金,并由此來維持社會的穩定和秩序。開放準入秩序通過政治和經濟上的相互競爭以創設租金來維持社會秩序。
新中國建國初期,實習的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是典型的有限準入秩序,其結果導致了中國經濟在進入六十年代之后發展明顯缺乏活力。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建立以公有制為主體多鐘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混合經濟制度,這種舉措使得中國的經濟取得快速發展。同時國有企業改革、放寬外商投資限制以及允許民營資本投資等措施,使得中國由有限準入秩序逐步轉向為了開放準入秩序。
從新中國由有限準入秩序轉變為開放準入秩序的經歷,我們可以從中國不同時期借鑒的不同制度上找到一些縮影。
新中國成立后,實行的外交政策是“一邊倒”的靠向蘇東社會主義陣營,因此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就不可避免的具有高度集中性和封閉性。這種經濟體制在蘇聯及東歐國家中,幾乎都在高速發展近二十至三十年后遭遇了自身的較大社會政治經濟危機,甚至使全球的社會主義運動遭遇了巨大的挫折。
當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實施改革開放的政策后,中國開始有計劃的對經濟體制和職能進行改革。中國借鑒南斯拉夫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從中吸取了經驗和教訓,立足本國的國情,對經濟體制進行了中國特色的改革和實踐,為后來中國的持續高速發展奠定了基礎。
三、政府職能的轉變
奧爾森在其研究中提出經濟繁榮的必要條件,即:建設強化市場型政府。對此我們可以理解為一個政府如果有足夠多的權力去創造和保護公民個人的合法財產及財產權利,那么這個政府便是一個“強化市場型政府”。而強化市場型政府促進經濟發展必須具備兩個條件,一是要界定明確的財產和契約權利;二是不存在任何形式的政府掠奪行為。
從奧爾森的“強化市場型政府”理論模型出發,我們可以看到,如果一個國家的政府不能夠明確界定財產和契約權利,并且該政府存在機會主義的掠奪行為的話,那么這個社會的秩序不是開放準入秩序的,因此也不會出現經濟的持續高速增長。
2004年中國憲法修正案的決議通過并且頒布實施,標志著國家對于公民個人的合法私有財產開始進行保護,這實際上也是中國轉型為開放準入秩序的一個標志。十八屆三中全會中明確提出了,要讓市場成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力量。可以看出,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繁榮,法治化和公平、公開化的公共管理與行政已成為未來中國的重要任務,而建立在公平和有效的法治環境基礎上的,則是市場經濟的核心——契約公平與私法自治。
契約精神在市場經濟成熟的制度中占有著相當的地位,這不僅因為它具有了推動現代市場經濟發展的能量,更因為它的存在凸顯了規則意識作用的開放準入秩序的制度體系所必須具備的思想鋪墊。政府在開放準入秩序的環境中,只能依據契約精神和權力清單在有限的范圍內實施對市場的管理,真正做到管理該管的、嚴格禁止管理不該管的,最終使中國真正形成具有契約精神和法治環境的市場經濟體。
四、意識形態的改變
諾斯把意識形態的研究納入到“白搭車”這個具體問題的框架中,他認為意識形態(又稱信念)的作用可以有效的解決白搭車的難題,在研究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的無產階級革命時,其中關于階級革命的理論驗證了意識形態在解決白搭車難題中的作用,即社會發展的關鍵就是社會秩序由有限準入秩序向開放準入秩序的轉型。諾斯在其論文《理解制度變遷過程》中寫道:“經濟變遷這一過程的關鍵是參與者的意向性,是由參與者的感知所支配的”。諾斯重視意識形態的作用,他甚至同一歷史就是意識形態的戰場這種看法。在他的論述中,諾斯提到倫理道德和世界觀在制度的選擇和決策中的作用,但他更重視的是通過公民教育,建立一種意識形態,以保證制度規范的實施。比如在制度改革中,用靈活的意識形態來贏得新的利益集團的擁護和舊的利益集團的妥協。諾斯在論文中的結論指出,如果人人都白搭車,那么就等于制度完全無效,因此解決白搭車的問題除了意識形態的教育外別無他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