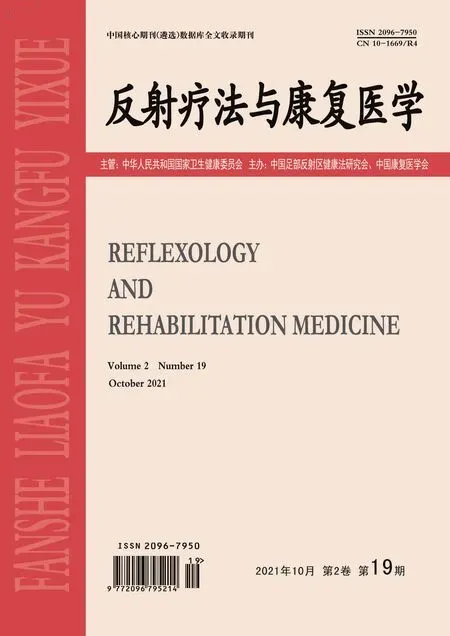五禽戲在腰椎間盤突出癥患者椎間孔鏡術后康復護理中的應用
徐金環
(山東國欣頤養集團淄博醫院中醫科,山東淄博 255120)
椎間盤退變是腰椎間盤突出癥(LDH)的根本病因,此外,腰椎損傷積累、遺傳、不良生活方式等均可誘發該病,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 手術是非手術治療無效LDH 患者的主要治療方法, 尤以椎間孔鏡術多見,但部分患者術后可能出現瘢痕組織,出現神經粘連、坐骨神經痛等并發癥,不利于其術后康復[1]。 因此, 采取合理有效的康復手段進行干預顯得尤為重要。常規康復護理是臨床針對該病患者的常見干預方法,雖能在一定程度上促進患者術后康復,但仍有部分患者的干預效果不顯著,生活質量較低[2]。五禽戲是一種模仿虎、鹿、熊、猿、鳥動作、形態的康復方法,具有通經活絡、益氣活血的功效,可改善腰骶部多裂肌功能,增加脊柱穩定性[3]。鑒于此,該研究選取2019 年1 月—2021 年 3 月于該院行椎間孔鏡術的 96 例LDH 患者為研究對象,通過分組對照,探究五禽戲在術后康復護理中的應用效果。 現報道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一般資料
選取于該院行椎間孔鏡術治療的96 例LDH 患者為研究對象。 納入標準:LDH 符合相關診斷標準[4],且經腰椎X 線平片檢查確診; 均在該院行椎間孔鏡術治療;認知功能正常。 排除標準:合并腰肌勞損、腰椎管狹窄癥、梨狀肌綜合征等疾病者;肝腎功能異常者;合并惡性腫瘤疾病者;軀體功能障礙,無法進行康復訓練者。 將96 例患者依據隨機數字表法分為對照組和觀察組,每組48 例。 兩組各項一般資料對比,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具有可比性。 見表 1。

表1 兩組一般資料對比
1.2 方法
1.2.1 對照組
采用常規術后康復干預,具體如下:通過發放宣傳畫報、 播放視頻等方式對患者進行LDH 相關知識宣教,提高其對疾病的認知;相關人員應主動與患者交流,引導其說出內心問題,叮囑家屬多陪伴患者,以便及時發現并疏導其心理問題;早期指導患者進行腰背、下肢、腹部肌力鍛煉,如取仰臥位,雙下肢置于臀下,微屈膝關節,而后緩慢上下擺動雙下肢,15 min/次,2 次/d;患者在康復師指導下下地行走,行走距離逐漸延長,后改為獨立行走。 持續干預3 個月。
1.2.2 觀察組
在對照組基礎上采用五禽戲干預,具體如下:(1)虎舉:康復人員指導患者雙手掌心向下,十指撐開,并彎曲成虎爪狀,之后雙手外旋,從小指開始依次彎曲握拳,而后雙拳緩慢上抬,至肩前時改為虎爪狀,繼續上提至手臂伸直,然后雙手外旋握拳,緩慢下移至肩前時,改為虎爪,繼續下落至腹前,期間眼睛一直注意雙手。(2)虎撲:囑患者雙手握拳,上提至肩前上方后,雙手向上、向前劃弧,之后變拳為爪,下按至膝部兩側,再上提下撲,而后變換部位;虎撲需注意手形的變化,上提時握空拳前伸,下按時呈虎爪。(3)鹿抵:囑患者握拳,雙腿微屈,兩臂向右側擺起,至肩前時變拳為鹿角,左腳落于右前方,以腰部帶動身體轉動,重心右移,而后兩手從左后方伸出,右腿蹬直。(4)鹿奔:囑患者左腳向前邁步,雙手握拳,兩臂前伸屈腕,重心前移成弓步,之后重心后坐,收腹拱背,變拳為鹿角,兩臂內旋前伸手背相對,含胸低頭,使肩背部形成橫弓,同時尾閭前扣收腹,腰背部形成豎弓,使重心前移。 (5)熊運:囑患者兩手呈熊掌狀置于腹下,上體前俯,兩腿保持不動,固定腰胯,身體順時針畫弧,同時雙拳沿右肋、上腹、左肋、下腹畫圓,重復一遍后,再逆時針做上述動作。 (6)熊晃:囑患者重心右移、提髖、屈腿,而后重心前移、后坐、前移,之后改變方向,重復上動作。(7)猿提:囑患者兩手成猿鉤置于體前,肩上聳、縮脖,提手,兩臂內夾,以膻中穴為中心含胸收腹提肛,腳跟提起,頭向左轉,而后回轉,肩放松,腳跟著地,兩手變掌下按至腹前。(8)猿摘:囑患者退步畫弧,丁步下按,上步摘果,變握固為托托桃狀,左腳左后方退步,右腳收回變丁步,右腳前跨重心上移再收回變丁步。(9)鳥伸:囑患者兩手上舉,聳肩縮頸,雙腿微屈下蹲,雙掌左右分開成鳥翹,而后重心右移,軀體向側后方擺起,抬頭、挺胸、伸頸。(10)鳥飛:囑患者兩手合于腹前,沉肩、起肘、提腕,側平舉,手背相對,提腿獨立,之后松肩、沉肘,向下按掌、落腿,并更換另一側腿做相同姿勢。 五禽戲鍛煉 1 h/次,1 次/d,最初只選擇 1~2 種動作,每個動作重復3~5 次,隨后逐漸增加動作種類及次數。 持續干預3 個月。
1.3 觀察指標
(1)康復優良率:參考日本骨科協會評估治療分數(JOA)[5]改善率評估兩組的康復優良率,改善率=[干預3 個月時評分-干預前(手術前)評分]/(干預前評分)×100%。康復優:改善率為100%,可正常工作及生活;良:改善率>60%且<100%,可從事較輕工作;可:改善率>25%且≤60%;差:改善率<25%。 優良率=(優+良)/總例數×100.00%。(2)腰椎功能及疼痛程度:干預前、干預3 個月后,采用Oswestry 功能障礙指數(ODI)[6]評估兩組的腰椎功能,量表包含 10 個評分項目,每個項目從無至嚴重以0~5 分表示,總分由各項目得分相加得到, 共50 分, 得分越低則腰椎功能越好;采用視覺模擬評分法(VAS)[7]評估兩組的疼痛情況,取一根10 cm 長移動標尺,上有10 個刻度,兩端分標0 和10,表示疼痛程度由無至劇烈疼痛,由患者根據主管疼痛感受移動游標,讀出分數,分值越高則疼痛越劇烈。(3)生活質量:干預前、干預3 個月后,采用生活質量綜合評定問卷(GQOLI-74)[8]評估兩組的生活質量,量表包含軀體功能(20 個項目)、心理功能(20 個項目)、社會功能(20 個項目)、物質生活狀態(10 個項目)4 個維度及生活質量總體評價 (4 個項目),共計74 個項目,每個項目由差至好以1~5 分表示,各維度總分為其所含項目得分之和經相關轉化得到,總分范圍均為0~100 分,得分越高,表示患者生活質量越好。
1.4 統計方法
采用SPSS 25.0 統計學軟件進行數據分析。 計數資料以[n(%)]表示,采用χ2檢驗;等級資料采用秩和檢驗; 以Shapiro-Wilk 正態分布檢驗VAS 評分等計量資料的正態性情況,符合正態分布的計量資料以()表示,采用 t 檢驗。 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兩組康復優良率對比
相較于對照組的康復優良率50.00%,觀察組70.83%更高,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見表 2。

表2 兩組康復優良率對比[n(%)]
2.2 兩組腰椎功能及疼痛程度對比
兩組干預前的ODI 評分、VAS 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P>0.05); 兩組干預 3 個月后的 ODI 評分、VAS 評分均下降,且觀察組各項評分均低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 見表 3。
表3 兩組干預前后 ODI 評分及 VAS 評分對比[(),分]

表3 兩組干預前后 ODI 評分及 VAS 評分對比[(),分]
注:與同組干預前對比,aP<0.05
組別觀察組(n=48)對照組(n=48)t 值P 值觀察組(n=48)對照組(n=48)t 值P 值時間ODI 評分 VAS 評分干預前干預3 個月22.37±3.25 22.24±3.21 0.197 0.844 15.13±2.16a 18.28±2.19a 7.095 0.000 5.17±1.03 5.13±1.01 0.192 0.848 2.15±0.46a 2.67±0.51a 5.246 0.000
2.3 兩組生活質量對比
干預前, 兩組的GQOLI-74 各維度評分比較,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干預 3 個月后,兩組的GQOLI-74 各維度評分均上升,且觀察組各維度評分均高于對照組,差異有統計學意義(P<0.05)。見表 4。
表4 兩組干預前后 GQOLI-74 各維度評分對比[(),分]

表4 兩組干預前后 GQOLI-74 各維度評分對比[(),分]
注:與同組干預前對比,bP<0.05
組別 時間 軀體功能 心理功能 社會功能 物質生活狀態觀察組(n=48)對照組(n=48)t 值P 值觀察組(n=48)對照組(n=48)t 值P 值干預前干預3 個月60.85±6.23 61.12±6.25 0.212 0.833 89.23±5.32b 83.62±5.34b 5.156 0.000 63.13±5.39 62.94±5.41 0.172 0.864 88.11±5.61b 82.48±5.58b 4.930 0.000 62.75±6.34 62.13±6.37 0.218 0.828 87.93±6.27b 81.37±6.23b 5.142 0.000 63.69±5.42 63.41±5.38 0.254 0.800 88.54±5.23a 83.69±5.49b 4.432 0.000
3 討 論
椎間孔鏡術作為治療LDH 的常見術式, 雖具有微創、恢復快、經濟等優點,但受個體、環境因素等影響,部分患者術后康復效果較差,需輔以合理有效的手段進行干預,以促進患者術后康復[9]。 目前,臨床針對LDH 患者椎間孔鏡術后的干預多以常規康復干預為主,雖可取得一定效果,但由于該方法的訓練方式過于單一,導致整體干預效果并不理想[10-11]。 因此,尋找一種更為有效的干預方法意義重大。
祖國醫學將LDH 納入“腰痛”范疇,以瘀血腰痛證最為多見,病因病機為外邪入侵、跌仆閃挫,以致經脈受阻,氣血不暢;或氣血阻滯,瘀血留著,以致經脈痹阻,氣血不通,發為腰痛,訓練應注重活血化瘀、通絡止痛。五禽戲是一種依據中醫學陰陽五行、臟象、經絡、氣血運行規律,主要觀察禽獸活動姿態,用虎、鹿、猿、熊、鳥等動物形象、動作創編的健身功法,已在多種疾病康復中得到應用[12]。
該研究中,相較于對照組,觀察組干預3 個月后的康復優良率較高,ODI 評分及 VAS 評分較低,GQOLI-74 各維度評分較高(P<0.05),表明在 LDH 患者椎間孔鏡術后康復護理中應用五禽戲的效果較好,可促進腰椎功能改善,減輕疼痛程度,同時提高其生活質量。分析原因為,患者練習虎舉的過程,通過升降雙掌,可調理三焦功能,且手在虎爪和握拳間變化,可增強握力,有助于改善其上肢遠端功能[13]。 虎撲、鹿抵等動作通過脊柱的前后伸展折疊運動及腰部左右轉動,可增強腰部肌肉力量,有助于患者腰椎功能的改善。 鹿奔動作中,患者兩臂的內旋前伸,可牽拉其肩、背部肌肉,利于增強其腰部力量;熊運、熊晃動作中,患者通過左右晃動身體,加上落步的微震,可增強髖關節周圍肌肉的力量,提高平衡能力[14]。 猿提動作中,患者通過快速變化“猿鉤”,可增強神經-肌肉反應的靈敏性;鳥伸、鳥飛動作中,患者通過提膝獨立,可提高其平衡功能,利于腰椎功能的改善[15]。 此外,患者在展開猿提動作時,通過左右環顧帶動頸部轉動,改善了腦部血液循環,緩解患者的緊張感,可減輕其疼痛感,有助于提高患者的生活質量[16]。
綜上所述, 將五禽戲應用于LDH 患者椎間孔鏡術后康復護理中的效果良好,可改善腰椎功能,減輕疼痛程度,提升其生活質量,值得臨床推廣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