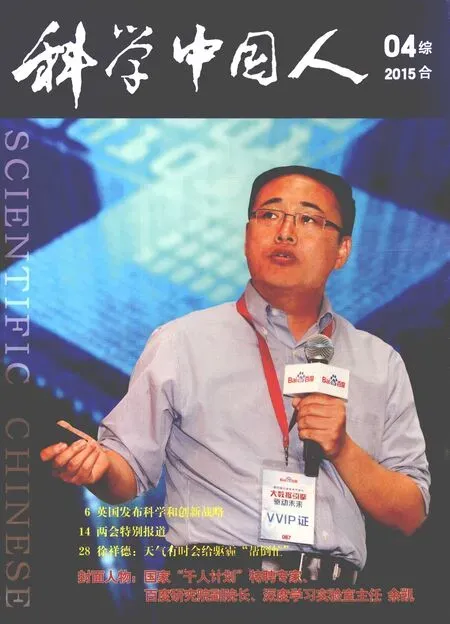心濟蒼生糧安天下
蔡巧玉



金秋十月,收獲的季節。
在田間地野考察的茹振鋼,又一次收到了從首都北京傳來的好消息——由于在小麥育種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就,茹振鋼獲得了2016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學與技術進步獎。櫛風沐雨數十載,這位堅韌不拔、執著書寫小麥傳奇的學者,終于用他刻盡風霜雨雪的勤勞雙手,獲得了來自家鄉人民、社會各界的極大肯定。
“很多人說,茹教授,以前我們一直沒能把您和那些品種優良的小麥掛上號,要不是這幾年您接連獲獎走進大家的視野,我們都不知道這些是您做的咧!”每當聽到父老鄉親說出這樣的話時,茹振鋼總是粲然一笑,說道:“不認識我沒關系,只要你們能種上優良的小麥品種就行,那才是最重要的!”在他心中,無論多高的榮譽和贊美,都比不過培育出一代代優良的小麥品種,讓人民過上豐衣足食的生活更讓他快樂和自豪。“糧安天下育蒼生”,這便是他此生最大的夢想。
一粒種子,一個世界“種子是農業的核心科技,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一個世界!”
農家少閑月,五月人倍忙。
夜來南風起,小麥覆隴黃。
每逢夏至過后,便是小麥成熟的季節了。漫山遍野翻滾著的層層麥浪,將大地染成了一片金黃。在這樣一個熱鬧與豐收的時節,茹振鋼同千千萬萬個眼望豐收的農家老漢一樣,幸福滿溢。
盡管現在的他早已與小麥融為一體,但小麥育種究竟有多重要,最開始,茹振鋼也是不清楚的。
1978年剛剛恢復高考之際,滿懷激情與抱負的茹振鋼走進了考場。盡管首擊即中,但從農村走出來、一心向往“學好數理化、振興新中華”的茹振鋼,卻被農業院校錄取了。不能一展心中抱負,還要回到田間地野,不得不說,他心里多少有些失落。
“你知道現在世界上最大的問題是什么嗎?”
“貧窮?還是戰爭?”
“你說的都不是。現在世界上沙漠化傾向越來越嚴重,等到地球都被沙漠侵襲,那人類也不能生存了。所以說,誰能將沙漠變綠洲、綠洲變糧倉,讓世人不再挨餓,那才是最了不起的事!”
高中班主任的一番話如醍醐灌頂,他意識到在田間地野一樣能干出一番大事業!出生于1958年的小鄉村,又經歷過3年自然災害的茹振鋼,原就比其他人更能理解糧食的重要性。從此之后,他便下定決心扎根農業,用科技裝滿國家的糧倉!
為了實現這個夢想,大學里,茹振鋼埋頭苦讀,一頭扎進知識的海洋,拼命汲取科學的養分:工作后,他又盡情地在田間揮灑汗水,風里雨里,一干就是30多年。
冬去春來,花謝花開。在一年又一年的默默耕耘中,茹振鋼將有用、好用的農業科技知識送到田間地頭,足跡遍布全省各地,惠及全國。
一粒種子可以改變一個世界!他深知育出好種子的分量有多重。因此,無論多忙,他都堅持親自選種,并且30余年來,先后培育并推廣了“百農62”“百農64”“百農160”和“矮抗58”等小麥新品種。特別是近些年培育推廣的“矮抗58”小麥新品種,不僅每畝小麥產量增長到1200斤,還具有抗倒伏、抗凍、抗病和耐旱等優點,迅速在黃淮海麥區推廣開來。截至2016年夏收,“矮抗58”已累計種植超過3億畝,增產小麥121.1億公斤,實現增產效益300多億元,被譽為“黃淮第一麥”。
“我國最大的一塊麥田就在我們黃淮區域,2億3000多萬畝,播種面積最適宜小麥生長。土壤條件好、產量又高、面積又大,擁有這樣一個得天獨厚的優良條件,我們就更應該努力,進一步提高小麥的產量水平,簡化生產過程,使之成本越來越低、產量越來越高、品質越來越好,不僅能滿足中國人的飯碗需求,還能支援世界,這些就是我們最想做的事!”茹振鋼笑著說道,語氣中充滿了對未來的無限信心與向往。
腳下雖是方寸,方寸間自有乾坤。他的目光,早已飛出了眼前的田野,飛到了全國各地,飛向這廣闊無垠的碧綠蒼穹!
鋼鐵是怎樣煉成的“事業需要傳承,精神也是。”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如果說,早期生活的困頓艱難造就了茹振鋼堅韌不拔、不畏困難的執著精神:那么,一路走來,那些德藝雙馨的前輩導師、一次次付出與收獲的快樂,早已將那一縷無私奉獻的精魄刻進他的靈魂,造就了如今無堅不摧、頑強堅韌的茹振鋼。
“我的導師黃光正先生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科學家,他對我的影響、對我們團隊的影響是巨大的。”不論取得了何種獎項和榮譽,茹振鋼總會想起恩師黃光正教授,他是茹振鋼心中一面永不倒下的旗幟。
1981年,23歲的茹振鋼從中牟農業學校(現河南農學院)畢業后,被正式分配到百泉農專(現河南科技學院),并有幸投身于當時育種界赫赫有名的國家級專家黃光正教授門下,從此跟隨導師開啟了他漫長艱辛的小麥育種生涯。
為了確保科研數據的完整性和準確性,幾十畝的試驗小麥,黃光正經常帶著茹振鋼深入田野,一株一株地手工脫粒,一連幾個星期,任憑風吹日曬、滿面塵霜,癡心不改。
“老先生的家鄉在廣東,家庭條件其實很好,但他卻選擇了育種事業,離開家鄉扎根河南,非常不容易。”茹振鋼說。
盡管出身優越的家庭環境,但黃光正卻放棄了家鄉富裕優渥的生活,一心扎根河南,服務河南農業。在茹振鋼的記憶中,工作中的黃教授,謹慎細致又敢于創新:生活中他為人謙和,平易近人,從不擺架子,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接地氣的”土教授”。最讓他感動的是導師想人之所想,急人之所急,處處為學生著想的高尚品質,他們是師生,更是摯友。正是黃光正教授對科研事業孜孜不倦、精益求精的精神深深影響了茹振鋼,也成為了他的科研和人生寫照。
然而,誰也沒有想到的是,這段寶貴的師生情只維系了不到7年時光。
1988年,長期殫精竭慮、嘔心瀝血的黃光正病倒了,等到醫院診斷結果出來時已經是肝癌晚期。當茹振鋼接到醫院病危通知趕到先生的病榻前,看到的就是他疼痛難忍、渾身冒汗的場景。
“從昏迷中醒過來的先生,看到我的第一眼就問,‘你什么時候來的?有沒有吃飯?到那個時候了,他競然還只想著關心別人,令人心如刀絞!”回憶到這里,茹振鋼的語氣中充滿了悲痛與懷念。更讓他沒想到的是,得知自己已經用過餐的老師,第二句話就是趕他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