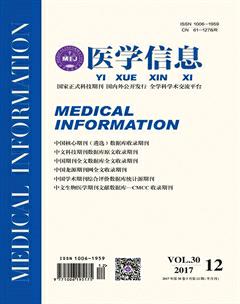精神疾患ICD—10分類疑難編碼及錯(cuò)碼成因探討
郝放
摘要:目的 根據(jù)醫(yī)院中存在的關(guān)于疑難編碼以及錯(cuò)碼形成原因的問題進(jìn)行深入研究,目標(biāo)主要在于分析精神疾患ICD-10分類中可能存在的難題以及造成錯(cuò)碼的原因。方法 將本醫(yī)院2014年3月~2016年8月住院進(jìn)行治療的患者中抽取160例,查找相關(guān)文獻(xiàn)中的資料予以參考,對160例情況再次審核,并做出一定的統(tǒng)計(jì)學(xué)研究。結(jié)果 本次進(jìn)行抽樣調(diào)查的160例中,32例存在錯(cuò)誤的編碼,其比例是20%。40例屬于疑難編碼,其比例是25%。可見錯(cuò)誤的編碼較多,比例明顯超過制定的標(biāo)準(zhǔn)。結(jié)論 為了應(yīng)對精神疾病 ICD-10分類中存在的錯(cuò)誤編碼以及疑難編碼明顯超過制定標(biāo)準(zhǔn),決定對原本存在問題的分類技術(shù)做出改良,同時(shí)應(yīng)該深入分析各種精神疾病的醫(yī)學(xué)概念、臨床癥狀、病癥產(chǎn)生的生理原因以及心理原因、與該疾病有關(guān)的健康情況的國際統(tǒng)計(jì)分類,只有這樣才可以對錯(cuò)誤編碼的存在做出一定的限制,使疑難編碼擁有更加合適的分類。
關(guān)鍵詞:精神疾患ICD-10分類;疑難編碼;錯(cuò)碼成因
在現(xiàn)代醫(yī)學(xué)史中,國際疾病分類(ICD-10)作為一種廣泛運(yùn)用的病例管理工程,而這之中的精神疾患的ICD-10分類則是ICD的分類學(xué)中十分重要的一種,可以幫助醫(yī)者更為準(zhǔn)確的區(qū)分病癥類別,避免由于錯(cuò)判誤判產(chǎn)生的對于治療的不良影響[1]。但是因?yàn)榫窦膊〉呐R床癥狀比較復(fù)雜,而且引起精神病的原因也有所不同,因此對于神經(jīng)病的分類以及確診存在著很大的分歧,各種派別沒有達(dá)成一致。雖然關(guān)于精神病的研究已經(jīng)存在較為長久的歷史,而且某些部分爭議并不大,但是缺乏達(dá)成一致的名詞學(xué)對這些現(xiàn)象做出系統(tǒng)官方的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