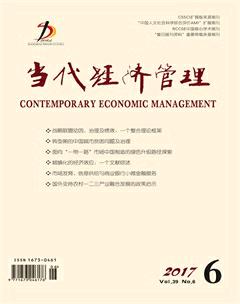城鎮化的經濟效應:一個文獻綜述
摘 要 城鎮化是現代化進程中最富活力的經濟社會活動,對經濟發展具有重要影響效應,一直以來深受學術界和政府部門的高度關注。因此,學術界和實踐界迫切需要梳理關于城鎮化經濟效應及其作用機理的相關研究。文章基于既有文獻成果,系統回顧和梳理了城鎮化對經濟增長、居民消費、產業發展、二元結構以及公共服務供給影響效應的理論與實證研究,闡明了城鎮化驅動經濟增長、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以及改善民生福祉的運行機制,為我國科學推進新型城鎮化戰略提供了有益的理論依據,也為今后新型城鎮化的經濟效應有效惠及民生提供了一個系統的理論分析框架。
關鍵詞 城鎮化; 新型城鎮化;產業結構升級;公共服務供給;經濟效應
[中圖分類號]F12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461(2017)06-0050-05
在當前世界經濟再平衡和再調整的復雜形勢下,我國經濟增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經濟轉型面臨多重挑戰,如何有效化解這些不利因素,確保我國經濟可持續發展,關鍵是要尋求引領經濟可持續增長的新動力和新途徑。經濟理論和實踐表明,工業化創造供給,而城鎮化則創造需求。因此,在外需不足、傳統投資過剩、內部需求尤其是消費需求疲軟的新情境下,城鎮化理所當然成為今后推動我國內需的重要平臺和有效載體。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曾經指出21世紀影響世界進程的兩件大事是美國的高科技和中國的城鎮化。隨著我國城鎮化率在2011年突破50%之后,意味著我國的城鎮化發展進入了新的發展周期,即進入倡導以人為核心以及提質增效的新型城鎮化階段。新型城鎮化重在體制機制創新,通過不折不扣的實施新型城鎮化戰略,將有效提高經濟增長質量、刺激居民消費、推動產業結構升級和全面改善民生,這些都將產生廣泛的經濟效應,對新常態階段中國經濟發展具有深遠意義。因此,為有效推進新型城鎮化戰略實施以及新常態階段我國經濟成功轉型,系統歸納和梳理城鎮化的經濟效應就顯得尤為必要,具有重要的理論參考價值和現實指導意義。
中國城鎮化發展歷史悠久,在世界城鎮化的歷史長河中長期占據領先地位,如唐代曾與300多個國家有過貿易往來,當時的長安城鎮人口達60余萬,絲綢之路經濟全線暢通,宋代經濟發展達到了高峰,中國人口首次突破1億,出現了如開封這樣的百萬人口的大城市,形成了全球最大的內需市場,此時中國城鎮化和工商文明曾達到了歷史上的空前繁榮。但自明清代以來,中國選擇了閉關鎖國和背對世界的治國之策,加上西方國家工業革命的誕生,世界時針開始偏離東方文明,逐漸指向西方文明,伴隨著工業化的快速推進,市場經濟的不斷繁榮,城鎮化問題不斷進入廣大學者們的研究視域,城鎮化與經濟發展論題也被學者們日益重視和關注,以斯密為代表的古典經濟學家對城鎮化發展的相關問題進行了系統的闡述(米爾斯,2003),但在新古典經濟學的論述中,具有空間特點的城鎮化問題長期被忽略,使城鎮化難以登入主流經濟學的大雅之堂,直到20世紀50年代,城市和城市化的相關研究才又一次被重視起來。中國的城鎮化源遠流長,但真正的快速發展時期是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這30多年,可謂早慧而晚熟。與此同時,我國城鎮化研究工作也相對滯后,吳友仁1979年《關于中國社會主義城市化問題》一文的發表才徹底揭開了中國城市化研究的序幕(顧朝林和吳莉婭,2009[1]),之后城市化問題得到了學術界的日益關注并且取得了階段性的重要研究成果。本文基于既有文獻,重點對城鎮化的經濟效應的理論與實證研究成果進行系統梳理,回顧城鎮化的經濟增長效應、居民消費增長效應、產業結構優化效應、二元結構消解效應、公共服務供給效應,闡明城鎮化驅動經濟增長、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以及改善民生福祉的運行機制,為新型城鎮化的經濟效應有效惠及民生提供了一個系統的理論分析框架。
一、城鎮化的增長效應
1.城鎮化的經濟增長效應
城鎮化是經濟社會高級化發展的必然路徑,而經濟增長又是經濟學研究無法繞開的一個經典命題,關于城鎮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相互作用及其內在機理,國內外學者持有差異化的觀點和結論。國外學者的學術研究起步較早,起初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經濟增長與過度城市化方面(Davis & Golden,1954;Sovani,1964;McCoskey & Kao,1998 ),之后主要探析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效應,大致可歸納為兩種截然不同的研究結論:一種結論認為城鎮化對經濟增長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是經濟增長的有效牽引力。Lucas(1988)基于內生增長模型重估了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作用關系,指出城市在經濟增長過程中起到舉足輕重的促進作用。Henderson(2003)利用不同國家的截面數據分析得出城市化水平與人均GDP對數之間的相關系數為0.85。Krey et al.(2012)[2]、Bruckner(2012)[3]在一定程度上對上述結論給予了肯定,也得出了基本相似的研究結論,同時以發展中國家為樣本進行重點實證分析,認為城鎮化對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正向推進作用尤為明顯。另一種結論則與第一種結論相悖,認為城鎮化并不能從根本上促進一國的經濟增長。Bloom & Canning(2008)[4]發現城市化對經濟增長率沒有影響效應,任何國家寄希望以城市化來達到經濟長期增長的目標都可能無法實現,Shabu(2010)[5]的研究也認為城鎮化與經濟增長之間并不存在必然的正向促進作用。國內學者的研究成果主要基于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增長與快速城鎮化之間的相互作用,一方面發現二者存在明顯的同向變動關系(徐雪梅和王燕,2004;李金昌和程開明,2006[6];程開明,2007;周小剛和陳東有,2008;賈云赟,2012[7];張彧澤和胡日東,2014;周慧,2016[8])。但另一方面也存在不同觀點,認為城市化與經濟增長不存在雙向互動的因果關系,若長期將城鎮化作為驅動經濟增長的籌碼,會嚴重影響城鎮化質量和經濟增長質量,也難以實現城鎮化推動經濟增長的預期效果(黃婷,2014[9]),傳統的城鎮化是一種高速度、低質量、重投資的城鎮化,本質上主要以投資為重要渠道來驅動經濟增長,而對能夠代表城市基本特點的消費性需求的釋放有限(王婷,2013[10])。作為一個全新的中國式命題,對新型城鎮化的經濟增長效應的觀點基本一致,即新型城鎮化不同于傳統城鎮化,能為中國經濟增長提供中長期的增長動力(孔令剛和蔣曉嵐,2013;張占斌,2014[11])。
2.城鎮化的居民消費增長效應
通過對城鎮化與居民消費增長研究成果的系統梳理,發現廣大國內外學者研究結論大致可以歸納為以下兩種。一部分學者認為城鎮化對于消費增長具有明顯的正向促進作用, Daniels et al.(1991)以美國為例,發現城市化推動居民消費增長的內在傳導機制主要體現在城鎮化能夠催化區域性消費市場。Fujita et al.(1999)研究得出城鎮化能通過“集聚效應”和“規模效應”促進消費需求擴張的結論,表明在經濟結構優化和產業結構升級過程中,人口、資本等重要生產要素高度集中于城市,促進了區域整體消費需求的加速擴張(Henderson,2005[12])。周建和楊秀禎(2009)[13]認為城鎮化對農民的消費行為具有明顯的刺激效應。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10)[14]、鄒紅和喻開志(2011)等的研究也得出基本類似的結論。趙永平和徐盈之(2015)認為新型城鎮化對居民消費增長具有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但另一部分學者卻持相反的觀點,認為城鎮化的迅速發展和擴張并沒有帶來居民消費的持續增長,城鎮化的居民消費貢獻率幾乎可以忽略(范劍平和向書堅,1999;劉志飛和顏進,2004;羅軍和鐘誠,2012[15]),從城鎮化與消費傾向的變化關系來看,兩者并不存在直接的關聯效應,城鎮化并不是居民消費增長的重要推動力量(石凱和聶麗,2014[16])。新型城鎮化是對舊型城鎮化的全面校正和系統優化,重在制度創新,有利于消費層次和能力的進一步提升(柳汶秀和趙新宇,2013[17]),有利于破除土地制度、戶籍制度以及社會保障制度等各種阻礙新型城鎮化發展和影響居民消費能力的各種制度藩籬,破解城鄉二元結構以及城鎮內部的新二元結構,加快城鄉一體化發展進程,全面釋放蘊藏在城鎮和農村的潛在消費需求(謝淑娟,2014[18]),有利于提高居民真實的消費水平和保證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楊靜和張光源,2014[19]),推動農民工市民化進程,使其消費結構和消費能力提檔升級(顧紀瑞,2014[20])。由此可見,新型城鎮化不同于傳統城鎮化,二者對居民的消費增長效應完全不一樣,從既有文獻可以看出學者們一致認為新型城鎮化對居民消費增長具有積極的促進效應。
二、城鎮化的產業結構優化效應
隨著經濟結構優化以及社會的高級化發展,城鎮化的步伐不斷加快,各種生產要素從第一產業向第二、三產業迅速流動和集聚,特別是對第三產業或服務業占比的迅速上升起到了積極促進作用,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城鎮化與產業發展之間存在著十分密切的關系。從現有研究成果來看,國內外學者對城鎮化與產業結構升級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許多有價值的研究,由此形成較為統一的結論,即城鎮化可有效的促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人口的集聚化發展,有利于思想交鋒、資源共享、信息交流和技術創新,對優化和提升城鎮化效率具有重要影響,城鎮化的高效率可以吸引更多的資源和人才,能夠產生重要的規模效應和和聚集效應,進而提高二、三產業的全要素生產率(Glaeser,2011)。任何產業的高級化發展都與其空間載體的不斷升級變換緊密相關(李誠固等,2004;苗麗靜和王雅莉,2007),可見隨著城鎮化發展水平的日益提高,其對產業結構升級的推進作用逐漸增強(劉艷軍等,2006;黃曉軍等,2008),城鎮化進程推動了產業的分工與重組,有利于現代新興產業和服務業的集聚發展(Kolko,2010;Michael et al.,2012[21];吳雪玲,2013[22];張占斌,2013[23]),應將城鎮化與調整產業結構、培育新興產業、發展服務業、促進就業創業有機結合起來(李克強,2012[24])。同時在城鎮化發展進程中,城市群或城市帶將成為今后城鎮化發展的主體形態,城市群或城市帶的要素空間集中產生的正向外部性以及人才要素集聚導致的技術創新水平的提升將對區域產業創新體系以及產業結構轉型優化產生重要的推進效果(吳福象和沈浩平,2013[25])。目前城鎮化率已經達到56.1%,意味著我國已經實現了從傳統的農村社會向現代的城市社會轉變,我國城鎮化進入新一輪的發展階段,因此,新型城鎮化道路成為今后城鎮化發展的必然方向和時代選擇,它強調以人為核心,倡導產業與城鎮互動的發展模式,有利于推動現代制造業、生產服務業和消費服務業的繁榮發展,有效推動產業結構升級。新型城鎮化強調從要素驅動走向創新驅動的轉變,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使新型城鎮化與新型工業化同步發展(辜勝阻和劉江日,2013[26])。新型城鎮化將產生巨大消費和投資需求,有利于帶動一系列相關產業的發展,使新型城鎮化與服務業的快速發展相呼應(中國金融40人論壇課題組,2013[27])。新型城鎮化的集聚效應、規模效應和分工協作效應能夠推動產業結構的高級化發展(黃錕,2014[28]),新型城鎮化與產業結構升級存在著顯著的空間相關性(藍慶新和陳超凡,2013[29]),作用程度按東部、西部、中部依次增強,呈現明顯的區域分異特征(趙永平和徐盈之,2016[30])。
三、城鎮化的民生改善效應
1.城鎮化的二元結構消解效應
涉及城鎮化與城鄉收入差距內在機理與作用關系的研究數量可觀,但從研究結論來看,依然存在分歧,并沒有形成被廣大學者普遍接受的統一性觀點。Lewis(1954)認為通過不斷地將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轉移,最終可以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Robinson(1976)則認為城鎮化與城鄉收入差距之間的關系表現為倒U型。藤田昌久(2011)的研究表明城市化有利于全社會福利水平的改善,但由于要素資源的空間集聚效應,城市的福利水平相比農村提升更為迅速,導致城鄉收入差距進一步擴大化。因此,關于城鎮化與城鄉收入差距的作用關系基本可以梳理為如下三個方面:第一,城鎮化弱化了城鄉收入差距。城市最重要的一個功能就是集聚,對人口、要素和其他資源等都具有很強的吸附力,城市本質上是一個消費中心,第三產業是城市的主要產業形態,隨著經濟全面轉型和產業結構高級化發展,服務業占比將日益增大(Keeble & Nacham,2002),三次產業中服務業的吸附勞動力能力最強,是有效轉移農村剩余勞動力的重要載體,從而提高農村居民收入,達到弱化城鄉收入差距的目標(Blum,2008[31];Mehta & Hasan,2012[32];陸銘和陳釗,2004;姚耀軍,2005;孫永強,2012[33];王學龍等,2012[34];李伶俐等,2013[35];劉雪梅,2014[36])。第二,城鎮化對城鄉收入差距的影響呈現先擴大后縮小的倒U型變化形態。從理論上講,當農村勞動力轉移到達劉易斯拐點時,農業勞動力報酬就開始上升,因此,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必然呈倒U的變化過程。Glomm(1992)、Anand(1993)和陳宗勝(1994)等學者從理論上對二者的倒U型變化關系進行了系統研究和證明。王小魯和樊綱(2005)的實證檢驗結果表明城鄉收入差距具有庫茲涅茨曲線特征,而且長期處于上升段,與王亞芬等(2007)的研究結論基本相同。莫亞琳和張志超(2011)[37]的研究表明,在城市化快速發展階段或初級階段將出現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態勢,當城市化處于成熟發展階段時,城市化將有利于弱化城鄉收入差距。周云波(2009)[38]通過理論分析與實證研究發現城市化是倒U現象出現的主要原因。第三,城鎮化加劇了城鄉收入差距。大量研究表明我國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以及由此衍生的一整套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是造成城鄉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林毅夫和劉培林,2003;林毅夫和劉明興,2003)。研究表明,政府的城市化偏向政策和城鄉二元經濟結構是國內收入分配差距不斷擴大的主要因素(陶然和劉明興,2007;程開明和李金昌,2007;雷根強和蔡翔,2012[39];胡晶晶和黃浩,2013[40])。
2.城鎮化的公共服務供給效應
城鎮化不僅是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進入城鎮,更為重要的是農村轉移人口進入城鎮后,就涉及新進人口的教育、醫療、保障和住房等方面的公共服務產品需求及配套問題,即如何全面覆蓋既有城鎮和新進入城鎮人口的公共服務,進而實現城鎮內部的公共服務均等化問題。因此,城鎮化進程中的公共服務供給問題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熱點,大量研究表明城鎮化有利于提升公共服務水平,但隨著經濟社會的縱深發展,城鎮化進程中公共服務分布不均衡、城鄉公共服務非均等化等問題日益凸顯,引起廣大學者的高度關注。主流公共產品理論認為,公共產品的外部性和“搭便車”等屬性決定了市場在該領域不能發揮其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也即存在市場失靈,因此政府成為公共產品最合適的供給者。Buchanan & Congleton(2006)基于“普遍性原則”明確界定了政府與市場的基本功能,指出政府必須按照均等化的原則為居民提供公共服務產品。在公共服務產品供給過程中應該形成政府、市場、社會與公眾多主體的協同互動機制(Denhardt,2000)。實踐表明中國的城市化進程顯著地影響了各地區公共服務的提供水平與規模(王偉同,2009[41]),但我國城鎮化發展水平的不斷提升與公共服務產品供給能力提升的步調并不協調(李燕,2013[42])。一貫的GDP錦標賽導致地方政府財政支出長期處于“重基本建設、輕人力資本投資和公共服務”的扭曲化分配狀態(傅勇和張晏,2007[43];丁輝俠,2012[44]),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更是迫于經濟增長的壓力,往往把做大GDP作為區域經濟發展的第一要務,對涉及民眾基本福利、公共服務以及生活質量的提升關注并不夠(徐盈之和吳海明,2010[45]),轉移支付項目并不能彌補地區財力差異,公共服務差距長期得不到改善(Tsui,2005[46])。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政府支出責任安排對交通基礎設施和醫療衛生服務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對基礎教育具有負向影響但并不顯著(賈俊雪,2012[47])。我國大部分地區依然存在義務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龔鋒和盧洪友,2013[48])。新型城鎮化重在破除體制機制的制度藩籬,打破城鄉區域雙重二元結構,改變以往以財政供給戶籍人口計算地方財力的傳統做法,按國際慣例實行常住人口均衡分配,使居民享受公共服務不再受戶籍限制(孫紅玲,2013[49]),因此,在新一輪的城鎮化進程中,應按照基本公共服務的流動性和邊際成本對其進行劃分,并據此來確定城鎮化進程中各級政府支出責任及成本分擔機制(童光輝和趙海利,2014[50])。顯然,不同于以往傳統城鎮化的公共服務供給模式,新型城鎮化重在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和進一步改善民生。
四、結 語
通過對既有大量文獻的追溯和梳理,發現國內外學者從多個層面系統分析了城鎮化的經濟效應,拓寬了城鎮化對經濟發展作用機理的認識,為新一輪城鎮化更好的發揮其積極作用提供了重要的研究基礎與理論啟示,但已有研究成果大部分基于傳統城鎮化的視角,而且其衡量指標基本都選取官方公布的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根據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的口徑,當前中國城鎮化率已經跨過了50%的歷史性門檻達到56.1%的水平,但這種數字成就背后是傳統城鎮化三十多年高速度、低質量的壓縮式發展,而真實的城鎮化率或戶籍人口城鎮化率僅為37%左右,存在嚴重的虛高成分,“半截子”城鎮化問題突出,城鎮內部的新二元結構亟待解決,傳統的城鄉二元結構慣性依然不減,城市經濟的結構性矛盾日益凸顯,多元社會性矛盾交織性出現,這些已經成為當前城鎮化發展之痛,傳統城鎮化面臨空前挑戰,已經無法承載當前城鎮化發展的所有內涵,亟須向以人為核心和注重質量的新型城鎮化轉變。新型城鎮化并不是對傳統城鎮化的全面否定,而是對傳統城鎮化的校正與優化,是內需的最大潛力,是改革發展的最大紅利,是改善民生的重要途徑,對經濟發展具有重大的影響效應。但遺憾的是,新型城鎮化的相關研究才剛剛起步,研究成果比較有限,目前對新型城鎮化的經濟效應研究大都還停留在政策的解讀和觀點的陳述等定性與規范研究層面,缺少全面、深入和系統的定量或實證研究。因此,客觀測度和反映我國新型城鎮化發展水平,突破傳統城鎮化重點關注經濟增長目標的研究定式,堅持以人為本、提質增效、科學發展、循序漸進、和諧共享的發展理念,破除禁錮城鎮化發展的各種制度藩籬、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級、有效破解新舊二元結構、推動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釋放新型城鎮化巨大的增長與發展潛力,進而重構新型城鎮化與經濟發展互動發展的研究框架。在此框架下考察新型城鎮化對化解我國各種經濟發展瓶頸問題的可行性和有效性,探索新型城鎮化推進我國經濟轉型發展的可行路徑與作用機理,提出具有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從而使城鎮化的經濟效應有效惠及民生,使全體人民共享現代城鎮發展的文明成果。
[參考文獻]
[1] 顧朝林, 吳莉婭. 中國城市化研究主要成果綜述[J]. 新華文摘, 2009(6): 151-155.
[2] Krey V, O'Neill B C, van Ruijven B, et al. Urban and rural energy use and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Asia[J]. Energy Economics, 2012 (34): 272-283.
[3] Bruckner M. Economic growth, size of the agricultural sector and urbanization in Africa[J]. Journal of Urban Economics, 2012, 71(1): 26-36.
[4] Bloom D E, Canning D, Fink G. Urbanization and the wealth of nations[J]. Science, 2008, 319(5864): 772-775.
[5] Shabu 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urbaniz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eveloping countrie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esearch and Investment, 2010, 1(2):30-36.
[6] 李金昌, 程開明. 中國城市化與經濟增長的動態計量分析[J]. 財經研究, 2006(9): 19-30.
[7] 賈云赟. 城鎮化、工業化、農業現代化與經濟增長關系研究[J]. 城市發展研究, 2012(12): 27-32.
[8] 周慧. 城鎮化、空間溢出與經濟增長——基于我國中部地區地級市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J]. 上海經濟研究,2016(2):93-102.
[9] 黃婷. 論城鎮化是否一定能夠促進經濟增長:基于19國面板VAR模型的實證分析[J]. 上海經濟研究, 2014(2): 32-40.
[10] 王婷. 中國城鎮化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及其時空分化[J]. 人口研究, 2013(5):53-67.
[11] 張占斌. 經濟中高速增長階段的新型城鎮化建設[J]. 國家行政學院學報, 2014(1): 39-45.
[12] Henderson J V, Logan J R, Choi S. Growth of China's medium-size cities[J]. Brookings-Wharton Papers on Urban Affairs, 2005, 33(3):263-303.
[13] 周建, 楊秀禎. 我國農村消費行為變遷及城鄉聯動機制研究[J]. 經濟研究, 2009(1):83-95.
[14]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 農民工市民化對擴大內需和經濟增長的影響[J]. 經濟研究, 2010(5): 4-16.
[15] 羅軍, 鐘誠. 我國流動性過剩問題研究[J]. 宏觀經濟研究, 2012(11):18-24.
[16] 石凱, 聶麗. 城鎮化對城鄉居民消費的影響[J]. 城市問題, 2014(6):87-93.
[17] 柳汶秀,趙新宇. 新型城鎮化進程中擴大內需的對策[J]. 經濟縱橫,2013(11):41-43.
[18] 謝淑娟. 在新型城鎮化建設中擴大農村居民的消費[J]. 宏觀經濟管理,2014(11):74-77.
[19] 楊靜,張光源. 推進 “三個同步轉變” 的新型城鎮化:以農民工市民化為突破口[J]. 中州學刊,2014(6): 41-46.
[20] 顧紀瑞. 新型城鎮化將推動消費潛力釋放: 以江蘇省為例[J]. 消費經濟,2014(12):3-6.
[21] Michaels G,Rauch F,Redding S. Urbanization and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J].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2012,127(2):535-586.
[22] 吳雪玲,鄧偉,謝芳婷,等. 四川省產業結構演變的城市化響應研究[J]. 地理科學,2013(9):1066-1073.
[23] 張占斌. 新型城鎮化的戰略意義和改革難題[J]. 國家行政學院學報,2013(1): 48-54.
[24] 李克強. 協調推進城鎮化是實現現代化的重大戰略選擇[J]. 行政管理改革,2012(11): 4-10.
[25] 吳福象,沈浩平. 新型城鎮化、基礎設施空間溢出與地區產業結構升級: 基于長三角城市群16 個核心城市的實證分析[J]. 財經科學,2013(7): 89-98.
[26] 辜勝阻,劉江日. 城鎮化要從“要素驅動”走向“創新驅動”[J]. 人口研究,2013(6): 3-12.
[27] 中國金融40人論壇課題組. 加快推進新型城鎮化:對若干重大體制改革問題的認識與政策建議[J]. 中國社會科學,2013(7):59-76.
[28] 黃錕. 中國城鎮化的最新進展和目標模式[J]. 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2): 109-116.
[29] 藍慶新,陳超凡. 新型城鎮化推動產業結構升級了嗎? ——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空間計量研究[J]. 財經研究,2013(12): 57-71.
[30] 趙永平,徐盈之. 新型城鎮化、技術進步與產業結構升級——基于分位數回歸的實證研究[J]. 大連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2):56-64.
[31] Blum B S. Trade,technology and the rise of the service sector: the effects on US wage inequality[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conomics,2008,74(2): 441-458.
[32] Mehta A,Hasan R. The effects of trade and services liberalization on wage inequality in India[J].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Economics & Finance,2012(23):75-90.
[33] 孫永強. 金融發展、城市化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研究[J]. 金融研究,2012(4):98-109.
[34] 王學龍,于瀟,白雪秋. 破解城鄉差距之困: 基于勞動力流轉模型的實證分析[J]. 財經研究,2012(8):38-48.
[35] 李伶俐,谷小菁,王定祥. 財政分權、城市化與城鄉收入差距[J]. 農業技術經濟,2013(12):4-14.
[36] 劉雪梅. 新型城鎮化進程中農村勞動力轉移就業政策研究[J]. 宏觀經濟研究,2014(2): 81-86.
[37] 莫亞琳,張志超. 城市化進程、公共財政支出與社會收入分配——基于城鄉二元結構模型與面板數據計量的分析[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1(3): 79-89.
[38] 周云波. 城市化、城鄉差距以及全國居民總體收入差距的變動 ——收入差距倒 U形假說的實證檢驗[J]. 經濟學季刊,2009(4):1239-1256.
[39] 雷根強,蔡翔. 初次分配扭曲、財政支出城市偏向與城鄉收入差距——來自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經驗證據[J]. 數量經濟技術經濟研究,2012(3):76-89.
[40] 胡晶晶,黃浩. 二元經濟結構、政府政策與城鄉居民收入差距: 基于中國東中西部地區省級面板數據的經驗分析[J]. 財貿經濟,2013(4):121-129.
[41] 王偉同. 城市化進程與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J]. 財貿經濟,2009(2): 40-45.
[42] 李燕,袁崇法,白南風,等. 我國城鎮化與公共服務均等化實證研究[J]. 城市觀察,2013(6):135-144.
[43] 傅勇,張晏. 中國式分權與財政支出結構偏向: 為增長而競爭的代價[J]. 管理世界,2007(3): 4-12.
[44] 丁輝俠. 財政分權、制度安排與公共服務供給: 基于中國省級面板數據的實證分析[J]. 當代經濟科學,2012(5): 105-111.
[45] 徐盈之,吳海明. 環境約束下區域協調發展水平綜合效率的實證研究[J].中國工業經濟,2010(8):34-44.
[46] Tsui K. Local tax system,intergovernmental transfers and China's local fiscal disparities[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2005,33(1): 173-196.
[47] 賈俊雪. 政府間財政收支責任安排與地方公共服務均等化: 實證研究[J]. 中國軟科學,2012(12): 35-45.
[48] 龔鋒,盧洪友. 財政分權與地方公共服務配置效率:基于義務教育和醫療衛生服務的實證研究[J]. 經濟評論,2013 (1): 42-51.
[49] 孫紅玲. 推進新型城鎮化需改按常住人口分配地方財力[J]. 財政研究,2013(3): 56-58.
[50] 童光輝,趙海利. 新型城鎮化進程中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財政支出責任及其分擔機制[J].經濟學家,2014(11):32-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