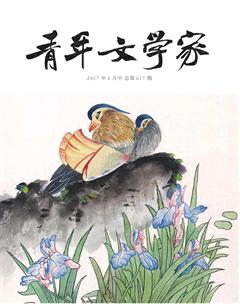“闖關東”與東北文化流變
段雨霖+高志偉+康香瑩+張婷
課題項目:本研究為2016年大學生創業創新計劃項目“從‘闖關東透視東北民俗變遷”成果之一,項目編號:x201610140015,負責人:高志偉;參與人:段雨霖、康香瑩、張婷。
摘 要:晚清以來,山東人民開始了“闖關東”,隨著大批移民進入東北,山東人民獨特的個性特征,生活方式,社會習俗都對東北原住民產生了深刻的影響,東北的文化習俗隨之發展演變,逐漸形成如今的“關東風情”,并孕育出內涵豐富的“闖關東”精神。而這種精神在今天仍然煥發生機,具有珍貴的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
關鍵詞:“闖關東”;關東風情;東北文化;現實意義
作者簡介:段雨霖(1997-),男,漢族,遼寧沈陽人,遼寧大學文學院2015級漢語言文學在讀本科生;高志偉(1995-),男,漢族,遼寧葫蘆島人,遼寧大學文學院2015級漢語言文學在讀本科生;康香瑩(1997-),女,漢族,河南蘭考人,遼寧大學文學院2015級漢語言文學在讀本科生;張婷(1997-),女,漢族,河南鄧州人,遼寧大學文學院2015級漢語言文學在讀本科生。
[中圖分類號]:G127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17-0-02
清末以來,由于天災人禍等諸多因素,大批山海關內的民眾被迫開始了“闖關東”。其中占比重最大的是山東人。本文以清末民初山東人“闖關東”事件為線索,從文化交流與民俗變遷的角度,試圖探尋“闖關東”對東北文化的影響,進而挖掘“闖關東”的時代意義。
一、探尋山東人“闖關東”
回顧歷史,我們會發現,“闖關東”既是大規模人口遷移史,又是悲愴的人民苦難史,更是不屈不撓的奮斗史。百余年間,數代移民的血淚與汗水,鋪成了漫漫移民之路,通向神秘未知的關東大地。
1.大規模人口遷移史
清朝末年,山東接連出現嚴重的自然災害。據《膠澳志》記載,咸豐五年(1855)黃河改道,自此到1912年,山東僅僅因為黃河決口就有52年之多,共決口263次,成災966縣次。[1]災害也導致了嚴重的人禍,清末一直到民國,社會持續動蕩不安,戰爭頻頻發生,人民一直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先后有太平天國的軍隊,八國聯軍,義和團,軍閥混戰等沖擊著這片多災多難的土地。于是,山東人民被迫背井離鄉,開始了大規模的人口遷移,“根據1921年至1930年歷年移民東三省的統計,10年內共移入618萬余人,移出326萬余人,留居者為291萬余人。”[2]如此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可見一斑。
2.悲愴的人民苦難史
在移民東北的漫漫征途上,山東人民用汗水與血淚寫下一部苦難史。故土難離,更何況是要離開祖祖輩輩生活的土地,前往千里迢迢的關外,其中的艱難險阻可想而知。因飽受戰亂、天災、饑餓和苛捐雜稅而背井離鄉的山東人,在“闖關東”途中必須經歷的不僅僅是疲憊的奔波,政府的阻撓,土匪的搶劫,更為凄慘的是命喪黃泉,客死他鄉。即使成功到達目的地,他們面前的也絕非一勞永逸,而是東北特有的寒冷氣候和當地人的排斥。
3.不屈不撓的奮斗史
山東人來到東北后,開始任勞任怨地用辛勤的雙手創造未來。在東北的白山黑水間,他們或開墾土地,自力更生;或經營商業,開辦商店;或從事工商業,辛勤勞動。《山東之苦力》中寫道:“彼等于旅行途中,能忍風霜雨雪之苦,敝衣襤褸,毫不介意……入夜不肯投宿客棧,常橫臥于人家之檐下。”[3]正是山東人民艱苦奮斗真實寫照。他們的辛勤付出超乎常人的想象,也正是這樣堅持不懈地奮斗使得山東人在白山黑水的土地上生根發芽,頑強不屈地生存下來。
二、“闖關東”對東北精神文化影響
山東人“闖關東”,不僅帶來了大量的勞動力人口,為東北注入了新鮮的“血液”,同時這樣一次大規模的移民運動本身也實現了跨區域文化的碰撞與交融。山東獨特的齊魯文化與東北的滿族文化,山東人與東北原住民不同的性格、習俗、喜好之間互相融合,塑造出東北人的性格,極大地豐富了東北的文化,形成了獨具魅力的關東風情。其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層次:
首先,“闖關東”本身就具有了極為豐富的文化價值,正如上文所述,作為一部慘痛的苦難史,它已經融入東北人血液中,滲透到骨髓里,成為一種深刻和久遠的文化印記,成為一代人的祖祖輩輩傳承的共同記憶。山東人民,東北人民都自發地通過各種藝術形式表現當時的“災難史”,例如“禿尾巴老李”的傳說。其主要流傳在山東、遼寧、吉林等地,大致內容是:山東文登一對夫婦生下一條小龍,小龍的父親一氣之下砍掉了他的尾巴,小龍從此得名“禿尾巴老李”。而“禿尾巴老李”后來修煉成了龍神,保佑渡海的山東人民平安無恙。再如,在當時黑龍江流域渡船上,每當船家要開船時,總會習慣性地問一問船上有沒有山東人,如果沒有,那么船家就不會開船。兩者共同佐證了 “闖關東”的移民歷史,反映出山東人與東北人團結合作,友好相處的現實。
其次,山東人的生活態度和處世哲學深刻地影響著東北人民的個性塑造,東北的民俗、民風、民情無不打上了山東人性格的烙印。作為禮儀之邦,山東獨特的齊魯文化是中國的傳統主流文化之一。在此影響下,山東人也擁有獨特的性格特征:他們節儉好客,忠實厚道,待人不吝嗇;他們豪爽豁達,樂善好施,十分講義氣;他們樸實勤勞,重義輕利,整個山東可以說民風淳樸。因此,當這些豪爽的山東人與東北原住民朝夕相處,長此以往,就潛移默化地形成了東北人直爽開朗、樂觀豁達的性格特征。同時,山東人思想也存在著保守與傳統的方面。受儒家文化長期浸染,山東人鄉土觀念很重,他們大多安土重遷。正如山東地區一直流傳的說法:“千行百行,種地才是本行”、“三十六行,種地為上。”體現出“在山東人的思想中,土地是最根本的,種地是最高尚、最正經的謀生方法。”[4]因此大部分山東移民在來到東北之后,依舊固守傳統小農思想,繼續著開墾土地的傳統農耕生活,這也與東北人性格中冒險意識較弱,相對傳統保守的性格特點相對應。總的來說,東北人直來直去,不拐彎抹角的思維方式,包容的胸懷,蓬勃的進取精神,重情重義,樂于助人的品質等諸多人格特征,都與那段“闖關東”的歲月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
最后,“闖關東”對于東北民俗與文化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人作為文化的載體,人的遷移就意味著文化的交流。因此,“闖關東”浪潮的興起,也促進了中原文化融入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間,意味著齊魯文化逐步對東北原生文化的分解、重組,進而熔鑄成一種嶄新的文化。它脫胎于中原文化、齊魯文化,又根植于東北原有的滿族文化,我們稱之為關東文化。以下從娛樂習俗與飲食習俗兩個方面進一步論述。
1.娛樂習俗
娛樂習俗方面,東北二人轉藝術的形成與發展與“闖關東”密切相關。二人轉是東北重要的民間藝術形式,具有濃郁的地方色彩。東北有“寧舍一頓飯,不舍二人轉”的說法,可見其在民眾心中不可撼動的地位。二人轉至今已有三百年的歷史,其主要來源于東北大秧歌和河北的蓮花落。而蓮花落當時流行在華北等地,隨著“闖關東”浪潮到來才開始在東北廣為傳播。因此,是“闖關東”移民潮推動了二人轉藝術的成熟與發展。再者,從二人轉表演手段上看,分為三種表演形式:“雙玩藝”,“單出頭”和“拉場戲”。“雙玩藝”是一男一女手持扇子或手絹,邊說邊唱邊舞,其中男的負責“逗哏”,女的負責“捧哏”;“單出頭”是指一個人且唱且跳;而“拉場戲”是演員扮成小旦、小生、小丑等角色,并用二人轉的曲調唱戲。無論是哪一種表演方式,目的都是逗觀眾開心,博人一笑。總之,二人轉的表演體現出東北人性格的開朗與樂觀的一面,表現了對生活本真的熱愛。而這種特征正是來自于東北人親歷過“闖關東”,
飽經滄桑的歲月后對現實反抗。正是因為東北多災多難,人們才從苦難中自娛自樂,催生了“二人轉”誕生。
2.飲食習俗
隨著“闖關東”移民潮的到來,東北地區的傳統飲食習慣,食品結構等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最具代表性的是東北菜的形成與發展。東北菜講究吃得過癮,吃得豪爽,被譽為中國“第九大菜系”。其發展演變經歷了漫長的過程,其中“闖關東”的作用不可忽視。“闖關東”之前,東北地區保持著相對原始的飲食習慣,正如俗語:“棒打狍子瓢舀魚,野雞飛到飯鍋里”。當時東北原住民的生產活動主要是采集和漁獵,他們飲食結構比較單一,以肉類為主,較少食用谷米類。在肉類的烹飪方式上,基本不借助加工工具,而采用較為原始的燒、烤、煮等方式。山東人民進入東北后,不僅把其主要飲食帶入東北地區,而且傳播了先進的食物烹飪技術。在其影響之下,東北的飲食習俗發生了深刻的變化。一方面,東北傳統的飲食結構得到改善,谷物糧食逐漸取代了肉類占據主導地位,人們的餐桌得到了極大的豐富。另一方面,東北人民逐漸掌握了各種烹飪技巧,逐漸形成了爆、炸、燒、蒸、燉等具有東北本土特色的多種烹飪技法。“闖關東”為東北飲食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來自不同地區,擁有不同飲食習慣人們在同一片白山黑水間共同勞作生活,研究更美味的烹飪方法,一起煮著同一鍋米飯,品嘗著同一道菜肴。在長期的交融中,東北自身的飲食文化逐漸兼收并蓄,博采眾長,最終發展為以醬骨架、殺豬菜、鍋包肉、豬肉燉粉條、小雞燉榛蘑等為代表的別具一格的東北菜系。
總之,大批山東人民 “闖關東”,不僅開拓了東北廣袤的土地,為東北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帶來新的希望,而且在長時間的生產生活中,形成了東北特有的衣食住行,婚喪嫁娶等風俗習慣,熔鑄成為獨特的關東文化。
三、“闖關東”精神的現實意義
“闖關東”作為中國近代史上極其獨特的歷史事件和文化現象,對整個東北甚至中國社會的發展演變都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其孕育的“闖關東”精神在當下仍然沒有過時。歸根結底,其內涵在于“闖”字,這就是中華民族面對天災人禍,面對生存困境的堅韌不拔,尋找出路的開拓精神;就是不怨天尤人,不安于現狀的冒險意識;就是不同地區人民和諧相處,以和為貴的處世理念。“闖關東”堪稱一部波瀾壯闊、驚心動魄、蕩氣回腸的民族史詩,而“闖關東”精神正是我們整個民族的精魂。現如今東北的振興與發展,更需要老一輩們的“闖關東”精神。
我們從民俗與文化的角度探討“闖關東”對東北地區的影響,旨在尋根溯源,對東北文化進行重新解讀,讓“闖關東”精神再次煥發生機,成為東北人的心靈支柱和人生信條,為振興東北老工業基地注入新的精神動力。
綜上所述,山東人民“闖關東”,選擇踏上東北的土地,揭開了東北近代發展的新篇章。無論是東北人民的性格,東北的社會民俗,還是獨特的關東文化風情,都受到山東人“闖關東”事件的深遠而持久的影響。
注釋:
[1]袁榮叟等.《膠澳志》第三卷[M].130.
[2]趙中孚.《一九二〇——一九三〇年代的東三省移民》[J].《近代史研究所期刊》.
[3]高勞.《山東之苦力》[J].《東方雜志》.1918年第15卷第7號,2.
[4]沈健.《歷史上的大移民:闖關東》[M].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2013,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