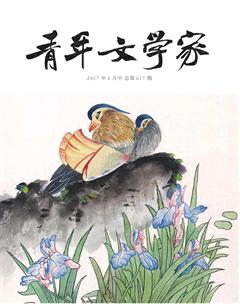英漢語(yǔ)言中“狗”文化異同的原因探究
摘 要:語(yǔ)言與文化相互依賴(lài)、相互影響。語(yǔ)言是文化的重要載體和媒介,文化對(duì)語(yǔ)言又有制約作用,語(yǔ)言交際離不開(kāi)文化。本文從跨文化交際學(xué)角度出發(fā),對(duì)英漢語(yǔ)言中有關(guān)“狗”文化詞匯、習(xí)語(yǔ)進(jìn)行對(duì)比分析,探究造成這種文化差異的深層原因。
關(guān)鍵詞:英語(yǔ);漢語(yǔ);狗;文化;差異
作者簡(jiǎn)介:吳磊,男,漢族,陜西安康人,四川大學(xué)文學(xué)與新聞學(xué)院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國(guó)際漢語(yǔ)教學(xué)。
[中圖分類(lèi)號(hào)]:G125 [文獻(xiàn)標(biāo)識(shí)碼]:A
[文章編號(hào)]:1002-2139(2017)-17--02
跨文化交際學(xué)的鼻祖霍爾著名的“冰山理論”指出:“文化中有少部分是顯性的,包括飲食、服飾、語(yǔ)言、儀式、文學(xué)等,如十分之一的冰山露出水面;而大部分文化是隱形的,如價(jià)值觀、世界觀、信仰、態(tài)度等,十分之九都隱藏在水面之下。”英漢語(yǔ)言中關(guān)于“狗”的詞匯、習(xí)語(yǔ)眾多,然而所包含的意義卻不盡相同,探究造成這些異同的成因就如同研究一座中西文化間的冰山,從語(yǔ)言表層的差異尋找其背后折射的文化內(nèi)涵以及東西方思維模式、審美態(tài)度以及價(jià)值觀念的差異。
一、英漢語(yǔ)言中有關(guān)“狗”的詞匯、習(xí)語(yǔ)羅列
漢語(yǔ):走狗、瘋狗、狗奴才、癩皮狗、狗腿子、落水狗、狐朋狗友、狼心狗肺、雞鳴狗盜、喪家之犬、偷雞摸狗、蠅營(yíng)狗茍、豬狗不如、狗血淋頭、狗急跳墻、雞飛狗跳、兔死狗烹、狗仗人勢(shì)、狗皮膏藥、人模狗樣、狗眼看人低、狗嘴吐不出象牙、狗改不了吃屎……
英語(yǔ): lucky dog 幸運(yùn)兒; top dog 勝利者 jolly dog 快活的人;sea dog 老船員;clever dog 聰明的人;gay dog 快活的人;old dog 行家老手;every dog has its day凡人皆有得意時(shí); love me love my dog 愛(ài)屋及烏;die dog for somebody 士為知己者死; as faithful as a dog 像狗一樣忠誠(chéng); work like a dog 像狗一樣拼命;
從上面的詞匯中我們不難看出,漢語(yǔ)和狗相關(guān)的詞匯、習(xí)語(yǔ)幾乎都是貶損意義的,可以說(shuō)都是“罵”狗的,狗的形象都是“丑陋、低下、卑賤”的;而在英語(yǔ)中卻恰恰相反,都是“捧”狗的,狗的表現(xiàn)的都是“忠誠(chéng)、忠心、富有經(jīng)驗(yàn)、歡樂(lè)”的形象。為何英漢語(yǔ)言差距對(duì)狗的態(tài)度截然相反,想搞清楚這些,需要我們做詳細(xì)的對(duì)比分析。
二、哲學(xué)層面的歷史唯物主義辯證思想分析
歷史唯物主義認(rèn)為:社會(huì)存在決定社會(huì)意識(shí),社會(huì)意識(shí)反映社會(huì)存在。社會(huì)存在是指社會(huì)的物質(zhì)生活過(guò)程,核心是物質(zhì)資料的生產(chǎn)方式。社會(huì)意識(shí)是指社會(huì)的精神生活過(guò)程,包括人們的一切意識(shí)要素和觀念形態(tài)。英漢語(yǔ)言中對(duì)狗的褒貶態(tài)度就是不同民族的社會(huì)意識(shí),而形成這種社會(huì)意識(shí)的原因則是不同的社會(huì)生產(chǎn)方式?jīng)Q定的。英語(yǔ)國(guó)家所在的歐洲大陸,因地理氣候位置的原因,水汽充足但缺少光照,畜牧業(yè)廣泛發(fā)展,形成早期的西方草原游牧文明,因此飼養(yǎng)牛羊?yàn)橹饕氖澄飦?lái)源。在此過(guò)程中,由于草原廣闊,需要狗作為得力助手來(lái)幫助放牧、警戒、抵抗狼群和其他獵物的侵?jǐn)_,狗的聰明勇敢在這片土地上發(fā)揮得淋漓盡致,從而深得人心。而東方大陸的土地上,土地肥沃光照充足,盛行的則是傳統(tǒng)的采摘種植農(nóng)業(yè),狗的作用僅僅局限于看家護(hù)院,“看門(mén)狗”的作用較于牧羊犬,能力似乎微不足道,而且由于只認(rèn)自家主人,對(duì)外人狂吠,會(huì)令人心生厭惡,產(chǎn)生抵觸心理。
另一方面,早期西方的游牧文明,飼養(yǎng)牛羊需要定期擇水草而居,是一種動(dòng)態(tài)生產(chǎn)方式;而東方的種植采摘農(nóng)業(yè),則是在固定的土地上勞作,是靜態(tài)的生產(chǎn)方式。動(dòng)態(tài)的游牧文明下,個(gè)體的遷徙往往需要獨(dú)自抗?fàn)幾匀弧⒌挚篂?zāi)害,在這樣的生產(chǎn)方式下的人們形成的文化就是追求、抗?fàn)幰约皥?jiān)持。《圣經(jīng)》創(chuàng)世紀(jì)里說(shuō)上帝分七天創(chuàng)造世間萬(wàn)物,萬(wàn)物生而平等。宗教理念反映在現(xiàn)實(shí)中,社會(huì)普遍堅(jiān)持眾生平等的權(quán)利,動(dòng)物也是如此,因而我們能看到西方國(guó)家有眾多動(dòng)物福利機(jī)構(gòu),出臺(tái)眾多關(guān)于動(dòng)物保護(hù)和反對(duì)動(dòng)物虐待的法律法規(guī)。這與造成他們對(duì)平等的追求對(duì)權(quán)利堅(jiān)持的文化息息相關(guān)。而較于靜態(tài)的農(nóng)耕文明,形成的文化就是遵從自然。因?yàn)橥饬Φ母缮鏁?huì)違背規(guī)律,反倒不能得到所需,因此儒家文化就倡導(dǎo)“仁、愛(ài)、和諧”。孟子《盡心上篇》就提到“食而弗愛(ài),豕交之也;愛(ài)而弗敬,獸畜之也。”談到只給吃的而不給關(guān)愛(ài),交往的關(guān)系和養(yǎng)豬是一樣的;給予關(guān)愛(ài)而不給予尊敬,和畜養(yǎng)動(dòng)物是一樣的。雖然這是講人與人交際關(guān)系的處理,但是從中我們可以看到,人與動(dòng)物的關(guān)系是有嚴(yán)格界限的。
三、東西方民族文化心理對(duì)比分析
中國(guó)傳統(tǒng)儒家思想早就提出“三綱五常”的倫理規(guī)范,儒家認(rèn)為尊卑分明,貴賤有序才能以禮樂(lè)教化于人,使得社會(huì)秩序規(guī)范。《左傳》里提到“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六畜即“馬牛羊雞狗豬”;我們看到狗的排位是位列倒數(shù)第二的,說(shuō)明位份低下;與此同時(shí),人們普遍認(rèn)為狗是由狼馴養(yǎng)而成的,因此狗的身上或多或少還是保留了狼的野性,所以成語(yǔ)才有“狼心狗肺”來(lái)形容心腸狠毒忘恩負(fù)義之人,在這一點(diǎn)上,狼和狗的本性違背了儒家傳統(tǒng)“仁、愛(ài)”的倫理規(guī)范;
從思維方式上看,中國(guó)人是直觀性思維,容易將人的道德情感賦予外物,而受到儒家文化影響,人們觀察評(píng)價(jià)事物的時(shí)候關(guān)注其德行以及與外部世界的和諧。梅蘭竹菊對(duì)于中國(guó)人而言幾乎是完美無(wú)瑕的,人們對(duì)其贊賞有加并用它們的品行來(lái)褒獎(jiǎng)人。而反過(guò)來(lái)對(duì)于狗,人們看到的是狗看家護(hù)院,只擁護(hù)自家的主子,聯(lián)系到攀附權(quán)貴的人如狗一樣齜牙咧嘴、仗勢(shì)欺人,人們很容易將狗的天性附會(huì)在人的形象之上,卻忽略了這其實(shí)是狗“忠誠(chéng)、忠心”的本性。
西方人受古希臘羅馬時(shí)代的哲學(xué)思想影響,其思維注重理性,邏輯推理,這種嚴(yán)謹(jǐn)?shù)乃季S模式要求人們?cè)诟鞣N領(lǐng)域、人際交往、社會(huì)生活中要以“理性”的眼光來(lái)審視觀察外部世界。而早期的草原游牧文明,單個(gè)群體在與自然抗?fàn)幍倪^(guò)程中形成了崇尚個(gè)性、追求平等以及利己主義思想。狗在其社會(hu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是生活和家庭的助手,幫助主人狩獵,在主人孤獨(dú)時(shí)刻給予陪伴,聊以慰藉。西方人并沒(méi)有過(guò)多附會(huì)狗的“反面”形象于人,這與他們的理性思維有關(guān)的。
從上面兩種分析來(lái)看,東西方民族對(duì)狗的褒貶不一的確是有深層背景的,那么難道英語(yǔ)中完全都是對(duì)狗的溢美之詞嗎?事實(shí)告訴我們,并非如此。
四、英語(yǔ)中有關(guān)狗的貶損詞羅列
dirty dog 下賤胚子;dog eat dog 互相殘殺 ; a dog in the manger干占茅坑不拉屎; a dogs breakfast 一團(tuán)糟; go to the dogs 日漸衰落;A dogs life 悲慘生活; give a dog bad name 惡名難洗;a dead dog 廢物;dog-hearted 殘忍的;
從這里可以看到英語(yǔ)中的確也存在眾多對(duì)狗的貶損意義詞匯、習(xí)語(yǔ),較于上面對(duì)狗的褒義詞有很大差別。這又是何種原因造成的?由于人類(lèi)思維和語(yǔ)言又有許多共通性,不同民族、地區(qū)的人完全可能面對(duì)相同的事物而產(chǎn)生相似的認(rèn)知,表現(xiàn)在語(yǔ)言和使用的詞匯上,就使得詞義有世界性的特點(diǎn)。英語(yǔ)中對(duì)狗的貶義詞的出現(xiàn),是基于西方民族在對(duì)狗的認(rèn)知過(guò)程中產(chǎn)生了同東方民族同樣的感覺(jué),這也和人類(lèi)本身在進(jìn)化過(guò)程中對(duì)自然界的認(rèn)知經(jīng)歷有關(guān),正是這種認(rèn)知的相同經(jīng)歷和感受才使得英漢詞義在某些表達(dá)上如出一轍。
五、隱喻的共性與個(gè)性
隱喻作為一種思維方式,建立在已知經(jīng)驗(yàn)的基礎(chǔ)上,設(shè)定著兩個(gè)事物和概念的聯(lián)系,使得人們能夠通過(guò)一個(gè)已知概念來(lái)解釋另一個(gè)未知的概念。隱喻的本質(zhì)就是把握人與自然兩種基本存在的關(guān)系,揭示人與自然的相似統(tǒng)一,在不同的事物里建立起等值、相似的關(guān)系。英漢雖然屬于不同民族,但是認(rèn)知世界的機(jī)能是相同的,反映到各自的語(yǔ)言之中,就產(chǎn)生的隱喻的共性。英漢語(yǔ)言中對(duì)狗的貶損,大多都是用來(lái)比喻人或者人所處的境遇情形,只是從這些表達(dá)上看,英語(yǔ)的貶損意義多是具體的含義,用狗來(lái)罵人,側(cè)重狗的霸道兇殘、惹是生非的形象,而漢語(yǔ)多是概念性的抽象意義,表現(xiàn)的都是狗忘恩負(fù)義、得志猖狂的勢(shì)利小人形象。
隱喻的共性使得東西方民族在同一事物的價(jià)值觀念上表現(xiàn)出一定的共識(shí),但是由于社會(huì)文化的差異以及人們對(duì)事物的不同感知,又使得這些隱喻存在民族個(gè)性。一些話語(yǔ)詞語(yǔ)講出來(lái)能夠在一些人身上產(chǎn)生美感效應(yīng),而較于另一些人而言,卻完全不具有美的價(jià)值,相反可能會(huì)引起誤會(huì)。英語(yǔ)中說(shuō)“l(fā)ove me,love my dog”是因?yàn)楣繁划?dāng)做自己的忠誠(chéng)伴侶甚至家庭一員,這種表達(dá)就是漢語(yǔ)“愛(ài)屋及烏”的同類(lèi)表達(dá)。如果不了解狗在西方社會(huì)家庭中的地位以及人們對(duì)狗的寵愛(ài),很難理解為何“愛(ài)我也要愛(ài)我的狗”。倘若把中國(guó)對(duì)狗的鄙視、唾棄觀念放置在這樣一句話的背景下,是不會(huì)產(chǎn)生任何共鳴的。
六、審美的民族個(gè)性與差異
審美是人類(lèi)理解世界的一種特殊形式,是指人與社會(huì)和自然形成的一種無(wú)功利的、形象的情感的關(guān)系狀態(tài)。黑格爾曾說(shuō)過(guò):“自然美的意蘊(yùn)并不在于自然本身而在于人,人的心情和特征。狗的美,是因?yàn)楣飞砩系钠沸蕴卣髋c人的部分特性契合,才被認(rèn)為美,被人們所喜愛(ài);而狗被人厭惡和鄙視也是由于它的一些天性和人的惡性契合,才遭受唾棄和討厭。其實(shí)東西方民族對(duì)狗的不同解讀,喜好也罷厭惡也罷,都是把人的具體形象物化到了狗本身,這便是“移情”。通過(guò)移情,狗這個(gè)客觀的對(duì)象物體在與主體的情感交流中相互比照交融。由于東西方民族的觀察視角不同,因此所產(chǎn)生的對(duì)狗的具體審美也就各不相同。中國(guó)人過(guò)多關(guān)注狗的負(fù)面形象,忽略了它忠誠(chéng)友善的一面,借狗來(lái)宣泄抒發(fā)內(nèi)心的不滿和憎惡的情感,使得我們看到的有關(guān)狗的語(yǔ)言大都是不美的。而西方社會(huì),因?yàn)閭€(gè)體的生存,狗在生活中扮演了諸多得力角色,填補(bǔ)了人們情感上的空缺,人們賦予狗的多為溢美之詞,表現(xiàn)在語(yǔ)言中褒義多過(guò)貶義。從文學(xué)作品和影視作品里也能看到對(duì)狗正面的褒獎(jiǎng),比如杰克.倫敦的小說(shuō)《野性的呼喚》,電影《101忠狗》《忠犬八公》等。
七、小結(jié)
通過(guò)對(duì)比分析英漢語(yǔ)言詞匯、習(xí)語(yǔ)對(duì)狗的褒貶不一,我們看到產(chǎn)生這些現(xiàn)象的原因眾多。即便英語(yǔ)漢語(yǔ)中都存在對(duì)狗的負(fù)面“解讀”。但是這并非代表人們真的厭惡狗,相反,也許正是狗離人類(lèi)的距離最近,關(guān)系最為親密,人們能夠信手拈來(lái),借狗的形象來(lái)隱喻所厭惡的人或者事物,這種厭惡僅僅停留在語(yǔ)言層面,而對(duì)狗真正的喜愛(ài)還是發(fā)自?xún)?nèi)心的。無(wú)論是語(yǔ)言中的愛(ài)憎或是褒貶,狗作為一個(gè)摻雜人類(lèi)復(fù)雜情感的動(dòng)物,在現(xiàn)實(shí)中我們都應(yīng)該與它們和諧相處,因?yàn)樽鹬孛恳粋€(gè)生命就是尊重我們自己本身。
參考文獻(xiàn):
[1]楊文全.現(xiàn)代漢語(yǔ)[M].重慶:重慶大學(xué)出版社,2010.
[2]胡曉梅.跨文化交際[M].北京:外語(yǔ)教學(xué)與研究出版社,2015.
[3]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Z].北京:商務(wù)印書(shū)館,2009.
[4]何善芬.英漢語(yǔ)言對(duì)比研究[M].上海:上海外語(yǔ)教育出版社,2002.
[5]楊自?xún)€.英漢語(yǔ)比較與翻譯[M].上海:上海外語(yǔ)教育出版社,2002.
[6]黃紅娟.狗的負(fù)面義及其在漢語(yǔ)中的生成新論[J].廣西大學(xué)學(xué)報(bào),2010,6.
[7]梁園園.英漢“狗”隱喻的跨文化研究[J].語(yǔ)言文化,20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