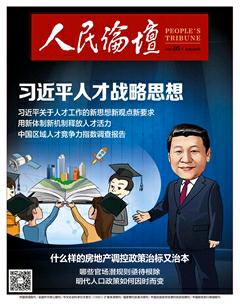社會治理轉型必須直面新媒體挑戰
王智勇
【摘要】移動互聯網的發展,從技術上給予了公眾發聲的可能性,促進了公共權力的上升。新媒體環境下社會治理轉型,要健全網絡法律規制,樹立服務意識,加強全社會的媒介素養教育,重視發揮社會力量在公共事務中的作用,從而實現公共利益最大化。
【關鍵詞】新媒體 社會治理 媒介素養 【中圖分類號】C916 【文獻標識碼】A
新媒體環境下社會治理轉型的必要性
現今我國正處在轉型期、全球化、媒介化三重巨變之中。互聯網的發展不僅加速了全球化進程,而且還對我國社會轉型期的權力結構調整和各方利益協調具有重要作用,促進了社會力量的發展和公共權力的提升,敦促社會管理者改變與民眾的溝通方式,對社會治理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新媒體的跨時空性和交互性,打破了傳統的自上而下的科層制管理體系,突破了地理空間的局限,新媒體作為第三方力量開始嵌入社會關系結構,形成虛擬社會關系。人際傳播不再只是簡單的“我—你”二者關系,而是呈現出“我—他—你”的三方關系。此時,社會關系的建立只需要遵守“共同認可的行為規范”及“個人興趣訴求”即可。
同時,這種虛擬社會關系的建立與聯系,突破了傳統的自上而下的社會動員模式,顯示出了具有自發性的“從線上到線下”的組織行動能力。如2011年由微博意見領袖于建嶸發起的“隨手拍解救乞討兒童”引起全國網友的自發性支持,并由線上討論發展到線下行動,還形成專門組織,由網友負責長期運行。2014年12月由網友發布的“78歲老人救命錢被偷”的視頻,引起了臺州上下全城搜捕小偷,短短兩天時間臺州警方收到來自全國各地網民提供的線索1000多條,大大加速了嫌疑犯的抓捕工作。這些都顯示出了社會力量開始融入到社會管理工作中,并發揮出強大的動員力和影響力。
新媒體以其特有的開放性、平等性、交互性,在一定程度上發揮著“社會解壓閥”的作用,使不同階層和身份的人通過互聯網公共空間發揮社會治理作用,自由表達意見與主張。當下中國,客觀存在著兩個輿論場,一個是以互聯網為基礎的新興媒體輿論場,一個是以黨報黨刊、國家電視臺、國家通訊社為主體的傳統媒體輿論場。新興媒體輿論場的演變方向具有不可測性,加大了政府單方面引導輿論的難度,且公權力易受到全民監督的“共景式”圍觀。因此要求社會管理者要與民眾就社會問題進行協調互動,否則如果失掉民意就會危及到公民對政治存在合法性的認同感。如2011年“烏坎事件”中,村民自發組建烏坎村村民臨時代表理事會,并及時在互聯網上公布上訪游行時間,引起國內外媒體高度關注,使得當地政府在輿論壓力下不得不與之進行協調對話。
新媒體加大了社會治理轉型的難度
新媒體容易加劇社會沖突事件的傳播擴散,容易放大社會黑暗面。新媒體的信息發布和更新速度具有瞬時性,議程之間的零和效應更加突出,再加上網絡上盛行的民粹主義,使得具有一定聳人聽聞力度的社會沖突事件高居熱門話題榜,隨著類似話題的持續,不僅給人造成社會黑暗不堪的恐怖印象,還引發社會上更多的模仿行為,加劇了社會治理成本。如2013年7月發生的醉酒男子韓磊摔死女嬰的案件,引起了眾多網友和知名人士的關注并表達出對案犯的強烈憤慨。隨后網絡上又一連出現了“河南警察摔嬰案”“重慶摔嬰案”等類似話題,給廣大網民造成社會暴力加劇、社會環境極度不安全的恐慌心理。此外,還有經常出現的“城管與個體戶的暴力沖突事件”,亦極大地損害了城管的集體形象和公信力,加大了執法難度。
網絡推手助推網絡謠言,加劇社會風險指數。新媒體的匿名性和開放性,加上海量信息呈現碎片化,加大了網絡把關的難度。近年來市場力量開始逐步滲透到網絡公共平臺中,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催生出眾多的網絡推手。網絡推手通過幕后策劃、包裝等各種手段,在網上推廣或制造已經存在或并不存在的事件與話題,對人或企業品牌進行虛假宣傳或惡意誹謗來吸引網民注意,營造輿論態勢,提升自身的網絡影響力,從中獲得最大化利益。此外,由于我國部分網民素養水平不高,信息辨別能力差,自發轉發網絡推手所發送的虛假信息,進一步擴大了網絡謠言的影響力和破壞力。如網絡推手秦火火炮制的“鐵道部天價賠償”“別針換別墅”“紅十字會強制捐款”等謠言,破壞了社會管理者與民眾的關系,損害了管理者形象,造成民眾價值觀念的混亂,加劇了社會風險指數。
社會管理者新媒體意識淡薄,難以有效應對公共危機。隨著網絡公共平臺的興起與發展,公共話語權上升,打破了以往官方“一言堂”的局面,公權力受到“共景式圍觀”。這就要求社會管理者轉變治理方式與理念,加強與民眾的溝通與協商。但是,現在我國社會管理者的新媒體意識普遍淡薄,媒介素養水平低下,尤其是面對突發事件時,一些地方政府的公職人員仍然采用傳統的封鎖消息、不發聲、斷然否認等硬性堵截式應對方式,最終導致事態升級。這不僅破壞了當地人民對政府的信任,也加大了有效推行與實施公共政策的難度。
新媒體環境下社會治理轉型,要健全網絡法律規制,樹立服務意識,加強全社會的媒介素養教育
健全網絡法律規制,做到有法可依。規制人們行為的一般有四個因素:市場、架構、行為規范、法律。這四種約束存在著區別,然而它們又是互相依賴的,每一個約束可以支持或反對其他的約束。社會規范通過社區施加的聲譽影響來進行約束,市場通過價格來進行約束,架構通過其施加的物理負擔來進行約束,法律則通過來自懲罰的威脅進行約束。在新媒體環境下,由于網絡的虛擬性、匿名性和開放性,以及市場力量的滲透,導致部分網民和團體組織拋棄公民責任意識,肆意傳播網絡謠言,煽動社會沖突。這不僅損害了社會凝聚力,助長了社會沖突,而且瓦解了各方利益沖突得以調解與對話的網絡公共空間,無疑加大了社會治理成本。法治社會的社會治理以社會組織、公民的法律責任為前提條件。而我國目前尚無完善的互聯網監管法律條文規范,使得不法者有機可乘,可能會破壞社會建設。因此,必須健全網絡法律規制,規范互聯網信息秩序,做到有法可依。
政府應樹立服務意識,擴大公眾參與。與傳統官僚模式重視標準化、部門化和勞動分工相比,互聯網時代的政府模式更重視協同網絡的建構,要求摒棄全能政府理念,建設服務型政府。所謂服務型政府,就是在社會本位和公民本位理念指導下,把為社會、為公眾服務作為政府存在、運行和發展的基本宗旨。通過擴大公眾參與,促進政府與公民的積極合作,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這也是實現善治的實質。以“平安北京”的政法微博為例,其微博粉絲數量達上千萬,發布非常細化和人性化,甚至滲透到民眾的日常生活,設置出行提示、新年話安全等話題,以與網民展開對話的方式進行安全法律普及,從而樹立了北京市公安局的良好形象,有利于法規政策的執行。
加強全社會的媒介素養教育,培養理性公民與合格管理者。媒介素養是指公民的媒介使用技能、媒介信息辨別能力、媒介信息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為自身服務的能力。在當今媒介化社會,媒介就是我們生存的環境。無論是對社會管理者還是普通公民而言,媒介都是其工作、學習與生活繞不開的渠道。加強媒介素養教育,提高普通公民與社會管理者的媒介素養能力,對普通公民而言,一方面有利于其學會辨別網絡信息的真偽,培養思辨意識和對媒介信息的批判能力,能夠就社會問題與他人進行理性探討與對話,對于社會問題的解決形成共識且提出建設性意見和方案;另一方面有利于其自主使用網絡媒介獲取經濟、政治、文化信息,并從中發現機遇,為自身發展服務,使個人在社會發展中獲取最大發展,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做出貢獻。
(作者為寧夏大學民族預科教育學院副教授)
【參考文獻】
①向鑫:《從社會管理到社會治理的邏輯轉換探究——群眾路線與社會治道變革》,《理論研究》,2014年第5期。
責編/賈娜 美編/于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