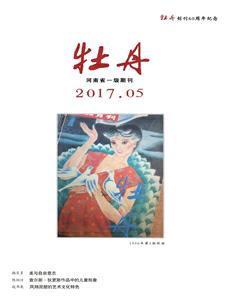童年陰影對希區柯克電影創作的影響
馬丁丁
創傷理論(童年陰影)是媒介批評之精神分析批評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指由一個災難性的打擊而造成主觀意識無法接受;有些理論也認為,創傷理論更是指向某些人被壓抑的內心壓力和欲望所造成的問題。根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童年的記憶在人的潛意識中占據了很大的空間,并對將來的一系列行為做出引導。”以此來看,“希區柯克式”緊張、焦慮、恐懼、懸念迭起、情節驚險曲折的電影一定與他獨有的童年生活有關。
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在長達六十年的導演生涯中,一共執導了五十三部電影。斯皮爾伯格曾贊譽他是“在懸念片和恐怖片領域里,可以說是當之無愧的開拓者”。希區柯克式的電影以豐富的電影語言、意想不到的情節懸念設置以及深刻的內涵底蘊獲得了世界的一致認可。他的電影總給人一種莫名的焦慮與絕望之感,他的一部影片《破壞者》在初次上映時的宣傳語為“當心背后有人”,這些電影都暗示著希區柯克無處不在的偏執的疑俱感。這樣獨特的電影風格必定不會無緣無故,可能是一定的心理動機促使他一再重復制造這種感覺。根據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論,人在童年時大腦的腦電波散發與收縮的數量和神經元運動的次數遠遠高于成人,此時兒童大腦正在發育,童年的記憶在人的潛意識中占據了很大的空間,并對將來的一系列行為做出引導。若此時某件事物(創傷)進入了他的潛意識,這個事物便在腦中成形,意識和潛意識都存在這件事物,然后一輩子都忘不了,也不可能好轉。因此,了解希區柯克的童年生活,也許有助于人們理解其電影風格的緣起。
一、謀殺及殺人犯
在希區柯克的電影中,大量描繪了謀殺的場景,希區柯克特別喜歡刻畫形象各異的殺人犯并賦予他們極強的神秘感,出人意料,觀后令人拍案叫絕。例如,《后窗》中的殺人犯推銷員蘇先生,他將自己的妻子殺害并且分尸,用推銷的箱子轉運,銷毀證據。這樣殘忍的情節來源于希區柯克童年時代的記憶中。“希區柯克童年時的英國,謀殺就像是一種連續劇般的娛樂,希區柯克家蔬菜商店顧客胳膊下夾著報紙走進來,議論著駭人聽聞的犯罪案件。”這是《希區柯克傳》所提到的內容。同時,他還說到這樣一件事,“從1888年開始(那一年希區柯克還沒有出生),在希區柯克家萊頓斯通倫敦東部白教堂去,一個被稱為殺人碎石狂杰克的殺人犯連續運用刺殺、肢解、剖腹、割喉等手段,殺了五到十位女性。而這一罪行就像它神秘地開始一樣又神秘地結束了,直達今天這個殺人犯的身份還是個謎。”可能希區柯克在小時候就經常聽說或者看見這些兇殘而神秘的殺人事件,留下童年陰影,從而創作出如此之多的謀殺題材的電影。同時,希區柯克式電影的謀殺事件并不是一開始就呈現在觀眾面前,他總是先講述一些看似無關痛癢的情節,讓觀眾在期待、疑惑和恐懼中等待著兇殺場面的出現。例如,《西北偏北》中觀眾在觀影的前一半時間中都是充滿疑慮的——不知道到底發生什么,綁架主人公羅杰的目的是什么,也不知道誰是好人誰是壞人。這種特殊導演風格來自于希區柯克童年時所獨有的內心體驗——他九歲那年被送到基督教學校讀書,他在那里接受的是一種將罪惡無處不在觀念和邏輯的嚴密性結合起來的混合式教育。例如,違反校規的同學要遭到鞭打,但他可以自行挑選懲罰的時間。通常孩子們總是選擇晚上,致使在受懲罰前的一整天內他們都是處于焦慮和恐懼之中。這種獨特的童年感受烙印在希區柯克的記憶中,他就時常不由自主地將其運用于懸疑電影之中,將自己童年的不悅之感分享給觀眾。
二、軟弱的警察及公共機構
希區柯克的電影幾乎每一部都涉及了謀殺,但是每一部中真正伸張正義和維護秩序的人絕對不是警察。例如,《后窗》中發現并且偵破案件的是意外摔斷腿,只能在家靜養的杰夫。而《迷魂計》中對警察這一角色更是諷刺,警察斯考第是一個在一次追捕行動中因高樓上失手驚嚇后得了無法治愈的恐高癥的人。還有電影《疑影》中,警察則走到了另一邊,放棄了正確的執行法律過程。原本應該承擔“英雄”角色的警察在希區柯克的影片中總是如此不堪,同時影片也總是表現出對警察的不信任,而且“無能的警察”這一角色不停地在他的作品中重復。這是因為在希區柯克一生中,他都是十分懼怕和厭惡警察的,以致于他有一次開車出門,僅僅因為從車窗中扔出一個煙頭怕警察追查而惶惶不可終日。這種創傷性原質的堅執頑念的真正成因可以追溯到他的童年時期,根據他的傳記,人們可以得知:一是他童年時閱讀的書籍中,狄更斯的《荒涼山莊》給他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這本書不僅講述了警察貪污和司法制度不公的故事,同時也表現出了對公共機構極度的不信任。這一點深深地影響了年幼的希區柯克,致使他一生都對公共機構抱持懷疑態度,因為他影片中的公職人員,例如,政客、警察等都是一群貪贓枉法、唯利是圖、膽小如鼠的形象。二是在希區柯克四五歲的時候,由于不聽話,他被父親送到了警察局。警察把他鎖進了牢房里,同時警告他這就是對不聽話的孩子的教訓。這件事在希區柯克幼小的心靈中留下了深深的童年陰影。隨后的人生中,他曾多次提到:“我永遠不會忘記門砰的一聲關上,接著牢房的門閂咯噔一聲合攏,這給了我極大的震撼。”恐怖的童年陰影使得希區柯克一生都無法擺脫對警察及公共機構的厭惡與恐懼,這種感受也幾乎貫穿于他的創作生涯之中。
三、驚險的行車及奇怪的燈光
人們總是會在閱讀或觀影之后,忘記其中絕大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內容,尤其是童年時期。這種經驗人人都有——你可能忘記了它的名稱,忘記了它的主人公,但是其中總有那么一點觸動你的地方悄悄地“溜”進你的意識中,就像希區柯克經常在影片中表現險象環生的行車鏡頭。例如,《西北偏北》中羅杰被灌醉后在海邊開車,迷迷糊糊險些落入海中的情節;《九十三級臺階》中漢內在高架橋以及崎嶇的山路上駕駛汽車遇到危險,使得觀眾緊張得都不敢眨眼,生怕主人公發生危險。在希區柯克的電影中,這樣的行車場景屢見不鮮。這個想法歸根結底來自于他小時候觀看過的影片《暴走列車》——火車在高山之間穿梭盤旋,結局是幾乎失控的火車一頭扎進隧道,暗示著即將發生可怕的故事和毀滅。這一影片是通過攝影技術增強了真實感,深深地吸引了年幼的希區柯克,這個鏡頭記憶留在了他的意識中。在之后的個人創作中,在表達危險的時候,希區柯克習慣性地使用這樣的鏡頭,這跟他的童年經歷是密不可分的。童年的記憶對他創作的影響不止于此,其影片中的特色色調和奇怪燈光也來源于童年的觀影經歷,如《迷魂計》中的朱迪身上籠罩著特殊的光芒。希區柯克在導演影片時,常給角色穿著特殊材質的服裝,投射具有象征意義的色光。這種創作方式根據他的傳記記述:他第一次看演出是在1905年左右,“一片陰森森的綠光被投射到壞蛋身上,伴隨著讓人毛骨悚然的音樂,女主人公則籠罩在明亮的玫瑰色的光芒之中”。這次視覺的奇幻經驗可能給年幼的希區柯克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童年印象,他就在長大后將這種表現形式用于自己的作品創作中。
四、出鏡式的作者簽名
希區柯克是個其貌不揚的胖子,但是他的形象總會出現在自己的作品中,哪怕只是一個路人甲。例如,《迷魂計》中他就只是從主人公身邊擦肩而過。這種獨特的簽名方式在幾百年的電影史上可能僅此一家吧。根據他的傳記,人們可以知道他一直是一個十分孤僻、孤立無援的人,他對童年的全部記憶就是孤獨:因為年齡差異無法與哥哥、姐姐很好地相處,也對父母敬而遠之,他還很害怕有權有勢的人,如老師、警察等。因為有這樣的童年經歷(童年陰影),所以筆者推測希區柯克的形象總是出現在自己的電影中是因為他渴望得到人們的關注以排解自己的無盡孤獨,但是又總是以小人物的形象出現,這可能是因為他討厭與他人過多接觸,因為他那無窮無盡的荒謬的憂慮。
五、陰郁和明朗并存的電影
雖然希區柯克被世界公認為驚悚大師、“電影界的弗洛伊德”,但是他的影片在陰暗之中也是充滿光明與溫暖的。例如《西北偏北》中,經過多次磨難,羅杰最終收獲了美妙的愛情;《后窗》中杰夫與女朋友在經歷了謀殺案之后終于相互妥協,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從這些童話式完美的結局中,人們不難看出希區柯克的童年雖然不全是陽光明媚的,但也并非充斥著詭異與陰暗。他的一本傳記里曾經提到這樣溫馨的場景:“房子后面是果實累累的棚架,里面的情景給大家留下了栩栩如生的印象:大串的香蕉在爐火搖曳的溫暖氣息中一天天成熟,那景象,那味道,還有依稀可辨的嘶嘶聲,都讓人回味無窮。他稍長大些后,一件讓他著迷的工作是給核桃去殼。核桃送到店的時候依然穿著鮮綠色的外衣,在準備出售前必須由店里的人把殼去掉。”
六、結語
電影是導演對現實生活的虛構呈現,同時也是虛構生活的現實表現,導演的現實生活狀況或多或少都會在其中有所體現,尤其是他們童年的生活經歷會對電影風格的形成產生巨大的影響。童年的經驗對于一個人的一生成長都是不可或缺的起點,藝術家終其一生都會從中獲得創作的靈感。對希區柯克來說,電影是一種使人焦慮不安、承受莫名內疚和恐懼的折磨方式,然后再通過導演的情節設置、場景安排等方式來排解觀眾內心的痛苦與驚恐。他通過這樣方法來確認人們是需要他的,從而享受著暫時在精神上支配他人的快感。筆者不想用變態這個詞來形容希區柯克,他只是一個孤僻的五歲小男孩,他默默地走在黑暗且悠長的樓梯上,他要回房睡覺,但是現在的他十分害怕,因為他總覺得樓梯拐角的黑暗中一定存在著什么可怕地怪物。他渴望他人的關注與陪伴來消解那跟隨自己一生的孤寂感。
(西安工程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