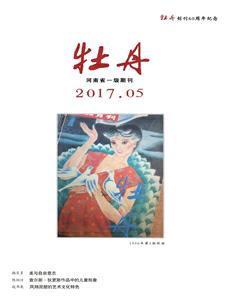“凝視”文化
袁春紅
本文從心理學、美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角度分析了“凝視”文化的不同意義,指出在當今視覺文化時代、圖像時代,“凝視”在不同領域中都占有重要的地位:“凝視”建構心理的自我,“凝視”產生美,“凝視”隱含性別意識與種族意識,“凝視”是一種權力。
“凝視”,就是看,即聚精會神地觀看。從施事與受事角度說,“看”包括看者與被看者;從視線指向角度說,“看”可以向外看和向內看。圍繞著“誰看,看什么,怎么看”等問題,學術界不斷挖掘出“凝視”文化的各種意義,大致有心理學意義、美學意義、社會學意義和政治學意義等。
一、“凝視”的心理學意義
“凝視”直接關系到每個人自我的建構。法國心理學家拉康提出的鏡像理論揭示了人類始于嬰兒期的自我形象的認同與自我意識的建構。拉康認為,6~18個月的嬰兒,在照鏡之前處于前語言階段,此時的嬰兒,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人、母親與自己等范疇均處于混沌的狀態。當母親第一次讓嬰兒位于鏡子之前并看到了鏡中之像時,嬰兒一面凝視鏡中的自己,一面凝視真實的母親與鏡中的母親——嬰兒關于自我的意識在凝視中逐漸形成,自我與他人之別也逐漸顯明,嬰兒開始重構自我的整體性,而這一切是以喪失原初的統一體、未分化的存在和與母親的融合為代價的。
嬰兒期的凝視對人類而言具有重要的識別作用。在心理建構的歷程上,人類經由“自戀”到“戀母”再到“戀他/她”。而這也是人類凝視自我——凝視母親——凝視他人的變化過程。
古希臘一個著名的神話故事描繪了人類最早的“自戀”,那就是那喀索斯的悲劇,也是水仙花的起源故事。那喀索斯出生后,他的父母河神與水澤神去向其他神求問孩子將來的命運,神說:“不可使他認識自己。”但無人明白神的話語。光陰荏苒,那喀索斯16歲了,長成了一位英俊無比的少年,引來無數林中仙女的愛慕,其中厄科(Echo)即是對那喀索斯一見傾心者。女神厄科向他求愛,遭他拒絕后幻化為回聲女神。他拒絕了所有向他求愛的女神,于是女神舉手祈禱:“但愿他有朝一日愛上一個人,卻永遠也得不到她的愛!”命運女神聽見了這個禱告,應允了。在一次打獵時,那喀索斯來到了林中的一個湖邊。湖水清澈見底,那喀索斯低頭時看到了水中絕美的倒影,頃刻間便被深深吸引并深情愛上了自己的影像。他久久凝視著水中倒影,流連忘返,茶飯不思,終于倒在了湖邊的草地上死去。那喀索斯倒下的地方長出了美麗的水仙花。
而《圣經》中人類的祖先亞當與夏娃,本來自由自在地生活在伊甸園中,身體也處于完全自然的赤裸狀態。但因未能抵御蛇的誘惑,亞當、夏娃偷吃了智慧樹上的果子,他們的眼一下子變亮了,開始凝視他人,彼此凝視,而人類最初的羞恥感便產生于這樣的凝視中。亞當、夏娃被逐出伊甸園,人類的歷史由此展開。
可見,“凝視”的確具有重要的心理學意義,它幫助人建構自我,形成羞恥感,使人類得以進入文明、進入社會。
二、“凝視”的美學意義
人類所獲知識的90%以上來自視覺。眼睛視覺是最重要的感官感覺。早在古希臘時期,哲學家便發現了視覺與美感之間的重要關聯。柏拉圖《大希庇阿斯篇》中,蘇格拉底說,“美是由視覺和聽覺產生的快感”。瑞士布洛的“距離說”進一步指出,視覺/凝視與審美之間的關聯主要在于看者與被看者之間距離的保持,尤其是心理距離。“距離產生美”——適當的超功利的心理距離有助于產生美。現代美學家已開始強調“凝視”狀態中看者的心態——非功利性,看者看的方式——直覺,以及被看者的方面——形式,即看者持非功利性的態度用直覺的方式關注對象的形式方面,這樣獲得的方為美感,這樣的對象方為美的對象。此種特別的“看”被稱為“凝神觀照”或“審美觀照”。
“凝視”的美學意義在繪畫中得到了最充分的體現,因為繪畫本就是“看”的藝術。早在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就找到了以“透視”的畫法來表達“看”的深度感和立體感,力圖在二維畫面展現三維真實。而被稱為“現代繪畫之父”的塞尚,其反傳統的重要創新也首先從“凝視”的角度開始——由傳統的焦點透視變為散點透視、多點透視,由此表達一種有別于傳統的“主觀真實”。
從理論上給予視覺非同尋常之地位的是德國格式塔心理學美學代表阿恩海姆,他的著作《視覺思維》第一次明確提出“視覺思維”這一重要概念,指出視覺也具有思維的理性功能。傳統觀點認為,感性與理性相反相對,感性認識屬于低級認識,理性認識屬于高級認識;當理性被高揚時感性也就被貶低、被忽視;而視覺被認為是純粹的感覺感性范疇,自然就不具有理性的“高貴身份”。但是,阿恩海姆卻說:“一切知覺都包含著思維,一切推理中都包含著直覺,一切觀測中都包含著創造。”知覺中的思維成分和思維中的感性成分之間是互補的,意象可以從不同抽象水平上被創造出來,知覺活動中的意象主要是捕捉或把握有意味的形式,從而體認出對象的某些最突出和最本質的結構特點。因此,思維需要意象,而意象中又包含著思維。這種意象的形成,其實是心靈對感性事物本質進行解釋的產物,它不是對物理對象的機械復制,而是對其總體結構特征的積極主動把握。
由此,視覺獲得了與理性同等高貴的身份,視覺遠不只是感覺,它也能思維——“凝視”在美學中的重要意義得以進一步彰顯。
三、“凝視”的社會學意義
當“凝視”進入社會學領域,其隱含的性別意識與種族意識便逐漸被學者揭示出來。男權社會的文化語境中,當看者為男性,被看者為女性時,兩者之間是否可互換、是否平等?充斥這個時代的各種封面女郎、廣告美女、影視女星等,是否是男性欲望、男性權力的投射和形象化表征?
女性主義者瑪爾薇提出的影視理論一語中的地道出了這種視覺的不平等現象,她在其著作《觀影快感與敘事電影》中說:“在一個性別不平衡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已被分裂成主動的男性和被動的女性。決定性的男性注視將其幻想投射到女性形象身上,她們因此被展示出來。女性在其傳統的暴露角色中,同時是被看的對象和被展示的對象,她們的形象帶有強烈的視覺性和色情意味,以至于暗示了某種‘被看性。作為性對象來展示的女性乃是色情景觀的基本主題。”
瑪爾薇認為電影為觀眾的“凝視”提供了兩種愉悅模式——窺視與認同。所謂“窺視”,即偷窺,電影提供一種偷看模式,可把影像中的人物作為性刺激對象來滿足觀眾的窺視癖。認同則表現為觀眾與影視主人公的對位認同。影視中,女人總是被展示的對象,而男人則是觀看這些對象的看者,兩者之間的關系就如同獵物與獵人。攝影機的鏡頭其實是隱藏的男性眼睛,而女性觀眾的眼睛也有意無意地被迫接受男性的視覺立場。
在諸如封面女郎和廣告美女的視覺消費中,男性往往是欲望的主體,而女性成為欲望的對象,這是男權社會性別之間的等級關系在視覺空間中的投射表現。而生活中的女性也逐漸自覺不自覺地把男性意識的審美觀內在化,成為自己主動追求的審美理想。
“凝視”除了具有性別意識外,還可能會具有種族意識。對有色人種的關注凝視,往往出自人種差異的等級觀念以及對他人景觀的奇異感。尤其是對黑色人種身體的凝視,常常是白人優越心理和特權的表現。
“凝視”所具有的社會學意義還體現在它已成為“圖像時代”最重要的行為表征。詹姆遜提出,我們已進入后現代文化的圖像時代,傳統的深度模式諸如現象與本質、表層與深層、能指與所指、本真性與非本真性等,都在這個追求無深度感與平面化的時代被削平解構了。
人們正面臨一個視覺文化的時代,視覺轉向已取代語言轉向,圖像作為霸主已坐上文化符號的王者寶座。電影電視、廣告畫報、卡通動漫遍布生活的每一個角落,連傳統以閱讀文字為主的印刷物,從報紙到雜志再到書籍,圖像占比也急速上升。在現代化進程中,人們不知不覺已從“前讀圖時代”進入到“讀圖時代”。人們“凝視”的對象變為圖像,而“凝視”的目光已不再深邃。
從“前讀圖時代”到“讀圖時代”,其變化的背后蘊涵是什么?前讀圖時代:文主圖輔——文字中心+文化啟蒙+理性主義——深度模式——“話語文化”——現代文化——現實原則;讀圖時代:圖主文輔——圖像中心+視覺愉悅+感性主義——平面模式——“形象文化”——后現代文化——快樂原則。
這種“只讀圖不讀書”趨向如果成為青少年一代的閱讀習慣,的確讓人堪憂,不能不引起人們的警覺和反思。
四、“凝視”的政治學意義
“看”是人最自然的行為,“凝視”是眼睛最基本的功能。不過,在現代學者的分析下,“看”其實是一種權力,“凝視”背后隱藏著意識形態,它具有政治學的意義。
當你凝視他人時,你是目光的操控者,你是主體,他人是客體;但他人也可凝視你,此時,他人是目光的操控者是主體,而你在他人的凝視下變成客體。主體與客體,自我與他人,看者與被看者,可以在凝視下彼此轉換。由于主體與看者擁有“看”的主權,可以操控“看”的方式和“看”的對象,而客體與被看者處于被操控的位置,有被監視、被約束、被限制之感,因此,人們的相互注視可以構成一個復雜的“視覺關系場”。卞之琳著名的詩《斷章》就是不同目光的相互注視以及主客體之間的相互轉換——“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的人在樓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詩中的“你”既是看的主體,又是被看的對象。
再比如,你站在美術館的一幅畫前,那么可能會有各種目光相互交織、彼此凝視,從而構成視覺關系場:你在看畫;畫中人物在看你;畫中人物彼此對看;畫中人物看他者;美術館的其他觀眾在看畫也看你;美術館的保安在看你……
現代文化中,最能體現凝視權力的當為監獄。現代監獄的建構思路最早可追溯到英國法理學家、功利主義哲學家邊沁。邊沁于1791年首次倡導圓形監獄即全景式監獄的理念,其基本結構是:監獄四周有環形建筑,監獄中心是一座眺望塔。眺望塔的墻上安有一圈大窗戶,方向均對著環形建筑。環形建筑被分隔成很多小囚室,每個囚室都有兩個窗戶——一個對著中心眺望塔,另一個對著外面,以使光亮能照進囚室。這樣設計的圓形監獄中,中心控制塔只需要安排極少數的監視者,甚至可以只安排一個人。因為利用逆光效果,這個監視著可以從眺望塔內與光源恰好相反的角度觀察囚室內被囚禁的每一個人,而被囚禁者卻看不到監視者。所以,被監視者被完全徹底地觀看,卻根本看不到監視者;相反,監視者可以觀看一切,自己卻不被觀看到。邊沁認為,罪犯因處于完全的監視下而不敢有作亂造反之心。此外,一個囚犯一間牢房,牢房之間彼此封閉隔離。這樣可以保證監視者與被監視者之間沒有直接的身體接觸,盡可能避免暴力事件的發生。
法國著名思想家、解構主義大師米歇爾·福柯于1975年寫了《規訓與懲罰》一書。在該書中,福柯指出,邊沁設計的此類圓形監獄完全以“監視”為核心。囚犯的境遇也由此變成了——“他能被觀看,但他不能觀看。他是被探查的對象,而絕不是一個進行交流的主體。”全景式監獄的主要后果是:“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種有意識的和持續的可見狀態,從而確保權力自動地發揮作用……全景敞視建筑是一種分解觀看與被觀看二元統一的機制。”福柯進一步分析:這種機制的意義在于“它使權力自動化和非個性化,權力不再體現在某個人身上,而是體現在對于肉體、表面、光纖、目光的某種統一分配上,體現在一種安排上。這種安排的內在機制能夠產生制約每個人的關系。君主借以展示其過剩權力的典禮、禮節和標志變得毫無用處。這里有一種確保不對稱、不平衡和差異的機制。因此,由誰來行使權力就無所謂了。”這樣一來,無須再使用暴力、枷鎖,權力的效能、強制力從某種意義上從應用轉向了“應用的表面”。外在權力拋棄了其“物理重力”,逐步趨向非肉體性,它造成“精神對精神的權力”。思想家預言這種全景敞視建筑注定要傳遍整個社會機體,它的使命就是變成一種普遍功能。這種匿名的“凝視”如今的確正以攝影頭、監控器的方式被普遍應用于社會領域,如醫院、交通、學校、銀行、酒店、工廠、軍隊等。現代社會的人們不得不在各種“凝視”的目光中獲得安全感,被監視與被保護合二為一,安全感的獲得必須以成為凝視的客體為代價。凝視主體的資格不得不讓位于各種現代高科技的“凝視”機器——這是現代人的無奈處境。
當代思想家為人們挖掘出“凝視”背后隱藏的意識形態,“凝視”所暗含的權力。在學者的層層剖析下,“凝視”所具有的政治學意義也就不言而喻。
(云南民族大學國際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