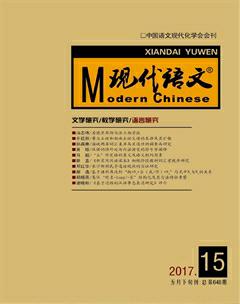從語言模因理論探討“黑”“白”“灰”義項發展的不平衡
劉雨薇+劉乃仲

摘 要:在語言學中,義項的形成受到很多因素的影響。本文首先介紹了“黑”“白”“灰”關聯義項的發展現狀,通過對《現代漢語詞典》中記錄的三種顏色詞的義項進行對比整理,指出“黑”“白”“灰”三種顏色詞在發展中除了具有義項發展的平衡性外,同時也存在著義項發展的不平衡性。其次,介紹了語言學界近年來新興的語言模因理論,從語言模因理論的角度來分析“語言模因”對這三種顏色詞義項發展過程中出現的不平衡現象的影響,并舉例說明。詞匯義項的發展促進了語言的發展,本文對這三種顏色詞義項發展的不平衡性進行探究,旨在應用語言模因理論來進一步研究漢語詞匯義項的發展。
關鍵詞:語言模因 義項發展 復制 傳播
一、“黑”“白”“灰”關聯義項的發展現狀
下表是對《現代漢語詞典》中記錄的“黑”“白”“灰”三種顏色詞的義項的對比整理:
顏色一直作為具有認知聯系的事物存在于人們的認知中,所以人們也習以為常地將顏色詞作為在義項上具有一定聯系的詞語。從上表中可以看到,“黑”“白”“灰”三種顏色詞的義項發展存在著一定的關聯性,但同時也存在著義項發展的不平衡性。這種不平衡性可能與多種因素有關,如:文化發展、價值觀念、認知心理等。本文主要從語言模因的角度來探討“黑”“白”“灰”三種顏色詞在義項發展中受到“語言模因”影響而產生義項發展不平衡的原因。
二、語言模因理論
語言的模因理論最早是由Dawkins在1976年發表的The Selfish Gene一書中提出的,與達爾文“優勝劣汰”的進化論相似,文化也會根據其適應社會發展的狀態而被保留或被淘汰,這樣說來,Dawkins有關文化基因與生物進化相同的學說確實具有一定的道理①。“模因”(meme)一詞在《牛津辭典》中的解釋是:“通過非遺傳的方式,特別是模仿的方式得到傳播的文化基本原理”。Dawkins把“模因”定義為:“文化傳遞的單位,它通過一個過程從一個人的頭腦跳入另一個人的頭腦,廣義而言,這個過程可以稱作是模仿”②。此后,Dawkins的學生Blackmore于1999年發表了專著The Meme Machine,這部著作的出版標志著語言模因理論發展到了一個新的階段。我國對“模因”思想的研究最早是由外語學界桂詩春教授在2002年為《語言與文化》一書作序時提到的。而對語言模因理論進行系統研究的是何自然先生,他在2005年發表了《語言中的模因》一文。
在模因理論中,“模因”根據“基因”一詞被創造出來,被認為是與“基因”有著類似遺傳與復制功能的個體,而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它本身就是“語言模因理論”中所提到的“模因”。語言模因是社會實踐的產物,它經常與具體的社會實踐緊密聯系在一起,新的社會實踐活動促使新模因生成③。模因依靠語言進行復制傳播,這既促進了文化的發展,也促進了詞匯義項的發展。因此,從語言模因理論角度來研究“語言模因”對顏色詞義項的影響以及對顏色詞相關詞匯的影響,能夠更好地闡釋“黑”“白”“灰”三種顏色詞在詞義演變過程中受到的社會文化的影響。
語言模因理論是根據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觀點而產生的,根據基因與生物進化之間的關系對模因與文化進化之間的關系進行探討,來尋找語言之間的關聯現象以及文化的遺傳和進化之間的規律。模因與基因一樣,依靠復制和傳播來發展和進化,如果把人體看作是文化,那么語言作為文化的載體就被看成是文化的模因。語言模因理論認為,模因是人類對現有語言的復制和傳播,而在復制和傳播過程中的異變促進了語言的發展。
按照語言模因理論,當“黑”“白”“灰”三種顏色詞中的某一個顏色詞根據社會的發展需要、通過對原有模因的復制和模仿而產生了新的形式時,人們在編纂辭書的時候就會對這種形式進行總結,這就成為了辭書中所記載的義項而被流傳使用,進而成為模因,并隨之產生新的詞匯。但辭書編纂也存在一些局限性,有很多發展的或正在發展中的詞匯沒有被辭書所收錄。
三、語言模因與“黑”“白”“灰”三種顏色詞各自的義項發展
語言模因的進化除了本身按照一定的規律在宿主之間傳播之外,還受到語言模因宿主的主觀能動作用的影響,宿主的情感、偏好和立場等心理狀態都是影響語言模因發生變異的因素,而這樣的變異引起了后續宿主在情感上的共鳴,并對此進行復制和傳播,這也是“黑”“白”“灰”三種顏色詞各自產生了感情色彩義項的原因之一。例如:“白身”最初是指穿著白色衣服的沒有官職的平民,通過宿主的主觀能動作用以及后續宿主之間的感情共鳴,“白”被廣泛看作是“平民”的象征,所以“平民”這一義項產生了“白~”的形式的詞語。例如:
(1)“白衣”:平民;未錄兵籍的民壯;文盲;古未仕者著白衣,后世稱布衣。
(2)“白士”:猶言寒士,白衣。
(3)“白丁”:平民;未錄兵籍的民壯;文盲。
(4)“白徒”:未受過軍事訓練的人。
“白~”形式的詞匯多含有“平民”義。而由于社會環境和文化傳統的原因,“白身”現象并沒有同時衍生出“穿著黑色衣服”的“黑身”與“穿著灰色衣服”的“灰身”。
高名凱在他的著作《語言論》中也提到這樣的現象,他認為:詞位變體是語言中的共時性的現象,這種變化也是語言中的共時性的現象,它們都不是語言演變的歷時現象;如果這種變化被語言社會所接受,成為語言事實,這種變化就成為了歷時性的變化④。這段話延續了他對語義發展的認識,他指出,語義的變化有兩種情形,一是語義在言語中的變化,一是語義在語言歷史上的變化⑤。這些顏色詞義項最開始的時候可能只是源于宿主個性的詞匯使用,這就是語義在言語中的變化,當這些語義因為具有實用性、合理性與時尚性而得以復制與傳播并被全民性地理解而作為語言中固定的義項被使用之后,就成為了語義在語言歷史上的變化,成為了新的語言模因。
在“黑”“白”“灰”三種顏色詞中,義項發展最多的是“白”,除了與“黑”“灰”在認知上具有關聯的一些義項外,“白”還有很多通過語言模因現象形成的義項。“沒有加上什么東西的,空白”這個義項就是通過“白~”形式在復制和傳播中的變異而產生的,宿主在需要表達能夠概括“沒有加上什么東西的,空白”的事物時發現了這些事物與“白”具有的一些相關性,于是新的模因就這樣產生。例如:endprint
(5)“白版”:書刊上沒有引出文字留下的空白(寫字的紙一般都是白色的)。
(6)“白頭”:不署名或沒有印章的文件。
(7)“白地”:沒種菜的地。
除了在概念意義上的復制和變化外,語言模因還在傳播的過程中產生了聯想意義,而文化基因也影響了人們的思維方式和聯想結果。在不同的文化基因下,推理在人們對語音模因的理解中起到重要作用從而形成語言模因。語言模因形成之后,人們在復制和使用的過程中對這些語言模因進行推理,使之在相應的語境中形成不同的義項,這些義項成功地與傳播時的語境一起凝固在語言思維中,人們在使用義項的時候,便不再需要經過推理,就可以直接判斷出運用的是哪個義項。
這些聯想意義也是由于人們對語言模因普遍的復制和傳播而得以形成的。語言模因受社會語境制約,它能在動態的社會中存在,表明它的傳播受到普遍的鼓勵和支持⑥。“黑”的“壞,狠毒”這一義項就是根據人們對“黑”的普遍理解所形成的。例如:
(8)“黑心”:比喻嫉妒,懷恨,邪惡等壞心腸。
(9)“黑店”:舊時指殺人越貨的客店;今指騙人,敲詐的商店。
(10)“黑巫術”:加害于人的巫術。
這樣的詞語是由于人們表達的需要而對已有語言模因進行復制,進而形成的新的詞語,這些詞語描述了某一類事物具有的共同特征,這些特征被人們認可并廣泛使用,形成了現今看到的“壞,狠毒”這一義項。在詞語中,雖然可以看到“白心”和“灰心”這樣的詞匯,但是卻沒有“白店”和“灰店”。從這個簡單的例子可以看出,人們創造這個模因并不是根據“黑”“白”“灰”三種顏色詞共有的內在認知聯系,而是對“黑”這個顏色詞本身獨立屬性中的一種進行聯想而引申出來的。另外,有一些人會認為“黑車”只是“黑顏色的車子”,之所以會出現這樣的笑話就是因為當事人沒有理解到“黑”具有“非法的”這一義項。
“白”的“象征反動”這一義項來源于巴黎公社時期,當時革命軍用紅色的旗幟代表自己的身份,而迫害革命軍的政府軍的旗幟是白色的,由此人們用“白色”象征“反動”,而隨著反動派不斷鎮壓革命的反動行為,宿主用“白色”象征“反動”這一概念得到了人們普遍的支持和理解,“白色恐怖”一詞也隨之而生,而“象征反動”這一義項也常被用在各種反動政府發動政變迫害革命軍的一系列事件上。于是人們在看到“白色恐怖”這一詞語時,馬上就會想到“反動”這樣的聯想意義。“白”還有“用白眼珠看人,表示輕視或不滿”這一義項,這一語言模因的產生很明顯地基于宿主對事物的觀察,在宿主觀察到人們用眼白來看人,是想要表達自己內心產生的被“輕視”和“不滿”的感覺時,通過對“白色”這一語言模因的復制和模仿,創造了“白眼”這個新的詞匯,這一詞匯的出現使后續宿主得以感同身受,故其傳播獲得了普遍鼓勵和支持,于是成為了新的語言模因。這些義項都是通過宿主對“白”這個語言模因的復制和傳播進而發生變異而出現的新的語言模因,一直以來辭書中對“白”義項的記載要比“黑”“灰”多上許多,這也說明了人們對“白”這個語言模因的使用頻率要高于“黑”與“灰”。
又如“灰”的“心情灰暗”義項的出現是由于宿主的主觀能動性,由于灰暗的天氣或者是“灰”自身帶有的“對物體燃燒后的無生命感產生的絕望心理”,使宿主產生了心情頹喪甚至絕望的感覺,宿主為了表達這樣的感覺使用了“灰心”這樣的詞語,這使后續宿主在相同的情境下有著與元宿主相同的感覺,于是不斷地派生出“灰念”“灰心”“灰溜溜”“灰頭土臉”這樣的詞匯來。這一義項最初使用的時候與模仿實際存在的“灰”這一具體事物有關,很少考慮到“灰”與“黑”“白”之間的聯系,所以“灰”關于“心情沮喪”這一義項與“黑”“白”所具有的義項之間的關聯性并不是很大。
相同地,語言模因的消失也是因為它的傳播失去了普遍的鼓勵和支持。例如,“白”在《辭源》中有“罰酒的酒杯”這一義項,但是在《現代漢語詞典》中,這一義項已經消失,甚至普通人如果沒有一定的歷史專業素養就很難想到“白”會具有“罰酒的酒杯”這一義項,其原因就是這一義項失去了普遍的鼓勵和支持,這種語言模因便消失在歷史中。相同的例子還有“黑”的“黑色的牲口”與“黑色的黍米”這兩個義項的消失。
四、結語
“黑”“白”“灰”三種顏色詞作為基本顏色詞被人們廣泛運用在語言中,它們的義項發展也經歷了漫長的歲月。語言本身就是一種語言模因,作為語言發展的因子,語言模因在語言的發展中起著重要的作用,它們因為自身的實用性、合理性和時尚性而形成,在后續宿主對元宿主的經歷“感同身受”的情況下進行傳播和發展,從而進一步促進新的語言模因的形成,這就是語言的發展現象,而詞匯則更明顯地體現了這一發展現象。通過語言模因理論對“黑”“白”“灰”三種顏色詞義項的變化進行探討與研究,可以發現漢語詞匯義項形成和發展的原因,也能夠更深刻地體會與探索漢語詞匯發展的內在規律。
注釋:
①Distin,Kate.The Selfish Meme——A Critical Reassessment[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②Dawkins,R.The Selfish Gene[M].New York:OUP,1976:192.
③謝朝群,何自然.語言模因說略[A].語言模因研究[C].成都:四
川大學出版社,2009.
④高名凱.語言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314-315.
⑤高名凱.語言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260.
⑥何自然.語言模因理論與應用[M].廣東:暨南大學出版社,
2014:51.
參考文獻:
[1]Distin,Kate.The Selfish Meme——A Critical Reassessment[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2]Dawkins,R.The Selfish Gene[M].New York:OUP,1976.
[3]謝朝群,何自然.語言模因說略[A].語言模因研究[C].成都:四
川大學出版社,2009.
[4]高名凱.語言論[M].北京:商務印書館,1994.
[5]何自然.語言模因理論與應用[M].廣州:暨南大學出版社,
2014.
(劉雨薇 劉乃仲 遼寧大連 大連理工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部中文系 116024)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