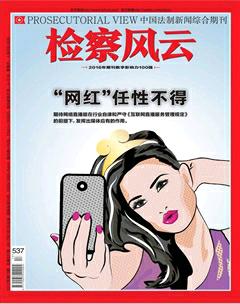直播時代,公民權(quán)益如何保護(hù)
柏立席
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在資本力量的推動下迅速壯大,其一旦發(fā)生侵權(quán)行為,借助網(wǎng)絡(luò)也會產(chǎn)生放大效應(yīng)。網(wǎng)絡(luò)直播對公民權(quán)益保護(hù)提出了更多的挑戰(zhàn)。
“網(wǎng)絡(luò)直播不同于網(wǎng)絡(luò)發(fā)帖和電視節(jié)目,后者可以通過內(nèi)容審查來實(shí)現(xiàn)有效的內(nèi)容監(jiān)管。但網(wǎng)絡(luò)直播是即時性的,只有內(nèi)容播出來以后才能發(fā)現(xiàn),因此,對其監(jiān)管就更加復(fù)雜和困難。”北京師范大學(xué)法學(xué)院教授、亞太網(wǎng)絡(luò)法律研究中心主任劉德良表示,“要應(yīng)對互聯(lián)網(wǎng)侵權(quán)行為,需把預(yù)防工作做到位。應(yīng)重點(diǎn)監(jiān)管侵犯人格權(quán)的行為,針對網(wǎng)絡(luò)直播的特點(diǎn),必須實(shí)施全程、實(shí)時、動態(tài)的監(jiān)管。”
“直播行為具有即時性,一旦行為發(fā)生,迅速傳達(dá)至受眾,便無法挽回。特別是當(dāng)某些主播從事淫穢表演、發(fā)表反動言論、鼓吹暴力或者從事其他違法甚至犯罪行為時,若不能事前防范,將造成惡劣的社會影響。”北京志霖律師事務(wù)所副主任、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協(xié)會信用評價中心法律顧問趙占領(lǐng)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他建議,對于網(wǎng)絡(luò)直播的監(jiān)管,需要結(jié)合業(yè)務(wù)模式、技術(shù)特點(diǎn)制定有效的措施,不僅包括實(shí)行主播實(shí)名制、黑名單制,還需要對主播建立一定的準(zhǔn)入門檻,通過比較嚴(yán)格的法律法規(guī)培訓(xùn),方可進(jìn)入網(wǎng)絡(luò)直播行業(yè)。對于平臺而言,不僅需要針對主播制定一系列的行為規(guī)范,更需要通過技術(shù)、人工等方式實(shí)時監(jiān)督主播的行為。
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關(guān)于貫徹執(zhí)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意見》第68條的規(guī)定,一方當(dāng)事人故意告知對方虛假情況,或者故意隱瞞真實(shí)情況,誘使對方當(dāng)事人作出錯誤意思表示的,可以認(rèn)定為欺詐行為。
在四川“偽慈善”事件中,主播顯然向“圍觀群眾”隱瞞了其“假慈善、真圈粉,偽捐款、實(shí)斂財”的真實(shí)目的,誘導(dǎo)大量網(wǎng)友關(guān)注的同時也通過“刷禮物”“購買虛擬貨幣”等手段斂財。依據(jù)《民法通則》及《合同法》規(guī)定,應(yīng)承擔(dān)欺詐的法律責(zé)任。此外,據(jù)《刑法》第266條、《慈善法》第107條的規(guī)定,如果網(wǎng)紅主播以非法占有為目的,虛構(gòu)事實(shí)或者隱瞞真相,騙取他人財物數(shù)額較大的,應(yīng)以詐騙罪論處。
加強(qiáng)行業(yè)自律,實(shí)名制、黑名單、分級制呼之欲出
在一系列“偽慈善”事件中,有關(guān)部門發(fā)現(xiàn),網(wǎng)絡(luò)主播的賬號被凍結(jié)后,往往很快又發(fā)布了新賬號,繼續(xù)吸引“粉絲”關(guān)注。業(yè)內(nèi)人士認(rèn)為,如果主播實(shí)名制登記和“黑名單”制度能夠嚴(yán)格執(zhí)行,那些劣跡主播將不再有生存土壤。中國智能多媒體終端技術(shù)聯(lián)盟秘書長、互聯(lián)網(wǎng)專家包冉表示,在移動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直播的產(chǎn)業(yè)規(guī)模迅速擴(kuò)大,如不出臺清晰的管理規(guī)范,行業(yè)很容易變得混亂不堪。“實(shí)名制+黑名單”可行,網(wǎng)絡(luò)直播不能再任性。
“‘黑名單在網(wǎng)絡(luò)直播行業(yè)意義重大。很多網(wǎng)絡(luò)平臺為了商業(yè)利益,不惜突破法律底線留住能夠獲利的主播,即便明知其是‘問題主播,平臺擔(dān)心主播‘跳槽,也不敢輕易得罪。”中國政法大學(xué)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表示,“黑名單”制度建立后,對納入“黑名單”的主播將“禁止重新注冊賬號”,并向省級和國家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辦公室報告。這樣一來,“黑名單”主播將不能肆意“用腳投票”來要挾平臺,也就讓法治與誠信重回直播市場。
在由多家業(yè)界研究機(jī)構(gòu)近日聯(lián)合舉辦的“數(shù)字論壇——直播行業(yè)監(jiān)管風(fēng)暴專家研討會”上,中國互聯(lián)網(wǎng)協(xié)會秘書長盧衛(wèi)提出施行直播“實(shí)名制”。他認(rèn)為,落實(shí)主體責(zé)任和黑名單制度都是實(shí)現(xiàn)“實(shí)名制”的重要手段。
中國傳媒大學(xué)媒體法規(guī)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李丹林認(rèn)為,直播行業(yè)應(yīng)建立內(nèi)容分級制度。比如,直播間可根據(jù)播出內(nèi)容種類和表現(xiàn)尺度、語言狀況確立級別,對于不同級別直播,具體監(jiān)管措施應(yīng)有不同。
筆者注意到,2016年12月1日起實(shí)施的《互聯(lián)網(wǎng)直播服務(wù)管理規(guī)定》提出要建立“信用等級制度”。《規(guī)定》明確要求,對直播實(shí)施分級分類管理,建立互聯(lián)網(wǎng)直播發(fā)布者信用分級管理體系,建立黑名單管理制度,對納入黑名單的互聯(lián)網(wǎng)直播服務(wù)使用者禁止重新注冊賬號。近期,主播“黑名單”制度已隨著《規(guī)定》出臺逐步建立。
“《規(guī)定》要求網(wǎng)絡(luò)主播享受的管理和服務(wù)與自身信用等級直接掛鉤。主播權(quán)限不是和關(guān)注度掛鉤,而是和信用記錄掛鉤,這就意味著商業(yè)利益將與信用掛鉤,誠信將重回網(wǎng)絡(luò)直播市場。”中國政法大學(xué)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認(rèn)為,這是新規(guī)最大的創(chuàng)新之處。
專項整治、加強(qiáng)立法,對直播野蠻生長說“不”
由于競爭過于激烈、平臺運(yùn)營成本過高等因素,一些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開始游走在灰色地帶,采取“擦邊球”策略,利用涉黃、涉賭、涉暴甚至涉毒等內(nèi)容吸引用戶,并催生出一批靠低俗內(nèi)容起家的“網(wǎng)紅”群體,滋生出行業(yè)各種亂象。這些都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對待網(wǎng)絡(luò)直播這樣的新生事物,要做到制度先行、規(guī)則完善、監(jiān)管有力,促進(jìn)其健康發(fā)展。
根據(jù)《全國人大常委會關(guān)于加強(qiáng)網(wǎng)絡(luò)信息保護(hù)的決定》《國務(wù)院關(guān)于授權(quán)國家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辦公室負(fù)責(zé)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內(nèi)容管理工作的通知》《中華人民共和國網(wǎng)絡(luò)安全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計算機(jī)信息系統(tǒng)安全保護(hù)條例》《互聯(lián)網(wǎng)直播服務(wù)管理規(guī)定》《互聯(lián)網(wǎng)信息服務(wù)管理辦法》《互聯(lián)網(wǎng)新聞信息服務(wù)管理規(guī)定》和《計算機(jī)信息網(wǎng)絡(luò)國際聯(lián)網(wǎng)安全保護(hù)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guī),中國已開展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專項整治工作。
“政策能否發(fā)揮實(shí)效,關(guān)鍵要看落實(shí)。”清華大學(xué)新聞與傳播學(xué)院教授沈陽表示,直播不能“向錢而生”,要遵循社會公德,傳播積極、健康、主流的內(nèi)容。直播經(jīng)濟(jì)發(fā)展極快,相關(guān)部門應(yīng)根據(jù)最新情況制定政策實(shí)施細(xì)則,進(jìn)一步加強(qiáng)引導(dǎo)和規(guī)范,讓直播更加健康有序發(fā)展。
近日,筆者從公安部網(wǎng)站獲悉,為切實(shí)加強(qiáng)對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的安全管理,依法打擊利用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實(shí)施的各類違法犯罪活動,進(jìn)一步凈化網(wǎng)絡(luò)環(huán)境,公安部網(wǎng)絡(luò)安全保衛(wèi)局召開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專項整治工作會議,決定在全國范圍內(nèi)組織開展為期三個月的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專項整治工作。專項整治期間,全國公安機(jī)關(guān)網(wǎng)安部門將全面檢查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安全管理制度措施落實(shí)情況,指導(dǎo)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全面清理各類違法有害信息,依法關(guān)停傳播違法信息的賬號、頻道,查處存在違法違規(guī)行為的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
工作中,重點(diǎn)整治三類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一是群眾舉報、網(wǎng)絡(luò)曝光或網(wǎng)民反映問題集中的;二是涉嫌存在色情表演、聚眾賭博以及其他違法行為的;三是企業(yè)自身管理秩序混亂、安全管理制度措施不落實(shí)的。公安機(jī)關(guān)表示:對利用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傳播、散布淫穢色情、暴力、恐怖、教唆犯罪等違法信息,或組織色情表演、聚眾進(jìn)行賭博、實(shí)施詐騙等違法犯罪活動的,堅決依法打擊,追究相關(guān)人員的法律責(zé)任。
2017年3月28日,全國“掃黃打非”辦公室做出部署,從3月至11月,開展“凈網(wǎng)2017”專項行動,聚焦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兩微一端”、彈窗廣告及網(wǎng)絡(luò)文學(xué)作品等四個領(lǐng)域,嚴(yán)打制售傳播淫穢色情信息行為,并督促網(wǎng)絡(luò)企業(yè)落實(shí)主體責(zé)任。其中,把整治違法違規(guī)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列為首要對象。對問題嚴(yán)重或無證經(jīng)營的網(wǎng)絡(luò)直播平臺,堅決關(guān)停網(wǎng)站并下架APP。
2017年4月10日,安徽省泗縣公安局法制大隊大隊長周楚接受筆者采訪時直言:網(wǎng)絡(luò)從來都不是法外之地,網(wǎng)絡(luò)文化也不能任由“毒草”侵害,要從規(guī)范網(wǎng)絡(luò)文化,促進(jìn)網(wǎng)絡(luò)管理法制化的角度來進(jìn)行思考和治理網(wǎng)絡(luò)直播。作為互聯(lián)網(wǎng)市場的參與者,必須在法律法規(guī)的規(guī)定下合法參與、有序經(jīng)營,這一點(diǎn)毋庸置疑。
鏈接
執(zhí)法直播,傳播正能量
提起“網(wǎng)紅”可能更多的評判是負(fù)面甚至貶義。而此時,全國范圍內(nèi)的交警執(zhí)法直播可以說讓廣大網(wǎng)友眼前一亮。執(zhí)法直播其實(shí)是順應(yīng)網(wǎng)民需求,大部分網(wǎng)友更愿意看到這種陽光的形象、更愿意聽到這種正能量的聲音。讓執(zhí)法交警成為“網(wǎng)紅”,為網(wǎng)絡(luò)直播帶來的是一股清流,能把正確的價值觀、應(yīng)遵循的法律規(guī)范以及實(shí)用的常識傳遞給網(wǎng)民。
從2016年8月9日起,公安部交通管理局組織多地公安交管部門,通過官方微博、直播平臺等渠道開展為期一個月的“全國交警直播月”活動,直播交警一線執(zhí)法現(xiàn)場。
2016年8月16日,湖北高速交警以“暑運(yùn)期間的重點(diǎn)違法行為整治”為主題開展了首次執(zhí)法直播,吸引了15.9萬網(wǎng)友觀看,18.3萬點(diǎn)贊。
2016年8月30日,安徽合肥交警在6個網(wǎng)絡(luò)平臺直播夜查酒駕行動,吸引150余萬網(wǎng)友觀看,并收到30多萬個點(diǎn)贊。
2017年4月,筆者參與了安徽省泗縣公安局交警大隊進(jìn)行的交通違法行為集中整治直播活動。在直播視頻中,可以清晰地看到交警執(zhí)法的全過程,也能夠聽到民警與受檢查車主們的對話。
在執(zhí)法前沿開展視頻直播,形成強(qiáng)大執(zhí)法直播矩陣,并與網(wǎng)友實(shí)時互動,幾個小時直播,共有超過5萬人在線觀看,收到3萬人次網(wǎng)友點(diǎn)贊。
采訪中,該縣交警大隊長陳保護(hù)對筆者說:“網(wǎng)絡(luò)直播就是讓民警在‘陽光下執(zhí)法。它既能讓廣大網(wǎng)民對交警執(zhí)法進(jìn)行監(jiān)督,也將交管工作的種種不易展現(xiàn)在公眾眼前,其過程也是一個普法過程。人們可以直觀地看到那些不文明、危險和違法的行為是如何接受懲處的。既可以讓旁觀者接受一次普法教育,同時還可以傾聽網(wǎng)友對公安交通管理工作和交警隊伍建設(shè)的意見和建議,使之成為公安交通管理部門聽民聲、察民意、解民憂的重要渠道。”
這是用網(wǎng)絡(luò)直播作為推進(jìn)交警執(zhí)法隊伍規(guī)范化建設(shè)的一種創(chuàng)新嘗試,把民警的執(zhí)法過程直接展現(xiàn)在鏡頭下面。要適應(yīng)這樣一種網(wǎng)絡(luò)輿論生態(tài),這就極大地推動了民警自覺下工夫提高執(zhí)法水平,以主動的姿態(tài)積極樹立文明規(guī)范執(zhí)法形象。
隨著機(jī)動車保有量和駕駛?cè)藬?shù)的不斷增長,道路交通安全的形勢也更加嚴(yán)峻。交警在日常工作中進(jìn)行的普法教育可能是一對一的,查處一起、教育一起,而執(zhí)法直播直接吸引網(wǎng)友“圍觀”,現(xiàn)場生動地通過“以案說法”的形式同時向幾十萬人講解了交通違法行為的危害性、處罰標(biāo)準(zhǔn)以及安全行車常識,極大地擴(kuò)充了普法教育的覆蓋面。
公安部交管局相關(guān)負(fù)責(zé)人表示,通過開展“全國交警直播月”活動,既能讓網(wǎng)民獲得交通安全法律常識和安全出行知識,形成遵守交通規(guī)則的良好習(xí)慣,也可以有效震懾嚴(yán)重交通違法行為,更可以大大促進(jìn)基層一線交通民警嚴(yán)格、規(guī)范、公正、文明執(zhí)法,切實(shí)提升交警隊伍正規(guī)化、專業(yè)化、職業(yè)化水平。
將交警執(zhí)法全過程通過直播平臺呈現(xiàn)出來,有何積極意義?中國政法大學(xué)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長王敬波認(rèn)為:第一,能起到促進(jìn)交警執(zhí)法規(guī)范化的效果;第二,能起到有效震懾交通違法行為的效果;第三,能起到最大限度普法的效果;第四,對整個執(zhí)法行為起到固化和留痕的效果。王敬波認(rèn)為,在很多執(zhí)法領(lǐng)域都可以推廣這種直播形式,尤其是在城管執(zhí)法、環(huán)境執(zhí)法等容易和執(zhí)法對象產(chǎn)生糾紛的領(lǐng)域。當(dāng)然也要考慮直播的行政成本,回應(yīng)社會關(guān)切,聚焦重點(diǎn)問題,實(shí)現(xiàn)直播效果最優(yōu)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