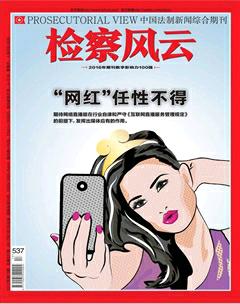在官,俸金外皆贓也
沈棲
大凡讀過《官場現形記》《廿年目睹之怪現狀》,大體都能窺察到晚清吏治的腐敗。其中描寫的各色官僚莫不是寡廉鮮恥、卑劣齷齪之徒,諸如做賊的知縣、盜銀的臬司、媚洋的制臺、貪色的候補道、賣官的觀察……讀這些譴責小說,確實猶如看一幅幅奄奄待斃的封建帝國社會圖卷。“政由賄成”,陜西糧道張集馨《道咸宦海見聞錄》以這四個字總結晚清每況愈下的現狀和最終覆滅的成因,還是頗有見地的。
客觀而言,“愛新覺羅”剛打下江山時,注重吏治,官場還是比較清明的。自雍正二年(1724)始,實行了“廉俸制”,即除正俸外,另給所謂由“耗羨”轉變而來的“養廉銀”,而且后者遠遠超過前者,這便給官場貪腐打開了巨大的空間。
晚清時期,整個官場形成了這么一種態勢:“有政則有賄,無賄不成政;有政皆賄,以賄為政。”光緒朝貴州舉人胡東昌曾憤激條陳:“當今之六部各院堂官,具有天良者無幾。其平日進署當差,司員之賢否勤勞不問,專以賄賂之厚薄為其優劣。”康熙治吏時有一個極為荒謬的論點:“所謂廉吏者,亦非一文不取之謂也”,以致形成“上以賄求之下,下以賄獻之上”的“賄賂公行”的官場頹勢。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清代諸多“陋規”如別敬、冰敬、炭敬、節敬、文敬等等,形成了官場灰色收入的常態。康熙五十六年,江西巡撫白潢按要求在奏折中向皇帝稟報自己每年有五項“陋規”收入:一、節禮五萬兩;二、漕規四千兩;三、關規兩千四百兩;四、鹽規一萬兩;五、錢糧平頭銀八千兩,總數達七萬四千四百兩。順治、康熙時代的吏科給事中林起龍曾這樣概括一個州縣官員所需敬送的禮金:“參謁上司,則備見面禮;凡遇時節,則備節禮;生辰喜慶,則備賀禮;題授保薦,則備謝禮;升轉去任,則備別禮。”連以清官著稱的林則徐也有公然收受“陋規”的劣跡。《道咸宦海見聞錄》一書云:“道光二十六年,陜荒,督撫將軍陋規常如支送”,其中的“撫”即是時任陜西巡撫的林則徐。
當然,清代還是有清正廉潔的官吏,如世人熟悉的“天下第一廉”于成龍。這里,我要特別推崇順治年間在福建任知縣的李爝,此人以耿介自矢,從不額外妄取一文錢。他在家書中交代:“在官,俸金外皆贓也,不可以絲毫累我。”李知縣不止是自己遠離賄賂,還嚴厲要求家人把各類“陋規”拒之門外,否則便是“累”我——辱了我英名,害了我仕途。他常年穿黑布衣,坐竹柴車,吃糙米飯,其上司以為他家眷多,俸祿不夠開銷,派人送上千金,還批文給他增加“食邑”,李爝一概謝絕,他說:“貧而不貪,以貧為師。”從這個意義上說,“貧官”與“清官”的距離是非常近的,幾可畫上等號哩!
應當指出:封建社會的清官“以貧為師”,雖有“不負民”的動因,但首先他是維護地主階級的根本利益,使國家機器在封建統治的秩序內運轉,其境界自是無法與共產黨的領導干部相提并論。盡管兩者的信仰、宗旨不同,但“官到能貧乃是清”的為官之道則是古今揆一的。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領導干部必須加強自律、慎獨慎微。”“慎獨”和“慎微”是一名領導干部“自律”的兩個方面。如果說,“慎獨”是測定領導干部在私底下、無人時能否做到“心存敬畏”,那么,“慎微”則是考驗其在細微處能否做到“手握戒尺”。
大凡貪官在落馬之后,懺悔自己墮落往往歸咎于兩個字:貪欲。從缺失“慎微”而貪欲漸長,最終收受巨額賄賂,這是一批貪官犯事的基本軌跡。北京市委原副書記呂錫文在獄中懺悔時說:“我現在想想,真的是從‘小意思拿起,一點點地放松、放縱,直至落入萬丈深淵了。”看來,我黨的領導干部還得接受“在官,俸金外皆贓也”這一箴言,并不妨列其于座右矣!
圖:付業興 編輯:鄭賓 393758162@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