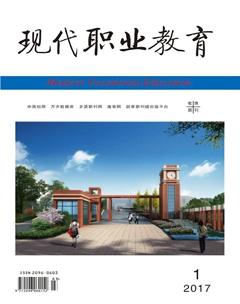淺析《飄》譯者主體性的體現
(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北京 100028)
[摘 要] 翻譯者不能將自己視為原作者背后忠誠的跟隨者,應透過說明語言令本人躍然紙上,以此來獲取類似原作者的重要位置。主要通過分析討論三個中文版本《飄》的截取部分,以翻譯者為中心來進行論述。
[關 鍵 詞] 譯者;主體性;《飄》
[中圖分類號] I106.4 [文獻標志碼] A [文章編號] 2096-0603(2017)03-0186-02
一、引言
從事文學翻譯的同時,翻譯者不應只是一個原文的說明者,而且也是一名原著的見證者,他發揮著連接不同語種不同文化的橋梁作用。因為原著文字含有“歷史性”,使得來自時空的間隙能在原作者和翻譯者之中產生,而翻譯者也無法準確再現原著中的情形布置,再加上原作者不能充分照顧到所有的讀者,因此這使得譯者對原文的主觀性創造才有了余地,譯者主體性的發揮才有了可能。誠然,翻譯者在自由發揮的同時,需要兼顧很多方面的問題,例如原著的文字層次、原作者的主觀意愿、審美標準和文化情形,而且翻譯工作并非簡單的照搬,譯文應該滿足出自原著,但又不僅僅是原著文字的要求,翻譯者應在其中融合自己的主觀想法。
二、譯者主體性的理論基礎
(一)基本內涵
按照哲學方面來講,主體性即“主體在行為運動中基本作用的展現,機動的喚醒客體,感染客體,掌握客體,令其作用于主體的特性”。通過對譯者身份和地位的分析可知,翻譯者的主體性主要表現在兩個層面:“展現在理解原著活動中的主體性和表現在欣賞再重生活動中的主體性”。
(二)譯者主體性在文學翻譯中的表現
像之前我們提到過的,對翻譯的人本身來說這種發揮就是定向的,主要原因是太局限于翻譯最初所受到的對象語言的風格影響和當地文化習俗等等,自身也有很大的原因,這一節主要是通過翻譯者的主觀和方法等角度來對他主體性表現力的解析。譯者主體性在文學翻譯中的表現有時也會成為其制約因素。
1.譯者動機
每一個翻譯者都是懷揣著某一個目標來展開翻譯工作的,這一種目標完全地表現在整個翻譯工作中,像文字摘選、段落層次、語言能力,而且還需要考慮目標讀者的感受。歐洲翻譯界嘗試過三種典型,那就是杰羅姆典型、赫拉斯典型和施萊爾馬赫典型,與杰羅姆典型和赫拉斯典型相比較,施萊爾馬赫典型則非常重視譯文能夠為讀者展現出原著的原汁原味。當然,此典型極大地提高了翻譯者在文學運動中的重要地位。
目標論將翻譯者的工作目的視為他們進行文學活動的方針,翻譯者會不擇手段地發揮自己的才學,提高自身的創造性,以及改變自己的翻譯手短和翻譯技巧來克服從事文學活動中的重重阻礙,以此實現他們心中的目標。翻譯者的目的性往往取決于他們所在的時間和空間以及他們不同的欣賞力水平。
2.翻譯策略
從事文學活動時蘊含著兩種翻譯的方針,最早來源于施萊爾馬赫的言論:“如果翻譯者可以使讀者朋友們主動去貼近原作者,而令原作者保持原樣;否則就應該使原著內容向讀者朋友主動表達原作者的意圖,而不改變讀者朋友的位置。”有很多時候,語言上的死板翻譯和在理解的基礎上有感情的翻譯將對翻譯者是否能夠發揮出主體性產生巨大影響。事實上,歸化與異化在翻譯批評中的爭議一直存在,歷史上流傳下來的有關翻譯技巧的看法令翻譯者應該把“對齊”“等同”在原著語言和譯文語言中達到一個近似相同的表現高度,并且不應出現直白的譯文,還強調翻譯者的工作不應僅僅是做出譯文,可是這種看法完全無視了文化語言與文化傳統上本質的差別,即語言的等同絕非能達到文化差異的等同,這完全是因為任何翻譯者都不可能將原著與譯文做到完全一致。當然,翻譯者的工作也并非是對原著簡單的照搬照抄,韋努蒂就覺得這樣做下去將使翻譯者的地位無從尋找,理所當然的,他認為翻譯者應該將目標語言的文化背景和特定的語言情境完美地結合在一起,與此同時,還要用這些東西適當地對原著語言的相關背景與歷史環境進行修改,這樣一來的話,由于譯文添加了一些原著不曾包含的東西,使得翻譯者的能力能夠被發現,那么也就不存在上文所述的翻譯者的隱藏狀態。
三、選取的三個譯本及其譯者的翻譯動機與策略
翻譯者不能夠將自己視為原作者背后忠誠的跟隨者,應透過說明語言令本人躍然紙上,以此來獲取類似原作者的重要地位。名著《飄》講述的是時隔美國南北戰爭時期,慘遭戰亂迫害的南方家庭婦女的內心真實痛苦與命運,她們懷揣著對戰爭之后美好生活的期盼,再到由于恐怖的戰爭無情地將身邊親人的性命奪取,內心的無可奈何將她們拉入命運的低谷,她們必須面對殘酷的命運和在戰爭中被摧毀故鄉流離失所的悲慟。不同的行為目的導致翻譯者在從事翻譯工作時選擇不同的翻譯技巧,不同語種間的文化差異、語言文字間不同的特征,再加上不同歷史環境等種種因素全部都要在譯文中得到表達,此時翻譯者的才能得到了充分的施展,他不再是簡單地解析原著,而是將自身文化特點適當地在譯文中進行融合,以達到不同文化間的融合。這一點我們能從很多譯文討論中察覺到譯者角度以及將自身文化與原著相結合的影子。總而言之,譯者角度是翻譯者將譯文完美地呈現在讀者面前的主要手段和翻譯技巧。
(一)選取譯本
本篇文章分別對來自不同歷史時期的翻譯工作者甚至處在相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性別的翻譯工作者的翻譯作品進行研究。這些作品就是來自曾一度任商務印書館編譯員的傅東華先生的《飄》、擔任廈門大學外文學院教授的李美華的譯本《飄》、擔任上海翻譯家協會理事的陳良廷的譯本《亂世佳人》。
“著作《飄》的流行并非是無厘頭的,國內的的確確應該出現一本它的譯本,況且,《飄》在大眾心理已經不僅僅是一本戰爭時期的小說,它更是一本充滿愛情色彩的小說。”傅東華下定決心準備從事《飄》的翻譯工作。本篇文章選取了1979年傅東華先生翻譯的《飄》重印本中的片段進行研究。而陳良廷翻譯的《亂世佳人》是在相隔50年的1990年完成的,李美華翻譯的《飄》是在相隔60年的2000年完成的,這個時間點跨度之大也是選取這三本的原因之一,正因為時間跨度大才能夠表現出這些來自不同歷史時期的、不同時代背景的翻譯者他們的不同翻譯的目的以及不同的翻譯技巧。
(二)《飄》譯者的翻譯動機與策略
1.《飄》譯者的翻譯動機
不同的行為目的決定了不同的翻譯工作者在從事文學活動時所表現出來的不同的翻譯技巧。施萊爾馬赫認為翻譯策略主要有兩種,即歸化和異化。翻譯者需要兼顧很多方面,因此要運用不同的翻譯技巧,比如在語言文字的摘選、句子的技巧提煉等許多層次,所以在很多譯文中會發現翻譯工作者通常會在原著基礎上適當添加或是刪減來達到想要達到的目的。
原著用極其詳細的文字語言對斯嘉麗的外貌特點進行生動的描述,看著三份翻譯作品,都能在紙上感受到斯嘉麗完美的相貌,然而原著文中并未有李譯的最后一句,似乎有點多此一舉。可是細讀之中便會發現,處于這個時期的斯嘉麗不正是在無憂無慮的年紀,再加上自己貌美年輕、家庭殷實、個性歡快等等,所以“鬼精靈”的比喻對于此刻的斯嘉麗再合適不過了。
2.《飄》譯者的翻譯策略
傅東華先生的翻譯作品中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對原著文段的刪減或是選擇省略一部分。譬如原著中第四章有好幾段是對佐治亞州南部民眾鄉情的詳細描述,但是在譯文中只是區區一小段;第十八章中斯嘉麗在亞特蘭大被敵人圍攻后所表現出來的憂傷感想與此時對母親和家庭的深深思念這一部分的刪減;第二十五章有好幾頁都是在描述斯嘉麗在回到塔拉后就下定決心不想再忍受饑餓的內心獨白也被翻譯工作者簡化成了幾百字。其實傅東華先生的譯本中還省略了好幾部分的原著內容。中西方在長篇小說的寫作上是有很大區別的,前者認為作品的發展情節非常重要,而不注重文章細節方面的表達;后者則認為一篇小說有關文章的時代背景等的細節對小說的影響巨大。
一直以來作為翻譯界的重中之重的就是文章翻譯的歸化和異化,曾有人認為“在很多情況下,翻譯工作者應該盡自己最大的能力將處于不同文化不同背景的原作者和目標讀者牢固地聯系在一起,讓他們之間不至于由于文化代溝產生間隙。萬一情況特殊,退一萬步講,也應該對原著文章進行適當的變通”。還有人認為所謂“歸化”應該是在文化語言文字方向上的歸化,而“異化”則是表現在不同文化特色背景下盡可能的異化。另外,從事翻譯工作還要盡最大可能地將原作者的寫作意圖、文字特點等傳達給目標讀者,而且,“出自異化的翻譯作品更能使自身的民族特色文化更加多彩多姿,同理,祖國博大精深的語言也會因為成功的異化而錦上添花”。
四、總結
從事文學翻譯的同時,翻譯者不應只是一個原文的說明者,而且也是一名原著的見證者,他發揮著連接不同語種、不同文化的橋梁作用。所以,聯系以上所講到的翻譯工作者的主體性表現,我們可以了解到,所謂的翻譯工作已經不僅僅是簡單刻板直白地解釋原著文字,而是要結合翻譯工作者本身所處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色在譯文中適當地發揮展現出來,同時也要兼顧目標讀者的接受能力,盡最大可能地降低目標讀者的接受成本,使原著思想能夠最大化地被目標讀者所吸收。誠然,由于不同文化、不同地域等的局限性,不同的翻譯工作者也不可能對同一本名著釋以相同的理解。譯者的主體性在文學翻譯中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在此,我完全有把握說出我的想法:伴隨著時代的進步,伴隨著文學工作的發展,不同地域文化間的不斷碰撞與交流,作為翻譯工作者所表現的主體性將會愈發顯得重要。
參考文獻:
[1]李慶明,劉婷婷.譯者主體性與翻譯過程的倫理思考:以文學翻譯為例[J].外語教學,2011(4):101-105.
[2]劉國兵.翻譯生態學視角下的譯者主體性研究[J].外語教學,2011(3):97-100.
[3]屠國元.布爾迪厄文化社會學視閾中的譯者主體性:近代翻譯家馬君武個案研究[J].中國翻譯,2015(2):31-36.
[4]楊柳.從接受美學視角看譯者的主體性:以傅東華翻譯的《飄》為例[J].重慶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7):104-106,120.
[5]張睿思.女性主義視角下的譯者主體性在《飄》譯本中的影射[J].吉林省教育學院學報(下旬),2013(9):120-122.
作者簡介:劉佳銘(1990—),男,山西大同人,2012年6月畢業于大連外國語學院日本語學院,獲文學學士學位,2012年8月供職于北京外交人員服務局,任曰語翻譯助理,2013年8月至今在職攻讀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英語(經貿翻譯)碩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