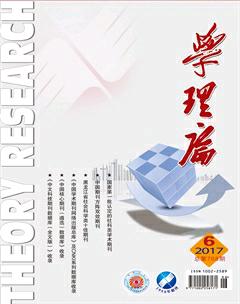周恩來與1954年日內瓦會議
李銳
摘 要:20世紀50年代的援越抗法是中國第一次軍事援助,采取了基本可能用到的方式,全力援助。確保了援越抗法戰爭的最終勝利。在這一問題的解決過程中,中國代表團特別是周恩來個人發揮了積極的作用,最終實現了國際局勢在一定程度上的緩和。
關鍵詞:周恩來;援越抗法;日內瓦會議
中圖分類號:D82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7)06-0036-03
國際關系的分析層次可以分為體系、國家和個體三個層次。其中個體層次即從微觀上分析個體因素對外交決策的影響。人們在提及外交決策時,往往只會以國家或政府的名義來冠名,比如日本明治政府的“大陸政策”,俄國的“遠東政策”,中國的“一邊倒”政策等等,而實際上,外交決策是由個人或者由個人組織起來的群體做出的。因而形式上作為國家行為的外交決策,實則是領導人的個人行為。因而外交決策者個人的因素也是不能忽視的,它往往能成為左右一個國家做出外交決策以及領導人在外交場合做出舉動的重要依據。本文即從個體層次對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上解決國際爭端所起的作用進行分析。
一、中國決定援越抗法
任何一個問題的形成,都有其復雜的原因,印度支那問題也不例外,這一問題的形成一方面包含了一個國家基于現實主義層面的考慮,另一方面,也與領導人個人想法有關,領導人的想法上升為國家意志,那么國家機器就會以此為宗旨行事。這一問題產生,首先是由于進行了第二次工業革命的資本主義法國,其經濟是外向型的,需要大量的原材料和資本輸出市場,而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是,法國也是迷信堅船利炮的,他們一直以此作為其經濟發展的后盾,因而把印度支那半島納入其殖民體系之中就成了法國的不二選擇。另外,第二次工業革命之后,帝國主義列強開始掀起了瓜分世界的狂潮,作為老牌資本主義強國的法國自然不甘落后。從19世紀40年代開始,中國正處在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深淵的過程中,對于越南事務已經無暇顧及,這也從客觀上使法國有了可乘之機。因而入侵越南主要是基于法國國內的經濟發展狀況,以及當時的國際形勢做出的決策。此外,新航路開辟特別是工業革命之后,直到二戰結束初期,法國政府領導人頭腦中所固有的殖民主義思想也是法國入侵越南的主要原因,當法國領導人的這種思想上升為國家對外政策之后,對越南采取的軍事行動也就成了法國的國家行為,這也直接導致了近代以來法國對于印度支那半島的兩次主要軍事行動。
法國對越南的入侵可以追溯到19世紀50年代末,直到二戰結束后,法國仍沒有放棄對印度支那進行控制的想法。這也直接推動了20世紀50年代新中國在成立伊始進行的第一次大規模的對外軍事援助——援越抗法。其實早在新中國成立前的1945年的8月16日,在越南獨立同盟(簡稱越盟,越共前身)的領導下,越南發生了全國性的大起義。接著起義迅速擴展到全國,最終推翻了阮朝末代皇帝保大的統治,建立了以胡志明為主席的越南民主共和國。但越南原來的宗主國法國不甘心失敗,于9月出兵越南,企圖恢復其在越南的殖民統治。以胡志明為首的越盟領導人民進行了堅決斗爭,但人數和武器裝備方面處于絕對劣勢。“當時法國在越南全國重要地帶部署的軍隊達10多萬人,而越南的武裝力量只有8萬人;且使用的多是簡陋的武器,沒有經過嚴格的訓練”[1],因此形勢并不樂觀。在這種情況下,胡志明開始尋求外援。當時與胡志明及其領導的印度支那共產黨有一定聯系的中國共產黨通過中共中央設在香港的支部對越南提供了一些援助[2]119-120。但由于當時中國革命正處于關鍵時期,所以中共提供的援助是有限的,可以說,越南此時的抗法斗爭基本上處于孤軍奮戰的狀態。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新中國的成立大大鼓舞了越南人民,為胡志明爭取大規模物資援助,甚至請中國直接出兵提供了契機。于是1950年初,胡志明秘密來華求援,中共領導人出于“唇亡齒寒”的古訓認為,印度支那半島與中國的西南邊界毗鄰,一旦法國占領整個印度支那半島將對中國自身的地緣安全帶來嚴重威脅。另外,在1949年6月劉少奇秘密訪蘇之時,斯大林提出了革命分工的建議,于是,在自己國內仍然處在百廢待興狀態的情況下,中國仍然決定援助越南,向越南提供了大量的武器彈藥及其他物資援助,在軍事援助的問題上,中國采取了一種相對折中的方案,即派遣軍事顧問團,幫助越南培訓軍事干部,以及在制定戰術的過程中提供建議和意見。通過這一方案的實施,確保了高平戰役、奠邊府戰役等一系列戰役的勝利。特別是奠邊府戰役的勝利,為后來日內瓦會議上爭取談判的主動權,提供了巨大幫助。
二、周恩來積極參與日內瓦會議相關工作
印度支那半島的緊張局勢引起了大國的關注。1953年9月28日,蘇聯政府已經向美英法等國政府發出照會,建議在日內瓦召開有中華人民共和國代表參加的五國外長會議,以便更好地解決印支問題。1954年2月,蘇美英法四國外長在柏林召開會議,蘇聯外長莫洛托夫建議把印度支那問題列入原本為單獨解決朝鮮問題的日內瓦會議的議程中,實現印度支那半島的停戰。對于這一提議,其他三國反應不一。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反對召開五國外長會議,但由于蘇聯的堅持以及英法等國對此與美國持相反的態度。希望盡快實現停戰,因而柏林外長會議最終達成了在日內瓦召開新的五國外長會議的決議。
(一)會前精心準備,參與制定談判方針
柏林會議之后,1954年2月17日和3月2日,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向中國政府分別提交了有關柏林四國外長會議以及邀請中國政府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材料,3月4日,中國政府復電表示接受邀請派全權代表參加會議。而在此之前,周恩來就開始了參加日內瓦會議前的一系列準備工作。2月27日,周恩來主持召開了日內瓦會議籌備工作的干部會議[3]356,強調了中國要在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這一重大問題上發揮作用。另外,他個人還為開好日內瓦會議做了積極準備,閱讀了有關召開日內瓦會議的大量資料,并為會議的準備工作和中國代表團人選以及談判方針等問題,和外交部的同志進行商談。
同日,周恩來出席了中央工作會議,會議通過了由他親自起草的《關于日內瓦會議的估計及其準備工作的意見》,指出召開日內瓦會議有新中國參加這件事本身,就“已使緩和國際緊張局勢的工作前進了一步”[3]356,美國低估日內瓦會議的作用,預言它將得不到任何結果。但美、英、法三國在朝鮮和印支問題上“意見并非完全一致,它們的困難也很多”[3]356。周恩來強調:“根據以上所述,我們應該采取積極參加日內瓦會議的方針,并加強外交和國際活動,以破壞美帝的封鎖、禁運、擴軍備戰的政策,以促進國際緊張局勢的緩和。”[4]356他的這一聲明,明確了中國代表團參加日內瓦會議的任務。確定了中國代表團出席會議時的基調,便于更好地在國際舞臺上開展工作。
通過以上的準備工作,可以看出,新中國已經為在國際舞臺上的首次亮相做足了功課,而作為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部長的周恩來對此事的重視,事必躬親的負責任態度即是推動準備工作順利進行的保障。體現了他作為一個外交家的嚴謹認真態度,為日后積極發揮中國在日內瓦會議上的作用開了個好頭。
(二)會中努力奔走,促使協議達成
準備工作做好之后,中國代表團于1954年4月20日啟程,24日抵達日內瓦。在日內瓦機場,周恩來發表了簡短講話,再次重申了中國代表團此行的目的,即積極促成兩大問題的解決,緩和國際緊張局勢。這大大鼓舞了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和國家的信心。
隨后,周恩來即以此為宗旨,開始了他在會議中間的一系列旨在促成印支問題解決的外交活動。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當時處于冷戰初期,美蘇兩大陣營劍拔弩張,因而參加討論印支問題的各國同樣主要分成兩大陣營,中蘇越為一方,美英法為一方。而且談判方針都是各自商定好的,因此在討論問題的過程中也往往針鋒相對。當然,周恩來作為中國的代表,在很多問題上也同樣與美英法代表有分歧。但同時又不乏靈活反應的一面。
1954年5月10日,越南民主共和國代表范文同在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第一次全體會議上闡述了關于解決印度支那問題的基本立場,即“和平、統一、獨立、民主”。和平即結束戰爭狀態,實現印度支那半島的和平,統一即實現越南南北方的統一,獨立即實現越南民族獨立,民主即進行普選,建立由越南人民主導的民主政權。并提議高棉和寮國代表參加會議。周恩來在隨后的發言中也表示支持范文同關于恢復印支和平的意見,以及寮國、高棉兩國代表參加會議的提議。這一提議很顯然是合理的,但美國代表出于對其法國盟友的支持,對此合理請求置之不理。會議由此陷入僵局。最后大會主席、英國外交大臣艾登宣布“爭執問題留給會外協商解決”[4]119-120。雖然經過蘇聯與西方國家協商,沒能同意高棉和寮國代表直接參加參與解決印度支那問題討論的提議,但還是有一定成效的,兩國最終派出了代表,在會外進行工作[4]119-120。
對于越南的合理要求,周恩來給予了堅決支持,但并不是越南所有的要求,周恩來都給予支持。在當時的情況下,為了實現和平,必要的妥協也是必不可少的。印度支那問題解決的關鍵點主要有兩個,即印支三國的問題是否應該分開解決以及停火問題。關于印支三國問題是否應該分開解決的問題,越方認為,由于在之前反抗侵略的斗爭中,三國的武裝力量是統一行動的,而且越軍是反抗殖民侵略,爭取印度支那民族解放的主力軍,所以在戰后和談的時候,三國問題應該作為一個整體來解決。周恩來經過和高棉、寮國代表接觸后指出,三國的國情不同,應該區別對待。周恩來這么考慮是有其道理的,如果三國問題放在一起解決,那就應該有一個統一的標準。越南劃線停戰,那么寮國、高棉就也應該劃線。但實際上這兩國的問題遠沒有越南問題復雜,所以劃線是沒必要的。如果按照一個整體的問題來處理會很煩瑣。也容易引發爭議,讓西方國家認為越南想在印度支那建立聯邦,這樣會進一步刺激西方國家聯合其他的東南亞國家采取針鋒相對的措施,甚至會導致美國直接出兵。因而三國問題分開解決有利于避免這種情況的發生。隨后周恩來與蘇、越代表協商之后,就這一問題達成了一致。為后來停火問題的解決奠定了基礎。
停火問題主要包括兩方面,即就全面停火問題達成一致以及劃分停火線。中蘇越一方認為,應當在印支半島全境實現全面停火,而西方國家則認為,寮國和高棉的戰火是由于北越軍隊的存在而導致的。所以要想實現停火,只需要北越軍隊撤軍即可。對此中蘇越一方表示堅決反對,表示北越并沒有軍隊進入兩國。雙方圍繞這一問題唇槍舌劍,僵持不下。會后,在中蘇越的磋商中,周恩來指出:為了避免談判破裂,可以先承認越軍過去在兩國有部隊,只是沒來得及撤出。等達成協議后,可以按照外國軍隊從兩國撤軍來辦理。在隨后的會議上,周恩來明確表示,中蘇越愿意就此問題同西方國家達成妥協。可以看出,在達成全面停火這一點上,周恩來做出了很大的貢獻,避免了會議的破裂,使之得以順利進行。
停火問題的另一方面,即劃分停火線的問題。在這一點上,周恩來強調,“應當準備像朝鮮那樣劃定一條停火線,使自己能夠保有一塊比較完整的地區,進而實行普選,完成統一。”[3]358但越南方面對此有異議,他們認為自己的很多軍隊和根據地都在南方,一旦劃線,軍隊就不得不北撤,南方的根據地也將失去。不利于國家的統一。再加上奠邊府戰役中所取得的優勢,使得他們產生了一鼓作氣南下,統一全國的想法。周恩來認為北越軍隊雖然取得暫時的優勢,但戰線拉得太長,部隊過于疲勞,不利于連續作戰,因此應當劃線談判,中國代表團采取這一方針主要基于國內和國際兩方面考慮,國內主要是由于中國的國內建設需要有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國際上主要考慮到美國直接軍事干預的可能性和蘇聯新領導人上臺之后外交政策趨于同西方緩和,由此,在日內瓦會議談判策略上,蘇聯建議中國要采取比較現實的選擇。在上述因素的影響下中方建議越方也采取相應的策略,以求得和平。越方一開始對此表示同意,但奠邊府戰役的勝利使越南黨內的一些人相信他們能夠掌握談判的主動權,于是依然堅持自己的主張。中方認為這是不成熟的,應當趁戰場形勢有利于我方,迫使對方與我方盡快達成協議,實現和平,但越方代表范文同一開始對此持懷疑態度。后來在周恩來的耐心勸說下,范文同同意了周恩來的建議。經過激烈的討價還價,各方最終達成了以北緯17度線,9號公路為停火線,印支三國全境實現全面停火。
隨著以上兩大問題的解決,印度支那停戰協定也在隨后簽訂。這份協議以三國問題分開解決為宗旨,包括了在越南、寮國、高棉三國停止敵對行動的協議,具體內容包括外國軍隊從印度支那半島撤軍以及在印度支那全境進行普選等。從此法國殖民者退出印度支那半島,印支人民希望和平的愿望得到了實現。
周恩來在日內瓦會議的整個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親自主持參加了多次準備日內瓦會議的中央會議,并閱讀大量相關材料,做到知己知彼。辦事之細致嚴謹這一點在他身上體現無疑。而在會議進行過程中,周恩來一方面遵循新中國成立初期所奉行的“一邊倒”外交政策,堅定地與蘇聯、北越站在一起,支持越南的正義要求,另一方面又在各方分歧一時難以化解,談判面臨破裂的情況下,主動提出應變之法,積極同雙方代表進行溝通,最終使雙方分歧得到調和,保證了會議的順利進行,并最終達成恢復印度支那和平的協議。這體現了周恩來作為一個外交家所具備的長遠眼光、靈活頭腦以及雄辯之才。可以說,印度支那問題能夠得到解決,一部分要歸功于中央領導人乃至中蘇越一方談判策略的得當,這是整體布局,而另一部分則有賴于周恩來根據具體情況而采取的具體實施策略上。雙管齊下,終使印度支那問題得到解決,大大緩和了當時的國際緊張局勢。
參考文獻:
[1]李家忠.援越抗法和1954年日內瓦會議[J].東南亞縱橫,2004(6).
[2]Jian Chen,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M].Chapel Hill: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2001.
[3]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來年譜(1898-1976)[M].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
[4]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檔案選編(第一集)1954年日內瓦會議[M].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