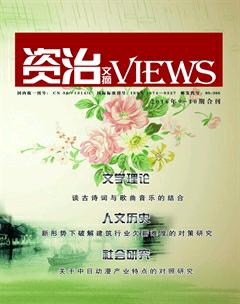以王某侵財案辨析盜竊罪與詐騙罪的認定
徐妍
【摘要】侵犯財產犯罪在司法實踐中屬高發性犯罪,法律不能夠清晰地對相關犯罪進行細致解釋,在此罪和彼罪之間界限不明晰。在實踐中,行為人為非法獲取他人財物,使用的手段既可能為欺詐、亦可能為秘密竊取。導致在案件定性上出現爭議。本文通過案例引出該案的爭議焦點,并闡明筆者觀點。
【關鍵詞】侵財;盜竊罪;詐騙罪
2014年10月,犯罪嫌疑人王某到某電腦城周某攤位,謊稱為某單位采購人員,采購電腦配件共計3萬余元貨物,要求貨到付款。在周某裝貨途中,犯罪嫌疑人王某趁周某不備,將部分配件裝入自己包內。在運貨途中,犯罪嫌疑人王某謊稱下車取東西,逃跑。
2015年7月,犯罪嫌疑人王某到某聯想專賣店,謊稱為單位采購人員,訂購3臺臺式機、3臺筆記本電腦,要求送至某辦公樓,貨到付款。聯想專賣店工作人員同犯罪嫌疑人王某到某辦公樓下,犯罪嫌疑人王某謊稱先將部分貨物運至樓上,后與工作人員一同將其余貨物送至樓上再進行付款。犯罪嫌疑人王某將2臺筆記本電腦拿走進入辦公樓后,從后門離開。
本案中,兩起盜竊行為,主觀方面:犯罪嫌疑人均有非法占有的目的,客觀方面:犯罪嫌疑人均非法取得他人的財產,侵犯了被害人的財產權利。雖然犯罪手段大致相似,犯罪嫌疑人均虛構事實,取得被害人信任,后在送貨途中取得財物,但兩次取得財物的手段不盡相同。第一起行為,犯罪嫌疑人在被害人裝貨途中,趁人不備,采取秘密竊取的方式,非法取得他人財物。雖然其使用了欺詐的方式,但本質是為非法獲取他人財物創造條件,其非法取得他人財物的關鍵,即為秘密竊取,被害人對財物的轉移并不認知,并非基于欺詐自愿交付財物。故第一起行為應屬盜竊,爭議不大。本案爭議的焦點在于第二起的定性問題,應認定為盜竊罪還是詐騙罪?
一、定性爭議
1王某的行為構成盜竊罪的理由
首先,犯罪嫌疑人客觀方面實施竊取財物具有秘密性。其主觀上不想被對方知悉,并為自己能夠轉移財物創造單獨一人的秘密環境。另外,其手段具有秘密性,其竊取財物的行為并不被對方知悉。
其次,被害人并無自愿轉移財物的意圖。被害人雖被騙至指定地點,但財物尚未轉移,犯罪嫌疑人尚未結款,財物尚在被害人的管控之下,財物的所有權尚未發生轉移。
2王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的理由
首先,被害人將財物交付給犯罪嫌疑人屬于處分行為。被害人對財物的占有轉移有認識,且基于犯罪嫌疑人虛構的事實,自愿將財物的控制權轉移給犯罪嫌疑人,使自己失去對財物的控制權。這種處分行為即為自愿交付,并不需要對所有權轉移有明確認識。
其次,被害人失去對財物的控制是基于犯罪嫌疑人的欺騙行為。被害人失去對財物的控制,是因犯罪嫌疑人虛構事實,使得被害人相信其具有購買的意圖,并能夠完成該購買行為。基于對犯罪嫌疑人的錯誤信任,將財物交付犯罪嫌疑人控制,對財物的損失具有關鍵作用。
再次,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的行為過程并不具有私密性,全程在被害人的陪同之下,且財物的轉移被害人亦有認知并認可。
二、本案關鍵行為分析
秘密竊取,是指行為人采取自認為不被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所知的方式,將財物秘密竊取。“秘密”,首先,具有主觀性,只要行為人認為自己的行為不為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察覺,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客觀上是否發現,不影響認定。其次,取得財物秘密手段應始終貫穿全程,如改變方式,采取奪取或暴力手段或使用欺詐的方式進行的,其行為性質便不再是秘密竊取。再次,行為人的秘密行為只針對財物所有人或保管人,其與第三人發現,不影響秘密性。
欺騙行為,是指行為人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使他人陷入錯誤認識,并基于這一錯誤認識處分財物,而行為人取得財物的行為。對于自愿交付財物的認識,我國刑法并未作出規定,但實踐中,首先被害人對自己所處分的財物是有認識的,并不知道被騙,自愿將財物交付給行為人。其次,自愿交付意味著將財物的控制權轉移給行為人,被害人喪失對財物實際控制權,就動產而言,財物交給行為人即可完成。
三、侵犯財產犯罪的具體把握與分析
詐騙、盜竊等財產犯罪的定性應當根據刑法關于犯罪構成的規定,只是在定罪的實施環節,如何在不同類型的侵犯財產罪中,正確運用定罪的標準,準確界定詐騙、盜竊等犯罪。筆者認為應當把握對案件起決定性作用的關鍵行為。侵犯財產犯罪在實踐中的突出特點為行為人為達到非法占有的目的,通常會使用多個手段,手段行為的表現方式可能是欺騙、秘密竊取等多種形式,故應當對實施環節的關鍵行為進行分析,即對法益產生實際侵害的行為作為認定犯罪的關鍵。
本案中第二起行為,犯罪嫌疑人以非法占有的目的,虛構自己為單位采購人員的事實,使得被害人相信其具有購買能力并能夠最終付款。在送貨過程中,基于因犯罪嫌疑人虛構事實而產生的此種信任,被害人自愿認同將部分財物交由犯罪嫌疑人控制,從而使財物脫離自己的控制之下,即控制權發生轉移。綜上所述,本案中第二起行為中,犯罪行為人取得財物的直接關鍵是因欺詐行為產生錯誤認識,而非趁被害人不備而竊取財物,故其行為應認定為詐騙罪。